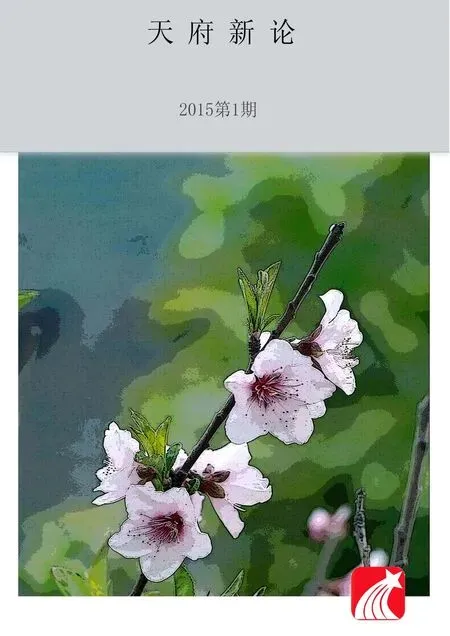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论析
朱培源
人们在谈论“中国社会主义”一词的发明权的时候,往往将它归功于孙中山、梁启超等近代国人,但事实上,相比于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早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这一名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社会主义”的提出
即使推迟两至三年时间写作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很可能不会在该著的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增加“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元月提出的“新名词”——这一类“社会主义”的内容。事情是这样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在外患内忧的侵蚀下日见动摇。就内忧而言,时至1850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时,在中国度过了20个春秋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 (Karl Fri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回到了西方,恰巧他又遇上了正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当听完人们解释“欧洲社会主义”的大概意思之后,郭士立先生便惊叫了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暴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这位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新鲜奇闻”主要可以概括为互相关联的两个层面内容:一方面,自五口通商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清朝中国“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而闹事,迁怒于皇帝的官吏和佛教僧侣,打击并杀戮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着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另一方面,更为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的“社会主义运动”。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以下的评论:“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1〕
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与所谓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像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差别一样。因为,在《共产党宣言》的语境中,以“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为参照物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凡是面向过去,从低于资本主义的水平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就称为“反动的社会主义”,诸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都属于这种类型;凡是面向现在,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的自身批判,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保守的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是以保住资本主义的现有成果,而不是以超越资本主义作为目标的;凡是立足于未来,从高于资本主义的水平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称为“批判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中包括“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包括“批判的实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批判的实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仅以自己的美好愿望作为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根据;后者则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就是“批判的实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相比较而言,以“中国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期,由于本地区资本主义文明程度太低,其所发起的所谓“社会主义运动”只能以低于资本主义形态的文明为参照对象,因此,它不可能算是一种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或“东方社会主义”这类提法又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方面,这种“原生态的社会主义”的亚细亚经济社会形态,因存在着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因素”的“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文化传统等优点,所以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罪恶的“卡夫丁峡谷”,而在充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直奔社会主义的坦途。事实上,这构成了晚年马克思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只需要看看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回信〔3〕便可知道。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是,“东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当然也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接榫的合理因素!后文将对此点展开重点论述。
另一方面,它放宽了对“社会主义”的界定视线——以“世界历史”为基准,而不仅限于资本主义文明笼罩下的欧洲社会。所以,后来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解释“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时会这样说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4〕普列汉诺夫 (1856—1918)后来也有这样的论说:“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但那时,社会主义仅仅是个别人的信仰,充其量不过建立了几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宗教派别而已。只是在目前,在生产技术本身要求人们进一步集体化的资本主义典型时期,社会主义才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因为单独一个人已无法占有并操作机器,工人如果不想永远依附于厂主,他们就应当共同占有机器”。〔5〕可见,我们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仅可从狭义 (即以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私有制度“资本主义”为参照物)上进行界定,也可从广义 (以人类历史上所有形式的私有制度为参照)上进行理解,但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为参照物!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社会主义”素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中国社会主义”的“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这种实况,为他们观察和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社会形态,进而构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众所周知,黑格尔在用“绝对精神”解释世界历史行程的时候,认为世界历史无非就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而这种进展的不同程度表现为:
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6〕
与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用演绎方式的解释进路不同,对于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出发,运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7〕的归纳法来进行诠释的。
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解释过“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现象,但是,他们深入展开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和研究却是在1850年代以后的事情。就当时的东方世界而言,马克思大体上认同了黑格尔“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这个判断,但是,他是从作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财产关系中的“所有制”这个角度来切入研究的。
1853年6月2日,马克思在致信恩格斯的时候,一方面表示恩格斯5月26日前后的“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使他“很感兴趣”;一方面向对方推荐了他正在研读的一本书——法国旅行者兼医生弗朗索瓦·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等国游记》,并认为: “贝尔尼埃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很快在6月6日的回信中,对马克思这个判断表示完全赞同:“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 (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8〕
关于这两封书信,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就寡闻所及,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土地私有制”首先是特指“现代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制”。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我们要特别注意恩格斯在回信中使用的“甚至”这个连词!根据常识,或者从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9〕——中,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比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低级的所有制形式。在恩格斯看来,东方各民族既然连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都没有达到,又怎么会达到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
其次,这里实际上涉及到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另一侧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0〕因此,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所有制”的历史演进形态,也是“从事后开始的”,亦即从当前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出发,而不断往“前史”推导和追溯的。这从马克思后来写的《资本论》手稿之一《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等文献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思索的路径。但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将这里的“土地私有制”一直固定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充其内涵和外延,进而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上升为普遍意义上的,即人类历史上所有形式的私有制。至于东方各文明具体“不存在”何种土地私有制,则视乎该地区的历史状况而定。换言之,这里的“土地私有制”应该是所指与能指的相结合。 “所指”,即特指“资产阶级私有制;能指”,即人类历史上所有形式的私有制。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中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体现了马克思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独特看法。与对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等其它东方国家情况的掌握——特别是在1853年前后,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即将期满,英国国会为此展开激烈的辩论,大量有关印度的资料纷纷登载于报刊,为马克思研究印度以及亚洲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对中国的了解在材料上相对缺乏。但历史地看,这并不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土地制度的判断。与长期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的印度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时的清朝中国存在土地私有制,否则,他们就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有“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的描述了。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当时中国的这种土地私有制是一种低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却又高于原型“亚细亚形态的土地公有制”的存在形态,实际上属于“次生形态”的亚细亚所有制。〔11〕从纯粹“公有制”的判断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并非全然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至少不典型。亚细亚公有社会的特点仅存于印度、俄国等国,而中国不同”。〔12〕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对当时中国土地制度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中国古代出现过井田制形式的原始公有制,但这个制度在春秋战国时,经过“初税亩”和“商鞅变法”等改革,趋于废除。井田制的废除使中国土地私有成为可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庄园经济盛极一时。北魏至初唐,由于均田制的颁行,土地私有制经济曲折生长。后来“均田制”被废除后,中国出现了大地产庄园经济、地主租佃经济、小农自耕经济三种模式。降及明清,地主租佃制与小农自耕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土地制度模式。要之,在战国之前,中国存在着亚洲式公有制,但此后则以地主租佃制和小农自耕制为主要形式。因此,从经验层面来看,属于“亚细亚次生形态”的前现代中国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而非原始公有制,所以,当下中国土地流转与改革的阻力和成本理应要比印度、俄国等“亚细亚公有”国家小得多。
虽然前现代中国的土地私有制比印度的发育程度要高,但两者均属于“广义的亚细亚所有制形态”。因而,就经济的社会形态而言,前现代的中国也就共享有和印度一样的“一无对抗、二无变化”,“只有相同的利益而没有共同的利益”等亚细亚社会结构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除了不存在 (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之外,相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而言,亚细亚所有制的第二大特征便是“一无对抗、二无变化”。当然,“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13〕在东方公社所有制下,由于缺乏“个体”的观念,个人不是实体,而只是属于某一共同体的“一无所有的工人”,因而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生长出一种“对抗”意识。质言之,在东方公社所有制下,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虽然他们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产品,即剩余产品,——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14〕这种以追求剩余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为财富形式的所有制,长期保留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因而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无变化”的—— “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15〕所以,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道:“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由此可以推知,“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6〕
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评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进行侵略所带来的殖民罪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以蒸汽机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文明在瓦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推动人类社会整体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不自觉的历史进步工具”的作用:“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7〕如此一来,也就破坏了半野蛮半文明的东方公社,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在亚洲造成了一场空前的社会革命。
前现代的中国虽然存在“能指”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但是,基于财产之上的现代性个体观念仍然不发达。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极端“为私论”的说法,但在实践中,往往是以家族等共同体利益本位为优先考虑的。或者用艾恺的话来说,传统“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养育出了一种趋向于公共财产的势态”。〔18〕因此,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也就很难生长出一种真正的对抗,而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亦恒少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无对抗、二无变化”的特征是符合前现代中国的。
亚细亚所有制的第三大特征体现为“只有相同的利益而没有共同的利益”。在亚细亚所有制下,由于各个公社之间互相处于彼此孤立的隔绝状态,因而,“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19〕所谓“相同”,即模样相同,表现为一个个松散的“公社原子”;所谓“共同利益”,是建立在交往基础上产生的,但“彼此孤立隔绝的”东方公社不可能有普遍的交往,因而也就不会有“共同的利益”。缺乏“共同利益”的社会,充其量只能达到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而不可能产生“有机团结”。
综上,就当下的中国而言,这种落后的、不合理的亚细亚社会僵化结构的彻底打破和终结,有赖于改革事业的全面深化。
三、对“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
前文述及,中国古代出现过井田制的“亚细亚形态”原始公有制,但这个制度在春秋战国时,经过“初税亩”和“商鞅变法”等改革,趋于废除。结果,土地慢慢集中到新生的地主阶层的手中。至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化这一趋势更为加剧,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最终确立。此外,国与国之间无量的兼并战争,使生灵涂炭、礼崩乐坏。“‘靠牺牲别人来经营’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20〕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例如孔子的“均无贫”与“老安少怀”,墨子的“兼爱交利”,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至德之世”,许行的“君臣并耕”与“国中无伪”,孟子的“井田制度”和“王道仁政”,等等。这些社会理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向往“公”、 “平”,反对“私”、“不平”,实质上是对当时土地财富私有化现实严重不满的公开表示——实质上也是对亚细亚“井田制”的追忆,因而可以归类于前述的“广义社会主义”这一范畴,但又都因现实条件的不允许而实际上沦为空想的“乌托邦”。
中国这种原典的“社会主义”构想,因其集中系统地表达于儒家“十三经”之一的《礼记》“礼运篇”之中,所以也被统称为“儒家社会主义”。《礼记》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诠释《仪礼》的文集,作者主要为孔家门徒,成文时间参差不齐。现在通行本为西汉的戴圣所编,由49篇文章组成。此书较为系统地记载了儒家的制度理想,堪称儒家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儒家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体现为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与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的相统一。〔21〕
“儒家社会主义”的“大同——小康”二阶论,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既深且远。从董仲舒、师丹到王安石,再到龚自珍等历代改革思想家,从王莽的“王田制”到乾隆的“井田实验区”,无一不以“大同”理想为职志。历代农民起义也大都打着“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向往“大同”的理想旗帜。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如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也共享了从“小康”走向“大同”的理想路径。历史已经证明,“儒家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亲和条件。尤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将“儒家社会主义”的二阶论演绎为“小康——共同富裕”思想。而江泽民同志的“全面小康”和“促进共同发展”思想,胡锦涛同志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以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无一不可以溯源至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思想。要之,自春秋战国以来积累了以“大同理想”为核心的中国本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这些思想越过了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顺着历史的长河蜿蜒而下,一直影响至今——为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结合提供了最直接的前提。
然而,当我们在说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的时候,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文化地位,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对“儒家社会主义”进行扬弃,以求进一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和时代化。所谓的扬弃,简单说来,就是要继承和发展“儒家社会主义”中关于“天下为公”等积极思想,同时要摈弃它的“空想”和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消极思想成份。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讲过这样的话:“主义是什么呢?主义就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主义”,更是一种理想、信仰和力量。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中的道理”,则绕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课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23〕这就阐明了我们所要追求的,包括“中国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也昭示着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定的发展道路”。〔24〕习近平总书记在阐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的同时,再次重申:“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25〕
仔细看来,习近平同志所论述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一观点,其实是非常崭新的。因为,以前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在阐述中国道路独特性的时候,大多是从中国的国情及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即“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这两方面着力的,很少涉及传统文化的视角。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这里所说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无疑应该包括传统文化在内。而习近平同志使用的“注定”这两个字,既是唯物史观的反映,同时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新一届领导人在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理论资源。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橥的“中国社会主义”以及寻其广义而得的中国传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则提供了这种“寻资”的契机。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人民出版社,1998.277.
〔2〕马拥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820—84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4卷〔M〕.人民出版社,2009.475—476.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M〕.人民出版社,1983.492.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06—10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巻〔M〕.人民出版社,1995.31—32.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人民出版社,2009.111—113.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59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2009.93.
〔11〕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M〕.东方出版中心,2000.4—12.
〔12〕盛邦和.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东亚文明的进化〔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5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人民出版社,1998.413.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人民出版社,1995.466.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人民出版社,1997.114.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2.856—857.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680.
〔18〕〔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54—155.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9.397.
〔20〕列宁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84.377.
〔21〕盛邦和.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J〕.史学月刊,2007,(4).
〔22〕孙中山全集:第9卷〔M〕.中华书局,1986.184.
〔23〕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出版社,2013.2—3.
〔24〕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1.
〔2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人民出版社,1995.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