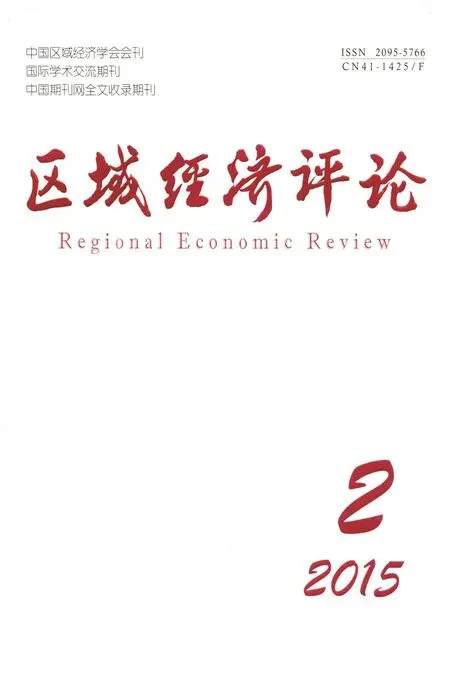“三大战略”的特点与中国区域经济新阶段
廖元和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上述方针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格局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它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点是实施“三大战略”,“三大战略”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国内的空间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起来,将中国的沿海开放、沿长江开放和沿边开放联结成一个对外开放的整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四条对外开放的丝绸之路:第一条是从古长安、现西安出发的北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侧到中亚和中东。这条丝绸之路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开放历史,源远流长,为世人所熟知。第二条是南方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印度古称“身毒”,“蜀身毒道”即从成渝经济区到印度和东南亚的对外开放通道。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四川有两条道通往云南:一条由成都出发,经宜宾、昭通、昆明到达楚雄,称为“灵关道”;另一条从四川出发,经雅安、西昌到达云南楚雄,称为“宋提道”。这两条古道在云南楚雄会合后经大理、保山、腾冲或瑞丽出境,通向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蜀身毒道”是历史上成渝经济区通向南亚和中亚的道路。第三条丝绸之路是从扬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地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第四条是从元大都即北京出发经内蒙古草原、新疆到中亚的“马可波罗”记载之路。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起点,但却有南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分。2014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对内对外全面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这一指导意见清楚地表明了三大战略同对外开放的紧密联系。
将国内的区域经济和空间格局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决策者们正在用全球眼光和时代望远镜看待和指导中国的区域经济,是中国空间格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二是将国内的空间发展格局及区域经济与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经济发展未来面临三大严峻挑战。第一,面临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供给不足的挑战。据中国科学院郎一环主编的《全球资源态势与中国对策》一书的分析,在主要的45种矿产中,中国有27种矿产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22种属于对经济建设不能保证或基本保证但存在不足的矿产,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主要国内资源难以保证国内在2020年的需求,需要通过进口予以解决。当然,我国也有许多独有而国外必须从我国进口的战略资源。第二,面临出口需求不确定的风险。众所周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源泉。自2007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带来了严峻挑战,致使沿海许多面向欧美发达市场的企业因开工能力不足而减产。制造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是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第三,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协调的矛盾。中国未来面临全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任务。城乡统筹的基本途径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工业可以高度集中,城镇却不能高度集中。从现状来看,东部地区集中了中国60%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由于产业支撑不足,一方面造成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中西部地区就业,另一方面又导致中西部许多地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乏力,缺乏城乡统筹的较强经济基础,只能依靠转移支付解决。
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既可以保障中国所需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进口,又可以开辟俄罗斯、中亚、中东、印度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增加出口的渠道,减少发达国家出口需求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还可以缩小东中西差距,促进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协调发展,解决东中西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协调的矛盾。
三是将空间发展格局和区域经济同打破行政区划、注重顶层设计、加强区域合作、按经济规律办事紧密结合起来。
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各自都有内在的紧密经济联系,同时又是跨行政区域的战略。实施“三大战略”,它一方面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壁垒,通过协同发展解决跨区域的重大问题,例如京津冀区域的雾霾问题,陆上丝绸之路的风沙治理问题,长江经济带的水资源保护问题,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立体交通问题等。另一方面可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和地方政府协同行动来完成。这将减少地方政府不恰当的干预,打破行政壁垒,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三大战略”的上述特点也是“三大战略”的显著优点,它标志着中国的空间发展格局和区域经济已经进入重点协调式发展新阶段。
区域经济是近代工业产生以来才形成的,在近代工业产生之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空间发展格局和区域经济是畸形的。这种畸形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工业高度集中于沿海的上海、广州、大连、天津、青岛和沿江的武汉、重庆与东北的沈阳等少数大城市,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官僚资本主义操控的残破工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空间发展格局和区域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区域产业布局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只是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产业布局意图,区域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空间布局的目标是建立初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空间发展的重点和内容是建设一批重化工企业、关系国计民生的轻纺工业、铁路和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业和工业体系,解决了各个区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但它存在一些弊端。其一是过分强调均衡发展,平均主义倾向抬头,抑制了东部沿海优势的发挥;同时,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区域竞争。其二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各省区工业出现“大而全”“小而全”布局的倾向,重复布局、盲目布局项目较多,致使资源浪费,效率较低。
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今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阶段。从1978年起,中国的区域经济进入了非均衡发展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历史性变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非均衡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三:其一是充分发挥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区域优势,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三大增长极;其二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制度创新,实施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三是在东部三大增长极的带动下,在全国形成了新的工业部门,建立了更为强大的工业体系。但是“非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也暴露出诸多弱点。首先,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已高度集中,环境容量已呈饱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其次,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较早,经济特区较多,加上地区优势和政策优势,生产要素的综合成本较低,但现阶段生产要素成本在区域之间已发生显著变化,中西部的地价、水价、电价、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正在日益突现出来。再次,工业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导致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难以充分发挥。
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既有利于充分发挥非均衡发展阶段的优势,又有利于克服其弊端,形成重点协调式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这种新格局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中西部地区将出现一批新的类似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如: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尔滨长春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二是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将迈上新的台阶。
“三大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进入重点协调或发展新阶段,但重点并不等于全部。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发展一方面要扬长,另一方面要补短。“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是中国区域经济现阶段的“长”之所在,是充分发挥优势的战略。中国区域经济的“短”又在何处呢?在贫困地区,在省区交界的边远山区。而贫困地区和省区交界的边远山区基本是重合的。例如: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区,湘、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区,云、贵、川交界的长江上游地区等。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增加造血机能。要增加造血机能,一是要培育贫困地区的增长极,二是要改善贫困地区的交通条件。贫困地区的增长极就是贫困地区的中心城市。比如,湘、渝、黔交界处的秀山,云、贵、川交界区的昭通或习水等。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的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将对中国区域经济的“短板”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将实施重点协调或发展的“三大战略”与贫困地区增长极的培育结合起来,就是扬长补短,就会对中国区域的发展和空间格局的优化产生巨大的政策推动作用,也将为中国区域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开辟新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