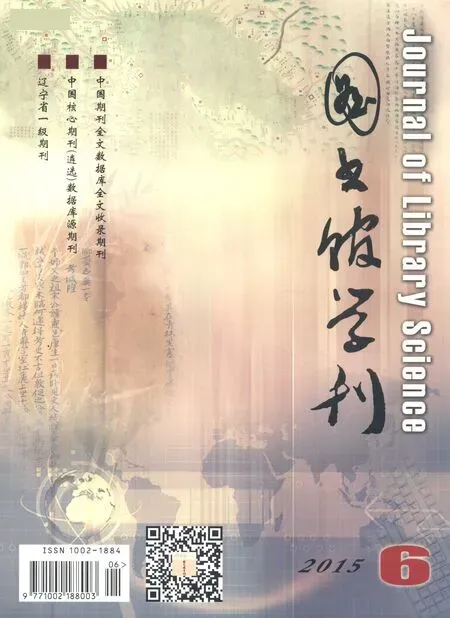姚际恒的目录学成就
邵风云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00)
1 姚际恒生平
姚际恒(1647-1715年),祖籍安徽桐城,后寄居浙江仁和(今杭州),清代杰出经学家。县诸生,初为贡生,折节读书,涉猎百家,但史无传记。清代吴振械《国朝杭郡诗辑》:“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钱塘监生”,“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精治经。”清代毛奇龄《西河诗话》卷四:“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祗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予婚嫁毕而注《九经》”[1],于是,遂屏绝人事,一心致力于著述。其毕生精力的著作为《九经通论》,可惜遗稿多散佚。仅有《九经通论》中的《诗经通论》以及《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完整地传了下来。《礼记通论》散人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尚书通论》的某些内容见引于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中。今天有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辑编有《姚际恒著作集》(1994年出版),搜罗较全。
2 插架与腹笥俱富
姚际恒生平酷爱藏书,所居海峰阁,西窗面湖,里边储藏古籍善本和金石书画甚富。加上其精通目录学,所以经他鉴赏过的书画,往往分寸不爽。姚际恒从小发奋读书,先是诸子百家无所不读,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攻经书。旧抄本《好古堂书目》4卷,不注撰人名次,书前有康熙乙未夏杪钱塘人姚之驷所作序,云:“予世父首源先生,束发受书,已能沉酣故籍。乃一生坎螓,兀兀穷年,惟手一编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乃复搜之市肆,布诸巾箱,久之而插架与腹笥俱富矣。末附收藏宋元版书目凡数十种。”吴振械《国朝杭郡诗辑》“首源博究群书,撑肠万卷”。毛奇龄《何氏存心堂藏书序》,请其兄大千过目。大千说:“何氏藏书有几多,不如姚立方腹笥耳。”可见,姚际恒被人敬佩程度,“著书之富,与藏书相埒”[2]。
3 辨伪专科目录
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是一部著名的辨伪专科目录。全书分“全部伪作者”“真书杂以伪者”“非伪而撰人名氏伪者”“书不伪而书名伪者”“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五大类。立论严谨,构思精深,为学者所推崇[3]。认为全部是伪作的,有“经部”《易传》《古文尚书》《尚书汉孔氏传》《诗序》《用礼》等19种。“史部”《竹书纪年》《十六国春秋》《隆平集》等13种。“子部”《关尹子》《六韬》《文中子》《李卫公问对》等38种。认为真书中有伪的,有《庄子》《列子》《管子》等10种。认为书不伪而撰人伪的,有《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等6种。书不伪而书名伪的,有《春秋繁露》《东坡志林》等两种。不能定其作者的,有《国语》《孙子》等4种。先列前人考证已经明白之书。不收录佛经、道书、古集中的小部伪作、今世不传者和琐细无多者[4]。
《古今伪书考》的收书原则:凡近代不传于世的,或传子世而琐碎无价值之书,皆不收入;凡苟人辨证精确,又有可取之处者,悉载于前,以期征信,并不是自己枉说,以使半百年之疑案,昭然若揭;一集部图书,他人不好伪造,即或宥一二附益伪撰,不足称数,故亦不收;“子类中二氏之书,亦不及焉。”(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序》),所以“大抵际恒所著力求创获,故惊世骇俗,在所不顾刀”。
一部目录,就是一部学术史。它能告诉读者书的存佚完缺、流传情况、篇卷分合、版本优劣等,有的还能直接告诉读者某书为伪。这些都能为辨伪提供很多方便。如《易》,《汉志》著有《易》;《隋志》著有《归藏易》;《新唐志》著有《连山易》。人们俗称《连山易》为《夏易》;《归藏易》为《商易》。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称:“《连山》出于刘炫之伪作,北史明言之。度《归藏》之书,亦此类耳!”姚际恒在使用其他方法辨伪时,有时也结合使用目录,有的则直接利用书目辨伪。如古《三坟书》,姚《考》说:此书“出于宋,晁子止日:‘张天觉言得之比阳民家。《七略》《隋志》皆无之。世以为天觉伪撰。”姚氏利用《七略》《隋志》所载,判所见的本子为伪书[5]。
《古今伪书考》中子史部书,考辨也有不少精当之处。如对《竹书纪年》《汲冢周书》《穆天子传》等书的辨证。姚际恒认为,《穆天子传》据《左传》和《史记·秦本纪》而为书,又“多用《山海经》语,其体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于明德马皇后,故知为汉后人作。”《汲冢周书》的内容也仿袭《史记》《吕氏春秋》《周礼》等书,不是当时的真品。接着姚际恒又指出这三本书的注也是伪作,如《穆天子传》,“称(郭)璞注者,盖印取璞所注《山海经》以移入之,故因谓璞注也”。在“有真书杂以伪者”类中,收《三札考注》《文子》《庄子》《剜予》《管十》《贾谊新书》《伤寒论》《金匿玉函经》8部书。如对《列子》的辨析,姚际恒认为:“战国时本有其书,或庄子之徒依托为之者;但自无多,其余尽后人所附益也。以庄称列,则列在庄前,故多取庄书以入之。”这是说《列予》一书有不少内容是抄自《庄子》一书。在“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类中,收《尔雅》《韵书》《山海经》《水经》《阴符经》《越绝书》6部书。姚际恒认为这些书本不伪,其作者是后人伪托的[6]。其中多采汉唐以来前人旧说,间或对前人之说进行补充、驳正,但论辨多较简略,编次和论辨也有一些不当之处。如将《忠经》(托名马融,张溥辑《汉魏六朝文集》,列入马融集中)编入经部,将《天禄阁外史》(称汉黄宪撰,为明王逢年伪撰)编入史部,此为不察其内容性质,仅观其名而胡乱归类。论辨中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如辨《文中子》,他据《挥麈录》证实王通确有其人,并说“予谓既有其人,又其书为所作,则适见通一妄夫耳”。继而又采纳别说,认为该书出于其子福郊、福畴之所为或阮逸之伪造。所以又持模棱两可之说,称:“通耶,郊、畴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辨《诗序》,既据《后汉书》证为卫宏所作,又曰:“非伪书而实亦同于伪书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梁启超称其“体例颇凌杂,篇帙亦太简单,未能尽其辞,所断亦不必尽当”。顾颉刚也称其“或微折衷,不尽证实,弗能谓博议无遗也”。然而他又认为,姚际恒“敢于把人们不敢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骤然听到一个大声的警告,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由于姚际恒的勇于疑辨古书尤其是疑辨儒经,因此他的著作唯有一部《庸言录》被《四库全书》存目,其他著作如《九经通论》是被人为禁毁,还是自然散逸,不得而知。但从现存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在经书考辨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
综上,《古今伪书考》是一部考辨群书的著作,辨及经、史、子三类中凡91种书,经书部分与《九经通论》相表里,并多集前人之说,自序已发其例,其所辨,除确认的伪书之外,另参考胡应麟《四部正讹》的分法而又有所发展[7]。
4 综合性目录
姚际恒对其丰富的藏书还编有书目,名之曰《好古堂书目》。《好古堂书目》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分为四部。前冠有康熙乙未(1715年)姚之骃序。序曰:“予世父首源先生,束发受书,已能沈酣故籍,乃一生坎壞,兀兀穷年,惟手一编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乃复搜之市肆,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暇时录于簿籍,予小子写为副墨。”书后附有收藏宋、元版本书目,凡数十种。其分类表为:经部十二类:经总、易、书、诗、春秋、三礼、乐类、四书、孝经、尔雅、小学、汇集。史部二十类:正史、编年、霸史、杂史、集古、时政、礼仪、传记、典故、职官、法令、食货、器用、虫鱼、地理、方物、名胜、川渎、谱系、簿录。子部十五类:儒、道、墨、法、名、纵横、汇集、杂、小说、兵、天文、医、艺术、类、释。集部十类:志奏、策论、骚赋、四六、尺牍、别集(以时代分)、总集、诗文格评词曲、经史子集总,附缺书目。
姚际恒的目录学成就总结如下:①类目设置比较详细。四部之下共有57个大类。其中史部分类尤详,计占20个类目。既便于类分图书,也不令人感觉繁琐。②有所创新。如集古、时政、虫鱼、方物、名胜等类,在以前的史目中均不见,这是姚际恒所独创。书中有些类目,根据需要,从下位类中析出,与上位类并列。如器用、虫鱼,同食货并列,名胜、川渎,同地理并列。而没有将其置于食货、地理之下。但是书也有其不足之点,如正史类有陈深《诸史品节》、吴崇节《古史要评》等,则已并史钞、史评两类于正史类中,编年类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郎璧奎《古史约言》等,已并纪事本末于编年类中。这些都未免过于简略。除上面提及的目录学著作外,姚际恒还有其推论经史、理学、诸子的《庸言录》一书在世间流传[8]。
[1] 杨荫深.中国学术家列传[M].上海:光明书局,1948:123.
[2] 余章瑞.藏书故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143.
[3] 庞朴.中国儒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21.
[4] 罗孟祯.古典文献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04.
[5] 叶树声,许有才.清代文献学简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132.
[6] 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83.
[7]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60.
[8] 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