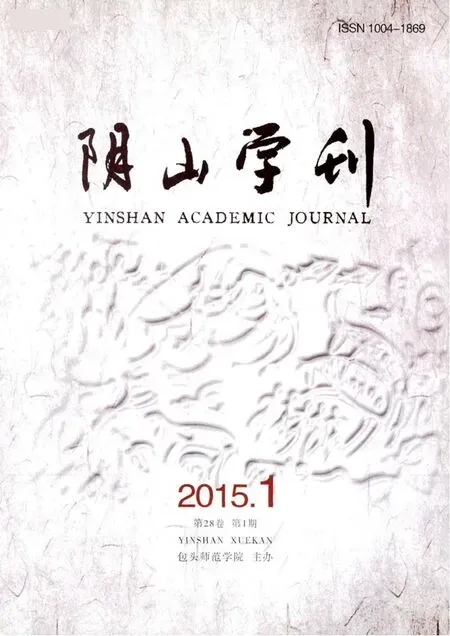“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考论
杨 军 民
(河西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考论
杨 军 民
(河西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陕甘总督是清代常设定制八总督之一,为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掌控西北边防战略基地陕甘两省。因此重要军政地位,自康熙七年起,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雍正元年,又改参用蒙古及汉军。相比于其他常设定制总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呈现鲜明的个性特点,因陕甘总督专用满员的规制,满洲出身,特别是上三旗出身的满洲官员成为陕甘总督群体的主体。与清代满汉关系的演变轨迹相一致,陕甘总督群体的结构特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前期主用满洲,自嘉庆以降,汉人逐渐增多,至同光时期,湘系将帅基本垄断陕甘总督一职。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既是清代督抚制度发展演变的表征,也是清代满汉关系历史走向的风向标。
满缺制;陕甘总督;群体结构
官缺制是清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即规定特定职位官员的民族成分,分满洲缺、蒙古缺和汉官缺,一般情况下,满洲出身的官员可以补蒙古缺和汉官缺,而汉人则不能出任满洲缺和蒙古缺的官职。为保证以满蒙联盟为基础的满清政权的统治,一些重要的军政职位为满洲缺和蒙古缺。其目的在于保证一些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职位为满洲所控制,并为八旗子弟保留一定的职位作为迁进之阶。其中,边塞地区,即具有重要边防意义的边疆地区军政职位一般为满洲缺,如贯穿整个北部边疆的军府建制下的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等职位专为满洲缺,并参用少量蒙古。由于陕甘地区在西北边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自康熙七年起,西北督抚被定为满洲缺,自康熙时期至同治初元,历代清帝以此为圭臬,少有更改。同治以降,随着湘淮地主阶级的崛起和满汉力量的重大变化,陕甘总督一职始为湘系所把持,直至新政时期。
一、山陕督抚的满缺制
陕甘总督作为常设定制八总督之一,始于顺治二年四月(1645年2月)陕西三边总督的设置,其间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调整变化,先后设置过陕西三边总督、川陕总督、陕西总督、山陕总督、甘肃总督、陕甘总督等建置形式,定制于乾隆二十五年六月(1760年6月),以陕甘总督为常设定制形式。演变动力来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从清王朝内部来看,西北、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是推动建置演变的动力之一;从外部原因来看,西北准噶尔势力的消长是影响建置演变的动力之二;陕西和甘肃在西北边防体系中地位的变化是推动建置调整的动力之三,陕甘总督建置演变和定制是以上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陕甘总督建置沿革
西北军政建置始于顺治二年四月(1645年2月)建置的陕西三边总督,驻固原,至顺治十年六月(1653年6月),兼督四川,为川陕总督。顺治十八年九月(1661年9月),川陕分治,析置陕西、四川两总督。康熙五年十一月(1666年11月),陕西总督兼辖山西,为山陕总督,移驻西安。康熙十一年四月(1672年4月),罢兼辖,陕西总督专辖陕西。康熙十九年十一月(1680年11月),恢复川陕总督建置至康熙五十七年十月(1718年10月)。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恢复四川总督建置,以作康熙五十八年川省兵事之预备。康熙六十年五月(1721年5月),因西征军事需要,陕西总督鄂海督理军需,而以四川总督年羹尧兼督陕西,第三次建置川陕总督。至雍正九年。雍正九年二月(1731年2月),雍正帝以川陕辽阔,川陕总督难以兼顾两省事务为由,析置四川、陕西两总督,川陕第三次分治。雍正十三年十二月(1735年12月),西疆军务渐竣,恢复川陕总督旧制至乾隆十三年。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1748年11月),尹继善总督陕甘,分设陕甘总督和四川总督,是为陕甘总督建置之始,至乾隆二十四年七月(1759年7月),恢复川陕总督旧制并新置甘肃总督,而以甘肃总督兼辖陕西绿营。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1760年12月),西疆底定,恢复陕甘总督及四川总督旧制,陕甘总督常设定制,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移驻兰州,并兼甘肃巡抚事。
(二)山陕督抚的满缺制
《清史稿·职官志》云,“康熙七年,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但又说雍正元年“谕山陕督抚参用蒙古、汉军、汉人,纂为令甲”[1](P3339);而福格在《听雨丛谈》中却说“康熙七年,钦定川陕、甘肃、山西督抚为满缺,至乾隆间仍遵其制”[2](卷3)。而徐珂《清稗类钞》却认为,“康熙时,三藩既平,仅议定陕西、山西两抚不用汉人而已”[3](P1339),似乎“山陕督抚专用满洲”仅指陕西山西两抚,明显是错误的。福格之说则对于康熙七年上谕的适用时间判断有误。实际上,自雍正元年以后,山陕督抚已开始参用蒙古、汉军、汉人。从汉军出身的年羹尧再到汉家之岳钟琪、刘於义,八旗满洲垄断西北督抚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不过,咸同之前,在西北督抚的人选上,八旗满洲仍具绝对之优势。自康熙七年确定这一规制以后,至同治五年,仍基本遵行。虽然在雍正元年以后,清廷做出了山陕督抚参用蒙古*蒙古出身的甘督有:长龄、升允、松筠、全保、惠龄、和宁、汉军*汉军出身的有年羹尧、杨应琚、李侍尧。的调整,但八旗满洲仍居绝对优势。同治以后,湘淮系汉族督抚的激增,而陕甘总督一职基本上为湘系所垄断*杨岳斌、曾国荃、左宗棠、杨昌濬、谭钟麟、魏光焘。,这两个因素降低了陕甘总督群体中满洲督抚的比例。但在自康熙朝至咸丰朝两百年内,满洲督抚仍然是包括陕甘总督在内的西北督抚的主体。
康熙帝将山陕督抚定为满缺的动机,其中的政治军事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康熙帝认为,“边塞地方必兼用旗员,方有裨于政事”[4](P2224),而乾隆帝亦认为,“以满洲骑射、比汉人为纯熟。于控制北边为相宜”[5](P303)。可见,以长于军旅的满洲将帅确保西北塞防安全的政治军事需要是“山陕督抚专用满员”政策产生的主要原因。康熙时代,准噶尔成为清帝国西北边防的严重挑战,清帝国西北边防长期受准噶尔的牵制和威胁,以致西北边境只能到达河西走廊的甘、凉、肃一带,陕西、甘肃因此成为西北塞防重地。而康熙帝从维护满洲民族利益和对汉人的偏见出发,认为边防重任和军务大事只能依赖满洲,因此,自康熙以后,西北督抚长期以满洲为主体。
由此可见,康熙帝钦定西北督抚为满洲缺的深意,在于西北地区在清帝国边疆防卫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陕甘地区作为西北边防重地,其事权必须为长于骑射的满洲八旗所控制,方能保证清帝国的国防安全。另外,陕甘驻防绿营在有陆疆防御任务的行省中是最多的,为“天下劲兵处”[1](P10367)。旗营交错,重兵云集,从保证满洲民族的统治考虑,这一重兵集团也必须为满洲将帅统领。同时,西北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多变,清前期的长时期内,其对清王朝的离心力和可能发生的反叛行为也是清廷不得不考虑应对的隐患,因此,以满洲将帅出任甘督,是未雨绸缪之战略防范。
二、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的一般特征
陕甘总督的群体特征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清前期顺治、康熙、雍正诸朝,因长期征战的需要及山陕督抚专用满洲的政治原则,长于弓马骑射的满洲将帅和八旗汉军垄断了西北总督一职。顺治时期,八旗汉军构成西北督抚的主体,自康熙七年起,西北督抚又为满洲将帅所垄断。雍正时期,虽然做出了兼用蒙古汉军的调整,但八旗满洲仍据主导地位。乾隆及其以后嘉道诸朝,在八旗满洲仍具主导地位的同时,汉人已崭露头角;同光以后,随着湘淮系地主阶级的崛起,满汉地主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方向性变化,湘系出身之将帅基本垄断甘督一职,至清末新政时期始有改变。
从陕甘总督群体出身的时代性特点来看,也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康雍时期非科甲正途的侍卫、笔帖式、行伍等途是这一时期陕甘总督迁进的主要路径;到了乾隆时期,科甲正途出身之甘督明显增多,而笔帖式、侍卫、行伍出身之甘督仍占很大比例。至嘉道以后,正途科甲出身比例有较大增长,咸同以后,在以汉人为主的陕甘总督群体中,正途科甲出身占据了主导地位。陕甘总督群体特征的时代差异背后的历史动因,既有入关以后民族风尚逐步演变,崇文之风逐渐扩大的因素,亦是清廷满汉政策调整的结果,也反映了满汉力量变化,汉族地主阶级力量逐渐增强的历史过程。
(一)西北督抚群体满汉比例及其变化
从清代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对于清帝国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满汉关系之发展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顺康时期的怀柔,雍乾时期的压制,同光时期的依赖。推动这一运动变化轨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满洲统治民族主动调整的原因,亦有满洲民族自身衰败和汉族地主阶级力量成长的影响,但其根本动力则是满汉力量对比的历史演变。清初顺治至康熙初年,清帝国尚处于稳定统治的时期,需要汉族地主阶级的大力支持,再加上顺康二帝政尚宽大的为政风格,对于汉族,笼络怀柔多于暴力震慑;雍乾二帝在位时期,满洲民族已经稳固确立了对于其他民族的统治,清帝国日益强大,自信日显;同时,雍正为政尚苛,乾隆于宽大与严苛中执其两端,因此,在满汉关系上,对于汉人,一味压制成为主要特点。到了同光时期,满洲帝国在内外挑战中,尽显衰象,满洲贵族与八旗军事力量尽不可恃。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依靠湘淮系新兴政治军事力量,满汉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湘淮系新兴地主阶级成为满洲王朝的政治军事支柱。清代满汉关系的发展变化反映到陕甘总督群体特征上,虽然山陕督抚专为满缺,但是陕甘总督的群体结构也呈现出与清代满汉关系发展演变轨迹一致的阶段性特征。
与清代督抚政治演变的历史轨迹相一致,陕甘总督的民族构成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清初顺治一朝,汉大臣出任督抚甚至多于满洲,至雍正时期,八旗汉军督抚又呈现急剧的增长态势;至乾隆以后,随着雍乾诸帝对于满洲民族特色的强调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设计,满洲出身之督抚在督抚群体中又处于绝对优势。嘉道时期,汉人出身督抚逐渐增多。到同光以后,由于湘淮地主阶级群体的崛起,湘淮系将领群体又成为督抚群体中的主导力量。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随着新政改革的推行,作为加强满清贵族统治的主要措施,满洲贵族又占据了直省督抚的绝大多数,“当同治初八九年间,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是以天下底定,各国相安,成中兴之业者十三年……。光绪二十年后,满督抚又遍天下矣,以迄于宣统三年而亡”[6]。
在山陕督抚的人选上,雍正元年参用蒙古、汉军的规制得到执行,而且八旗汉军在雍正一朝的督抚群体中数量急剧扩大,成为行省督抚的主要力量,就川陕总督和陕西总督来看,雍正朝之年羹尧、刘於义、岳钟琪等,一人为汉军、两人为汉家。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的陕甘总督中,也有少量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不过数量较少,蒙古出身的甘督有长龄、升允、松筠、全保、惠龄、和宁;汉军出身的有杨应琚、李侍尧。总计8位,占12.9%。从比例上来看,依次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与清代政治的本质基本一致,即八旗满洲的优越地位和西北边防大臣主用满洲的政治原则,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出任甘督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嘉道时期。而乾隆一朝的陕甘总督群体当中,八旗满洲已占绝对优势。随着清代满汉关系和督抚政治的演变,到了嘉道时期,陕甘总督群体中的汉人比例已悄然上升,至同光两朝则一反常制,汉人已基本垄断陕甘总督一职,直至光绪二十七八年间,始有改变。
陕甘总督由康雍乾时期的主用满洲而演变为同光时期的汉人为主,其历史契机则是咸同军兴和湘系的崛起。咸丰季年,满人督抚尚居天下督抚十之六七,而至同治初年,仅一官文为湖广总督,满洲督抚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已经让位于湘淮系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力量,湘淮系将领及幕僚成为督抚的主要力量,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系功臣占其大半,自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六年,陕甘总督几乎为湘系所垄断。新政改革时期,清廷借改革之名,行集权之实,企图改变汉族地方督抚专政的不利局面,改变同光以来满汉关系的不利趋势[6],但为时已晚,且措置失当,反而加强汉族地方督抚的离心力,加速了王朝的覆亡。
不过,同光以前的汉人任职的实际意义不大,除毕沅外,陆有仁、方维甸、杨以增、邓廷桢、林则徐、林扬祖、沈兆霖等都是短暂的署理;而在同光以后,情形转有不同,大多为实授,而且任期都较长,一般都在四年以上*左宗棠、杨昌濬、谭钟麟,更有左宗棠从同治五年到光绪六年任职陕甘达十数年之久,创下了陕甘总督之最长任期,这是同光之前的旗人都不曾有的殊荣。
(二)陕甘总督群体的军事化特征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始终,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1](P12022)。这一论断虽是针对同光时期的湘淮系将帅而言,但却同样适用于大部分陕甘总督。“与兵事相始终”是陕甘总督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的七十余年间和同光时期的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及收复新疆的十余年间表现最为突出。康熙时期的西北督抚*康熙一朝,陕甘川地区先后建置陕西总督、川陕总督、陕甘总督。大部有从征经历,如莫洛、博霁等;雍正时期的如年羹尧、岳钟琪;乾隆时期的福康安、张广泗、永常等,同光时期的杨岳斌、曾国荃、左宗棠、魏光焘、都兴阿等。
自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但近代以前的中国却是一个重视陆权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原王朝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于西部和北部边疆[7],东部海疆长期未有有竞争力的对手,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局面。因此,终清一世,西北方向的边患始终是清廷时刻需要应对的危机。从康雍乾时期的准噶尔势力,到击败准噶尔以后的自乾隆至道咸时期持续百余年的南疆回部分裂势力,对西北边防安全的威胁从未停止。近代以来,沙皇俄国对于西北边疆的蚕食鲸吞又成为西北边防的心腹之患。可以说,终清一世,西北边患从未消除。因此,作为西北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总督在群体结构上呈现出军事化的特征。这种军事化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制度设计,陕甘总督专用满缺和西北边防大臣的满缺制使得陕甘总督在总体上以长于骑射和军事征战的满洲人为主,兼及少量八旗蒙古与汉军。第二,自康熙中期反击准噶尔开始,至同光之际平定阿古柏叛乱和西北回民起义,西北社会长期处于战乱当中,作为西北边防体系支柱的陕甘总督和陕甘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军事征战是对其技术性要求,否则难以有效应对辖区内的内外危机,保卫西北边防,维护陕甘社会稳定;第三,陕甘总督当中,满汉名将和治边能臣比例较大。如“三朝武臣巨擘”岳钟琪,嘉道名将杨遇春,治边能臣那彦成、长龄;“满洲诸名将,半出其下”的名将都兴阿[1](P12093);同光名将左宗棠、杨岳斌、曾国荃、魏光焘等,长于军旅边务成为陕甘总督群体的显著特征。
其次,陕甘总督作为西北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廷对于甘督一职的技术性要求,即必须有一定的军旅背景,以便妥善应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内外危机;同时,必须拥有处理西北各少数民族事务的资历和能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文官体制之下,分别有5位行伍出身的甘督*杨遇春、穆图善、杨岳斌、魏光焘、都兴阿。5位甘督获得“巴图鲁”称号*都兴阿为“霍钦巴图鲁”,杨岳斌为“彪勇巴图鲁”,穆图善为“西林巴图鲁”,曾国荃为“伟勇巴图鲁”,杨遇春为“劲勇巴图鲁”。见《清史稿》都兴阿传、杨岳斌传、穆图善传、曾国荃传、杨遇春传。。
(三)陕甘总督群体中的文武关系
从文武关系上来看,在清代文官制度下,作为文官的总督,主要还是从文官中简擢调补。自顺治到光绪十朝总计107位西北总督*包括先后建置的陕西三边总督、川陕总督、陕西总督、山陕总督、甘肃总督、陕甘总督。中,文官系统的总督、巡抚、六部尚书及侍郎总计81位,占75.7%,武官系统的都统、驻防将军、内大臣、西北边防大臣总计26位,占24.3%,体现了清代以文统武的基本国策,也体现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对官员选任的影响[8]。
陕甘总督为满缺,从陕甘总督群体特征上来看,由于满洲重骑射不重科目的民族性格的影响,陕甘总督整体上表现出教育水平较低,笔帖式和侍卫出身的满洲世家子弟较多,故长于武事而弱于文教和治民;两江总督群体则整体上文教水平较高,即使出身满洲,其教育水平在满洲民族当中,也属于较高水平,如满洲状元麻勒极,被乾隆帝赞为“真知学者”的尹继善等[1](P10545~10549)。而在陕甘总督群体当中,其长于武事的特点则较明显,如被称为“三朝武臣巨擘”的岳钟琪[1](P10367~10377),被称为“中兴名将”的都兴阿,以绿营行伍出身而荣膺封疆的杨遇春,治边能臣黄廷桂、那彦成、长龄、松筠等。出身一般为科甲、荫生,首科甲,次荫生,再次为行伍,其中满洲科甲出身21位,荫生9位;汉人18位当中,15位为科甲出身,3人为行伍出身,5人获得“巴图鲁”称号,足以反映这一职位的特征。
而在陕甘总督当中,进士比例则较低,进士比例之提高是在道光以后,且汉人占绝大多数。从康熙朝西北总督*包括陕西总督、山陕总督、川陕总督。的情况来看,除了年羹尧为进士以外,在已明出身的总督当中,鄂善、博霁为侍卫出身,佛伦、鄂海为笔帖式出身,哈占为八旗官学出身。显然,正途之科目出身在康熙朝陕甘总督当中比例很低。与康熙朝甘督群体结构相似,雍正朝甘督当中,查郎阿、岳钟琪为行伍出身,年羹尧、刘於义进士出身,黄廷桂为侍卫出身,正途科甲出身比例仍较低。
在乾隆朝25位甘督当中,也只有尹继善、吴达善、勒尔锦、毕沅为进士出身,勒尔锦作为翻译进士,还算不上正统的正途进士。与康熙朝相比,笔帖式、侍卫仍然在甘督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侍卫、笔帖式出身之甘督相比于其它出身之甘督,任期更长,更受朝廷器重,影响也更大一些。如庆复、傅恒、永常、福康安为侍卫出身,鄂弥达、勒保、宜绵、惠龄为笔帖式出身。另外,傅尔丹、瑚宝为行伍出身;庆桂、杨应琚、李侍尧为荫生出身。
(四)陕甘总督群体中的科甲正途
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宣统三年(1911)间150年的时间内,总计有62人次出任陕甘总督*包括实授和署理,但不包括护理。在实授与署理之间不做区别,因为由署理到实授及署理而不实授两种情况,由署理到实授有时并不标明时间。在实录的表达上,凡实授均为调、补陕甘总督、兼管陕甘总督等,凡实授皆表述为陕甘总督;而署理皆为“署理陕甘总督”、“兼署陕甘总督”;以大学士而兼管总督,有的为实授,有的为署理。,在此期间62人次的陕甘总督当中,从出身来看,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为科甲出身,一类为笔帖式、侍卫出身,一类为行伍出身。其中,从已明出身的58位甘督来看,其中荫生出身9位,满洲科甲出身21位,汉人总计18位,其中科甲出身15人,行伍出身3人,行伍出身满汉总计6位。督抚为文官,是清代文官制度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出身来看,大部分为正途出身,行伍在武职为正途,在文职则为异途。18位汉人中,其中15位为科甲出身,3人为行伍出身。科甲出身满汉总计39位,科甲出身占总数的62.9%;荫生8位,占12.9%;行伍出身满汉各3位,总计6位,占9.7%。
科甲正途出身虽然在陕甘总督群体中占了多数,但是考虑到翻译科的科甲成色不足以咸同以后汉人督抚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科甲出身的多数并不能正确反映陕甘总督群体的出身特征。在39位科甲出身的陕甘总督中,汉人占了18位,道咸以后汉人督抚群体的崛起急剧提高了科甲出身的比重。因此,以道咸以后,特别是咸同以后科甲出身的比例激增的时代特征并不能掩盖陕甘总督群体的一般性特点。另外,在汉人出身的陕甘总督当中,在同光以前以署理居多。科甲出身之甘督主要出现于嘉道以后,且汉人远多于旗人。
(五)上三旗与西北督抚
满洲八旗有旗份之别,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为天子为旗主,天子亲为统帅,是为上三旗,亦称为内务府三旗。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为下五旗,地位低于上三旗。下五旗出身之官员如有重大业绩与突出功勋,则可抬旗,改换旗籍,入上三旗。上三旗出身的满洲官员成为陕甘总督陕甘总督群体的重要力量。
关于上三旗所指,在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时期并不一致。自顺治时期,始确定两黄旗及正白旗的上三旗地位。努尔哈赤时代上三旗为镶白、正白、镶黄三旗。而在皇太极时代,随着满洲八旗内部的力量消长和关系变化,上三旗又演化为两黄旗及正蓝旗[9](P2)。自顺治时代起,自顺治时期,始确定两黄旗及正白旗的上三旗地位,以为定制,不复有新的变化[2](P31)。
从旗籍来看,从已明出身的甘督来看,其中上三旗满洲19位,上三旗蒙古、汉军8位,下五旗17位。从满汉关系来看,其中八旗*包括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总计38位,汉人18位,而汉族出身之西北督抚中,同治和光绪时期就占了7位。可见,康熙七年和雍正元年关于陕甘总督一缺的任职规定基本上是得到了遵守的。同治以前的陕甘总督中,满洲八旗,特别是上三旗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上三旗出身之甘督较多,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清代诸帝对陕甘总督这一职位的高度重视。因为西北边防对于清帝国军事国防的重要地位,清代诸帝将亲辖的上三旗子弟派往西北地区,以保证西北边防的稳定并加强对西北军事力量的控制。其次,陕甘总督的迁进路径特点也加重了上三旗子弟在陕甘总督简擢中的优势地位。上三旗的满洲世家子弟较多,而世家子弟仕进以侍卫和笔帖式为主要路径。在侍卫中,一等侍卫60名,均出自上三旗,每旗各20名;二等侍卫150名,每旗各50名;三等侍卫270名,每旗各90名。上三旗自一等至三等侍卫总计570名,为上三旗子弟提供了充足的上升机会和稳定的迁进路径。在乾隆时期25位陕甘总督*包括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十三年间的川陕总督和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五年间的甘肃总督。中,侍卫出身5位,笔帖式出身4位,科甲出身4位,荫生出身3位,荫袭4位,监生3位,出身不明2位,侍卫和笔帖式出身总计9位,满洲世家子弟在甘督简擢中无疑占据了优势地位。同治以前的陕甘总督中,满洲八旗,特别是上三旗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同治五年(1876)的百余年的时间内,只有毕沅、陆有仁、方维甸、杨以增、林扬祖、易棠、邓廷桢、林则徐出任陕甘总督,但皆为署理,只有易棠、杨遇春为实授,而且时间很短。而在从同治元年(1862)光绪二十六年(1900)38年的时间内,就有沈兆霖、杨岳斌、左宗棠、杨昌濬、曾国荃、谭钟麟、陶模、魏光焘等8人次的汉人出任陕甘总督,除陶模、魏光焘为署理外,其余均为实授。
余论:陕甘总督群体特征的时代差异
陕甘总督的群体特征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清前期顺治、康熙、雍正诸朝,因长期征战的军事需要及山陕督抚专用满洲的政治原则,长于弓马骑射的满洲将帅和八旗汉军垄断了西北总督一职。顺治时期,八旗汉军构成西北督抚的主体。自康熙七年起,西北督抚又为满洲将帅所垄断。雍正时期,虽然做出了兼用蒙古汉军的调整,但八旗满洲仍居主导地位。乾隆及其以后嘉道诸朝,在八旗满洲仍居主导地位的同时,汉人已崭露头角;同光以后,随着湘淮系地主阶级的崛起,满汉地主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方向性变化,湘系出身之将帅基本垄断甘督一职,至清末新政时期始有改变。
从陕甘总督群体出身来看,也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康雍时期非科甲正途的侍卫、笔帖式、行伍等途是这一时期陕甘总督迁进的主要路径;到了乾隆时期,科甲正途出身之甘督明显增多,而笔帖式、侍卫、行伍出身之甘督仍占很大比例。至嘉道以后,正途科甲出身比例有较大增长,咸同以后,在以汉人为主的陕甘总督群体中,正途科甲出身占据了主导地位。陕甘总督群体特征的时代差异背后的历史动因,既有入关以后民族风尚逐步演变,崇文之风逐渐扩大的因素,亦是清廷满汉政策调整的结果,也反映了满汉力量变化,汉族地主阶级力量逐渐增强的历史过程。
从康雍乾三朝甘督的出身来看,其时代性特征是明显的。侍卫及笔帖式出身所占比例较高,侍卫及笔帖式出身之甘督构成康雍乾三朝西北督抚的主体。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康熙七年钦定山陕督抚满缺制的限制作用,官缺制保证了满洲督抚在西北督抚群体中的主体地位,而侍卫和笔帖式是满人入仕的主要路径。另一方面是西北地区自顺治朝延续至康熙朝初期不断的反清斗争影响到西北督抚的选择上,长于军旅成为必要的技术性要求,否则难以贯彻清廷西北的统治意图。自康熙朝中期至乾隆初期对准噶尔的军事斗争实践催生了一大批侍卫及笔帖式出身的满洲将帅,在长期的征战当中,成长为西北督抚。
相比以清前期,清中后期陕甘总督的群体特征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从出身来看,在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出身的陕甘总督中,正途科目出身比例呈现急剧增长趋势,举人、进士出身总计10位,占了八旗出身的40%,8位汉家陕甘总督则皆为进士出身。而在同治、光绪时代,科甲出身之比例又有进一步的提高。科甲出身之比例激增,源于同光时代满汉势力之重大变化,及湘淮系地主阶级的兴起。由于汉人大多以科甲为进身路径,湖南为理学重镇,湖湘学派渊源,湘系将帅均具程度不同的科举背景。而以行伍出身荣膺封疆,则又反映了同光时期西北地区持续的边疆危机对西北督抚人选的技术性要求。
18世纪清帝国文官系统的官僚表现出一种技术化的倾向,即各行省督抚必须具备与各自所治理下的行省相适应的事务技术背景[10]。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河工、漕运、边务、军旅、农桑等技术背景是行省官僚的必备素质,而这些技术背景由于治下的地域社会特点密切相关,行省督抚必须具备相应行政技术能力,方能履行封疆之责。如两江总督与南河事务,直隶总督与北河事务,两广总督与外交通商事务,云贵总督与苗务,陕甘总督与西北边疆事务。在18、19世纪,清帝国的行省官僚所需要的技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即边务、河务、盐务、夷务。于此相适应,各行省督抚必须具备与各自治理的区域社会特点的相应技术背景,才能履行封疆之责,李鸿章能够长督直隶,左宗棠久据西北,其主要原因在于直督对于外交和甘督对于军事的技术要求。同样,自康熙初年确定的有关山陕督抚皆用满洲的规定就是考虑到了山陕督抚所辖之区域的军事地理位置,所以长于骑射而短于治民的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就成了西北督抚的首要人选。
满洲之民族性格必然影响其治下的地域社会,给特定地域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西北督抚的技术性要求是偏重于军事征战,满洲出身的西北督抚在国语骑射的教育背景下,本身就缺乏民生吏治的知识储备。从宦途履历上来看,八旗出身的甘督缺乏基层州县经历,即所谓担任“亲民之官”的任职经历,亲民理事的技术比较薄弱;同时,满蒙民族的民族性格及教育背景及仕宦履历又决定了其缺乏汉族官僚的经世技术,一般汉族官僚所熟谙的治理农业社会的经世技术,如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等知识与技术,对于满蒙出身的西北督抚来说,既不甚熟练,也不屑于学习。从同光以前西北督抚的奏折来看,有关农业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奏报垦田升科和灾歉请求蠲免等方面,这与同光时期湘系督抚的施政理念和治理举措有很大的不同,封疆大吏之民族性格及为政特点必然对于治下社会之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陕甘总督之群体特征是解读清代乃至近现代陕甘社会落后的原因的重要依据之一。
[1]赵尔巽.清史稿(卷116)[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福格.听雨丛谈(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康熙起居注(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清高宗实录(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张祖翼.清代野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孟晓旭.海疆危机与近代国家安全战略之调整[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3).
[8]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二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刘凤云.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J].清史研究,2010,(4).
〔责任编辑 韩 芳〕
A Study on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hangan Viceroy Group in Qing Dynasty
YANG Jun-min
(School of Historic Culture and Tourism, Hexi College; Baotou 014030)
Shangan Vicero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Viceroy system in Qing Dynasty. Comparing with the other systematic viceroy, Shangan Viceroy has its own traits. Because its importance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Defence System of Qing Dynasty, the Viceroy of Shan-xi and Shan-xi Province had unique rule from Kang-xi emperor, Man-zhou ethnic official had been the majority of Shangan Viceroy.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hangan Viceroy group in Qing Dynasty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Viceroy System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n-zhou ethnic and Han ethnic.
Shangan Viceroy; Group structure
2014-09-10
杨军民(1970-),男,甘肃庆阳人,硕士,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清史及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
K249
A
1004-1869(2015)01-007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