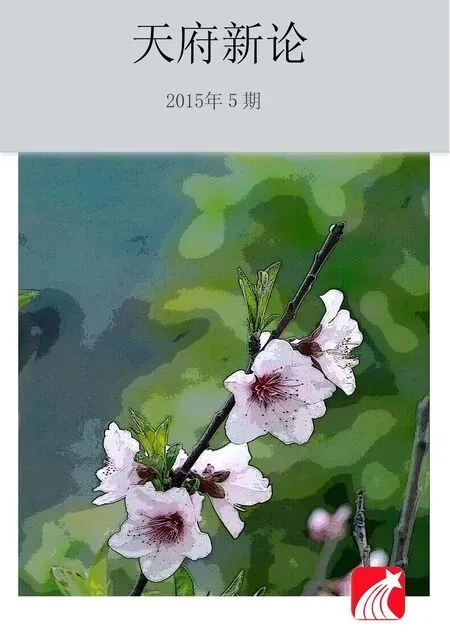断裂中的延续:新文化时期新旧文明转变中的阶级观念
张文涛
一、引 言
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专注于近代启蒙思想,后期则转向苏俄共产主义,前后两期的过渡很短,存在一种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感在已有的学界研究中比比皆是,且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革命史的书写中更是夸大这一断裂,以昭示社会主义 (当然主要是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国人向往的道路归宿。最典型者莫过于,学界传统认为,经过新文化运动尤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近代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迈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在革命的领导力量、指导思想、革命前途等方面有了质的转变。这种简明的划分的确有助于认清历史的主流,但同时也难掩遮蔽历史复杂性的划约之感。①历史的复杂性及其逻辑往往突破理论的逻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就是一例。相较之下,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关注远在资本主义之上。换言之,社会主义成为国人救国道理的目标值确立其实渊源有自,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旧文明的断裂程度可能并没有现今学界所言之深。学界对此问题已有所论及,如张玉法《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但对社会主义传播的重要性的估计仍有所不足。此问题关涉较大,笔者当另文详论。
强调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文明的断裂的研究,近年又有推陈出新之作。其中,汪晖主要通过考察当时趋新激进的《新青年》和相对保守的《东方杂志》后,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共和危机使18、19世纪的欧洲现代性模式处于深刻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系统,突然失去了自明的先进性;共和危机与国家危亡不再仅仅被归咎于中国传统,而且也被视为19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汪晖视此过程为20世纪新文明 (社会主义)对18、19世纪旧文明 (资本主义)的断裂。他认为: “没有一种与19世纪的政治—经济模式断裂的意志,中国的激进政治不可能形成;同样,没有这一断裂的意识,中国的那些被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也不可能形成”;所以如此,在于作者清楚地看到了政治态度相左的《新青年》和《东方杂志》竟然“都批判18、19世纪的‘旧文明’(从政治模式到经济形态),都拥抱20 世纪的 ‘新文明’(社会主义)”〔1〕。
新文化运动时期,国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新旧文明的认识和选择上的断裂感,不仅存在于激进的《新青年》陈独秀等人,也见之于给人保守印象的《东方杂志》,因此,这种趋新弃旧的断裂尤显得更为彻底与全面。汪晖的上述观察无疑是深刻的,但这种观点主要是就历史趋向而言,且仅强调在中国语境下,国人认识中20世纪新文明与18、19世纪旧文明在欧战、民初的共和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序列事件中的断裂面,无形中低估了两种文明在国人思想世界中的延续性。从思想的传播和国人认识的实况而言,这种延续至少有两方面内容:(1)就作为“新文明”的社会主义而言,完全可以追述到20世纪初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从被断裂一方的“旧文明”资本主义来说,低估了其内在转向“新文明”的可能性。这在国人对阶级观念和社会主义的接受中,表现得相当清楚。
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的影响,及他们对社会主义态度的异同,此处不必详论。〔2〕这里需要强调的是:(1)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实则等同于社会政策,与梁启超所谓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去不远,后又因共和未真正建立,革命接连再起,革命党人的“民生主义”未得施行。但他们把“平均地权”写进了同盟会纲领,民生主义也成为革命党人的指导思想之一,且孙中山等不断为之奔走,起码就其象征意义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就无由理解经过短暂的疏离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就通过创办《建设》、《星期评论》等杂志迅急介入、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3〕也无由理解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尤其副刊《觉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镇;更进而言之,也无由理解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所言“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4〕。(2)在承认“阶级”、但试图用“社会革命”政策“预防阶级斗争”的革命党主流之外,也出现了诸如“献身破产,铲平阶级”、“以经济革命”“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等于赞成“阶级斗争”的激进言论。〔5〕换言之,在国人思想世界中早于20世纪初就已经埋下转向新文明的火种,只要新的时代环境和舆论主流酝酿形成,其发展成燎原之势就不难理解。此等外因无疑就是前述汪晖所强调的欧战、民初的共和危机,还有继之而起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以下主要从内因着手,解读新文化运动时期国人对新旧文明之认识和取舍上的内在一致性,凸显其断裂中延续的一面。
二、新旧文明的内在转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国人眼中18、19世纪资本主义“旧文明”向20世纪社会主义“新文明”内在过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还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归趋、服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媒介。换言之,18、19世纪资本主义“旧文明”和20世纪社会主义“新文明”也存在着断裂中的延续,并非截然断裂。
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敬告青年》一文第一目“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开宗明义就说: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 (女)权之解放也。〔6〕
陈独秀此处将“均产说”置于“人权平等说”和欧洲“解放历史”的序列中,视其为人权平等在政治、宗教、经济、女子参政等领域演进中的一环,并没有显而易见的断裂之感。当然,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还只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不过,当他言及“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时,虽不敢称他距马克思主义已为时不远,但说它为陈独秀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作了思想铺垫似不为过。事实上,陈独秀从最先的思想启蒙到转向社会主义,也是循着上述“人权平等说”由政治、宗教再及经济、社会渐次扩大的序列实现的。
就在陈独秀上述言论发表后不久,读者褚葆衡就致书《新青年》讨论社会主义。在对《新青年》思想启蒙、 “反对孔教”表示一番“钦佩无似”后,褚氏笔锋一转,称“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为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强权者势愈甚,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觏,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仆愿如此,不识足下以为如何。”褚氏此论大有以社会主义“最新之思潮”倒推《新青年》由思想启蒙“更上层楼”的意味。附带需要指出的是,褚葆衡论社会主义却未提及其时进行正酣的欧战,可见他并非因反省欧战而推崇社会主义,只能归之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不绝如缕。对此,陈独秀的回答未免会让他失落:“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7〕
如果说褚葆衡上述期待《新青年》于思想启蒙基础上更进一步还属一厢情愿,三个月后陈独秀在回答署名“I·T·M”读者的回信时态度就大不相同:“足下于本志所持论,独垂询三事,可谓目光如炬矣。欧美政家学者,方劳精竭智以事此三者之讨论,而尚无完全之解决,智识浅薄如记者,更何论焉。既承下问,姑略陈所主张,其详情俟诸异日。”“I·T·M”所问的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即为:“足下云,道德堕落原于人口加增,经济制度未及改良,富力失其平均,金钱造成罪恶,敢问改良经济制度之道。”陈独秀的回答诚恳且详尽。他回答道:
今世经济制度,过重利权,是以兼并盛行,贫富悬隔,极其流弊,不至以贫富为善恶智愚之标准不已。欲救此弊,虽未必即能悉废今世之经济制度,而限制土地之过量兼并,及废除遗产制度,未始不可行也。记者所谓改良经济制度之道,即以此二者为始基。盖土地与人口之比例,倘不过失其平均量,自非生性懒惰者,皆有生存之余地。然后世之所谓罪恶,或真乃罪恶。否则贫而求生,虽盗窃亦未必即为罪恶也。遗产制度不废,则坐拥先人厚资,且以之造成罪恶者,其勤勉,其智力,未必有加于贫无立椎之善人也。〔8〕
显而易见,陈独秀从启蒙角度对中国社会道德的批判已触及经济制度。以启蒙立场对中国社会道德的批判是决绝和革命的,那么,对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否定当为期不远。当然,此处陈独秀对经济制度的批判有雷声大雨点小的嫌疑:“未必即能悉废今世之经济制度,而限制土地之过量兼并,及废除遗产制度,未始不可行也。”陈独秀对私有经济制度流弊的揭露是革命性的,但其对策却是改良的。不过,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作为18、19世纪“旧文明”象征的启蒙思想已向经济领域渐次扩充吗?
“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前半月,陈独秀发表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其中说道,“现在时代的国际强权,政治的罪恶,私有财产的罪恶,战争的黑暗,阶级的不平 (原注:贫富男女贵贱官民尊卑名分等问题,都包含在内),以及种种不近情理不合人类自然生活的法律道德,四面黑暗将我们团团围住。”〔9〕陈独秀此处将阶级不平的范围界定为贫富男女贵贱官民尊卑名分等,在其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形成中至关重要。“私有财产的罪恶”、“阶级的不平”,已形之于纸上,但他此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在几天后的《多谢倪嗣冲张作霖》中,他依然认为“中国资产社会和劳动社会都不很发达,社会革命一时或者不至发生”。〔10〕在同日的随感《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他肯定了俄国革命,并将其意义与法国革命等量齐观:“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不过,有意思的是,引发他这一随感的却是“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11〕
表征陈独秀所宣传的18世纪、19世纪“旧文明”向20世纪之“新文明”内在转化的最好证据,莫过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的《实行民治的基础》,这是一篇需要细致讨论的文章。他几乎不易一字照引了杜威对民治的态度:“(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12〕陈独秀认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 (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他进而阐发对杜威民治主义的认识:
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民治主义” (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 (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所以杜威博士列举民治主义的原素,不限于政治一方面。
陈独秀所谓“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的说法,无疑是18世纪、19世纪“旧文明”向20世纪“新文明”内在转化的最好诠释。在陈独秀看来,上述四种民治主义中,政治的民治主义只是工具,而非目的,他劝说国人莫把工具做目的,他更看重社会经济上的民治主义:“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他还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13〕
陈独秀写作此文时显然有鉴于俄国革命的现实关怀,但其学习目标却非苏俄:“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他继而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民治社会的方案:“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他在文末对苏俄阶级斗争的道路有所保留,“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恶作剧 (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14〕陈独秀这段话耐人深思,他不情愿阶级斗争的发生,但分裂的社会与人心又似乎让这一切不可避免。
学界对陈独秀此文的评价颇为有趣。周策众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陈独秀提出的地方单位自治和同业工会的建议,至少表明暂时放弃了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显示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15〕陈独秀是否受基尔特社会主义影响姑且不论,①陈独秀的地方单位自治和同业工会建议,与孙中山1905年在第二国际书记处的言论非常相近:“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以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时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将比许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会议所取得的还要多。”参见:柏纳尔.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J〕.近代史资料,1979,(3).说他放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则未必属实,因为直到此时陈独秀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更别说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放弃一说显然乃无的放矢,言之过早。同时,一些学者认为此文表明“一方面他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和意义;另一方面又指望资本主义制度自然的渐渐的消灭,不情愿阶级斗争发生,这表明,陈独秀此时还没有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遗留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16〕此处所论从后人标准看本没有问题,但事实上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后出标准来衡量此时陈独秀的“进步不够”,实有强人所难之处。如果回到彼时陈独秀民主主义者的实态,则可以想象他先前所传播的18、19世纪“旧文明”向20世纪“新文明”转化中的巨大张力。随后的1920年,陈独秀朝着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17〕很快突破了18、19世纪“旧文明”的藩篱。此看似偶然,但若着眼前述新旧文明的内在转化,实则水到渠成。
三、民治的扩展与阶级观念
“五四”时期,看到18、19世纪“旧文明”向20世纪“新文明”内在转化、而非截然对立的不仅仅是陈独秀,他的《新青年》同事李大钊、胡适,还有他们的学生一辈,亦即他们所期待的新青年中,也都隐然有所反映。
李大钊在1916年《民彝》创刊号上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中,就有“夫代议政治,虽起于阶级之争,而以经久之历验,遂葆有绝美之精神焉”的认识。〔18〕此时,李大钊虽已稍有社会革命的意识,却依然完全肯定资本主义代议制的价值。在1918年12月给曾崎《国体与青年》一书的题跋中,李大钊就认为“今日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它看作与Democracy是两个东西。”〔19〕李大钊此处所谓“Democracy”是“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的认识,实可与陈独秀前述“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的说法相互发明。
在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性文献《庶民的胜利》中,他以为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 “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为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20〕李大钊这里虽然以“劳工主义”否定“资本主义”,但还是完全肯定“民主主义”,并将其与“劳工主义”并称。即使在后来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也一再强调“德谟克拉西”,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一文堪称代表:“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21〕可见,断裂中依然有延续,并非截然两断。①对李大钊民主观念的相关探讨,可参见:童世骏.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A〕.许纪霖,宋宏.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C〕.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81-507.
“五四”时期,不仅作为老师辈的陈独秀、李大钊有上述认识,在主办《新潮》、后来转向自由主义的学生一代傅斯年、罗家伦中也不乏这种思想。傅斯年在《新潮》一卷一期上刊发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文就认为:
吾于俄国状态绝不抱悲观。以为近世史之精神,全在思想自由。自“文艺复兴”而后,此思想之自由一现于“宗教改革”:试验之者德意志列邦也。德国为此试验损失至大,数世不竞。然世界竟借此试验之结果,精神上脱离宗教专制:其供献于文化之演进为不少矣。再现于政治革命:试验之者法国也。法国为此试验乱八十年,国势上之损失至巨。然世界竟以此试验之结果重建政府,世谓真国家者,美列邦独立,法国革命以后之新生产不为虚言。凡此二种运动,皆文明史上应有之阶级:凡为此试验之两国,进化之先锋也。今步此二种运动之后更待改革者何事乎?社会而已。凡今日之社会,本其历史上之遗传性质组织,多有不适于现在者;或有仅有形式更无灵性者;或有许多罪恶凭傅之而行者。推翻之另建新者,理想上所有事也。俄国既为此第三度改革之试验,自不能不有绝大牺牲。〔22〕
傅斯年将俄国革命视为“近世史之精神,全在思想自由”的第三阶段表现。思想自由恰是现代性“普遍理性主义”的体现。同为“五四”学生一代弄潮儿的罗家伦在同期的《今日之世界新潮》文中也认为: “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23〕
当然,与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思路最为相近的是杜威的学生胡适。
1926年,胡适在游历苏俄期间经过与蔡和森“舌战”的刺激,意欲组织政党作政治活动。②罗志田对此问题有详论,此则材料亦受其启发。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五四运动到北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9-197.他在当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24〕。胡适强调自由主义渐渐扩充,无疑和陈独秀眼中杜威民治主义由政治方面而社会经济的主张属同一理路。
美国学者林亨特在《人权的发明》中认为,“人权”的观念像革命本身一样,为讨论、冲突和变化打开了一个无法预测的空间。对权利的期望虽然可以被否定、遏制,但只要没有实现,就不会消亡。其内在逻辑在于,“只要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高贵的群体被讨论,那么那些处于同一范畴但是在想象到的范围内较低的群体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议事日程上”。〔25〕杜威、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胡适眼中的“民治主义”、“Democracy”和“自由主义”也是如此。无产阶级的“民治”和“自由”——社会主义——就成为权利的内在逻辑的延伸。
四、结 语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说,国人在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告别18、19世纪资本主义“旧文明”,接受20世纪社会主义“新文明”,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渐变中的突变。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承认突变,就是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续反应的划时代影响,也就是承认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的或然性;承认渐变,就是承认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持续性,和承认18、19世纪“旧文明”向20世纪“新文明”内在转化的可能性,也就是承认中国接受社会主义的最终必然性。不承认前者,就无法理解欧战和新文化运动转向的意义,也就无法理解其后中国激进政治的形成。不承认后者,就难以理解孙中山系革命党人的“革命之再起”,也难以理解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趋近,也在事实上难以理解阶级观念在中国兴起的内在理路。
学界既有的研究,在廓清时代主流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国人在接受新旧文化中的断裂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就阶级观念本身,它并没有否定新文化运动前期所倡导之民主,就其被国人接受的轨迹而言,事实恰恰相反。阶级观念是民主观念在阶级领域延伸后的结果,克服阶级壁垒是民主自我逻辑扩展过程中的试金石。民主观念与阶级观念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其间的复杂关系在新文化时期所向往之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显而易见。
〔1〕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9,(4).
〔2〕张玉法.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1-111.
〔3〕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 (1914~1924)〔J〕.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9,(57).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C〕.中华书局,1986.355.
〔5〕壮游 (金天翮).国民之新灵魂〔J〕.江苏,1903,(5).
〔6〕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1).
〔7〕记者 (陈独秀).答褚葆衡 (社会主义)〔J〕.新青年,1917,2(5).
〔8〕记者 (陈独秀).答I·T·M(社会道德)〔J〕.新青年,1917,3(2).
〔9〕陈独秀.我们应该怎么样?(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J〕.新青年,1919,6(4).
〔10〕只眼 (陈独秀).多谢倪嗣冲张作霖〔J〕.每周评论,1919,(18).
〔11〕只眼 (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J〕.每周评论,1919,(18).
〔12〕袁刚,孙家祥,等.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13〕〔14〕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J〕.新青年,1919,7(1).
〔15〕〔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236-237.
〔16〕贾兴权.陈独秀传〔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78.
〔17〕任建树.陈独秀传 (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79.
〔1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2006.149.
〔1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2006.264.
〔20〕李大钊.庶民的胜利〔J〕.新青年,1919,5(5).
〔21〕李守常.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J〕.新青年,1922,9(6).
〔22〕孟真 (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J〕.新潮,1919,1(1).
〔23〕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J〕.新潮,1919,1(1).
〔24〕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 (1923-1927):第4册〔C〕.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39.
〔25〕〔美〕林·亨特.人权的发明〔M〕.商务印书馆,2011.13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