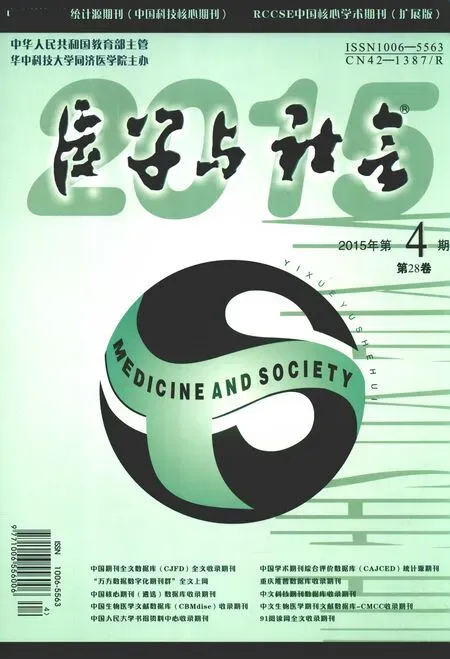我国医学课程整合的发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王晶 曾志嵘
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广州,510515
我国医学课程整合的发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王晶曾志嵘
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广州,510515
摘要将整合理念引入医学课程改革是推进医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医学院校在经过反复地探索和实践之后,形成了以模块化课程模式为主、临床前期课程为重要补充、小范围试点先行为实施策略的医学课程整合趋势和特点。但在改革取得进展的同时,在整合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如整合课程中知识的分离与遗漏,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重点冲突,以及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培养、新课程考核方式改革、新课程评价体系建立等问题。
关键词医学教育;课程整合
随着医学技术及医学模式的进步,医学科学的发展更趋向综合化和社会化,这促使医学教育更强调对学生胜任能力的发掘和培养,强调医学课程必须顺应现代医学科技和社会需求,并以团队为基础的结合跨专业教育和信息技术进行课程模式的转型[1]。在这样的背景下,医学教育者不断寻求胜任能力教育的土壤,随之医学整合课程应运而生。课程整合是指通过科目的整合、科际的整合实现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结构优化与重组[2],将医学课程进行整合,旨在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医学知识的融会贯通。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西余大学推出第一期医学整合课程起,医学课程整合因其先进的教学理念,逐渐被世界各国的医学教育学者所认可,并于20世纪末期引入我国,掀起了我国医学课程改革的浪潮。
1 医学课程整合在我国的发展
国内医学整合课程的探索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国绝大部分医学院校的课程模式是以学科为中心,课程设计强调基础性和系统性,但在学科课程之间缺少联系,也较少关注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随着医学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的发展更新,国内的医学教育者开始重新思考传统课程模式的弊端。1999年,经过对国际医学教育趋势的重新判断,中国医科大学借鉴美国哈佛大学的课程模式启动了该校的课程改革[3],与浙江大学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等院校一起,成为国内首批开展课程整合的医学院校。在课程整合的初步探索阶段,以器官系统为基础的课程模式成为院校主要选用的模式,而在整合方式上,大多数院校以横向整合为主,整合范围主要在基础医学部分。此外,同时期进行课程整合的院校,也有立足于学科课程体系实施整合的,如中山大学医学院开发的“243”型课程,该课程在沿用传统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吸收了综合化课程模式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扩充了选修课的门类,并采用了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实现课程模式的优化[4]。
2008年9月,教育部、卫生部联合下发《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文件中特别强调,“医学院校应积极开展纵向或(和)横向综合的课程改革,将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合理整合”以及“医学院校必须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和‘自主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注重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关注沟通与协作意识的养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极大地推动了医学院校参与课程整合的热情,越来越多的院校认识到课程整合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我国的医学课程改革随即进入了一个高潮期。这一阶段,各高校在课程整合的程度和范围上均有所加深,整合推及到临床医学课程,并开始注重人文课程和预防医学课程与临床医学课程的纵向整合。同时,对相应的教学方法、考核方法和课程评价方法也进行了探索和改革。
2 我国医学课程整合的趋势和特点
2.1 模块化课程模式成为主流
纵观医学课程模式的发展史,先后出现了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模式、以器官系统为基础的课程模式、以问题为中心的课程模式、以临床表现为基础的课程模式、模块化课程模式、以及以胜任力为导向的课程模式。其中模块化课程模式,即将医学知识按照某一主题或器官系统进行区段或模块划分的模式,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汕头大学医学院,该院于2002年9月启动教学模式改革,改革后课程的核心部分由公共基础模块、人文社科模块、系统整合模块、技能模块和临床核心模块组成,其中系统整合模块又将医学基础和临床课程整合为11个课程模块[5]。浙江大学医学院在进行整合课程设计时,以人体系统为基础形成了囊括医学基础I,神经、精神与运动I,心血管、呼吸和肾脏医学I等八个部分的模块化课程[6]。此外,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在八年制医学整合课程的探索中也运用模块化的整合模式,形成了人文素养模块、人体形态学模块、临床医学导论模块等9个模块课程[7]。
2.2 临床前期课程受到重视
在国内传统的临床医学课程体系中,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缺乏有机连接,学生在学习临床知识之前对医疗实践缺少感性的认识[8]。为了有效弥补传统教学中的不足,提早培养医学生的职业认知,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认识到设置临床前期课程的重要性。关于临床前期课程的类型,一类是理论授课和讲座,通过语言和文字让学生了解医学史以及现行的医学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知识;另一类是临床见习和社区实践,丰富学生对职业角色的认知和体验。在整合课程的设置中,为了体现课程的综合性和连贯性,通常临床前期课程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以“临床医学导论课”的形式,如中国医科大学,已经形成了由医学篇、医生与病人篇和临床篇三部分构成的临床前期课程,课程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质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9];二是以课程模块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课程内容更加宽泛,如四川大学,该校的“临床医学导论模块”,课程涉及医学生能力培养、医学史、生命伦理学、行为科学、医学各学科概论、社会实践等多方面内容[10]。
2.3 小班试点先行
我国的医学教育模式不同于欧美国家的精英教育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是我国发展医学教育首先要考虑的部分。因此面对有限的教学资源,和相对大规模的学生人数,在医学课程整合的探索阶段,大多数学校会选择以长学制小班为课程整合方案的试点单位。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为例,该校自2007年起设立“侯宗濂医学实验班”项目,从每年入校的临床医学七年制新生中择优选拔40名进入“侯宗濂医学实验班”学习,以试办八年制医学教育为契机,开展以课程整合为基础的教学实践,进行教育教学的全面改革[10]。这种实施策略,一方面是考虑到参与课程整合学生的整体素质,包括自主学习和批判思维等能力;另一方面是希望借助小班试点,循序渐进地探索和完善适合学校校情和未来发展的教学方案,减少新课程方案对整体教学的冲击。
3 医学课程整合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课程内容的分离和遗漏
在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教学中,课程内容的有序性、重点难点及教学方式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课程自身的知识体系较为系统,各学科的教学前后也有必要的过渡和铺垫,因此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时都驾轻就熟。但在设计整合课程时,由于尚无一种成熟可靠的整合模式做借鉴,参与课程整合的领导者、组织者及教师对课程整合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因此整合过程中常会出现各种分歧和问题。特别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知识分离和遗漏的情况常有发生[3]。在课程整合之前,我们常常会将知识按照器官系统或主题做一个分类,希望在分类的框架内将课程内容清晰的做出排列和组合,但事实上总有一部分专业知识不确定整合到哪个课程[11],这些知识由于不能划归到某一简单的分类,致使它们最后不是被独立出来就是被暂时搁置,这样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课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延伸至课堂教学,就容易因为不同学科间知识融合的不够,以及教师的频繁更换,让学生产生一种知识分离的感觉[12]。理念指导操作,课程设计出现问题与对整合理念的认知偏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课程整合强调的是模糊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培养学生用系统和联系的思维学习的能力,并不是按照新的条条框框对医学课程重新分割,所以在实际整合过程中教师们并不必拘泥于某种框架或模式,而应该从医学知识的内在逻辑出发组织课程和教学。
3.2 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重点冲突
课程整合强调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但在传统的课程体系中,两者相互交叉的知识在学习目标以及重点难点上并不一致,一些在临床课上已经略过或只要求了解的疾病,其生理病理等基础医学的相关知识却是学习重点。回首基础医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发展,从默默无闻到成为医学教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础医学课程的数量和内容不断增加,学科分类不断细化,但与临床实践却渐行渐远[13]。因此,重新审视学习基础科学对培训未来医生的重要性很有必要,尤其在生物医学知识大规模扩容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努力限定哪些学科领域是真正重要的,并且要思考我们是否能够寻找一种将基础科学教育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13]。在整合过程中,当基础内容与临床内容出现冲突时,建议在系统整合模块中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组织课程,但如果过滤掉的基础内容属于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大纲中考点,可将这部分知识转移到基础医学总论中做补充,从而保证在融合的前提下不发生知识点的遗漏。
3.3 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薄弱
在新课程模式的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者,而转换为学生学习知识的推动者。这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更广泛的教学能力,能够跳出本学科教学的局限,将能力延伸至跨学科的、整体的教学。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所表现出来的跨学科教学能力却并不令人满意。一部分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讲授自己专业的知识,而不与相关专业进行联系;还有一部分教师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知道所有的医学知识,扩展联系其他学科的时候也会显得力不从心[9]。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很多院校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对参与课程改革的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学生普遍反映教师们除了关心自己的讲授内容外对整个课程知之甚少,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很少关注哪些内容已经讲过或者学生还应该学点什么,导致课程与模块的其他部分脱节,错失了许多真正可以达到整合目的的良机[14]。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医学院校缺乏清晰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师并没有意识到加强自身综合能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教师缺少对整体教学方案的把握,课题组内成员也疏于交流,导致课程的整体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3.4 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滞后
课程、教学和考核,这三者之间具有连续且密切的联系。在原本以知识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是被动接受者,考试主要考察的是课程结束后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掌握,很少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以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进行考核。如华中科技大学,该校在其基础医学整合课程的考核中,采用的是9门传统学科出一张考卷的方式,考题总分为100分,具体分值情况:人体解剖学10分、组织胚胎学8分、生理学5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32分、医学遗传学l0分、免疫学4分、病理学24分、病理生理学2分、药理学5分[15]。面对这样的试卷,学生常会选择放弃分值较低的学科的复习,使教学效果打折。考核方式难以实现突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国家执业医师的考试仍以记忆性知识考核为主,因此学校和教师都不愿意放弃这种利于训练学生通过执照考试的方法,毕竟通过全国医师资格考试是成为一名医生的前提;二是出于对就业市场评估标准的考虑,避免学生在应征用人单位时因成绩的特殊表达而失去比较优势。
3.5 课程评价体系亟需完善
课程评价是判定课程设计效果,做出修订完善课程决策的必要过程。一直以来,我国的医学课程评价都是以单一主体评价和总结性事实评价为主,即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课程效果的主要手段。但这样的评价模式缺少对课程价值的判断,尤其是在能力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课程评价不仅要揭示“课程实际做到了什么”,更要清晰“课程应该做什么”。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面对改革的不确定性,课程评价的意义更加重大,实现课程评价主体和方法的多元化是稳步推进课程改革的重要保证。在评价主体的选择上,可以借鉴斯克特的教学评价思想,将与教学活动相关的教师、学生、课程负责人、教学管理者等都作为评价的主体,因为这些主体对教学活动、课程制定、修改意见具有切身的体会[16]。在评价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量化考评之外,应当适量增加主体的自我定性评价,如通过观察法或档案袋法来记录和跟踪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变化,从而全面评价课程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柴文戍,张锦英.浅谈医学教育转型与临床课程整合[J].医学与哲学,2014,35(11):78-80.
[2]于翠翠.课程整合的现实问题与可能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33(34):61-64.
[3]乔敏,路振富,孙宝志等.学习哈佛经验建立基础医学整合课程体系的实践[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2(4):44-46.
[4]王庭槐,王淑珍,陈琼珠.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243”型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27(3):1-4.
[5]冯东.基于通识教育的课程系统变革方式探析——兼谈汕头大学当前的课程与教学改革[J].复旦教育论坛,2007,5(2):40-43.
[6]罗本燕,唐敏,许毅,等.医学八年制课程整合模块化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以神经精神与运动模块I为例[J].西北医学教育,2013,21(5):1020-1022.
[7]万学红,卿平,石应康.“从树干到树叶”:医学八年制课程整合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9,9(4):367-370.
[8]赵芳,熊世熙,周斌,等.对高等医学院校“早期接触临床”课程建设的思考[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3,27(5):586-588.
[9]张阳,孙阳,伦施斯,等.以培养能力为目标的《临床医学导论》课程整合教学改革[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2,11(12):1208-1211.
[10]臧伟进,王渊.八年制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教育改革的探索[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1(1):26
[11]高岳,张东华,郭劲松,等.医学课程整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2(1):60-62.
[12]曾静,卿平,左川,等.临床医学专业系统整合课程改革初探[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3,13(5):548-552.
[13]David J Weatherall. Science in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during the 20th century[J]. Medical Education,2006,40(3):195-201.
[14]Muller JH, Jain S, Loeser H, et al. Lessons learned about integrating a medical school curriculum: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curriculum leaders[J]. Medical Education,2008,42(8):778-85.
[15]付四清,晏汉姣,王小丽.“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医学概论整合课程研究[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3,12(1):27-30.
[16]李冉.从斯克特课程评价观审视大学课程评价[J].课程教育研究(上),2014(8):24.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and Main Topics of Medical Curriculum Integration
Wang Jing et al
SchoolofHumanitiesandManagement,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 510515
AbstractLeading integration in medical curriculum refor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many medical universities join in medical curriculum reform. After repeated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ur country formed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based on modul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focusing on pre-clinical curriculum, and starting with little scope to 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lso appeared some problems of isolation and missing knowledge, teaching priority conflict on basic and clinical, unsatisfactory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examination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et al.
Key WordsMed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2014-12-12;编辑冯达)
通讯作者:曾志嵘,jmgw2016@163.com。
中图分类号R197.3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723/j.yxysh.2015.04.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