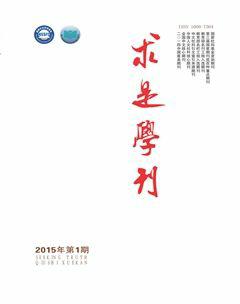矫正要素比价扭曲、资源错配与发展转型
谢攀,龚敏
摘 要:要素比价扭曲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它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性原因。劳动力、资金、土地以及能源等要素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扭曲了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导致厂商在隐性补贴的成本体系中,弱化了自主创新和推进产品优化升级、节能环保的动力,固化了对要素比价负向扭曲的路径依赖;居民受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影响,消费占GDP比例不断下降。要素比价扭曲加剧了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并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提出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微观基础保障这一结论。
关键词:矫正要素比价扭曲;资源错配;发展转型
作者简介:谢攀,男,经济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研究;龚敏,女,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3&ZD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JJD790026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1-0066-08
引 言
要素比价扭曲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运用行政力量压低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价格,扭曲要素之间的比价关系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实现以GDP与财政收入增长率最大化为目标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基本政策手段。由于人为地压低要素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超出市场均衡水平的高投资、高积累,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以压低要素价格为基本特征的要素比价扭曲,使居民作为要素所有者在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低于应有水平,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严重依赖“投资驱动、出口拉动”。久之势必形成严重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一旦世界经济萧条,萎缩的国际市场势必使高投资所形成的庞大国内生产能力难以实现,增长率因此急剧下滑。与此同时,倾向资本、利润驱动的社会再生产方式背离了我国社会生产的基本目标,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比例使社会矛盾不断累积,严重地威胁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恢复要素市场均衡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以及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微观基础,更是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向现代发达经济体过渡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要素比价扭曲问题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从资源错配视角分析国别经济增长也成为增长文献的重要发展[1]。本文对要素比价扭曲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与评析。首先,探讨要素比价扭曲的成因及程度;其次,以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为例,剖析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及效率损失;再次,从理论模型、实证方法和微观数据等层面,分析现有文献不足;最后是结论和引申。
一、我国要素比价扭曲的成因及其程度
要素价格扭曲是指由于市场不完善导致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与其边际产出或机会成本之间的偏差或背离[2]。其中,正向扭曲是指要素价格大于或超过其机会成本或边际产出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负向扭曲则是指要素价格小于或低于其机会成本或其边际产出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大部分现有研究认为我国要素市场目前存在着负向的价格扭曲。
(一)要素比价扭曲的成因
世界经济史上,实行赶超发展战略的后发经济体对要素比价进行干预,通过扭曲要素市场实现倾斜式发展并不罕见。日本、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为了达到更快增长,也曾实行过要素市场扭曲的发展模式[3]。但是在我国,要素比价扭曲的程度、范围以及时间长度,则都要深、广、长得多,根源何在?从体制层面上看,以追求经济增长率为主要目标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是阻碍我国要素比价扭曲得以调整的根本原因。这一体制性因素根深蒂固,导致了要素比价不能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随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一方面,决策层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远滞后于推进产品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无论是通过压低要素价格促进资本积累来实现的工业化,还是通过劳动力转移和户籍制度约束来实现低成本的城市化,本质上,都为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一条直接、便捷、有效的途径。一旦保增长、抗通胀、调结构三大目标发生矛盾时,被弱化和放缓的往往是调结构,厂商在隐性补贴的成本体系中,受投入产出激励机制驱动,形成并固化了对要素比价负向扭曲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竞标赛竞争的压力,频繁干预要素市场的交易活动,普遍存在对要素资源的分配、定价和使用等方面显性或隐性的管制,各级政府通过有意识地压低要素(包括劳动力、国内资金、土地以及资源环境等)价格,吸引资金,扩大投资规模。短期来看,这无疑促进了招商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由于生产要素价格(工资、利率、地价等)严重偏离市场供需关系,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发展水平良莠不齐,正面溢出效应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国在对外开放中所应取得的福利[4],并削弱或抑制企业R&D投入,让外资企业利用寻租活动来获得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所带来的低成本要素投入和租金收益[5]。同时,与外资企业相比,要素市场扭曲对本土企业的出口激励效应更大[6],加剧了对外需的依赖和外部失衡。
(二)要素比价扭曲程度测定
在要素比价扭曲程度测定方面,郝枫、赵慧卿(2010)通过考察实际生产状态与潜在生产状态之间的差距,来反映资源利用效率与市场扭曲程度,将各类市场扭曲分为生产无效率与要素市场局部价格扭曲、产品市场扭曲、要素市场全局价格扭曲等三类,并发现总体扭曲程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呈上升趋势;在改革初期则明显下降,80年代基本保持稳定;90年代初期再次上升,其后下降并基本保持稳定[7]。黄益平和陶坤玉(2010)的估算认为,资本成本扭曲占整体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的40.5%[8]。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进一步发现资源误置是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而国有企业又是造成资源误置的主要因素;行业内部的资源重置效应近似于0,进入和退出效应没有发挥作用;此外,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资源误置程度越低,并且不同地区的资源误置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明显的收敛趋势[9]。
二、要素比价扭曲与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
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整体滞后于产品市场,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与资源错配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资源错配程度
1. 劳动力价格扭曲与劳动力资源错配
受户籍、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制约,劳动力价格扭曲由来已久。劳动边际产出与劳动价格之间的偏离程度相差很大[10],尤其是制造业工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的增长差距扩大,竞争性部门的劳动工资增长长期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11]。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ULC) 呈下降趋势,2009年的ULC甚至不及1999年的90% [12]。更严重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化依然严峻,体制外劳动者收入和福利被挤压的境遇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快速上升。据统计,2008年,全国受理劳动争议数量创出近70万件的历史纪录,是1994年的36.3倍。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近两年,劳动争议案件总量有所回落,但因劳动报酬引起的争议占比仍然较高(1/3左右,见图1)。一些计算劳动要素误置引致的福利损失的研究也发现,1998—2007年间,劳动要素在制造业两位数代码产业内、产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配置扭曲[13]。这也印证了中国制造业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增长快于工资率增长,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状况正在进一步恶化的事实。
2. 资金价格扭曲与资金错配
有些研究认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前,更为稀缺的资本要素甚至比劳动要素的扭曲和错配程度更严重[14]。一方面,从全国看,资本回报率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扩大[15]。2005年,两者的差距增至15.46个百分点,比1996年最低时期上升了6.14个百分点(见图2)。较低的资金成本和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恰恰是投资占GDP比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资金价格双轨制大行其道。国有部门融资时,不仅资金价格总体上比较便宜,而且渠道多,品种丰富;相反,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获得资金的成本普遍偏高。扭曲的资金价格体系,通过供应链向实体经济一步步传导,致使产业内和产业间资金错配愈演愈烈。无论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行业,还是光伏、风电等新兴行业,在地方一次次“大干、快上”的热潮中,涌入了巨量资本,产能过剩突出。国内外需求稍有波动,沉淀资金的财务压力就陡然上升,部分本应退出的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宁可亏损,也不停产”,阻碍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横向比较,日本在相同发展阶段,正是由于银行业的宽容贷款(forbearance lending)将稀缺的信贷资源从健康企业转向了“僵尸企业”和“僵尸企业为主的产业”[16],从而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前车之鉴,不容忽视。
3. 土地价格扭曲与土地资源错配
与劳动力和资金不同,在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之前,土地是无偿划拨的,几乎没有价格,政府更无法通过抬高土地价格来增加财政收入。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政府作为土地市场上实际上唯一的出让方,为了吸引投资商,争相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以零地价,甚至负地价出让工业用地,补贴投资;同时,放任住宅用地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土地要素演变为补贴资本的工具。土地介入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越深,“低工业用地价格”与“高住宅用地价格”两种体系下的地价扭曲就越严重。反观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通过直接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显著增加了家庭收入,进而支持了居民消费的强劲增长。相比我国城市化中,失地农民仅仅获得基于农业产出价值的微不足道的补偿,而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却获得了土地增值的大部分。越来越多的国民财富以土地为媒介从居民手里转移到政府与资本所有者手中,加剧了土地资源错配。而如果消除资本和劳动配置的扭曲,农业TFP有望再增长20%以上,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改进空间超过30%[17]。
4. 能源价格扭曲与能源错配
受资源税改革进程缓慢等因素的影响,能源价格扭曲与资源错配也不容小觑。首先,以市场化进程相对较快、占能源消费总量68.4%的煤炭为例。“重点合同”的电煤交易价格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的。直到2012年底,《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取消“重点合同”,才终结了电煤价格双轨制。其次,石油工业上下游产品市场化改革步伐不一致导致的扭曲也较为严重。下游石化生产由于定位为普通制造业而走在石油产业链价格改革的最前端,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基本实现市场化改革。而上游的成品油价格(主要是汽油和柴油)到目前仍然实行政府指导价。特别是,成品油进口权的垄断,导致不仅民营油企因无法获得稳定油源,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且由于缺乏竞争,国内缺乏对中石油、中石化经营效率进行对比的数据,其经营成本通过油价由全社会来埋单。最后,频频出现的天然气气价倒挂表面上压低了产品出厂价格,实际上却抑制了厂商的供给意愿,助推了高耗能产业的肆意扩张,缓滞了天然气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步伐。
(二)资源错配引致的效率损失
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技术等要素在企业内部及在产业间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的总产出和效率。在长期,基于供求双方充分博弈而形成的要素比价体系将引导经济行为主体合理配置要素资源,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或产出。反之,扭曲的要素比价尽管能换来一时的高增长,但最终将导致产出水平下滑和社会福利损失。
资源错配引致的国内企业创新驱动力匮乏,产业结构演进缓慢。如果将改革和开放政策视为驱动中国投资、生产、出口高速增长的制度背景,那么要素比价扭曲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造就了可观的利润空间,提升了厂商的盈利水平和投资者的回报率,但不可避免地也弱化了企业家自主创新的激励和推进产品优化升级、节能环保的动力;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低成本相当于对这些要素的所有者,主要是家庭部门征税,从而减少了家庭可支配收入,抑制了消费支出。持续的刺激投资和压抑居民消费,加剧了供给和需求的脱节,最终导致内外部失衡和效率损失。全国制造业产业组合效率在1999—2005年保持了下降趋势,制造业的资源利用潜力还远未得到发挥,而且各省(市、区)的产业技术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18]。国际研究也发现,市场摩擦阻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进而导致总量TFP降低[19]。而如果去掉扭曲,人均GDP将增长115.61%,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9.15%[20]。
三、研究方法、数据与不足
(一)理论模型
目前,有关要素比价扭曲的理论模型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为评估产品市场改革和要素市场改革之间的交互效应,Hertel和Zhai(2004)首先将对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纳入动态递归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中进行考察,发现针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要素市场改革大有作为;而且,如果将加入WTO和要素市场改革结合起来,将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改善收入分配不均[21]。另一些文献则从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出发,将资源错配引致的效率损失纳入增长核算框架下来考察。Aoki(2008)将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大约17%的总量全要素生产率(TFP)差距归因于产业层面(sector-level)的资源错配。而且,总量TFP与错配效应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55[22]。陈永伟、胡伟民(2011)沿用了这一框架并结合传统的Syrquin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大约造成了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15%的缺口[23]。Hsieh和Klenow(2009)进一步在具有异质性厂商的标准垄断竞争模型中,测算了中国和印度的政策扭曲所导致的在4位代码产业内工厂间的要素错置,发现假定资本和劳动像在美国观察到的那样,按照其边际产品来重新配置,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TFP可分别提高30%—50%和40%—60%[24]。
(二)实证分析(前沿分析与非前沿分析)
关于资源错配引起效率损失的实证分析,可以概括地划分为前沿分析法和非前沿分析法两大类。前者在构造生产前沿的基础上,通过距离函数,度量技术效率。后者主要包括增长核算法、增长率回归法和代理变量法等。
根据是否已知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采用前沿分析的又可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两种。涂正革、肖耿(2005)采用以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为代表的参数方法,研究显示,前沿技术进步已经成为TFP增长的最重要动力,而企业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几乎没有贡献,年均贡献仅为0.02个百分点[25]。而盛誉(2005)应用类似方法,对中国要素市场跨地区和跨行业的分布进行了测度发现,要素市场扭曲严重的部门主要分布在公共服务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越是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就越高。与非参数方法相比,SFA的优点是考虑到了随机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将实际产出分为生产函数、随机因素和技术无效率三部分。但现有文献往往忽视了对所选生产函数合理性的考察。SFA中生产函数通常选择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下简称C-D函数)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以下简称Translog函数)。选择C-D函数的主要优点是其形式简洁,参数有直接的经济学含义;选择Translog函数的主要优点是考虑了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对于产出的影响,克服了C-D函数替代弹性固定为1的缺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C-D 函数是Translog函数的特殊形式,但不意味着选择Translog函数就一定比C-D函数效果好。现有文献在应用SFA时往往直接主观地选择了C-D函数或Translog函数,不够严谨,而正确的做法应根据统计检验来决定选择使用哪种生产函数。
另一类文献则采用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 Analysis,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方法。例如,赵自芳、史晋川(2006)以1999—2005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制造业为样本,发现产业组合效率在考察期保持了下降趋势,并据此说明,我国制造业的资源利用潜力还远未得到发挥,而且各省(市、区)的产业技术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采用DEA的一个优点是能直接处理多产出的情况,其不足是把实际产出小于前沿产出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技术效率,忽略了随机因素对产出的影响。
总体来看,无论是采用SFA还是DEA,本质上是从技术效率的视角,间接地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而且度量的技术效率都是相对效率,其效率值在样本内部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但在不同样本间计算出的效率值可比性不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前沿分析法的应用范围和解释力度。
(三)微观数据与拓展主题
从数据的维度观察,针对要素比价扭曲的研究正逐渐由宏观层面向企业微观领域深入,目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企业领域,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2001—2007)被使用的频率最高。此数据库的优点在于:样本大、指标多、时间长,但诸如样本匹配混乱、指标存在缺失、指标大小异常、测度误差明显等方面的不足也十分明显[26]。因此,如何对相关数据进行系统、合理的预处理,规范使用,也是后续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同时,着眼点由工业企业拓展开的主题也逐渐丰富。张曙光、程炼(2010)对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财富转移的规模进了初步估算,并分析了财富从一般部门向行政性垄断部门、从个人向政府、从劳动者向资产所有者等三种不同途径的国内转移效应和国际间的逆向转移[27]。康志勇(2012)对加入了赶超行为和要素扭曲变量的就业需求方程进行估计后强调,中国各省份地区的经济赶超行为及要素市场的扭曲,不仅从总量上遏制了就业的增加,还通过对企业产生有偏的技术进步,遏制了就业的增加[28]。王希(2012)通过VAR模型,发现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互动关系,而且1978年以来,中国劳动力、资本、能源价格的绝对扭曲度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不过,这一看法与绝大多数研究结论相左,值得进一步思考。
(四)现有文献不足
以上文献拓宽了分析视角,将要素比价扭曲引起资源错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研究的着眼点从需要过多假设并相对抽象的技术效率,延伸至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对要素扭曲程度考察大都采用间接方式。通过对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总体市场化进程指数进行二次加工,来构造测度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指标,这类方法固然消除了指数的不可比性,还可以体现要素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化进程这一经验判断,但是缺乏较强的理论依据,也无法区分劳动、资本等不同要素的扭曲程度及其对指数的贡献,而且对省(市)级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出现负值时的解释也较为牵强。二是,或用TFP的离散程度简单代表资源误置程度,或将地区总量TFP分解,通过回归得到的要素弹性,来估计地区要素扭曲的均值和发散程度,现有文献大都回避了对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价格与其边际产出或机会成本之间具体偏差或背离情况的测算。而这恰恰才是要素价格扭曲最原本的含义,也是测度资源错配,进而引起效率(福利)损失的关键。三是,一些研究估算参考的资料略显陈旧,需要进一步的数据佐证。例如,从对垄断部门折旧和营业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与其增加值占国民收入比率的横向比较,来匡算社会财富向垄断部门转移的程度;或从政府、企业、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来测度财富向政府转移的规模,对认识价格扭曲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有一定意义,但以中国加入WTO不久的投入产出表(2002年)为计算依据,与近年实践有较大出入,说服力有待加强。
四、结论和引申
与以往更多从宏观体制方面关注结构失衡的文献不同,本文剖析了要素比价扭曲的成因和程度,以及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等要素比价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进而产生效率损失的情况,得到以下四点结论和引申:
(1)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的滞后,以及地方政府出于对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最大化追逐的压力,导致厂商在隐性补贴的成本体系中,受投入产出激励机制驱动,形成并固化了对要素比价负向扭曲的路径依赖;居民受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影响,消费占GDP比例不断下降。这一切昭示着,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向中等收入经济跨越的经济发展方式,并不适用于从中等收入水平向现代发达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才能保证后赶超阶段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实现向现代发达经济跨越。
(2)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等要素市场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催生了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引起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加剧了宏观失衡。对内而言,生产层面,资本回报率和使用成本之间缺口扩大使经济严重依赖“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分配层面,劳动者报酬占比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下降,抑制了居民消费。对外而言,双顺差格局依然延续,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尽管小幅下降,但依然保持高位,贸易摩擦此起彼伏。
(3)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利润驱动”的特征,而不少经验研究均发现,多数经济体内需是“工资导向(wage-led)” 型的;仅当净出口的分配效应大到足以弥补国内需求时,才选择“利润导向(profit-led)”型,而且仅对小型开放经济体,才存在这种可能[29]。这意味着,对采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的赶超型经济体,尤其对大国而言,未来,工资的上升(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高)能否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4)现有文献对要素比价扭曲宏观影响、技术效率研究得较多,对结构失衡、福利损失研究得较少;对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能源等单一要素市场分割开来分析得较多,在统一框架下,结合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得较少;基于对要素比价扭曲含义的不同理解,测度扭曲程度较多,讨论矫正现阶段的要素价格扭曲会产生怎样的宏观经济影响较少。因此,后续研究可在以上方面进一步探索,弥补不足,并将焦点从劳动进一步拓展至资本、能源,甚至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深入分析我国既有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原因及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可能产生的经济结构调整效应,进而为后赶超阶段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和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
[1] Charles I.Jones. “Misalloc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put-Output Economics”, in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2011.
[2] Chacholiades.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Auckland, Singapore: McGraw-Hill, 1978.
[3] 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 “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 in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09,27(5).
[4] 盛誉:《贸易自由化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测定》,载《世界经济》2005年第6期.
[5] 张杰、周晓艳、李勇:《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
[6] 张杰、周晓艳、郑文平、芦哲:《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激发了中国企业出口》,载《世界经济》2011年第8期.
[7] 郝枫,赵慧卿:《中国市场价格扭曲测度:1952—2005》,载《统计研究》2010年第6期.
[8] Huang Yiping and Kunyu Tao.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in China”, in Asian Economic Papers, 9(3) No:1-36, 2010.
[9] 聂辉华、贾瑞雪:《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载《世界经济》2011年第7期.
[10] 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11] 李文溥、陈贵富:《工资水平、劳动力供求结构与产业发展型式》,载《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2] 李文溥、郑建清、林金霞:《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变动趋势探析》,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8期.
[13] 杨振、陈甬军:《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及福利损失测度》,载《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14] 史晋川、赵自芳:《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载《统计研究》2007年第6期.
[15] Ichiro Muto,Tomoyuki Fukumoto.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ome Insights from Japans Experience”, in MPRA Paper No.32570, 2011.
[16] Caballero,R.J.,T.Hoshi,A.K.Kashyap,“Zombie lending and depressed restructuring in Japan”,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5), 2008.
[17] 朱喜、史清华、盖庆恩:《要素配置扭曲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18] 赵自芳、史晋川:《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产业效率损失——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0期.
[19] Chari,V.V.,P.J.Kehoe, E.R.McGrattan.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 22-27, 2002.
[20] 罗德明、李晔、史晋川:《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
[21] Hertel Thomas, Zhai Fan,et al. “Labor Market Distortions, Rural-Urban Inequality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s Economy”, i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455, 2004.
[22] Shuhei Aoki. “A Simple Accounting Framework for the Effect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in MPRA Paper No. 12506, 2008.
[23] 陈永伟、胡伟民:《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理论和应用》,载《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
[24] Hsieh, Chang-Tai and Klenow, Peter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Quarterly Jounal of Economics, Vol. CXXIV, Issue 4, 2009.
[25] 涂正革、肖耿:《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机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26] 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载《世界经济》2012年第5期.
[27] 张曙光、程炼:《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扭曲与财富转移》,载《世界经济》2010年第10期.
[28] 康志勇:《赶超行为、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的数据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1期.
[29] Engelbert Stockhammer,Ozlem Onaran. Wage-led Growth: Theory, Evidence, Policy,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2012.
[责任编辑 国胜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