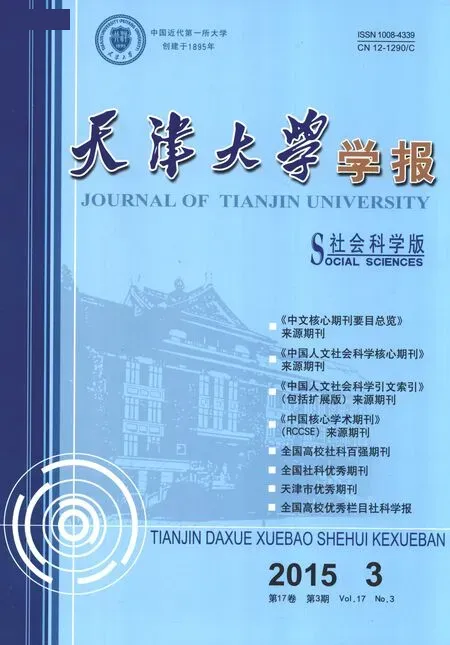不仅仅是亲爱的山鲁佐德
——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经典化过程
傅燕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不仅仅是亲爱的山鲁佐德
——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经典化过程
傅燕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女性写作繁荣时期,孕育了不少优秀的女作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关于这一时代女作家的研究一直局限于乔治·爱略特、夏洛蒂·勃朗特等极少数几位经典作家。同时代的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维多利亚时代即已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但她在英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却是直到近期才完全确立。在经历一个半世纪多的盛衰沉浮之后,盖斯凯尔以强有力的社会批评家的形象跻身英国文学史,同时也以身兼社会与家庭责任的形象印刻在众人心中。盖斯凯尔研究对于面临诸多道德困惑的当代社会及当代女性都极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盖斯凯尔夫人;盖斯凯尔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
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中的女作家为数并不多,勃朗特三姐妹、乔治·爱略特等。在其两百周年诞辰纪念日(2010年9月25日)之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810—1865,下文简称盖斯凯尔)的名字被正式绘到了“哈伯德纪念彩绘花窗”上。盖斯凯尔成为进驻“诗人角”的少数女作家之一,这也意味着其在英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获得官方认可,荣升经典作家之列。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女性写作蓬勃发展,女作家层出不穷,脱颖而出的乔治·爱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在女性文学传统中被追溯为两大重要源头,爱略特更是在英国大批评家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占据极为重要地位,成为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即已享有文学盛誉的盖斯凯尔却似乎一直难以找到她的位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以“盖斯凯尔夫人”之名屈居英国文学的偏僻角落,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起,受到冷遇的命运才开始变化,其地位历经了一个半世纪,到了21世纪之交才算是尘埃落定。那么,在这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长河里,盖斯凯尔在英国的文学批评传统中,经历了怎样的沉浮变迁?她又是以怎样的形象跻进经典作家之列?为什么我们今日仍然在研读与铭记?维多利亚人常称她为“盖斯凯尔夫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但在不同时代却有着不同的隐喻。从“盖斯凯尔夫人”到“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称呼的变化,足可窥见后人对其认知的演进。盖斯凯尔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问题的敏锐洞见,以及她身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所展现出的对社会和家庭责任、担当和勇气,皆是现代人可引为参考的典范,值得我们研习借鉴。
一、“盖斯凯尔夫人”的影子
维多利亚人从一开始就亲切地以“盖斯凯尔夫人”之名称呼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既符合维多利亚人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亦强化了她的家庭主妇身份。同一时期的女作家中,夏洛蒂·勃朗特在38岁时成为了尼克斯太太;乔治·爱略特(玛丽·安·伊万斯的笔名)与当时大名鼎鼎的评论家乔治·刘易斯同居多年,刘易斯过世后,爱略特嫁予约翰·克劳斯为妻。在英国文学史册上,此二人均未曾以“某某夫人”留名,大概也因她们身为家庭主妇的时日过短,但更为根本的缘由还在于她们的个性自我很是突显。盖斯凯尔却是不然。她在22岁时即嫁给一神教牧师威廉·盖斯凯尔为妻,定居曼彻斯特,既悉心照料家庭又以牧师妻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当时的行善大业。因而,“盖斯凯尔夫人”这个名号对曼彻斯特的穷人来说也是亲切无比。据说当时有工人还常到曼城城郊,透过普利茅斯小树林遥望盖斯凯尔的家院,盼望着能瞧见这位给予穷人温暖帮助的牧师夫人。威廉·盖斯凯尔忙于传道教书,家中4个女儿全靠盖斯凯尔夫人照顾培养。“盖斯凯尔夫人”实非虚名,她一直以社会和家庭责任担当为业。因此,在她过世时,维多利亚时代评论家兼盖斯凯尔的出版商——乔治·巴内特·史密斯精辟点评道,盖斯凯尔的一生最有力地证明了女性通常都能取得比对该属性预期的更大的成就,但同时她又不缺乏使得家庭成为“人间天堂”的所有品质[1]。盖斯凯尔的一生都在兼顾家庭责任和写作大任的重任,这是为维多利亚人点头称道的。
对盖斯凯尔而言,除却探访穷人、教授穷人技艺,写小说亦是行善大业的延展,可有效引起维多利亚社会关注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盖斯凯尔一生主要创作了6部中长篇小说、1部传记以及约30个短篇故事。她的作品按题材通常被划分为工业/社会问题小说和田园/家庭小说两大类,再现了当时的曼彻斯特工业城、纳次福(knutsford)或是18世纪晚期的惠特比(whitby)小镇的生活状态。她的小说并不从遥远的时代或地域汲取源泉,始终以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为背景,揭示日常生活中蕴藏的诗性,意在传达普通生活的真实。盖斯凯尔擅长讲故事,但又不止于此,故事构思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亲爱的山鲁佐德”是维多利亚时代大文豪狄更斯当年对盖斯凯尔的亲切称呼。言外之意,她讲故事的禀赋超常,可说无人能出其右,堪比《一千零一夜》里的王后山鲁佐德。在狄更斯的盛情邀约之下,盖斯凯尔为《家常话》(household words)献上了许多短篇故事和两部小说。然而,她又不仅仅是擅长讲故事的王后。狄更斯当年创办这份刊物,旨在求得社会状况的总体改善,这恰与她的志向相投。盖斯凯尔胸怀深切的道德关怀,以笔为利器,希冀引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对持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小说一向不屑,极力宣扬文学教化社会的严肃功能。盖斯凯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1948)因其“对每个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大有好处”,指向了“这么久一直都无人提及,但又早应让大众知晓的重大话题”,得到卡莱尔的高度赞赏[2]。对于劳资问题,当时的维多利亚人尚在努力把握问题的真相,寻求解决的出路。盖斯凯尔小说中对劳资问题的尖锐洞察,构建了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盛誉。
盖斯凯尔的写作特点在维多利亚时代亦已深得肯定。她的工业小说显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宠儿。不过,《克兰福镇》(Cranford)、《妻子与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等也同样让维多利亚人爱不释手。从1848年到1865年的17年间,她的作品陆续走进维多利亚人的视野,写作技艺日渐获得认可。最早的肯定之声还是来自卡莱尔,他指出,优秀作品的精粹在于“精练”与“真实”,盖斯凯尔的“真诚”溢于笔端[2]。及至她过世时的60年代,以在情节中埋布夸张离奇事件而得名的惊悚小说兴盛,盖斯凯尔的小说特点被有意识地与此类小说作比较,其小说中的宁静与日常生活气息备受赞许。《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认为,盖斯凯尔身为女性,更富同情心的性情促使她对生活细节观察细致,这是其小说技艺之关键[3]。著名评论家亨利·詹姆斯亦表扬《妻子与女儿》技艺精湛,小说细节引向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处,盖斯凯尔的天分明显是“她的情感的产物”[4]。虽然缺乏后世评论的严密论证,这一时期提及的几个关键问题,如小说与社会的互动、小说的功用、作者的女性同情心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等,却都是后世盖斯凯尔研究的持续关注点。
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现代英国文坛转向巨大,形成了迥异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评判标准,在此标准之下,盖斯凯尔的小说与其他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一同,受尽批评界冷落。时过境迁,盖斯凯尔的工业题材小说似乎因为丧失了时代性,渐渐失去读者的厚爱,田园小说转而更受青睐。1906年纳次福版本的盖斯凯尔小说全集出版后,《学术》(academy)上的书评写道:现代人试图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寻求逃避的去处,阅读盖斯凯尔的小说则为现代人提供了某种心理安慰[5]。但是,这在当时的小说家、批评家眼里却未必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现代小说显然更为“简练”,所以不解当时的人为何还要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6]。伍尔夫不满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沉迷于人物外在细节的描述,不满其忽视对人物内心的体察,这是众所周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从主题到写作技巧都遭遇现代小说家及批评家的敌意排斥,其名声一落千丈。塞西尔就是现代批评家中的典型代表。不过,这一时期对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批判,后来的文学批评都将重新给予评估①。
20世纪30年代戴维·塞西尔勋爵站在当时的时代立场,无视维多利亚社会女性身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对不合20世纪早初英国社会女性角色定位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妄加批判。塞西尔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作家》(1934)中对她盖棺论定,一个循规蹈矩的“盖斯凯尔夫人”形象跃然纸上。塞西尔自信满满地将盖斯凯尔定性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说道:关于盖斯凯尔夫人的“极为显著”的事实是她的“女性气质”,她温柔如鸽子,动不动受惊吓、掉眼泪,缺乏智性结构等“男性气概”的特质,没有“热烈”的情感,安然接受时代对女性的限制[7]。把她的小说归类为工业/社会问题和田园/家庭两大类小说之后,针对盖斯凯尔的工业题材小说,塞西尔更是谴责道,她不可能找到比这更“不适合她才华”的题材了[7],这完全不是她的女性理解力所能把握的范围,因为写工业题材必然涉及经济学和历史知识,且其中涉及到“情感”时,也必然是“男性的、剧烈的”[7]209。“盖斯凯尔即便有更多讲故事的天赋,她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整个时代的精神都在与她作对”[7]236。其实,塞西尔对盖斯凯尔写作中的长处也有所肯定,认为她有着“女性对细节的敏锐把握”[7]203,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到位。但是,大肆批判之后,这样的言辞似乎也显得有些屈尊俯就。塞西尔给盖斯凯尔贴上的“女性化”标签遮掩了她的所有优点,不仅掩盖了盖斯凯尔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盛誉,而且他笔下那个中规中矩的“盖斯凯尔夫人”在很长时期亦成为盖斯凯尔的主导形象,遮蔽了盖斯凯尔的多面复杂性。塞西尔确实捕捉到了问题的根本,维多利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对女作家书写工业题材小说着实设置了诸多障碍,但他却忽略了盖斯凯尔在看待工业问题、参与社会讨论时所借用的女性优势,无视盖斯凯尔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限制有所超越。这也留待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及新历史主义批评等视域下的盖斯凯尔研究来挖掘。
二、从“盖斯凯尔夫人”到“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盖斯凯尔研究的复兴在两大批评潮流——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带动下拉开帷幕,因其对劳资问题的揭露与反思,盖斯凯尔作为维多利亚社会批评家的角色被重新考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视野下的系列文学评论著述,包括凯瑟琳·提勒森的《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1954)、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法国学者路易斯·卡扎米昂的《英国社会小说,1830—1850》(1903)等,其中以威廉斯的评判影响最为深远。威廉斯对盖斯凯尔的中产阶级立场褒贬参半。他的基本观点是,《玛丽·巴顿》中的情感结构,即中产阶级对工人的“饱含同情的观察”和“想象性的认同”很具感染力,同时此情感结构中的另一情感——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暴力的恐惧又削弱了小说的表现力度。对于盖斯凯尔的这两部工业小说,威廉斯似乎都不满意其情节走向,批判小说从工业问题拐入个人故事里,且最后也未能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当然,威廉斯的此类论断并不只针对盖斯凯尔一人,同样覆及同期其他的工业小说。不过,威廉斯对盖斯凯尔的工业小说的力量是有所肯定的,而且他还说道,《玛丽·巴顿》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以很个性化的手法,努力地捕捉工人日常生活的那种感觉[8]99。这些对盖斯凯尔的肯定之音,无不是当年卡莱尔的赞许之声的历史回音,也表明了盖斯凯尔小说的力量在历史的延续中不断得到肯定和再肯定。不过,盖斯凯尔在她的作品中如何具体展示出这股力量,还有待后来学者深掘细嚼。
盖斯凯尔在女性主义批评兴盛的70年代是诸多女性作家“扬眉吐气”的时代,因其不合女性主义批评的范式,一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美的女性解放运动极大推动了英美学界对父权制文学传统的质疑,掀起了修正经典、建构女性文学传统的风潮,一系列女性文学批评著述应时而生。事实上,女性主义批评早在50年代就开始关注盖斯凯尔,1950年安娜·鲁本尼尔斯在《盖斯凯尔夫人的生平与作品中的女性问题》中,赞许盖斯凯尔精准地揭露时代的女性问题。然而,这一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大概从70年代起,英美学术界的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建构女性写作传统。维多利亚时代因其空前之多的女作家的出现和庞大的女性读者群,成为英国文学史中女性写作传统确立的关键时期。不过,盖斯凯尔此时并没有捕获多少关注。在《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性作家从勃朗特到莱辛》(1977)中,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构筑的女性写作传统的两大重要源头分别是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爱略特。虽然盖斯凯尔也多次被提及,但她依然摆脱不了30年代塞西尔所埋布下的“阴影”,她仍是“文学之鹰”的夏洛蒂和爱略特身旁温顺的“鸽子”。在另一女性主义批评名作——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盖斯凯尔似乎因其没有强烈意识到自己因女性身份而备受社会压迫,她的表象生活也太过平凡普通,更是难以纳入女性反叛的框架中。盖斯凯尔在此书中的“缺席”更似是应和了塞西尔的评判,即“她对那些加诸身上的限制不怒不恼,安然且心满意足地接受”[7]。
盖斯凯尔难以融入女性主义反叛体系,更可在以下事例中窥见端倪。1992年弗莉西娅·波拿巴特的《曼彻斯特的单身流浪汉:盖斯凯尔夫人的恶魔传》一书引发了相当多的书评,但几乎都是含蓄的批评。波拿巴特似乎也想尝试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做法,将女性反叛的思路应用到盖斯凯尔身上,在那里找出另外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但是,波拿巴特虽大胆假设,却未加谨慎求证。她假设读者所看到的“盖斯凯尔夫人”身上其实深藏着另一个“恶魔般的自我”,但这一点是连盖斯凯尔本人也没意识到的。波拿巴特觉得读者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找出。波拿巴特说道,“盖斯凯尔堆砌了细节,事件接连发生,并且拿出十足的精神劲头来掩饰,因为她想要遮掩这样的事实:她把真实的自我深藏”[9]。在她看来,盖斯凯尔在生活和书信中如此深藏的自我,完全裸露在她的作品中。但是,波拿巴特的书顶多被赞许为“大胆”的尝试。波拿巴特的书中臆断颇多,也证明了从“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女性反叛角度去研究盖斯凯尔,难度颇大。
不过,虽然盖斯凯尔在70年代的女性文学批评名作中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但终是进入了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的视野。有了这些铺垫,80、90年代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盖斯凯尔研究,开始推翻30年代塞西尔笔下安然接受社会限制的“盖斯凯尔夫人”形象,研究她对父权制社会的批判,逐渐代之以“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社会批评家形象,盖斯凯尔研究专著剧增。1987年英国学者帕西·斯通曼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敏锐指出,盖斯凯尔长期受尽女性主义批评冷落,原因在于其小说缺乏对父权的明显直接的反抗,也没有可做象征性解读的情境[10]2。斯通曼主要借用萨拉·鲁迪克的“母性思维”概念,揭示盖斯凯尔批判威权的滥用,指责传统的母性观其实被用于将女性“婴儿化”。盖斯凯尔的力量在于“对家庭与法律机制的理性挑战”[10]。斯通曼同时一语中的点明,盖斯凯尔在揭露不公正现象时,语气“温和理智”,没有“暴怒与反抗”,这其实是“有所抑制的怒气”的外在表现[10]15。不过,女性主义批评名家尼娜·奥尔巴赫也指出斯通曼采用“母性思维”的视角可能存在问题,即斯通曼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批评针对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做的研究,她只关注盖斯凯尔强调女性的“孕育照顾”能力具有改变社会的功能,这一视角可能会掩埋盖斯凯尔的社会关怀,似乎又让她变回“盖斯凯尔夫人”,安心满足于小女人的位置[11]。对盖斯凯尔广博的社会关怀的深度研究,尚留待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填补。
盖斯凯尔在英国文学史中重要性的提升,很大程度受益于80、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对她的重新评价。尼娜·奥尔巴赫在1994年指出:“一旦我们不再像那些屈尊俯就的评判者那样拿‘盖斯凯尔夫人’打发她,我们却也找不到任何简单的身份来界定她,她不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不是邪恶的姐姐,也不多愁善感地宣扬女性的互助伦理,而是坚持不懈记载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平静表象之下两性之间、经济、意识形态等矛盾。”[12]新历史主义在此担当了重新评价的艰难任务。新历史主义主张还原维多利亚时代的具体语境来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于当时社会的意义所在。批评家们摒弃了屈尊俯就的姿态,深入探讨盖斯凯尔的女性视角、女性同情心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在写作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探究其作品与同时代其他文本的互动。在新历史主义批评解读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过程中,盖斯凯尔的社会问题小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基本立足点也有别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后者将小说视为社会现实的被动反映,前者则主张小说是参与到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意识形态话语与小说叙事之间的深层关系。
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野下,评论家们开始关注盖斯凯尔的女主人公的社会作用。1985年凯瑟琳·加拉格尔的《英国小说中的工业改革:社会话语与叙事形式,1832—1867》一书,主要着眼于工业小说与工业话语两者间的关系。她在工业问题的背景之下探讨盖斯凯尔的女主人公的作用及其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趋合。加拉格尔认为,《北方与南方》似乎暗示,女主人公的影响力使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裂缝得以弥合,但是女主人公发挥影响力的先决条件似乎又基于这两个领域的分离[13]。不过,加拉格尔的结论才是关键所在。她指出,盖斯凯尔的小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裂缝,其根源并非小说家本身无力解答工业问题,而在于维多利亚社会的工业话语本身矛盾重重,工业话语把缝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裂缝的任务加诸女性身上,但该女性又须是来自与公共领域隔绝的私人领域。这一分析也冲击了威廉斯批评工业小说无力提供解决方案的论断。1995年玛丽·普维《创建社会机体:英国文化构建,1830—1864》的分析立足点则往前推进一步,指出工业小说参与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话语,这又进一步突显了身为女作家的盖斯凯尔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普维评述道,19世纪40年代小说家探讨英国工业问题之时,“政治经济学家与社会分析专家们已然在如何再现社会领域问题与提供决策方面成功确立了自身的权威”[14]。因此,女性创作工业小说实是在以女性自有的方式参与探讨原被定性为男性化的工业问题。当年塞西尔简单批判盖斯凯尔身为女性没有政治经济学知识就去触碰工业题材,普维在这里做出了另一番阐释,也更令人信服。她认为盖斯凯尔借用了女性化的情感与细腻观察,有效引导中产阶级读者去关注下层穷人的困境。有此为证,在社会学家们用数据说明贫困之时,盖斯凯尔却是刻画穷人家的茶杯如何匮乏,或是光靠吃燕麦度日,形象生动地传达了同样的旨意,且让人印象深刻[14]145。盖斯凯尔的同时代人即已注意到其写作中的女性情感因素,此处再次受到充分重视。这一方面的重要著述还包括1988年萝丝玛丽·波登赫玛的《维多利亚社会问题小说中的故事政治》、1995年黛博拉·诺德的《行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街道上:女性、再现与城市》、1998年芭芭拉·哈曼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政治小说》等。
新历史主义批评视域下的这些重要著作,避免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武断之处,避免了仅研究工业小说中的阶级问题而忽视其中对女性问题的探索,为深入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务的经历奠定了基础。盖斯凯尔的工业小说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著述中均占有重要篇章。塞西尔在30年代以现代小说的标准,无视维多利亚时代的具体语境即去评判盖斯凯尔的成败,这在新历史主义批评那里遭到了全盘推翻。新历史主义批评视野下的盖斯凯尔研究为确立盖斯凯尔在英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做了良好铺垫。
盖斯凯尔的女性除却参与公共生活事务,相当多是家居女性,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亦开始得到重视。总的来说,在对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的认识问题上,英美社会的20世纪60、70代是个分水岭。此前的认识较为单一,受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意识形态塑造的“家庭天使”意象的影响,倾向于认定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过着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生活。但是,70、80年代以来的研究注意到,尽管家庭意识形态在维多利亚社会非常强势,意识形态毕竟是“规定性的”,而非“描述性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的真实生活状况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当时的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学批评著述从多个方面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的积极生活方式及重要社会作用,关注女性角色的转变,注重探索维多利亚社会的女性在受束缚的生活中所做的艰辛努力,改变了现代人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消极看法。英国评论家伊丽莎白·朗兰较为系统地把20世纪70、80年代英美历史社会学领域的新研究成果应用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研究中。朗兰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天使:维多利亚社会文化中的中产阶级女性与家庭意识形态》一书,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家庭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用。盖斯凯尔的《克兰福镇》和《妻子与女儿》被列为重点研究对象。朗兰的研究关注了维多利亚家庭意识形态话语中的矛盾之处:约翰·罗斯金、考文垂·帕特摩的“家庭天使”是被动顺从的,但当时如艾利斯夫人等人所著的女性指导书却又在塑造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形象,因而,在这两种话语中,中产阶级家庭女性在性别政治中处于必须顺从的境地,同时在阶级政治中又处于统治地位,她们必须懂得如何管理家中的仆人,如何利用丈夫的钱财来创造家庭的文化资本,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15]。朗兰主要着眼于家庭女性在协助丈夫与管理家庭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一分析进而冲击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给后人留下的消极、软弱无能等印象。
盖斯凯尔作品研究的复兴热潮中,生平研究也日渐兴盛。盖斯凯尔常是从自身的直觉体验出发来写作,这也指向了其生平研究的意义所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盖斯凯尔生平研究并不成体系,零散研究居多,与当时其生平资料匮乏有关。可喜的是,1966年由查普尔与亚瑟·保洛主编的《盖斯凯尔夫人书信集》及2000年查普尔与艾伦·谢尔斯顿主编的《盖斯凯尔书信增补集》先后问世。书信推动了两本重要的盖斯凯尔传记的问世,分别由葛瑞与乌格萝所作,极大促进了对盖斯凯尔的多面性的研究。书信集出版之前,在“盖斯凯尔夫人”的“阴影”之下,盖斯凯尔的生平研究强调其母性的一面。在她的心目中,写小说、关注社会问题或是朋友往来,都比不上4个女儿重要。即便在成名之后,女儿也依然是她生活的重心,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爱。比起夏洛蒂和爱略特塑造的的女性形象,盖斯凯尔笔下的女性也更具母性。书信集问世之后,其生平研究展示了盖斯凯尔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女性,熟稔当时社会文化,与时代文化的积极互动。同时,生平研究还开始关注作为家庭女性和作家的盖斯凯尔同时肩负多重责任时须应对的矛盾,尤其注意把握她的多面性。2010年由盖斯凯尔研究协会主办的为期一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中,很受瞩目的是英国著名女演员嘉布里埃尔·德雷克在独角戏《亲爱的山鲁佐德》(dear Scheherazade)中演绎盖斯凯尔的一生。嘉布里埃尔在BBC广播4套的《女人时光》节目中,谈及自己对盖斯凯尔的诠释时,特别提到盖斯凯尔是在“餐桌”上写作,同时要照顾丈夫和女儿们,还要打理各种琐碎家务。当代人眼中的盖斯凯尔开始具有了多面的维度。身处维多利亚时代的盖斯凯尔如何应对妻子、母亲和作家的多重角色,这无疑对21世纪的女性极具参考价值。盖斯凯尔的婚前书信展现的是一个忙于抄写乐谱、阅读书籍、参加舞会、准备婚礼的“轻率、无思无想的小东西”[16]。婚后的书信则多次流露出对多重责任的体悟和焦虑。至今我们所知不多的仍是她如何调整自我,以适应作家、妻子、母亲等多重角色,又是如何神奇地从塞西尔眼中的“满足于闲聊家长里短”的邻家女人成长为优秀的小说家。但是,盖斯凯尔较为成功地兼顾家庭与社会责任,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也为她赢得了后人的敬意。
自1848年盖斯凯尔凭借《玛丽·巴顿》在英国文坛一举成名以来,评论界在提及这位女作家时惯以“盖斯凯尔夫人”相称。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起,批评家们渐渐改称她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这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更意味着评论界对盖斯凯尔这一历史人物的复杂多面性的认知逐渐深化。2002年,雪莉·福斯特在《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文学生涯》中指出,盖斯凯尔之前被认为是维多利亚社会的激进批判者,后来她的小说被看作是大众娱乐,现在她又重回激进批判者的形象[17]。2007年的《剑桥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指南》中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多面的盖斯凯尔:讲故事能手、心态复杂的传记家、焦虑的母亲、善于和出版商打交道的作家、现代社会里的田园诗人等。此外,“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称呼似乎也与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批评家的身份更相匹配。当代的多数学者都肯定她对维多利亚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力度,但这一共识是在学者们前赴后继提出并解答盖斯凯尔研究中一个个相关问题之后,历经一个半世纪多的时间沉淀才达成。有如刘意青教授所言,“虽然选定经典的过程相当复杂,但一般都同意有以下因素介入:它得到了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和推动……其次,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知名度高……等。”[18]在大众层面上,借助影视传媒网络的推力,近年来由BBC改编的系列经典电视剧《妻子和女儿》(1999)、《北方与南方》(2004)、《克兰福镇》(2007)、以及2009年的《重返克兰福镇》圣诞特辑等,将盖斯凯尔重新带回英国人的心中,带进世界各地观众和读者的视野,引发持续关注热潮。在历史见证中,盖斯凯尔的作品进入了英美高校文学课程,盖斯凯尔研究专著增多,盖斯凯尔在《牛津英国文学史》的分量也渐增。至2010年,最终在“诗人角”找到了自身的位置,也标志着其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
三、结语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当年正值盛年便遽然离世,她最出色的作品《妻子和女儿》亦成绝笔。当时,有报纸讣闻写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应受到敬重的人物之一——如此率真诚实——如此善良,惯于奉献自我,既在家庭生活和私人关系中展露智慧,又在公众生活中散发着良善影响……”。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沉淀之后,盖斯凯尔的作品依然活跃在公众心中,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跻进英国文学经典之列。与此同时,盖斯凯尔也以妻子、母亲及社会批评家等多重身份为后人所熟识所敬仰。她一生以兼顾家庭责任和社会关怀为重,不失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典范代表。在21世纪的今天,盖斯凯尔仍为我们所研读与铭记。
注释:
①弗·雷·利维斯的名作《伟大的传统》对提升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重要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被紧随其后的现代批评家所诟病,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浓厚道德训导倾向。利维斯把严肃的道德关怀作为评定优秀小说的重要标准,以此确立英国小说的“伟大的传统”。盖斯凯尔此时虽未能位列“伟大的传统”中,甚至被利维斯所轻慢,她却间接受益于这一传统的建立。虽然利维斯在文学批评中忽视历史性,这在后来也受到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流派的批判,但他所确立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的标准仍然影响深远。F R 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
参考文献:
[1]Smith G.Mrs Gaskell and her novels[C]//Sanders V.Lives of Victorian Literary Figures:Elizabeth Gaskell,the Carlyles and John Ruskin by Their Contemporaries.London: Pickering&Chatto,2005:106.
[2]Carlyle T.On Mary Barton[C]//Easson A.Elizabeth Gaskell: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72.
[3]Anonymous.An unsigned review of Wives and Daughters [C]//Easson A.Elizabeth Gaskell: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479.
[4]James H.An unsigned review of Wives and Daughters[C]// Easson A.Elizabeth Gaskell: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464-65.
[5]Anonymous.The works of Mrs.Gaskell[J].Academy,1906 (7):519.
[6]Woolf V.Mrs.Gaskell[C]//Sanders V.Lives of Victorian Literary Figures:Elizabeth Gaskell,the Carlyles and John Ruskin by Their Contemporaries.London:Pickering&Chatto,2005:341.
[7]Cecil D.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Essays in Revaluation [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48:198.
[8]Williams R.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63:100-02.
[9]Bonaparte F.The Gypsy-Bachelor of Manchester:The Life of Mrs.Gaskell’s Demon[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2:6.
[10]Stoneman P.Elizabeth Gaskell[M].Brighton:The Harvester Press Ltd.,1987:16.
[11]Auerbach N.Elizabeth Gaskell by patsy stoneman[J].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1989(8):133.
[12]Auerbach N.The gypsy-bachelor of Manchester:The life of Mrs.Gaskell’s demon by felicia bonaparte[J].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1994(1):184.
[13]Gallagher C.The Industrial Reformation of English Fiction: Social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Form,1832—1867[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166-84.
[14]Poovey M.Making a Social Body:British Cultural Formation,1830—1864[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132.
[15]Langland E.Nobody’s Angels:Middle-Class Women and Domestic Ide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1-23.
[16]Chapple J.Introduction[C]//Chapple J,Shelston A.Further Letters of Mrs.Gaskell.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xii.
[17]Foster S.Elizabeth Gaskell:A Literary Life[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172.
[18]刘意青.经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82.
Not Merely Dear Scheherazade:
A Review of the Canonization of Elizabeth Gaskell Fu Yanhui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Victorian England has been well known for the flowering of women writings and the birth of distinguished women writers in large numbers.Victorian women writer studies,for a long period,were confirmed to a few canonical women writers including George Eliot,Charlotte Bronte and the like.Elizabeth Gaskell had been highly regarded in the Victorian literary world,and yet her great significance to British literature has not been fully confirmed until recent years.After more than one and a half century’s hovering between literary fame and obscurity,Gaskell has firmly established herself in British literature as a forceful social commentator,and concomitantly impressed many people with her persistence in undertaking both social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The Gaskell studies undoubtedly shall provide penetrating insights to both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more liberated modern women that are confronted with moral conundrums.
Keywords:Elizabeth Gaskell;Mrs.Gaskell;Gaskell studies;Victorian women writers
通讯作者:傅燕晖,yhfum@163.com.
作者简介:傅燕晖(1980—),女,博士.
收稿日期:2014-06-01.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5)03-2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