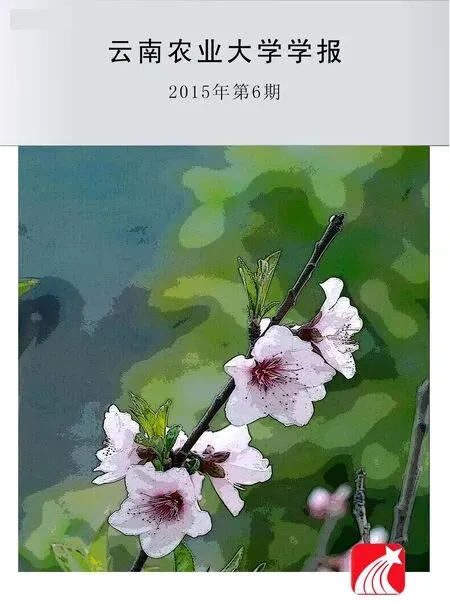当下大众传媒在社会整合中的新方向
——康德宗教哲学的启示
马成益,李国春,熊继华
(1.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201;2.云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云南昆明650201;3.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云南昆明652503)
当下大众传媒在社会整合中的新方向
——康德宗教哲学的启示
马成益1,李国春2,熊继华3*
(1.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201;2.云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云南昆明650201;3.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云南昆明652503)
长期以来,大众传媒在社会整合中扮演着无可厚非的重要角色。从其功能来看,通过信息的传播加强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群体间的频繁交流,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整合。但是,从深层次来看,或者说从这种活动的实质效果来看,很多时候适得其反。因此,要让大众传媒在运行中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就需要找到其在当下运行中应该遵循的较为恒定的价值标准。康德的宗教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大众传媒;社会整合;宗教哲学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各种社会问题开始凸显。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反而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的舞台。如何在这种形势下发挥自身的载体作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如何利用自身驾驭信息的优势在大市场中获得更高的利益,包括加强自身的品牌效应,这些成为了大众传媒开始深思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改进大众传媒在整合社会过程中的标准。
一、当下大众传媒在社会整合中面临的挑战
(一)传统社会的变迁
传统社会,这里主要是指以农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城镇化是传统社会发生变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到改革开放之间的阶段,我国的城镇化速度比较缓慢,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但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加速阶段。“1978—2000年城市化水平由17.92%上升到36.22%,年均增加0.83百分点,设市城市由193个增至663个,建制镇由2 173个增加至20 312个(见表2),增加迅速。”[1]那么,很显然,城镇化的内在驱动力就是我国的工业化。工业化的开展吸引了农村的大批劳动力进城,这些人群开始由农村社会背景逐步向城镇社会背景转变。费孝通先生笔下的 “乡土情结”的特征开始受到了城镇化的严重挑战。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中,对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考察中有精辟的论述:“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2]由此可知,费孝通先生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主要是以血缘为基础而非地缘。“地缘是从商业社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观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2]从这样的社会特征可以看出,在 “乡土社会”中,跨地区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很少,人们之间的信息基本对称,很少会出现道德风险。这种人与人之间依靠信用、品德、社会风俗、礼仪的交往模式是我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一大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一大优点,这种社会的凝聚力比较强劲。当然,这一时期的大众传媒的功能是很单一的。改革开放前的大众传媒主要是以政治宣传为主要功能,其为社会经济、文化服务的内容微乎其微。但是,由于传统社会结构本身比较单一稳定,所以大众传媒面临的社会整合任务较为轻松,也可以说它起到辅助作用不是特别明显。
进入城镇化以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开始转向更多的地缘关系,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这一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契约慢慢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很多时候会存在失效的风险。在这样的局势下,法律的功能开始变得尤为重要。为了能够使城镇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顺利地开展活动,法律的公正性和强制力成了最为基本的要素。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其实这种现象导致了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名誉、信用、道德等观念的边缘化,社会整合所需要的基本要素逐步减少。当下经济市场和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基本可以看作是上述问题的表现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传媒除了就政府而言的“喉舌”功能,就市场而言的 “经济主体”功能外,应该开始反思就社会服务的 “整合”功能。
(二)新媒介的挑战
新媒介的诞生造就了一场媒介领域的狂欢。关于新媒介的社会功能,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述,诸如打破了传统媒介独霸天下的局面,信息的传播将会变得更加频繁,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更加明显,能够促进社会民主等等。诚然,新媒介的出现的确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面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更加通畅甚至更加个性,媒介市场也变得繁荣起来,这些无须赘述。但是,辩证地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新媒介给社会带来新气象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这种技术出现的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里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新媒介对传统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带来的挑战。
首先,从媒介技术本身来看。“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 (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 (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起一种新的尺度。”[3]虽然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是一种宽泛的感念,泛指一切媒介,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运用其理论指导我们的分析。新的传媒技术的诞生,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麦克卢汉所说的 “地球村”成为了可能。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开始频繁起来,对传媒工具的选择也日益丰富。
但是,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出现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由于人们对传媒工具的偏好种类不同,导致了因为媒介工具种类而形成了不同的传媒人群。也就是说,传媒工具本身将社会人群分割成了不同的群体。这实际上是对社会的一种切割而不是整合。
其次,从媒介的传播内容来看。当下的媒介发展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 “内容为王”的时代。新媒介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众群体的年轻化,导致了媒介内容出现了与传统媒介传播内容截然不同的情况。为了吸引受众,新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往往比传统媒介充斥着更多的博取眼球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大多缺乏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恒久价值观的成分,充其量是一些琐碎的信息堆积,其中还不乏涉及暴力、色情等内容。这样的 “信息大爆炸”模式已经完全将新媒介的使用者淹没在了海量的信息之中。严肃主题的娱乐化、边缘化导致了媒介使用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冷漠,社会的重大事件的讨论无法得到民众的积极参与,新媒介实质性地伤害了传统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
二、康德宗教哲学观的启示
大众传媒面对上述社会形态和媒介技术两个方面的变化,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找出一条社会整合的新路子呢?笔者认为,康德的宗教哲学观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示。诚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选取的并不是康德宗教哲学的具体的论述内容,而是康德论述其宗教哲学观的思维方式。
(一)康德宗教哲学观中的主要思路
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启蒙运动思想批判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传统的基督教。基督教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西方社会的价值之源。那么可以认为,基督教其实是西方社会整合的一个强力的工具。作为一个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者,康德并不是想消灭宗教,而是试图通过哲学上的论证,为宗教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基础,即以理性作为宗教的基础,而不是像以往那种自然宗教。康德的宗教哲学事实上并不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延伸,而是具有独立的地位。康德的宗教哲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1793年出版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来看,康德不仅用大量篇幅叙述了人性的善恶问题,上帝的道德证明问题,同时界定了什么是宗教,并且区分了宗教与伪宗教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康德的宗教哲学都是为了解决“我们可以信仰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人类是否需要宗教,是否需要上帝?如果人类需要宗教,那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或者说是什么种类的宗教?按照学者陈嘉明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究竟应当用宗教还是它的何种替代物来对社会进行整合。”[4]如果从康德的著作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来看待康德思维路径的话,康德首先是分析了人性的善恶问题,并讨论了人应该重新向善的原初的禀赋力量。“就道德的宗教而言,(在迄今为止所存在的所有公开的宗教中,唯有基督教才是这样的宗教),一条原理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其所能去做,以便成为一个更善的人。”[5]
紧接着,在对上帝是否存在的证明中,康德认为需要限制知识,从而为信仰留下余地。即康德把知识限定在了 “现象”的范围内,而把 “本体”域留给了实践理性的道德和信仰。康德从知识的角度上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仅仅认为它只是一个理念。在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之后,康德试图通过人自身的理性,建立起一种道德的宗教。所以,在康德那里,宗教的性质是一种道德的宗教。“接受一种宗教的基本原则,这是在高级形式下的信仰 (神圣的信仰[fides sacra])。因此,我们一方面把基督教信仰视为一种纯粹的理性信仰,另一方面把它视为一种启示信仰(规章性的信仰[fides statutaria])。”[5]康德在区分了两种信仰之后,充分认定了纯粹的理性信仰才是每一个人自由地接受的信仰。那么,更进一步地说,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接受的信仰,才是具有普遍性的信仰。“而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仅仅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从而缺乏真理的重要标志——普遍性的要求,因此它们的传播受到时间与地域的限制,无法产生普遍的影响。”[4]由此可见,康德的宗教是一个理性具有自主性的宗教,自由成了康德哲学的最高精神。那么,反观我们国家,依靠宗教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首先,我国境内的宗教信仰人数有限,没有普遍性。其次,各个宗教的教义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教义对社会整合方面的指导性缺乏统一的标准。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境内的宗教缺乏康德意义上的自由。对此,武汉大学哲学学者邓晓芒有精彩的论述:“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在超越教派和具体的某个宗教之上建立起一种信仰,就是所谓的精神性的信仰。我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对 ‘真善美’这样一些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要抱有一种信仰。这些价值是绝对的,真善美的价值都是绝对的。正因为是绝对的,所以它是永远也追求不到的。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这些是永远也追求不到的。正因为永远追求不到,所以它可以作为信仰。”[6]邓晓芒先生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完成社会整合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方案。这样的想法其实是符合康德宗教哲学观的内在逻辑的。
(二)康德宗教哲学研究思路对大众传媒社会整合的启示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新闻传播是其日常活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活动,大众传媒拥有雄厚的传播设施和丰富的内容资源,其影响力可以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可以说,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无时无刻不处于它的影响之中。“新闻事业不仅仅只是传播一条条的新闻,同时更是在为一个越来越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一整套应付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和价值体系,而这就更不是任何私人所能做到的。”[7]从硬件方面来看,在社会整合方面,大众传媒无疑具有强大的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从其 “软条件”方面来完成社会整合。从康德的宗教哲学中可以看出,通过确立信仰来完成社会整合具有可行性。
首先,大众传媒需要树立起以理性为根基的传播体系,这里的理性体系就类似于康德的 “理性神学”。但是,不同的是,我们这里的至高存在者不是康德意义上的 “上帝”,而应该是对应于我国现实条件的真、善、美三种标准。也就是说,大众传媒在其内容的传播过程中,应当以以上三种标准来作为信息传播的原则,即使是必要的负面信息,也应该在舆论导向上符合上述原则,从而也就是符合了理性原则。通过长期的渗透与培养,把真善美的标准提高到信仰的高度,大众传媒才能完成实质意义上有效的社会整合。虽然2015年两会期间,新闻传播的立法成了今年两会提案的一个亮点。新闻传播法的确立,将可以为规范传播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新闻立法不仅是新闻工作者的事,也不仅仅是新闻界、出版界、法律界和文化界的事,而是关系全社会的大事,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予以关心的大事。”[8]但是,我国新闻传播法如果出炉,里面究竟含有什么样的内容现在还不得而知。所以,从当下的现实来看,我们的确可以按照康德宗教哲学的 “理性神学”、“道德的宗教”这样的相似的思路来让大众传媒完成社会的整合。
其次,康德宗教哲学中,自由是最高的精神。康德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自由理性来建构上帝、宗教、价值和意义。在当今发达的媒介技术条件下,每一个民众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大众传播中的被动的 “受众”,而开始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由此,当今的传播个体在参与大众传媒传播活动的过程中,也应当发挥康德所说的人类的自由理性来按照我国实际的情况 (即在科学主义的推动下,让民众相信 “上帝”的存在不现实)来构建真善美的价值体系,让每一个信息传播者都可以在理性的指引下,将真善美作为一种信仰去追逐,为我们的社会整合出一份力。日拱一卒,相信在每一个传播主体的参与下,构建起一个具有真善美信仰的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可行性的目标。
需要说明的,对大众传媒在社会整合中所持的理念的遵从和坚持,并不会影响到信息传播的多样性。正如新闻的报道和舆论导向的引导并不矛盾一样,我们同样坚持媒介信息的多样化传播,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不同信息需求。但是,这些信息传播的导向应该遵从大众传媒塑造社会信仰,整合社会的理念内容,而不应该与其背道而驰,造成社会的分化。
[1]刘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问题和趋势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3):20-26.
[2]费孝通.乡土中国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
[4]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7.
[5](德)康德(Immanuel Kant).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M].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67.
[6]邓晓芒.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C]//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性、信仰与宗教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411-424.
[7]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1.
[8]孙旭培.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 [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50.
The New Direction of the M ass M edia in Social Integration:The Kant′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MA Chengyi1,LIGuochun2,XIONG Jihua3
(1.College of Maxism,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650201,China;2.Headmaster Office,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650201,China;3.Yunnan Land and Resources Vocational College,Kunming 652503,China)
For a long term,the mass medi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integration.In terms of its function,it strength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romotes the frequentexchanges between the groups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eventuall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However,from a deeper level or the essence of the effect,it often backfires.Therefore,to let themassmedia realizemeaningful social integration during the operation,we need to find the relatively constant value standards to be obeyed in its present operation.Kant′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can provides us with the certain enlightenment.
themassmedia;social integration;religion of philosophy
G 206;B 516.31
A
1004-390X(2015)06-0053-04
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6.010
2015-07-08
2015-09-29
时间:2015-11-25 9:13
马成益 (1989—),男,甘肃静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科技史、新闻传媒研究。
*通信作者:熊继华 (1964—),男,云南大理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1125.0913.0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