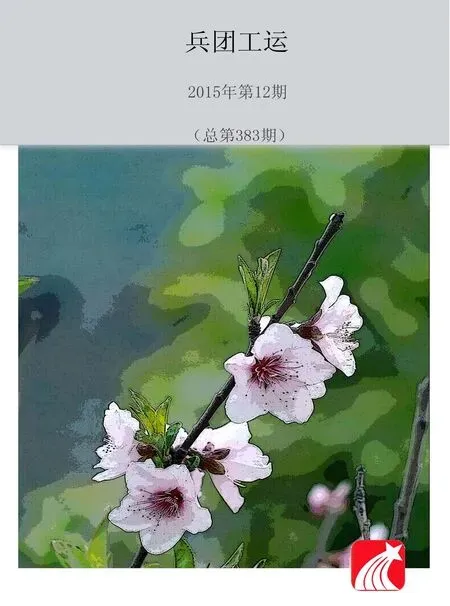父是灯塔
□ 裴桂革
父是灯塔
□裴桂革
我的父亲裴显合于1929年出生在山东省曹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家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1944年家乡来了八路军,给地主扛活的父亲如枯木逢春,那时的他还没有枪杆子高,但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之后无论是打小日本还是连年的内战,父亲尝尽了南征北战、枪林弹雨的艰苦与惨烈。从此,只要见到了“南征北战”字词就会想起父亲,感觉上竟是那样的亲切。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相貌英俊、身材高大魁梧,话不多但是为人和蔼可亲。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母亲就因一场意外事故而致残,生活不能自理,家中的几个孩子年纪都还小,于是奶奶(其实是外婆,情感上我们习惯称她奶奶)来到了我家。父亲对待奶奶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很是感激和敬重。虽然贵为一连之长,但他完全“放权”给奶奶,每月领取工资都如数交给奶奶。每到用钱时,他则会大大方方地向奶奶要,一点也不难为情。饶是这样,我家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张,即便是到了80年代想要吃顿肉还要等到过年。
记得有一天,奶奶破天荒地做了一小碗红烧肉。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看见后都垂涎欲滴,赶忙围了过去,奶奶却压低声音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这两天在外面挖大渠,很辛苦,这是给他做的,你们到时不许跟他抢,听见没有?”我们只好咽着唾沫,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天快黑时,父亲才回来。奶奶见他进门,便端出了饭菜,招呼我们洗手吃饭。我伸出筷子,犹豫半天也没敢吃红烧肉,弟弟妹妹亦如是。
后来,父亲还是看出了这其中的端倪,他不动声色地拿起筷子,先往我最小妹妹的碗里夹了一块红烧肉,接着又给我和我弟弟各夹了一块。“吃吧,好长时间都没闻到肉味了,是该给你们烧顿肉吃。”父亲怜爱地对我们说。
然后,他扭头看了看卧床不起的母亲,风趣地对她说:
“你们的妈妈一定和你们一样馋肉了。”说着,端起红烧肉向母亲走去。奶奶见状却急了,冲着父亲直嚷:“你都给他们吃了,你吃啥?”父亲转过头来看着奶奶,笑着说:“我没那么娇气,吃不吃都不打紧。”
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低,却酷爱读书。上世纪70年代,单位给我家分了一套大约60平方米的带套间的土块房。里间是我们几个孩子和奶奶的卧室,外间因为有父亲用土块砌的炉灶和火墙,也被隔成了两个小间——外面靠门的一间是厨房,里面一间则是父母的卧室兼书房。这间小小的卧室里除了勉强能放下父母的床之外,剩余的空间都被一张简陋、笨重的旧书桌占据,床脚处放着一个大纸箱,箱子里整齐地码放着许多的书报。父亲吃过饭,会倚在床上看书读报。
过去,我经常凑到父亲身边,缠着他,指着书报上的内容问这问那,他总是耐心地回答我那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问题。
有一次,我指着父亲手中的书问:“爸爸,你这些书是从哪来的?”他说:“在连队订购的。”“那你也给我订些书吧。”我央求他。
他笑着问我:“你想看什么书?”“《作文》《作文通讯》《故事会》《大众电影》。”于是,我就把以前在别处看见过的杂志讲给他听。他笑笑,没有多说什么。半个月后,这些杂志便陆陆续续被父亲带回了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敢说,我写字有多勤奋,但是阅读却成了我的习惯,而这习惯的养成与父亲有着莫大关联。
战争年代,父亲曾多次负伤,残留的弹片长期以来都折磨着他,经常痛得他脸色发白、浑身冒虚汗。即便如此,他从来没耽误过工作。团里进行大规模的“开荒种地、挖排治碱”的劳动,有一次,父亲带着全连职工正忙着挖排碱渠,忽然旧病复发,他咬紧牙关,使劲扶着坎土曼才没有倒下。然后,他慢慢地蹲下,把脊背紧贴在渠埂边休息,蜡黄的脸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呼吸渐趋粗重。当大家纷纷劝说父亲回家时,他却摇着头说:“我不能走。比起战争年代,这点疼不算啥,我得带好这个头。”
最终,父亲因为积劳成疾,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一周后,我们见到父亲时,他已是弥留之际。
我记得那天见到父亲时,他的脸色煞白,眼睛陷在眼窝里,似睁非睁。年幼无知的我从未见过父亲这般模样,有些害怕,便躲在奶奶身后,不敢直面父亲。奶奶早已泣不成声,她使劲地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推向父亲身边。父亲轻颤着没有血色的嘴唇,一张一合,像是在说什么,可是听不见一丝的声音。他盯着我的哥哥,仿佛在向他嘱咐着什么。哥哥那年刚满18岁,看着父亲的眼神,他局促不安……在父亲最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们都在病房里陪着他,直到他不舍地合上双眼,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从此,我们陷入了对他无尽的思念中——站着,你的伟岸有如高山;倒下了,你的风采好像江河!多年以后,我愈加清晰地意识到,我与父亲虽生死相隔,但是他犹如屹立在我心中的一座灯塔,始终指引着我,让我在这纷繁复杂的人世间做个坦坦荡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