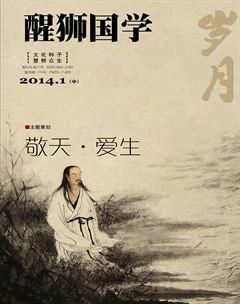天地
杨雪瑾
典籍中说,水土之气升为天。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昱天,冬为上天。南方曰炎天,西南方曰朱天,西方曰成天,西北方曰幽天,北方曰玄天,东北方曰变天,九天亦名九野。东西南北曰四方,四方之隅曰四维,天地四方曰六合,天地曰二仪,以人参之曰三才,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或谓天地为宇宙。凡天地元气之所生。天谓之乾,地为之坤;天圆而色玄,地方而色黄。日月谓之两曜,五星谓之五纬,五星者,东方岁,南方荧惑,西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镇。日月星谓之三辰,亦曰三光;日月五星谓之七曜;天河谓之天汉。亦曰云汉、星汉、河汉、清汉、银汉、天津、汉津、浅河、银河、绛河。
《河图括地象》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未分,其气混沌;清浊既分,伏者为天,偃者为地。《礼记》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所谓“天行一何健,日月无高踪;百川皆赴海,三辰回泰蒙。”从古至今,“天”这一概念就在中华文明中深深扎下了根。祭祀地与敬畏天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两个重要主题。是以成公绥在《天地赋》说道:“天地至神,难以一言定其称。故体而言之,则曰两仪;性而言之,则曰柔刚;色而言之,则曰玄黄;名而言之,则曰天地。若乃玄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烛曜,五纬重光,众星迁而环极,招摇运而指方;白虎时据于参昴,青龙垂尾于心房;玄龟匿首于女虚,朱鸟奋翼于轸张;垣屏络绎而珠连,三台差池而雁行;轩辕华布而曲列,摄提鼎峙而相望。”
在神话中记载,最初的世界是一团晦暗,天地浑沌如鸡子,而盘古生其中。当盘古一万八千岁时,以利斧开辟天地,清浊二气分作阴阳,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初开的天地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在他的努力下,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他自己也日长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后来,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然而盘古却累极而亡,他的头化做了高山,四肢化成了擎天之柱,眼睛变成太阳和月亮,血液变成了江河,毛发肌肤都变成了花草,呼吸变成了风,喊声变成了雷,泪水变成了甘霖雨露滋润着大地。
盘古创造了天地,又把一切都献给了天地,让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然而共工与颛顼却发起了帝位争夺战。共工战败,愤而以头触山,将不周山撞倒了。支撑天的柱子折了,系挂地的绳子断了。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所以太阳、月亮、星星都朝西北方移动;地的东南角陷塌了,所以江湖流水都朝东南方向流去。壮士欻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
支撑苍天的柱子断了,天下的土地出现了裂缝,天象异常,地震频繁,火焰燃烧,无法熄灭,水灾浩荡,无法止住。凶猛的野兽和禽鸟以人为食。于是女娲烧炼了五色彩石修补苍天,割下一只大鳌的脚作为四根柱子来支撑天地,杀死黑色的龙来安抚北边的土地,烧出芦灰来堵住肆意的洪水。苍天被补上了,四根天柱也得以安放,肆意的洪水被止住了,北边的土地平定了,凶猛的野兽死了,平民百姓得以安生。
神话的时代逐渐远去,天也渐渐成为了一个久远的印象。于是屈原扬天长叹,提出了一百七十九个振聋发聩的质天之问———《天问》。屈原被逐,忧心愁惨,旁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然而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屈子问的是天,宇宙生成是万事万物的先决,这便成了屈原问难之始。问天体,问宇宙变化,问星辰为何不会坠落,问太阳每日行路多少,问月亮何以有阴晴圆缺?《天问》中先天地自然后三代史实,而以楚国的贤君愚臣作为结尾,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是正杂说之意,屈子《天问》以惝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钜制,这就是屈子所以为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
西汉时期,武帝问大道之要,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以天人之关系答武帝之疑惑,留下了垂名青史的深刻篇章。他杂揉诸家,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深化发展了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自然中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于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写道:“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然而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汉书·董仲舒传》载:“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谏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尽管随着历史的演进,“天”这一概念已由自然的天体慢慢延伸出人格化、神格化的含义。如《五经通义》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宝也;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一。其佐曰五帝。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慓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纽。”时隔千年之后,柳宗元跨越时空回答了屈原《天问》的《天对》。柳宗元认为在天地形成之前,只是一团混沌的元气,“庞昧革化,惟元气存”,根本不存在有意志的天帝。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是元气自身的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阴阳二气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神秘的动力。除此之外,他还对天与人的关系也进行了思考与发问:天是什么?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还是无意志、无感知的自然物?天体和人类分别处于什么地位?有无“天命”?“天命”与人们的努力的关系如何?“天”能够向人们禀赋什么?人的“天性”如何?“天性”与后天实践的关系怎么样?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自然哲学思想,以朴素唯物主义为探索“天”的奥秘做出了尝试。
随着唐五代大批佛经的翻译,来自西方佛教的“天”的概念也涌入我们的视野中。在梵语中,“天”音译作提婆。与天上、天有、天趣、天道、天界、天上界等同义。指在迷界之五趣及六趣中,最高最胜之有情,或指彼等所居之世界;若指有情自体时,称为天人、天部(复数)、天众(复数),相当于通俗所谓“神”一词。此外,说明死后生天之因(十善、四禅、八定)之教,称为天乘。在初期佛教中,其教法以涅槃为中心,对在家信徒之教说,则以生天为主,谓依道德行善,即可生天。据佛经之记载,天之世界,乃于距离地上遥远之上方;由下向上,依次为四大王众天(又称四天王;持国天、增长天、广目天、多闻天等及其眷属之住所)、三十三天(又称忉利天;此天之主称释提桓因,即帝释天)、夜摩天(又称焰摩天、第三焰天)、睹史多天(又称兜率天)、乐变化天(又称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又称第六天、魔天),合称“六欲天”,为“属欲界六天”之意。此外,尚有地天、水天、火天、风天、伊舍那天、帝释天、焰摩天、梵天、毗沙门天、罗刹天、日天、月天等十二天(护世界、护世之天部)。在密教亦有金刚面天等二十天。
两仪始分元气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东征,悠悠万物殊品名,圣人忧代念群生。纵使“天”是如此神秘而浩瀚,千百年过去了,天仍是我们头顶上空一方值得敬仰的蔚蓝。《河图·挺佐辅》曰:“百世之后,地高天下,如此千岁之后,而天可倚杵,汹汹莫知始终。”说的正是如此。天道郁离,就像刘孝绰在《三光篇》中说的那样:“三光垂表象,天地有咎度;声和善响应,形立景自附;素日抱玄鸟,明月怀灵兔。”习习谷风,洋洋绿泉;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所以我们应怀着敬畏天地的心,去敬天、赞天。正如郭璞在《释天地图赞》中说道:“祭地肆瘗,郊天致烟。气升太一,精沦九泉。至敬不文,明德惟鲜。”如是而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