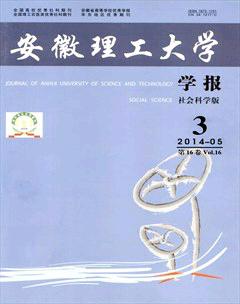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之艺术辩证法分析
摘 要:古希腊悲剧题材大多一悲到底,悲的彻底,很少有喜剧因素植入其中;中国古典早期悲剧大多以大团圆方式结局,悲的不彻底,除结尾外故事中也鲜见喜剧因素。莎士比亚大胆将喜剧因素植入悲剧题材,创造出令人称快的悲剧艺术;中国从封建末期的讽刺小说开始,也随处可见悲中带喜、悲喜交融的悲剧作品。这些都说明了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这可以从作品本身、作家层面、读者角度和审美世界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其合理性、必要性、科学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坎卦;无蔽;“距离”说;艺术真实;主体间性;二律背反;审美境界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3006805
收稿日期:2014-01-03
作者简介:严天武(1988-),男,彝族,云南省丘北县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Analysis of dialectic art of processing tragic theme in comic ways
YAN Tian-w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Most ancient Greek tragic subjects are thoroughly tragic with few comic elements embedded. Chinas early classic tragedies mostly ended happily with incomplete sadness and rare comic factors except in the endings. Shakespeare boldly embedded comic factors into tragic subjects and created marvelous tragic art. From the late feudal satire novel, there have been tragic works blended with joy. All these suggest that it is artistically dialectic to deal with the tragic theme, whose rationality, necessity, scientificness and modernity can be analyz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work per se, the writer, the readers perspective and the aesthetic world.
Key words:Kan Gua; no cover; “distance” theory; the truth of art; inter-subjectivity; antinomy; aesthetic realm
中西对悲剧、喜剧都有不同的定义与看法,但从对悲剧的肯定角度讲,大致是一样的。鲁迅为悲剧和喜剧做出了分界:“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220西方叔本华也说:“无论从效果巨大的方面看,或是从写作的困难这方面看,悲剧都要算作文艺的最高峰。”[2]67古希腊悲剧大多一悲到底,悲的彻底,极少数像埃斯库罗斯写的《复仇神》除外。中国古典悲剧大多以大团圆方式结尾,呈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悲的不彻底。悲剧与喜剧的界限似乎并不是特别明显,以致到后来莎士比亚大胆在悲剧创作中引入喜剧因素,被约翰逊等人认为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中国古典悲剧史中也有类似作品,如《儒林外史》中的科举制度下的文人悲剧。然而,事实证明,在悲剧题材中适当植入喜剧因素,不但不会降低悲剧作品的审美趣味,用得恰当反而可以提升悲剧的审美价值,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
这种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的艺术手法,在中西方文学史中,出现了许多成功的范例。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悲剧和喜剧的界限是分明的,直到文艺复兴时莎士比亚才大胆突破传统写作手法,以喜写悲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中国王被杀后类似中国丑角的门房的上场。之后,意大利剧作家瓜里尼也成功创造出新的剧本——悲喜混杂剧。到了18世纪,狄德罗提倡“严肃喜剧”,博马舍提出“严肃戏剧”,都得到了莱辛的肯定。中国古典悲剧之所以被一部分学者(比如王国维、鲁迅等)认为不是悲剧,只因其悲剧结尾多了个“大团圆”的尾巴,且它们也不算是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的成功范例,真正成功的尝试,当以清之讽刺小说算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到:“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佁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谪时弊,……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3]到了近代,鲁迅运用和发展了这一艺术写作手法,创作了《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等成功的悲剧作品。
该艺术表现手法的特点是:1.以喜写悲,即用喜剧化的手法描摹悲剧主人公的人物性格、人物心理活动、语言动作等;2.以喜衬悲,即在人物命运发展过程中制造喜剧性气氛,以鲜明对照来衬托悲剧的悲;3.以喜促悲,悲哀有时也会以“欢喜”的方式作为其出现的预兆,尤其是大悲、大哀,往往深藏在“欢喜”中,喜剧的登场能促进悲剧的真面目早日揭开;4.悲喜交融,即悲中带喜、喜中含悲,读者在悲喜交加中融入故事情节,与主人公融为一体,进入“我即他、他即我”的无障碍艺术审美境界。就单纯的喜剧或悲剧而言,此艺术手法有其独特的审美效果。赵凯老师将其归纳为两点:“1.在悲剧创作中,悲剧性与喜剧性就是一对即可混合又可互转的审美范畴。悲剧艺术家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表现手法,可以使喜剧因素成为刻画悲剧性格、表现悲剧冲突的有利手段。……2.从观众学的角度来说,悲喜交错的手法,可以调动和丰富观众或读者对悲剧艺术的审美感受,悲剧的内容若在幽默、诙谐和乐观的情感形式中表现出来,可以达到‘哀而不伤、悲而不馁的艺术效果,从而保持悲剧正面或乐观的素质。”[1]218-221endprint
接下来我们分别从作品本身、作家层面、读者角度和审美世界等四个方面来对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之艺术辩证法的合理性、必要性、科学性和时代性作一一分析。
一、从作品本身分析其合理性
一个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该悲剧不会就此失去其审美趣味与审美价值,反而更能体现艺术的辩证法,使作品更丰满,更具有生命力。
从中国古代思想角度讲,关于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的艺术辩证法,古人早已有所体现。《易经》中将道分为阴阳,阴阳组成八卦,八卦组成六十四卦,每卦又有卦辞、爻名、爻辞、彖传和大小象传,以诠释宇宙万物繁衍生息的道理。悲剧是一个艺术作品,亚里士多德曾给悲剧下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值得认真关注的行为的描述,行为本身具有完整性,具有一定意义……通过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4]而人的感觉又有五种“怒喜思悲恐”,对应五行的“木火土金水”,五行皆与阴阳相对应,悲对应金,金是阳消阴长的状态,所以悲剧就是阴,喜剧就是阳,纯悲剧就是坤卦,纯喜剧就是乾卦,而在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便是坎卦。坎卦,上下为阴,中蓄一阳,象征“水”以阴为表,内中却蕴藏着阳质。所以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是合理的,它可以蕴藏阳质,即通过引起读者喜的一面,从而起到对读者审美教育作用这阳的一面。比如在《阿Q正传》中滑稽可笑的阿Q在每次被赵老爷打后,或被别人嘲笑后总说:“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以此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读者在捧腹大笑之余,也得到了教育:我可能就是阿Q,我可不能像他一样自欺欺人。所以,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不但不使悲剧变味,反而使悲剧题材散发更强大的生命力。
凡事有利必有弊,西方悲剧悲的彻底也不见得是好事。庄子在《庄子·人间世》中写到:“散木也,以为丹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才之木也。无所不用,故能若是之寿。”[6]47散木无用,故能成其寿。古希腊悲剧过渡强调一悲到底,反而断送了它的生命,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道:“希腊悲剧的灭亡不同于全部早期姐妹艺术类型,它死于自杀,由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冲突,因而死得悲壮,而所有那些早期姐妹艺术则寿终正寝,死得最为漂亮、安宁。”[7]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正是一种调和悲剧自身内部矛盾冲突的良方。悲剧不能没有喜剧因素来衬托,正如老子在《老子·天下皆知章》中写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从西方存在主义美学代表海德格尔角度分析,“真理是存在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9]69而“艺术是真理之自行放置入作品,艺术让真理脱颖而出。”[9]65要想让悲剧这一独特艺术更好地诠释真理,达到“去蔽”的目的,就得从非悲剧——喜剧角度去揭示真理,如海德格尔所说:“真理从来不是他自身,辩证地看,真理也总是其对立面。”[9]41悲剧的对立面就是喜剧。清代作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就假托明代故事,写了18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风俗画,辛辣地讽刺了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底下悲惨的命运。范进考了二十多次,54岁还是童生,进考场时“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中举后,他的丈人胡屠户先前骂范进是“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却说“才学又高,品貌友好”,是“天上的星宿”。范进母亲为此惊讶、困惑、欣喜,以致“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归天去了”。张大侠张铁臂演了个闹剧“人头会”,得了钱财,哄两位公子广招宾客,自己却飞上房梁,“一片瓦响,无影无踪去了。”
这些都体现了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的合理性,因为它增加了作品的生命力,符合艺术的辩证法。
二、 从作家层面分析其必要性
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对作家写作是一大挑战与考验,诚如赵凯老师在《悲剧与人类意识》中写道:“悲剧创作中注入喜剧因素,这并非作家别出心裁、哗众取宠,而是作家的美学观念在创作中日趋成熟的表现。”[1]216
针对作家本身而言,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也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10]28作家在创作悲剧的过程中,往往以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为自身写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父亲扔了一个苹果陷入甲壳虫体内,导致腐烂,使格里高尔加速了死亡,正是现实生活中卡夫卡与父亲关系不和的真实写照。但这容易把作者与读者拖入悲剧情节中,跳不出来。西方现代心理学美学代表瑞士的爱德华·布洛便提出一种“距离”说,他所说的“距离”是在审美活动中要与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布洛指出:“距离是通过把客体及其吸引力与人的本身分离开来而取得的,也是通过使客体摆脱了人本身的实际需要与目的而取得的。”[2]139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一味写悲,一味把自己和读者带入悲剧中,而是在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使读者与作品有一定的心理距离,更使作家从作品中跳出来,专心构思。艺术家和诗人的长处就在能够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诚如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里说:“我们何以有情感而不能表现于艺术作品呢?这就是由于不能在自己和自己的情感中写出‘距离来,不能站在客观的地位去观照自己的生活。凡艺术家都须从切身的利害跳出来,把它当作一幅画或是一幕戏来优游赏玩,这本来要有很高的修养才能办到。”[11]20
作家在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看似不真实,其实这更能体现艺术辩证法中艺术真实的创作理念。生活中固然有一悲到底的悲剧发生,固然有一喜到底的喜剧发生,但艺术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也不等于科学真实。作家对对象世界的理解、反映和阐释,只要合情合理,他的作品就有真实性。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的必要性正基于此。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中这样解释艺术真实:“它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识和感悟。”[12]61比如《狂人日记》中喜剧因素随处可见:“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5]25《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跟两个掘坟小丑的谈话也颇有喜剧因素:“哈姆雷特:你给什么人掘这坟墓?是男人吗?小丑甲:不是男人,先生。哈姆雷特:那么是个女人?小丑甲:也不是女人。哈姆雷特: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么谁葬在这里面?小丑甲:先生,她本是一个女人,可是上帝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息,她已经死了。”[13]正是莎士比亚以喜衬悲,以喜促悲,悲喜交融,寓庄于谐,才使主题升华。因为它能调剂戏剧气氛与情感,这就有利于激发观众的理智,从而收到更大的悲剧效果。endprint
这些都是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的必要性,它能很好的体现作家创作技艺的成熟,符合艺术的辩证法。
三、从读者角度分析其科学性
读者是文艺作品的受众,欣赏悲剧是一种文艺消费,它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作品能否流传,就看读者对作品的评价。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对方。”[10]8文学消费具有二重性,即商业(交换)价值与审美价值、价值规律与艺术规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二重性,这二重性既是互补的,又是常常冲突的。
读者通过作品与作家间接联系,读者能否肯定作者,就看作品的审美趣味了。一悲到底的悲剧固然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但除了引起怜悯,却更少地能让读者体会其中的审美趣味。而在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则把读者与作者拉的更近,符合艺术的辩证法。在鉴赏过程中,读者是主体,作品中的审美世界是客体,如何将客体转化为主体,现象学代表胡塞尔为此在他的哲学中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杨春时在《美学》中解释道:“主体间性哲学不再把世界看做实体,而是将其看做另一个主体,并从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来考察存在。主体间性是指在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中确定存在,存在成为主体之间的交往、对话、体验,从而达到互相之间的理解与和谐。”[14]这样,读者与作品中的审美世界之间的对立便消除了,读者在欣赏悲剧题材中达到了无差别的境界,审美同情得以充分体现。比如周星驰的悲剧电影《大话西游》中,山贼帮主至尊宝爱上了白晶晶,通过月光宝盒却穿越到另一个世界,遇到另一个女人;在痛失爱人后,又迫不得已挑起西天取经的重任,其间闹出了一系列悲喜剧,让读者在捧腹大笑中消除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仿佛自己就是那个被命运捉弄的至尊宝。人皆有私心,当至尊宝欺骗紫霞仙子编出谎话时,这一谎话却赢得了无数观众的肯定与效仿——“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尽管这是一个谎话,尽管当时至尊宝并未爱上紫霞,如《西游降魔篇》中唐三藏当初并未爱上段小姐一样,但最终结局都是美人香消玉殒。这对于有过类似感情经历的读者来说,在观看电影中更能与作者产生共鸣。
其实,从艺术辩证法角度考虑,悲剧本身就有“距离的矛盾”。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指出:“同一作品,就内容来说,当时人和本国人比后世人和外国人欣赏较易,就实际的牵绊容易压倒美感态度说,当时人和本国人却也比后世人和外国人欣赏较难。……这就是由于‘距离的矛盾。”[11]25这也许就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鉴赏的二律背反:“1)正题:鉴赏判断不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因为否则对它就可以进行争辩了(即可以通过证明来决判)。2)反题:鉴赏判断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因为否则尽管这种判断有差异,也就连对比进行争执都不可能了(即不可能要求他人必然赞同这一判断)。”[15]185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康德继续解释说:“对于一个二律背反的解决仅仅取决于这种可能性,即两个就幻相而言相互冲突的命题实际上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可以相互并存的,哪怕对它们的概念的可能性的解释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能力。”[15]185所以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两者是可以并存的,是辩证统一的,尽管悲剧与喜剧的概念是相反的。这样一来,二律背反解决了,读者在欣赏悲剧中不会有主客体的对立,就可实现审美鉴赏与审美体验的有机统一。
这些都体现了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的科学性,消除作家与读者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探索解决审美阅读中“二律背反”的新方法,符合艺术的辩证法。
四、从审美世界分析其时代性
美国当代文艺作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有四要素:作品、作家、读者和世界。悲剧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少了世界不行。世界有多种,关于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的艺术手法,我们可以从审美世界中的通过提升审美境界达到审美教化作用来分析其时代性。
庄子在《庄子·养生主》中写道:“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6]33悲剧题材中植入喜剧因素,犹如牛骨中留出的空隙,让读者可以“游刃有余”,从而辩证地提升审美境界。比如契科夫的小说《公务员之死》写了一个小公务员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把唾沫星溅在前座的一位将军的秃头上,他三番五次向将军道歉,但唯恐不原谅,最终惶惶而死去。还有《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整天穿雨鞋,带雨伞,戴黑眼镜,穿棉大衣,口头禅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读者在欣赏中,当回想自己过去类似心理想法或经历时,都会觉得仿佛作者在写自己,自己仿佛就是那个坐在后排的小公务员,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从而在欣赏中达到王国维说的“无我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6]关于此审美世界中的艺术境界,宗白华也在《美学散步》中谈到:“人类这种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这充沛的自我,真力张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17]这也许就是悲剧美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审美境界的提升,是作家创作作品是无功利性与功利性辩证统一的审美体现,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中说:“第一,作为作家或读者的话语活动,文学虽然与直接的功利目的无关,当间接地人就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诚然不同于商人对森林财富的占有欲和科学家对森林科研价值的探究欲,但却显现为审美地掌握世界这一深层目的。……第二,作为再现现实社会生活的话语结构,文学的功利性在于,它把审美无功利性仅仅当作实现其再现社会生活者一功利目的的特殊手段。”[12]62我们欣赏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从以喜衬悲、寓庄于谐的手法中,都可以从中体会出作者对主人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良苦用心。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5]23这正是鲁迅针对当时半殖半封社会,“揭出痛苦,引疗救的注意”创作的最终审美教化目的,有很强的时代性。endprint
正是悲剧,尤其是适当以喜剧方式处理的悲剧题材,使读者在审美世界中的审美境界得到提升,完成作者的审美教育目的。正如别林斯基在一篇专门讨论文艺批评的文章中所说的,每一部艺术作品一定要在与时代、与历史的现代性的关系中,在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得到考察;对艺术家的生活、性格以及其他等等的考察,也常常可以用来解释他的作品。这些都体现了以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的时代性,通过提升审美境界达到审美教化作用,符合艺术的辩证法。
五、总结
归根结底,将喜剧因素植入悲剧题材中,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既增加了作品的生命力,又体现了作家创作技艺的成熟;既消除作家与读者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又通过提升审美境界达到审美教化作用;是合理性、必要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这种嫁接,体现了恩格斯在文艺创作中关于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创作理念。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大的特点之一。”[18]
中西文艺史上,不同作者都尝试了不同题材的悲剧创作,并大胆将喜剧因素植入悲剧作品中,创作了众多成功的艺术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杂文小说等等,它们都是悲剧史上的瑰宝,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放出更加熠熠生辉的光彩,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 赵凯.悲剧与人类意识[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2] 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2.
[4]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M].郝久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23.
[5] 鲁迅.鲁迅经典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6] 庄子.庄子[M].刘旭,刘英,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 尼采.悲剧的诞生[M].杨恒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61.
[8] 文选德.《道德经》诠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52.
[9]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M].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剧集[M].吴永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74.
[14] 杨春时.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0.
[15]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6]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624.
[17]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81-88.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2.
[责任编辑:吴晓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