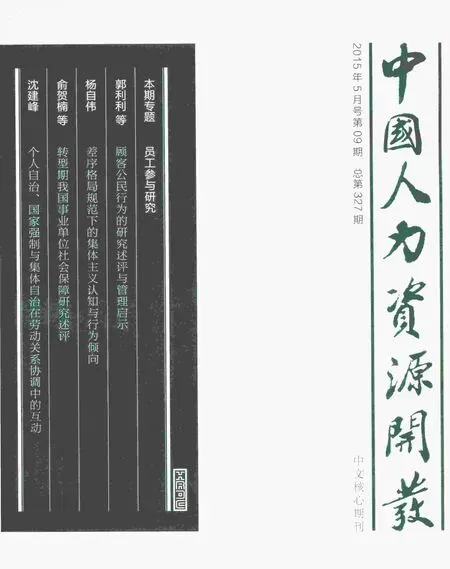个人自治、国家强制与集体自治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互动——基于对德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梳理
● 沈建峰
劳动法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领域,它与传统法律部门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其多元的法律调整机制:劳动合同、劳动基准、集体合同,参与管理等共同协调着劳动关系。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不同机制如何产生,不同机制之间如何协调和互动以避免冲突并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目标?随着我国劳动法治建设的进行和法律框架的完善,必须整体思考不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劳动关系协调问题具有其特殊性,也有其共性。与我国同为大陆法系的德国,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此背景下,梳理和分析德国劳动关系协调的不同机制及其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之间的协作规律,对完善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完善应该会有较大借鉴意义。
一、德国多元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形成
现代德国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发端于19世纪工业革命到来之后。其初始的协调机制植根于传统民法的合同制度中。但是由此带来的雇主压榨劳动者的不合理经济现象和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导致立法者开始通过公法措施干预劳动关系,出现了最低工资、工时、工作年龄等规则,所以学者们认为,“劳动法起步于公法。”(瓦尔特曼, 2014) 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劳动者结社——工会等现象,但直至1869 年工会等劳动结社在德国都是受到禁止的,此后尽管结社的合法性得到了承担,但直到1918 年的《团体协议条例》才最终承认了团体协议对劳动者和雇主直接且强制的效力。此后,1919 年的《魏玛宪法》通过第165 条等条文承认了劳动者及雇主的结社促进和维持劳动条件的权利以及结社的自由。与上述团体协议发展过程相伴的是工厂中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法律制度。早在1890 年威廉二世皇帝的“二月谕令”中就提出了劳动者选举代表参与共同实务调整的思路,该思路最终在1891年的《帝国营业条例》中得以落实。据此,“雇主有义务在颁布劳动规章前听取全体(成年)劳动者或事实上存在的工人委员会的意见。”( Krause, 2009 ) 劳动者参与管理的制度雏形出现。最终“1920 年2 月4 日的《工厂委员会法》规定了劳动者以及职员在工厂中的代表,赋予给他的任务是协同建构企业秩序。”(瓦尔特曼, 2014) 德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多元框架已经基本形成。20 世纪50年代以后,德国劳动法又引入了一个新的机制——企业(unternehmen)层面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1951 年德国通过了《五金矿业产业参与决定法》,1952 年《工厂组织法》中加入了三分之一参与决定规则,1976 通过了《参与决定法》,最新的涉及参与决定的立法是1996 年的《欧洲工厂委员会法》。至此,现代德国多元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已全部建立,形成了私人自治、集体自治(团体协议与参与管理)和国家强制三个层面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二、德国劳动法中多样性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内涵
德国法中劳动关系的协调总体建立在私人自治、集体自治和国家强制的框架基础上,上述框架具体落实为如下法律制度:
(一)私人自治性的协调手段
“宪法保障根据私人自治原则自主建立、终止劳动关系以及建构劳动关系内容的原则性自由。”(瓦尔特曼, 2014)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劳动关系存在的基础是私人的意志安排,在此基础上才存在国家强制和集体自治规则的适用问题。私人意思自治性的协调手段主要包括如下几种:
1.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雇主之间达成的合意,据此劳动者承担有偿劳动给付义务,雇主承担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同时雇主和劳动者还因此而承担信赖和保护义务。在德国,劳动合同是雇佣合同的一种类型,被界定为债法上的双务合同。( Klaus Weber,2004)劳动合同原则上无需采取书面形式。
2. 雇主指示
根据《工商业条例》第106 条,雇主享有单方通过指示单方确定劳动条件的权利。只要劳动合同、工厂协议和可适用的团体协议规定或法律规范对该劳动条件没有确定,雇主则可以在公平裁量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劳动给付的内容、地点和时间。“雇主指示权是劳动关系的标志!”(瓦尔特曼, 2014)
3. 劳动法上的特别现象
除了上述通过双方意思表示和单方意思表示确定劳动关系内容的制度外,德国劳动法上还存在着如下特别的通过意思表示确定劳动关系内容的现象。(1)总体允诺(Gesamtzusage),也即雇主以一定形式公开向所有员工或一个劳动者群体所做的有利于其的补充性给付允诺(Preis, 2009;瓦尔特曼,2014 年 )。主流意见认为雇主的上述允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要约”,劳动者通过模式形成予以接受,在雇主和劳动者之间成立对劳动关系予以调整的补充合意。(2)工厂习惯(Betrieblicheb ung)。所谓工厂习惯是指“从特定行为有规律的重复中可以推断出表意人内容具体、指向未来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瓦尔特曼,2014 年)德国司法机关认为在雇主的重复行为中包含着一个要约,劳动者对该要约予以承诺,所以产生了合同约束力。
(二)集体劳动法上的制度设计
使得劳动法从传统民法中分离出来,日益独立的独特制度设计是集体劳动法上调整劳动关系的团体协议、参与决定等重要制度。
1.团体协议(Tarifvertrag)
团体协议是由具有团体协议能力的当事人为了调整团体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及规范性的调整劳动条件和经济条件而签订的合同。团体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具有团体协议能力(Tariffh igkeit)的工会;另一方面可以是单个雇主或者雇主联合会。团体协议的条款可以涉及劳动关系的内容、订立和结束以及工厂规范和工厂组织规范等等。上述规范一方面对单个劳动者和企业具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对确定其权利义务具有直接性和强制性(沈建峰,2012);另一方面对签订团体协议的工会和雇主联合会或单个雇主具有债权性效力,违反该协议应承担违约责任。
2.参与决定制度
和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集体劳动法相比,“德国集体劳动法最具特色的是劳动者利益代表一方面由自由组成的工会代表,另一方面由法律规定的工厂委员会代表的二元主义。”(Krause, 2009 )在此基础上,劳动者的参与决定又被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通过工厂委员会(Betriebsrat)、欧洲工厂委员会和代言人委员会进行的参与决定,另一方面是通过劳动者在监事会和董事会或执行机构中的劳动者董事实现的参与决定。”(Wolfgang Hromadkaet al.,2010)
(1)企业层面的参与决定
企业层面参与决定的基本内容是劳动者选出的利益代表参加到大企业、矿山及五金企业等特定企业的监事会或董事会,通过享有与其他成员同等的经营决策权利而进行的劳动者参与。根据企业的性质和规模,劳动者在监事会中的代表可以在2000 人以上的大企业和煤钢五金企业占监事会成员人数的一半;而在500 人以上的企业则占三分之一。 此外,在企业的董事会中还可以有一名劳动者董事。这种参与决定完全在公司法中公司治理机构的体制内进行,分享雇主的经营决策权,并不是劳动法上特殊的协调机制,也不与其他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发生规则上的冲突。
(2)工厂层面的参与决定
按照德国《企业组织法》第1 条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雇佣至少5 个具有选举权的劳动者,在其中三个可以被选举时,企业应选举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由本工厂劳动者从由劳动者或者工会做出的选举建议名单中选出的劳动者代表组成。其可以在社会、经济和人事事务上参与共同决定,其权限被区分为参与决定权和参与作用权,并由《工厂组织法》予以列举。在前者的情况下,工厂委员会不同意则雇主无法作出有关决定,而后者主要是知情和听取意见。一般认为,工厂委员会在工厂层面上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保护功能)并平衡同一工厂中劳动者的利益冲突(利益均衡功能)。
(3)工厂协议(Betriebsvereinbarung)
工厂中的人事、经济和社会事务,工厂委员会都享有参与管理权。如果工厂委员会和用人单位就上述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则这种合意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工厂协议。工厂协议是雇主和工厂委员会之间“具有规范特征和债权效力的私法上的合同。”(Preis, 2009)该协议以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工厂组织和经济事务为对象,也涉及到工厂中的劳动关系。根据《企业组织法》第77 条第4 款第1 句,该合同首先对于工厂委员会和用人单位具有债权性效力,其次,对不论是签订工厂协议时已有的劳动者还是将来入职的劳动者以及用人单位都具有直接且强制的法律规范效力。工厂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不具有书面形式的工厂协议,不能发生工厂协议的效力。在德国劳动法中,团体协议和工厂协议共同构成广义的集体合同(kollektiver Vertrag)范畴。
3.国家强制
协调劳动关系的最后一个机制是国家强制。劳动法中的国家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法律设置了协调劳动关系的基础框架,规定了劳动合同制度、团体协议制度以及工厂委员会制度等协调劳动关系的其他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和前提。其二,直接调整劳动关系本身,包括劳动保护法——保护劳动者免受身体、健康等既有利益的侵害,和劳动条件法——保护劳动者分配劳动成果利益时免受不利益。
三、多元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根源:利益代表的层次性
德国劳动法中多元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立在多元主义的国家观念基础上,但它也体现了不同层级的利益代表对劳动关系协调的参与。
1.私人
劳动关系的双方——劳动者和雇主,首先是私的利益主体。按照现代国家的理念,私人之间的利益首先由私人来判断,私人认为对自己公正的结果,肯定是最公正结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实现这种私人利益判断的机制主要是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是私人(Privatpersonen)所缔结的私法上的合同。”(Hueck-Nipperdey, 1970)
2.劳动结社(Koalition)
尽管劳动关系是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是在劳动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作为私法自治前提的、当事人之间力量的差不多均等(在劳动关系领域)原则上是缺失的,所以仅仅通过合同法无法保障利益恰如其分的得以均衡。”(Waltermann, 2012)为了保证这种利益均衡的实现,德国《基本法》第9 条第3 款第1 句规定了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保障所有人和所有职业为维持和促进劳动条件、经济条件而结社的权利”。通过势均力敌的劳动结社进行的集体合意来安排劳动条件。在产业工会原则的背景下,劳动结社所代表的是整个产业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志。
3.工厂委员会
如上所述,在劳动关系协调中,个人代表的是个体的利益,工会等结社代表的是整个产业劳动者或整个产业的雇主利益,特别是当德国的主流理论和实践要求工会应当具有超企业性的组织结构(b erbetriebliche Organisation),原则上不存在企业工会时,在协调劳动关系时如何顾及特定工厂及其特定工厂中劳动者调整自身利益的需要?实现这一利益代表的机制就是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至少首先是同一工厂劳动者的利益照管者。”(Krause, 2009 )
4.国家
在德国,理论和实践界认定,对劳动条件和经济条件的规制首先不是国家的任务,而是劳动结社的任务。但是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工会等结社的成员,因而可能不能得到团体协议等制度的保护,也因为劳动力市场运作和劳动关系的协调需要基本的法律框架等原因,在传统中,国家之手也非常慎重的介入到劳动关系的协调中。在很大程度上,它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秩序利益以及当事人之间利益分配的最低底线。
四、德国劳动法中不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
当存在多元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多层级利益代表时,如何协调上述机制和利益代表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德国的立法、司法和理论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
(一)合同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完成,这种要求表现在法律上就是通过私人之间的劳动合同,通过私人意志安排来完成。所以,在德国法中,调整劳动关系的基础性机制是劳动合同等私人自治的制度。在法律所设置的界限范围内,劳动关系建立、内容等的安排是劳动合同当事人的事情。
(二)劳动合同与国家强制、集体自治的关系
1.劳动合同与国家强制的关系
对劳动者和雇主而言,劳动法律中的强行法可以分为(1)单方强制的法律。大部分劳动法规范原则上用以保护劳动者,是单方强制的。它们只允许做有利于劳动者的排除适用。(2)双方强制的法律。劳动法的制定法规范偶尔是双方强制的;维护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则就是这样。
2.劳动合同与集体自治的关系
在集体合意的产物——团体协议和工厂协议与个体自治的产物——劳动合同的关系问题上,德国立法、司法和理论的基本立场是:团体协议和工厂协议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具有直接并且强制的规范效力。上述规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1.集体合同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具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对签订团体协议的工会会员和签订团体协议的单个用人单位或者雇主联合会的会员来说,团体协议的规定相当于法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违反,当事人也不得通过合意降低之。2.集体合同的规范性效力对劳动者和单个用人单位具有直接性和强制性。首先,集体合同的规范性内容对劳动者和单个用人单位直接生效,也就是集体合同“既不需要相关主体的参与(即无需其知悉),也无需任何转化行为”( Zl lner et al.,2008; Preis, 2009) 就当然的成为个别劳动关系的内容,成为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出请求的请求权基础。其次,集体合同的内容对个别劳动关系强制生效,“个别劳动关系当事人不得变更团体协议规范的内容。”(Preis, 2009) 上述集体合同规范效力的强制性和直接性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一,有利原则。允许个别劳动合同对团体协议做出有利于劳动者的变更。其二,开放条款。所谓开放条款是指团体协议的缔结者在团体协议中约定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排除的条款。3.具有规范效力的团体协议内容主要涉及劳动关系的内容、订立和结束以及工厂规范和工厂组织规范。团体协议的内容可以非常多样,但并不是所有团体协议的内容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具有规范效力(Preis, 2009; Zl lner et al.,2008) 。
(三)国家强制与集体合同的关系
在引入集体合同制度时,我们一般容易将其原因归结为劳资双方的地位失衡。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力量失衡,为什么国家不通过强行立法规定劳动条件?为什么不通过强大的劳动基准法而是通过团体协议来规定劳动条件?从德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劳资双方力量失衡只是前提之一,在集体合同和国家强制的关系问题上德国法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审慎态度。学者们认为,“劳动结社通过团体协议自我负责且实质上没有国家影响的特别调整工资和其他劳动条件,在该领域国家的规制权限保持的极为审慎;在此程度上,劳动结社自由有助于形成有意义的劳动生活秩序。”(Waltermann, 2012)国家在劳动条件建构中仅居于辅助性(subsidiaritt prinzip)。但在集体合同无法充分解决劳动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冲突或者实现公共福祉之处,社会自我管理即至其界限。这也就形成了国家采取影响措施的空间。尽管基本法第9 条第3 款保障团体协议自治,但并不排除国家辅助性的介入。一旦国家就特定问题符合宪法的做出了强制性规定,除非其将自身设定为允许当事人通过集体合同等排除其效力的法律,则集体协议必须遵守强行国家法的规则。因此,可以说,集体协议在功能上对国家强制具有优先地位,在效力上对国家强制具有劣后地位
(四)不同集体合同之间的关系
德国法中团体协议和工厂协议,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二元制的形成首先是历史发展的产物(Krause, 2009 ),其次才是逻辑建构的结果。到现在为止,人们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协调团体协议与工厂协议、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关系:1.功能上的差异。工会或者说团体协议的任务是以超越单个企业的方式调整劳动条件和报酬等;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整个社会利益、产业利益的角度出发,预防企业自利主义;工厂委员会以及工厂协议的任务是监督团体协议的落实、补充团体协议的规则,并限制雇主的决定权。2.取向上的差异。工会或者结社的取向为对抗;工厂委员会的取向为合作,《工厂组织法》第2 条第1 款规定了雇主和工厂委员会在遵守有效团体协议的基础上,在工厂中代表的工会的协助下,为劳动者和工厂的福祉而充满信任(vertrauensvoll)的合作。3.调整对象和效力上的区分。工厂协议在调整对象上和在效力上劣后于团体协议,“团体协议或者团体协议习惯对工厂协议具有阻滞作用”(Preis, 2009),工厂协议不得违反强制性的团体协议规定。除非团体协议通过所谓的“开放条款”明确允许缔结补充性的工厂协议。
(五)作为补充的雇主指挥权
雇主指挥权赋予了雇主单方决定劳动关系内容的权力!过大的指挥权将会给劳动者带来过重的法律负担。所以,在位阶上,雇主指挥权是效力最低的协调劳动关系的手段。根据《工商业条例》第106 条,只有劳动合同、工厂协议和可适用的团体协议的规定或法律规范对该劳动条件没有确定时,雇主才可以根据公平裁量进一步确定劳动给付的内容、地点和时间。
(六)新趋势:从集体自治为心中向国家强制强化的过渡
1.20 世纪末以来的新挑战
德国上述形成于上世纪20 年代以集体合同为核心的劳动关系协调体制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却因为劳动关系如下的新发展而面临新挑战:服务产业日益发达,全球化的发展,劳动关系的基本图景逐渐告别以工厂烟囱为中心,以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为原型的模式,出现工作方式更加多样、工作地点和时间更加灵活等趋势,在此背景下工会的入会率下降几乎成为全球趋势,工会与雇主抗衡的能力也在下降。理论界提出,“在改变了的劳动世界中,团体协议自治在建构力量上不再像工业社会时代那样极为有效。首先是在服务业劳动中,人们比以前更少的谈论集体模式。”(瓦尔特曼, 2014) 而德国立法者也意识到,“通过团体协议对劳动生活制度的调整在过去的多年间明显衰退。在当代工业和服务业社会中,劳动世界日益碎片化。这在结构上使得团体协议当事人难以完成基本法第9 条第3 款托付给的使命。”(Entwurf, 18/1558)
2.国家立法的应对
“在社会中日益出现的利益碎片化以及在意义日益增长的服务业劳动中劳动结社约束的回落使得国家急剧走上前台:对最低工资的讨论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体现。”(瓦尔特曼, 2014) 这最终导致立法者将最低工资法纳入立法议程!德国议会第18 届立法期的重要议题就是《团体协议强化法》,该法的第1 部分即为《最低工资法》。《最低工资法》共包含24 个条文,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效力,最低工资委员会、最低工资落实等制度,该法于2014 年7月3 日由联邦德国议会通过。
五、德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对中国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启示
上述德国多元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如下方面对中国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1.多方参与、协作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劳动关系涉及存在于结构性不平等关系中的私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的调整,不能完全通过传统私法意思自治的思路完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国家强制来实现,其协调必然是依赖于私主体、劳动结社以及国家共同之手来进行,这样才能较好处理国家、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发挥不同主体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作用,同时顾及到个人、群体和国家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也应建设包括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和劳动基准在内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但从目前来看,一方面有关制度并不完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有关制度的功能、定位以及制度根源和界限并没有被准确把握,制度之间的功能协调没有完全理顺。所以,完善各个制度本身以及完善各个制度之间的协调关系都是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2.多元协调机制建立过程中应注意完善有关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协调劳动关系的三种机制中,个人自治的实现依赖于个人意思自由的保障;国家强制的实现依赖于有效的执法和司法;而集体自治的实现依赖于有力且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代表机构,否则即使建立了有关制度,该制度也可能失灵。在这一认识下,在我国劳动关系协调制度建立过程中,除了保障个人在签订劳动合同中真实意志得以实现外,更重要的是应完善劳动行政执法、司法以及工会和劳动者代表制度的建设。尽管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了大量的劳动标准,但劳动者权利依然得不到实现,尽管我们一直在推动集体合同制度,但集体合同在实践中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的根源之一正在于有关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3.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建设应顾及全球趋势和本国发展阶段
德国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传统上是一个以集体合同(团体协议和工厂协议)为重点的协调体制。但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在美国,“私有部门的工会密度跌至不足10%”(巴德,2013 年),而且德国也出现了工会会员人数下降,工会谈判能力下降,集体合同的规制能力下降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德国的劳动基准立法得以强化。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建设也应该顾及到上述特殊的全球趋势,劳动基准立法应得到强化。但与德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在整个产业机构中依然居于重要的地位,而制造业领域向来是集体协商最有力和有效的领域。因此,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依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完善和发展集体协商制度势在必行。
4.几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除了上述整体框架外,德国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如下具体制度上也值得我们关注:其一,集体合同制度的定位。集体合同是一种劳动者一方和用人单位一方进行社会自治的模式,是通过市场调配劳动力资源的法律安排形式,也是一种市场机制。只要不超越法律的禁止界限,劳动者一方和用人单位一方就可以自主的通过集体合同协调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超过劳动基准的集体谈判诉求,并不是所谓的“法外诉求”,而是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自治领域。相反,照搬法律标准的集体合同是没意义的。其二,工会和职代会的关系。在我国,似乎和德国一样,都存在着工会和其他劳动者的利益代表机构并存的模式。但从目前来看,二者的设置、功能和调整对象在制度设计上却具有重合性:我国基层工会是企业工会,设置在企业中,但企业中同时还存在职代会;工会可以代表劳动者进行集体协商,职代会作为劳动者民主管理的形式也是一种平等协商机制;工会可以代表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职代会这种民主形式制定用人单位规章,并且集体合同和用人单位规章的调整事项具有重合性,二者都可以调整“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劳动合同法》第4 条,第51 条)。尽管现行法通过“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集体合同需要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等协调二者的关系,但这种协调本身却引发了其他问题,包括会员制的工会如何成为非会员制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会员制的工会签订完劳动合同后,为何不是通过会员代表大会通过集体合同,而是职工代表大会通过集体合同?因此,如何在规则和理论上协调二者的关系,在我国依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德国的经验是值得参考的。
1.瓦尔特曼著,沈建峰译:《德国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
2.Krause, Gewerkschaften und Betriebsräte zwischen Kooperation und Konfrontation, in: RdA, 2009, S121-140.
3.Klaus Weber, Rechtswörterbuch, Verlag C.H.Beck, 2004.
4.Preis, Arbeitsrecht, Individualarbeitsrecht, 3.Auflag, Verlag Dr. Otto Schmidt, 2009.
5.沈建峰:《论集体合同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效力》,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9 期,第95-99 页。
6.Wolfgang Hromadka, Frank Maschmann, Arbeitsrecht, Band 2 ,Springer,2010.
7.Preis, Arbeitsrecht, Kollektivarbeitsrecht, 2Auflage, Verlag Dr. Otto Schmidt, 2009.
8.Hueck-Nipperdey, Grundriß des Arbeitsrechts, Verlag Franz Vahlen GmbH, 1970.
9.Waltermann, Arbeitsrecht, 16.Auflage, Verlag Franz Vahlen, 2012.
10.Zöllner, Loritz, Hergenröder, Arbeitsrecht, 6.Auflage, C.H.Beck, 2008.
11.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tarifautonomie,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8/1558.
12.约翰·W·巴德著,于桂兰等译:《劳动关系:寻求平衡》,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版,第93 页。
——以《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