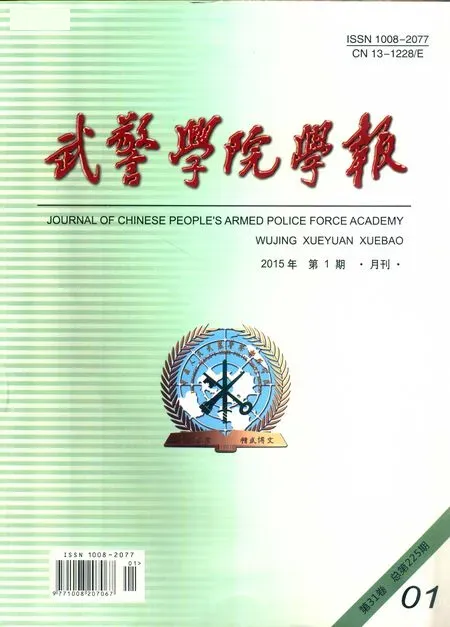论军人的权利与义务
——以军营法律文化为视角
●仲崇玲
(武警学院 基础部,河北 廊坊 065000)
论军人的权利与义务
——以军营法律文化为视角
●仲崇玲
(武警学院 基础部,河北 廊坊 065000)
军营法律文化是军营这一相对封闭的“亚社会”在长期军事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对法律所特有的思想观念、理想人格、情感倾向、行为趋势,即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价值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总和。对军营法律文化的概念,以及军营法律文化对军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进行梳理,对如何通过军营法律文化建设改善军人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探讨:打破现代法治理念与军营法律文化的隔阂,增强军人对法律的信仰;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对军营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真正重视军人权利。
军营法律文化;军人;权利;义务
2013年12月,部分战士体罚新兵的视频在网上曝光,引起舆论哗然。视频中几名班长对不听话的新兵实施所谓“惩戒”,拳打脚踢,甚至棍棒相加,其行为令人发指。几名新兵被打倒在地之后又一次次“归队”、“立正”,任由老兵施暴,毫无反抗意识,更是让人震惊。很明显,部分老兵违反条令条例殴打新兵的做法是错误的,当事人已被部队或公安机关进行了严肃处理。但新兵在暴行面前选择忍气吞声,真是让人百思不解、心痛不已。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在被施暴之后,他们没想过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为什么该事件最终是以网络视频的方式暴露在公众面前?难道军人权利的维护要靠网络舆论的大众监督才能起效吗?太多深层次的东西引发观者的疑问。笔者试从“军营法律文化”的视角出发,对军人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探讨。
一、何谓军营法律文化
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和战略研究专家马丁·范克勒韦尔德(Martin Van Creveld)在《战争的文化》(TheCultureofWar)一书中提到:“任何由人类组成的有凝聚力和纪律的群体,在共同工作一段时间后,都会形成自己的文化。……是文化维系了团体。……文化是团体的骄傲。”[1]自有军事活动以来,“军营”作为地域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直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正规的武装人员为主体,以国防和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封闭式的垂直领导关系为主线的社会实体,是武装集团赖以存在的重要社会形式。在军营当中,军人群体和军队组织在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上往往体现着一种“趋同性”,即军队成员在看待某个法律问题时,通常持有大致类似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倾向,在从事法律活动时,也通常具有大致类似的价值模式和行为倾向,这便形成了“军营”这一社会实体所特有的法律文化。
那么,这种“趋同性”是如何发生的呢?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e Kluckhohm)所说:“在一切有组织的动作中,我们可以见到人类集团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共同关联于一定范围的环境,由于他们住在共同的居处,及由于他们进行着共同的事务。他们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则或者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为明文规定,或是自动运行的。”[2]军队是奉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共同的使命、共同的居所、共同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必定衍生出共同的军人群体规范。这种规范是在军人群体活动中,被认为是合适的成员行为的一种期待,是军人群体所确立的标准化观念。它一经形成,便具有公认的强制力量,不断强化并最终形成人们的心理尺度,成为各种言行的判断标准。军营中的法律文化便是在军营法律实践过程当中自发产生并自动运行的特殊力量。它是军营之中“显性”的法律制度体系和“隐性”的法律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军营这个地域范围内的群体对于法律共同的认识、理想和信念。当然,军营中每个成员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乃至法律思想存在着一定差异,但对于整个军营来说,总有一些由于长久的历史发展沉淀下来的为大多数军队成员所接受的成分。主流的军营法律文化对于军营之中的法律行为而言,是具有极大权威性的。正如道德的权威性源于社会群体的情感认同、礼俗的权威性源于宗族观念对人们的内心约束一样,军营法律文化的权威性是内源于广大部队官兵对军事法律规范的价值认同,外化为稳定协调的军事社会关系以及纪律性、组织性、程序性极强的军事社会行为。
因此,军营法律文化是军营这一相对封闭的“亚社会”在长期军事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对法律所特有的思想观念、理想人格、情感倾向、行为趋势,即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价值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总和。它是法律文化系统中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文化现象中的特殊形态,是一种集宏观与微观、观念与制度、历史与现实、静态与动态于一体的法律文化。
二、军营法律文化对军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
有学者曾对权利与义务的数量关系作过细致的逻辑推导:“如果把不享受权利也不履行义务表示为零的话,那么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就可以表示为零起点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延伸的数轴,权利是正数,义务是负数,正数每展长一个刻度,负数也一定展长一个刻度,而正数与负数的绝对值是相等的。”[3]然而,在军营法律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之下,军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往往呈现出与普通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略有不同的特性。
(一)军营法律文化对“秩序”的尊崇,决定了军人义务的本位性
一般法律领域中,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代表了最为本质的人性需要,它位于法的价值的顶端;“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它成为自由之下制约其他价值的法律标准;而“秩序”则表现为实现自由和正义的社会状态,必须接受自由和正义标准的约束。然而,在军事法律领域中,由于军事法服务于国家最高军事利益这一重要特性,使得“秩序”的重要性与一般法律相比大有提升。也就是说,军队作为组织性和纪律性极强的社会组织,有着比普通社会更为严格的秩序追求。“秩序优先,兼顾其它”,便是军营法律文化在面临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时的重要标准。
毋庸讳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理念对军营法律文化中的“秩序”价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战争年代,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下级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有利于把千军万马置于统一的指挥和调配之下,形成巨大的战斗力,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和平时期,军队的主要行动由作战转变成遂行多样化任务,上级命令的迅速传达,有利于避免军队在新的任务环境下发生政令不通甚至各自为政的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把“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称为“军队的武德”。他强调军人的勇敢必须摆脱个人勇敢所固有的那种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地显示力量的倾向,它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守规则和方法”。*转引自军事学术杂志社:《军事漫谈》,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也就是说,只有强调服从的军队才能保证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因敌应变、井然有序;不服从指挥的军队难以构成万众一心的合力,必定破绽百出、一败涂地。
以保障“秩序”为目标,强调“服从”的社会群体,其在权利义务的关系模式中必定选择“义务本位”。军营法律文化中的“义务本位”,是指在军人的权利义务的关系中,义务更为核心更为基础,权利是附属于义务而存在的。同时,义务的强制履行在一定程度上比权利的保障更为重要。有学者将其具体表现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军事权利是围绕着军事义务进行设定的;其次,军事法对行为规则的描述不是“可以为”或者“有权为”一定的行为,而多表现为“不得为”一定的行为或“应当”、“必须”为一定的行为;再次,以军事义务的形式规定军事权利,如依法服兵役、参加军事训练、参加民兵组织等,法律都以义务的形式加以规定,虽然其本身也是一种权利;第四,军事权利和军事职权或者职责密不可分;最后,只有履行军事义务之后才能享有军事权利。[4]
反之,实行“义务本位”的社会群体,其法律文化必定呈现出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独有特性。第一,服从的意识需要严明的军纪作为保障,而军营中略显严苛的纪律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军人自由的思想。军人必须将自己紧紧地桎梏于军纪当中,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军人权利意识的形成和个人意志的表达。军人在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便很少会考虑到运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权利。第二,封闭的环境使军人习惯于听从首长的指挥,按照命令行事。另外,军人的日常活动也较为单一,除了部队的条令条例之外很少涉及到其他法律。因此,他们对法律没有天然的亲近感和依赖感,对自身的权利也没有特别的渴求。第三,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有限的法制教育活动,使军人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法律和了解法律,法律知识的匮乏使其无法形成对自身权利的理性认识。第四,由于服役的需要,军人与外界接触机会少,社会交往对象多是本部队的领导和战友。封闭的社交环境,使军人更容易受到群体的主流法律文化的影响,在尊崇秩序的法律文化背景之下,个体的权利意识往往被悄然扼杀。
(二)军营法律文化对“权力”的强调,弱化了军人对权利的认知
军队从建立之初就存在着区别于其他任何社会团体或组织所特有的管理体制。基于军事任务与军事行动的特殊性,军队需要通过不同于普通组织和团体的较为严格的内部规范对军人实施管理,从而导致军队内部上下级之间形成了绝对不平等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军队的这种严密的组织体系以及统一贯彻的指挥特性,使其被认为是“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表现的极致。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研究,科层化在组织形态上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具体而言,即通过行政机关中的最高级别开始,每一名现役军人必须服从他的上级,从而实现层层节制,确保命令统一,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效果。因此,强调科层化的“高度集中统一”是军营法律文化范畴中理解“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要准则。
高度集中统一,是指军队的领导与指挥权依靠强制力集中于一定的组织和人员统一行使。[5]具体体现为,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贯彻于军队的组织、编制、指挥、训练、管理以及装备、后勤保障等军事法律规范之中。如我军的《纪律条令》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和巩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正确实施奖惩,保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制定本条令。”第77条规定:“处分的目的在于严明纪律,教育违纪者和部队,加强集中统一,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军队作为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武装力量,需要集中行使作战指挥权,步调协调一致才能形成最强的战斗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军事斗争的需要。因此,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行为模式要求军事社会设定统一的训练、工作、交往、生活规则。同时,为了保证军事指挥权的顺畅运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行为模式还需要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
当然,现代军事社会并非中世纪欧洲或古代中国的具有森严权力等级的金字塔形群体。现代军事社会虽有明确的职务级别划分,下级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但这种职务级别划分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并以正当军事利益的实现为前提,同时以各自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划分为基础。军人上下级之间是职务隶属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下级对于上级命令的执行是以法律规定的义务为前提的,且上级下达的命令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与监督。但是,在金字塔形群体模式的影响下,仍然很容易导致部队首长或上级军官滥用军事权力,不尊重军人的独立人格,导致军事社会的失序。在其他法律领域,是这样描述“权利”与“权力”的:“权利是权力的本原,权利应该优于或高于权力;而权力应该是权利的后盾和保障。”[6]而在军营法律文化的范畴中,由于高度集中统一原则所要求的军人上下级关系科层化的存在,使得“权力”往往被置于高于“权利”的地位,对军人个体“权利”的实现有着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在此种军营法律文化的推动之下,作为下级的军人个体很难突破上级权力的束缚,在自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往往不敢鼓足勇气对抗权力、伸张正义。
(三)军营法律文化对“道德”的要求,压制了军人对权利的诉求
军营法律文化中的传统因素,是军营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心理等历史沉淀,是以往军事法律实践活动的智慧凝结,更是军营法律传统的历史文化遗留。这种历史文化遗留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惯性”力量,有着强大的传承力和渗透力,对军营法律文化的现在和将来能够产生“定向性”的重大影响。自汉武帝勒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统治者治国的根本理念与立法的指导思想,这种“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思想也贯穿于军事社会之中。一方面,传统的军营法律文化在强调“以法治军”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以礼治军”,形成“出礼而入刑”的法制方针;另一方面,传统的军营法律文化还利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伦理以及“忠义”的道德准则来培育军人的武德。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这种“以礼治军”的思想与我国现代的“以德治国”有相通之处,其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所蕴含的道德约束对于军事秩序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用高于法律的道德来要求军人在本质上是有害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L.L.Fuller)在其著作《法律的道德性》(TheMoralityofLaw)中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moralityof duty)和愿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前者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7],是人类最低且必要的道德要求;后者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7],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对军人的道德要求,应当同其他公民一样,是“义务的道德”,而非“愿望的道德”。用“愿望的道德”来要求军人履行超出法律义务范围的社会责任,最终是对军人权利的无形伤害。也就是说,在军营法律文化中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会使军人被高于法律的道德要求所“绑架”,使军人羞于主张自身权利,难以维护个人正当合法的利益诉求。最典型的表现是,在这种过分强调道德义务的军营法律文化作用之下,军人由于受到了更高的道德约束,在保护自身权益时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顾虑——要么害怕自己主张个人权利会被领导认为是思想不先进;要么害怕维护个人权利会伤害战友之间的团结关系;要么害怕自己过分计较个人得失会引起社会大众的议论,给军队抹黑——从而在无形中弱化了其对权利的正当诉求。
三、通过军营法律文化建设改善军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思考
公众对于“虐兵”事件的种种疑问,在前文“军营法律文化对军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的阐述中不解自明。现阶段,我国的军营法律文化更多的体现为对“秩序”、“权力”和“道德”的尊崇,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军人的义务本位,从而弱化了军人对权利的认知,压制了军人对权利的诉求。那些被虐的新兵或许只是简单地将班长的暴行归结为“新兵的必修课”,在暴行面前“习惯性”地选择了忍气吞声。在相对封闭的军营内,权利意识、法律观念、维权申诉这一切仿佛都离他们太遥远。瑞士军事理论家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所著的《战争艺术概论》(ArtofWar)一书中阐述道:“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财产去保卫国家的勇士们,还不如那些包税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受到尊重,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是非常可悲的!”*转引自黄隆规:《开创国防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履行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学习读本(第2卷)》,中国国防建设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这种“尊重”,既应当包括军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尊重,也应当包括社会全体成员对军人群体的尊重。因此,通过加强保障军人合法权益的法制建设,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增强现役军人自身的荣誉感和认同感,进而使其能够自觉自发地履行法律义务,是我国现阶段军营法律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打破现代法治理念与军营法律文化的隔阂,增强军人对法律的信仰
现代法治根源于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观念的人性化,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精神实质,以在社会范围内树立法律权威为价值追求,注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与个性色彩的张扬。必须承认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集体生活使军事社区中军人个体的法律意识与行为方式都与普通民众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因此,军营法律文化也必定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即在相对封闭的地域或人群范围内,努力维持自身的特性,并刻意与普通民众的现代法治理念保持距离。
但是,“军事”只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法治”则是人类以往历史业已证明的最不差的治理方式,同时也是目前世界公认的比较优越的选择。首先,军事力量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需要法治对其进行约束保障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其次,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目的可能是正义的也可能是邪恶的,当军事力量为邪恶的政治目的所把持时,其又会成为推翻政治的最终因素。“在宪政的前提下,统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法律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和运用过的,能够驾驭军事实力集团的最为有效的办法。”[8]最后,法治以其明确精炼的符号系统能够更好地适应军队快捷灵活的决策与执行机制以及复杂多变的作战指挥活动。因此,军营法律文化,作为“军营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媾和,既应当具有“军事”的自然属性,又应当具有“法律”的社会属性。在军事法中引入现代法的平等和自由价值,可以在保证公权的同时有效地保证私权,在保障军事利益的同时又能维护现役军人合法权益。
近年来,在国家和军队提供良好条件的情况下,军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例逐渐增多。自2000年以来,军地维权组织成功办理了一大批涉军维权案件。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适应新形势,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推动涉军案件的审判工作,保证绿色通道的畅通。2014年4月,中央政法委和总政治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涉军维权工作协调机制。广大部队官兵在维权行动上表现出的一系列积极行动,是其确立法律信仰的良好开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崇尚必将使军人的权益保障成为军队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对军营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真正重视军人权利
所谓法律工具主义,是一种关于法律本质和法律功能的法学世界观和法学认识论,它认为,在社会系统中,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9]当然,法律工具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法律的外形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工具,这是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然而,法律的工具功能并不能说明法律仅仅是工具,也不能就此形而上学地对法律产生工具主义的理解。我们必须承认,每一部良好的法律都应有超越工具性的内在特质。忽视这种特质,只重视法律的工具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蔑视法律、支配法律、变通法律、篡改法律的工具主义思想与惯性作为,这将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带来无可避免的伤害。
遗憾的是,目前仍有一些军事法学者宣扬军事法是围绕军事所展开的,军事活动的极端性决定了其必须要遵循战争的逻辑,即对军事胜利以及军事上占据优势地位无条件的服从。而法的价值必须服从这种逻辑,只能作为次要价值而存在。[10]他们这样论述道:“法学与军事学在军事法这一共同体中更多的体现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不是目的与目的的冲突与调和的关系,即军事法学是借用法学的理论来规范军事行为的一门社会科学。”[10]在此种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极容易衍生出过分的权利限制以及不受约束的权力运行模式。
在我国,实现依法治军首先需要的就是“法律至上”的信念支撑。惟其如此,才能形成与“依习惯治军”、“依权力治军”和“依个人意志治军”相抗衡的力量。尽管法律工具主义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由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和对法律的错误认识,在基层执法和部队管理当中,仍有许多领导干部仅仅将“依法治军”理解为通过纪律约束与治理下级,认为“依法治军”就是“依法治理士兵”。这种片面理解恰恰走向了“法治”的反面,造成“以权代法”、“以土政策代法”、“以言代法”的泛滥。因此,必须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依法治军是一种治军方略,它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条件,以军事司法公正为基本要求,以军事权力制约和军事权利维护为内在机制,旨在树立法律至上权威,以确保军事权力顺利运行和军人权利实现的制度构架及其合理运作的理想状态。[11]依法治军应当重在治理军事权的运行模式,其重点在于监督各级领导的权力行使,维护基层军人的合法利益。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依法治军,才能摒弃法律工具主义的不良影响,真正实现对军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在军营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做到:第一,增强官兵的主人翁意识。进行军营法律文化宣传时,必须使广大官兵认识到自己是法律信仰培育过程中的主人翁,调动其积极性,使其自觉参与到法律信仰的培育活动中。第二,尊重官兵的创造精神。广大官兵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军营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把培育法律信仰搞活,需要依靠官兵的创造精神,挖掘官兵的巨大潜力。第三,重视官兵的切身利益。在军营法律文化建设实践中,必须掌握官兵的思想动态,了解其实际困难,倾听其法律需求,让官兵通过法律切实使自身权益得到保障。
[1] [以]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M].李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39.
[2] [美]克鲁克洪.文化与个人[M].高佳,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5.
[3] 徐显明.公民权利和义务通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65.
[4] 秦前红.论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规定[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8.
[5] 张山新.军事法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31.
[6] 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9-10.
[7]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52.
[8] 肖泽晟.宪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70.
[9] 谢晖.法律工具主义评析[C]//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编委会.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法学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146.
[10] 赵会平.军事法的价值构成及其对立统一——军事法学价值取向的基础分析[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6):50.
[11] 宋新立.依法治军论[M].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3:6.
(本栏责任编辑、校对 刘彦超)
On Soldiers’ Rights and Obligations—In Perspective of Legal Culture in Army Camps
ZHONG Chong-ling
(BasicCoursesTeachingDepartment,TheArmedPoliceAcademy,Langfang,HebeiProvince065000,China)
The legal culture in army camps, including all unique legal factors such as ideas, ideal personality, emotional tendency and behavior tendency, which is gradually developed through long period military practices in the relatively closed sub-society, the army camps.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sum of value and behavior mode about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 abuse of the soldier in Wuhai demonstrated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in our legal culture in army camps. Therefore, the barriers between the modern law idea and the legal culture in army camps should be broken down to prevent bad influences of legal instrumentalism on legal culture in army camps, to balance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soldiers, to enhance soldiers’ faith in law.
legal culture in army camps; soldiers; rights; obligations
2014-12-20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宪法视角下我国军人权利保护制度研究”(SZ131006)阶段性成果;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军营法律文化建设机制研究”(201303398)阶段性成果
仲崇玲(1978— ),女,黑龙江肇东人,讲师。
●部队建设研究
E266
A
1008-2077(2015)01-008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