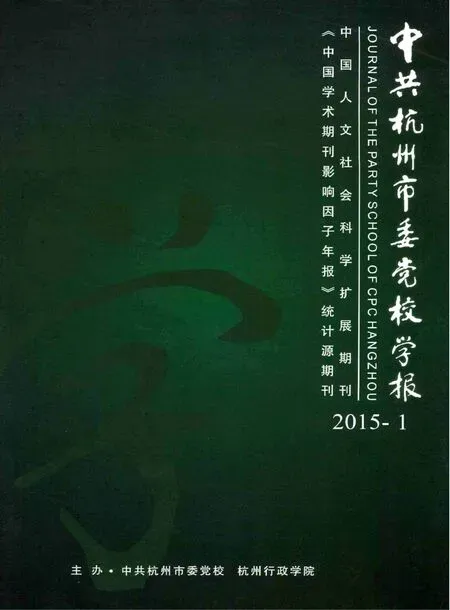理解中国:人民共和国政治的逻辑与演变
□ 孙培军
一、问题的提出:理解历史—社会—文化中的“中国”
理解中国及其政治,特别是对1949年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必须放到历史与现实的情境下细细考量,即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情境下审视。[1]通俗地讲,理解这种历史—社会—文化情境,就可以简要地从时间、性质和字面上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
首先,从时间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其政治的形成和转型就已开始。有学者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由反映它的首要特征和目标的不同模式来代表:一个是从1949-1957年的苏联影响时期和模式,中共在此期间在公认的苏联影响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从1958-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时期,全部努力都是按照毛泽东所规定的革命目标重新为中国政治导向;还有一个是从1976年至今的新时期和模式。[2](P21)本文对于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不做详细讨论。1949年至1978年这近30年的中国历史是人民共和国政治得以形成、演变乃至转型的历史坐标,清理和反思这段历史的成败得失经验对1978年后的中国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从性质归属上,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权体制模式可以分为集权主义或共产主义模式、发展中国家模式、中国模式三类。[2](PP13-20)不过,以政权(党和国家)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来看,中国更接近于中国模式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的复合体,如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政党、或是激进的或是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上述这些特征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政治在性质归属上的与众不同之处。
最后,从字面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分为三个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要素各指代的含义是什么?三者合一又意味着什么?与先前的中华民国的区别何在?具体地讲,“中华”意味着中华民族,体现了民族性,这是自反满清以来的自然体现;“人民”体现了国家政权性,“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名词,表明国家政权是掌握在人民手里的,这在国家的性质上是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言而喻了;“共和国”指民主共和国,这是新中国采取的政体形式(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践),是区别于传统专制统治的政体,是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的。与“中华民国”相比,关键的区别在于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新中国是在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情况下建立的,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成为国家的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的性质和形式上区别于传统封建的、专制的国家,又区别于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突出了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人民共和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路径都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进行的。
二、人民共和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形成与特点
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实质性意义就是:国家获得独立,国家权力回到人民手中,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掌握来自人民的国家权力,并由此开始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和努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和现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诞生。国家主权的独立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最为根本的政治基础。“最重要的,乃是全国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该政府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策的权威……恰恰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真正彻底地决裂了。”[3](P409)所以说,一个单一而且有权威的主体力量,即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建立是1949年以来中国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整合的首要条件,这也是共和国政治形成与演变的历史与现实前提。
(一)共和国政治的形成:革命路径[4]
一般地,通过革命掌握国家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也是依据这个政治逻辑进行革命实践的。通过政治革命,在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历史任务;通过社会革命,告别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农业文明,而且超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可靠的现实基础,包括稳固的政权、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组织化的社会以及有效的党的领导。[5](PP106-107)这种“革命政治”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自然选择,也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共和国政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必然体现。
1949年后人民共和国政治,或许可以成为“后革命政治”,譬如毛泽东时代的大众动员参与、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等表现形式。尽管这与大规模战争性的暴力不同,但却在指导思想和某些做法上保留着革命色彩,如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中的阶级斗争、打砸抢、反右、整风等政治和社会运动,这种革命逻辑的延续使得“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将许多差别转变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武装力量的使用或恫吓在政治过程中就成了核心的问题。正如在1911-1949年间的全过程所表明的那样。1949-1958年间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作用的减弱是革命政治衰落的一个具体迹象。自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作用的提升——先是象征性的,然后是一种威慑力量,直到最终形成与其他组织的政治团体相对抗的阵势——同样是革命复活的一个具体例证。”[2](PP2-3)可以说,这种“后革命政治”在1978年后的中国政治中仍然在某些层面遗留着,在诸多领域存在的运动式治理政党、国家和社会,这些就是典型表现。
(二)共和国政治的特点:制度、价值和组织
共和国政治的制度、价值和组织是在历史留给共和国的遗产、共和国的政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的政策)和苏联模式等国际因素影响下,即国情、党情和世情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详细地讲:制度架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它是以人民民主为精神核心,以中国社会的历史与国情为现实基础,以宪法为保障,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有机结合。[5](P219)人民共和国政治是以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也是以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本质规定性作为价值基础。这些价值既来自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来自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包括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规定性。[5](PP256-257)在组织体系上,中国共产党作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式的政党(思想、组织等)充当了制度和价值两者的桥梁,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将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融合在自身的组织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和价值也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这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的革命时代背景和任务下获得的主导地位。[6]这些制度、组织和价值的设置理念和具体架构,体现着前文所述关于历史—社会—文化情境下的“中国”概念,更是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进行的国家建设的路径下形成的政党国家的具体体现,党、国家和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三位一体”,这些特点随着历史—社会—文化的演进,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为共和国政治必须转型的内容和形式。
三、人民共和国政治的演变:革命后社会的秩序与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政治形态转型有两次:1949-1956年,由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对应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到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政治,1949年建立新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将中国带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这个过程中努力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1978-1992年,由与计划经济相对应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政治。[5]本文阐述的共和国政治的演变在时段上集中在1949 至1978年的这段时期,尽管这种演变在关键点上转型为新形态,如前文所述的新民民主主义政治到社会主义政治,但这里所讲的转型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相反,演变路径往往是有反复、重叠或连续的,这体现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在不同年代的政策和思想也不是一以贯之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政策和主张的初衷和实效在1949—1976年中是错综复杂的。
从革命到革命后的转型期,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的现实任务就是如何利用国家政权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赖以存在的所有制关系以及相应的经济基础。为此,掌握国家政权并使其发挥有效作用,必然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7]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一定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但恰恰相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践层面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权(作为生产关系一部分的政治上层建筑)反而充当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即通过政权建设和现代化(生产力的必然体现)的同一来发展中国,以社会主义取代现代化。这样的发展逻辑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所以,在中国,政治统一与社会发展,或者说政治和经济,在地位、序列上都颠倒过来了,即思想政治工作是统帅,是大局,是生命线等,在许多时候,秩序、统一压倒了发展,代替了发展,政治成为考量发展的唯一标准。概言之,政治统一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体现为社会主义与政治现代化,中国的发展逻辑是用价值推动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主导乃至代替了政治现代化。
进一步而论,政治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个方面。结合共和国政治得以形成的革命路径及在制度、组织和价值方面的特点,1949—1978年这段时期的中国政治发展体现在动员参与、民主法治和党建国家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人民共和国政治演变乃至转型的内容。首先,在政治—社会成长和发展的革命逻辑下,通过各种运动进行动员参与,更有甚者动员参与超过了政治制度化,这在文革中的“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中彰显卓然。分析这种动员参与背后的原因,可以发现:动员与组织是同时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大众动员式政党。当然革命有其历史必然,党治国家推动了革命式现代化,但其后来发生了病变,革命式现代化必须转向市场式现代化。[8]这种政党主导的动员式参与一方面与公民自主式参与相悖,仅仅是一种革命热情的理想主义表现,缺乏公民参与的理性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参与也没有被制度化,领袖崇拜和人治色彩浓厚,缺乏制度化的参与途径。易言之,这种动员参与仅仅是政党进行自身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工具,即经年累月、反复无常的各种运动。尽管在特殊时期取得过特殊的实效,但常态社会下的参与扭曲和缺失必然不利于公民生活、国家治理的健康开展。
其次,在民主法治方面,随着1954年《宪法》及其他一些党和国家法律的颁布及制度的实行,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和法治状况得到改善。不过在建国后的30年间,作为民主和法治体现的党和国家制度化的理论规定和实践效果在整体上出现了偏差,诸如领袖崇拜、党政不分、人治色彩等,在文革时期更是荡然无存。从理论上来看,亨廷顿将其放到政治制度化的范畴里考量,据此提出了政治制度化的标准包括四个方面,即适应性—刻板性;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不团结。[4](PP16-19)参考这四个方面的标准,依次看来:在第一方面,这时的各项制度刚刚建立,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离制度本意的偏差;在第二个方面,各项党、国家和社会的法律、法规及民主实践虽然在纸面上得到了保障,但鉴于前文所述的革命逻辑和党治国家的路径,特别是在这段处于摸索的历史时期,许多方面要么无法可依,要么有法不依,国家的重心在于求得艰难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生存,制度化的复杂程度显然不够;在第三个方面,从自主性-从属性来看,自主性意味着政治制度化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而国家制度完全出于党、行于党,谈何自主性;从第四个方面内聚力-不团结来看,组织的团结与否决定着内聚力的强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上,强调组织和纪律,民主集中制体现得尤为鲜明,但权力斗争也曾一度祸起萧墙。自主性和内聚力不是必然两者兼备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内聚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制度的自主性带来的危害,但在1958-1976年间,其弊端也暴露无遗。
再次,党建国家的逻辑,体现在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多层关系上。党通过国家政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很快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权力结构形态。这是与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党通过组织和整合建立的党的权力组织网络使得党权一元化(体现在党政关系、党军关系、政府间关系等方面),而国家或政府吞食了社会,进而党控制了国家和社会。[9]“虽然现代政治生活是现代政党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前提,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党则往往是构建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在许多国家,政党的纲领、组织、社会基础以及行动方式,直接决定着现代政治生活构建的成败以及现代政治生活的具体形态。”[10](PP7-8)但是,这样便形成了如下格局:政党建设国家、政党建设社会。罗兹曼指出,“根据日本和俄国历史所提出的先例,我们的观点是,现代化的后起之秀必须既要善于利用不寻常的集中手段;又要善于利用各个层次上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平衡。”[3](P443)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紧密的地方控制和巨大的城乡差距,这三条总是和现代化后起之秀的国家形影不离。但是,中国一直以来在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向地方主义妥协……整个70年代中央政府一直比较软弱。”[3](P449)因此,这种国家建设的党治国家路径,有其具体的理由、形态与限度。[11]从主体、结构和发展的三维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后中国的必然唯一主体,其自身的思想、作风,尤其是组织建设深深地影响乃至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兴衰。因为,在党、国家和社会的结构下,党和国家的制度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制度架构及其实践成效都体现着政党的主导力量。[12]总之,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党的发展战略、策略和政策,党的执政与发展能力决定着国家、社会的发展和治理状况,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之处。
四、结语与讨论:如何处理统一与发展的关系
历史和现实地看,人民共和国政治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建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依托的,这体现在以革命为发展逻辑和以制度、组织和价值等要素为内容的共和国政治,以及在动员参与、民主法治、党建国家等方面的演变。因此,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是国家得以发展、社会得以繁荣的关键所在,这体现在党内的统一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这在1949—1976年这段历史时期尤为明显。党要创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所以,中国共产党要解决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等问题,这是维护统一的责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努力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政治上,党和国家都要努力做到统一和团结,体现在制度上的国家形式是联合政府,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和纪律及国家和政府的行政区划和部门设置,以及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上,则要强调组织化和社会整合,如各个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抗日、爱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经济上则是计划经济,统一规划;文化上,诸如意识形态、整风、文革等自不待言。这种关于统一的认识是自古就有的,费正清认为,战国时期的混战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一旦统一实现了,就建立官僚政府加以维护。政府因有全国统一的象征——皇帝,而顺利行使其职能,因有全国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合法化。政府又是意识形态的保护者……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可被视为另一个统一的“朝代”。他们拥有“帝王”式的主席、“帝王”式的政府和“帝王”式的意识形态。[13]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所在,如何处理好这个连续性事关1949年以来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与失败。
总之,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历史表明,无论是封建国家、帝国、中华民国还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它们都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反映了传统王朝的治乱兴衰、现代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属于统一与发展的关系。尽管处理这对关系的方法不同,有变法改革、有叛乱起义、还有激进革命,但这在中国政治中一直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特别是随着现代政治中政党的出现,政党和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关系变得紧密。相对应地,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下,要理解中国特别是人民共和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路径,必须认识到:在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逻辑下,统一与发展的关系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国家与社会三者权力关系上,三者权力范围划分在根本上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即党的集权和分权。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建设中,关于党集权和分权的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都印证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发展路径的独特性,必须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在发展的战略、策略、政策上都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即是政治学家所关注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的问题,而不稳定的最突出事例大都发生于现代化初期或遭遇挫折的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决定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乃至发展。在近代中国及后续的1949—1978年这段时期,中国恰恰是在这两种情况的双重影响下建设现代国家的,更需审慎地做到统一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1]王沪宁.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4).
[2][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林尚立.走向现代国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解读[A].林尚立等编.政治与人[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A].陈明明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 辑)[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9]林尚立.集权与分权: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变化[A].陈明明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 辑)[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10][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A].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复旦政治学评论第7 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2]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13]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A].剑桥中国史(第14 卷)[M];后记:统一的重任[A].剑桥中国史(第15 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006.12 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