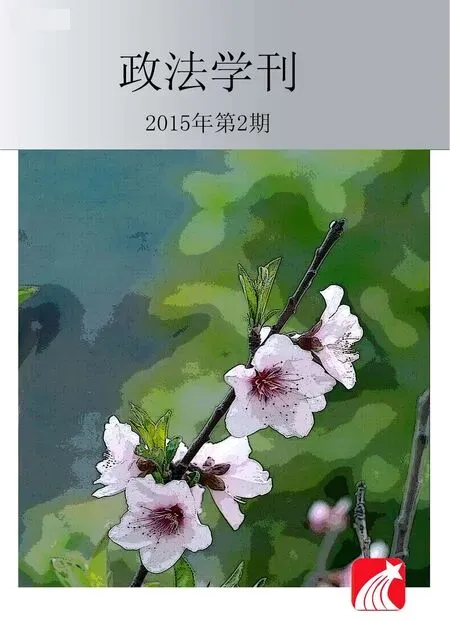消极保险利益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论一种非以法律责任为保险标的的消极保险利益
李伟群,夏明轲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消极保险利益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论一种非以法律责任为保险标的的消极保险利益
李伟群,夏明轲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长期以来,学界在论及消极保险利益时,往往仅将其与“法律责任”相联系,从而容易使人产生消极保险利益即“责任利益”的误判。然而,通过对Technical Land, Inc. v. Firemen's Ins. Co.案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实际生活中还存在一种不涉及法律责任,而是以当事人因事实强制而对有关责任的负担为标的的消极保险利益。如果在分析了保险利益的一般原理之后,通过论证除“法律强制”之外,消极保险利益中的“强制”被证明还包括了“事实强制”,那么一种全新的消极保险利益理论框架就可以建立起来,并且在这样的新框架下,医疗费用保险可以被证明是一种保障消极保险利益的财产保险,由此解决了长期以来医疗保险是人身保险,抑或又具财产保险之困惑。
消极保险利益;负担;事实强制;医疗保险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可以根据性质不同划分为积极保险利益与消极保险利益。依照关系说,保险利益乃被保险人与特定对象之间的利害关系。[1]56因此消极保险利益可被定义为,被保险人与某种“不利”之间的利害关系。当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会因该利害关系之存在而承受“不利”,进而发生财产上之损失。[2]107从目前学界通说来看,前述定义中的“不利”之内涵,除了“法律责任”之外似乎别无他物。然而通过对有关案例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消极保险利益存在的情形其实不限于此。因此,为了厘清概念,完善保险利益理论,应对现实问题,有必要对消极保险利益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二、通说中的消极保险利益
国内学者在讨论消极保险利益时,大多只将其与法律责任相联系展开论述。其中,有部分学者直接断言“消极财产的保险利益,指债务不履行所生债务或侵权行为所生债务之不利益。”[3]55或者“消极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原无积极利益,仅在危险事故发生时,有对他人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不利益,主要包括因责任不履行所生之责任,以及因侵权行为所生之责任两类不利益。”[4]64
另外一部分学者没有明确提出消极保险利益的概念,而以“责任利益”的概念取而代之。如认为,“财产保险利益可以归类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现有利益、因保险标的现有利益而产生的期待利益、责任利益三类。责任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承担的合同上的责任、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其他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5]93又如,“从性质上看,财产保险利益包括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三类。责任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违约或侵权行为而对第三人应负担的赔偿责任所具有的利益。”[6]49可以看出,此“责任利益”中的“责任”,实际上也是指“法律责任”。
以上这些见解,可以称之为我国现在的通说。笔者认为,通说受到美国保险法理论的影响较大。按照美国理论,保险利益存在与否的判断标准有二,即法定利益标准与实质性期待标准。对于前者,法院通常只承认三种严格的法定利益可以构成保险利益,即财产权利、合同权利,还有法律责任。[7]54而对于后者的“实质性期待”,法院则定得并不严苛,体现了相对的灵活性。
所谓实质性期待,指的是“被保险人对被保险财产续存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期待,或者反过来说,对被保险财产灭时会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期待。即便没有法定利益,这类期待也会存在;而且,在许多法官和学者看来,这种期待本身便足以构成保险利益”。[8]117由此可见,实质性期待标准逻辑上涵盖了除法定利益以外的一切可能构成保险利益的情形,实际上为不涉及法律责任的消极保险利益的深入挖掘和研究预留了必要的空间。
不过,由于实质性期待标准极具抽象性,无法像法定利益标准那样确定具体的内容,因而如果不对个案中出现的保险利益的形态作理论抽象、归纳的话,则很难与消极保险利益概念发生联系,因此,学者们在讨论消极保险利益时就难免只看到“法律责任”的身影,造成管中窥豹的局面。但事实上,消极保险利益的内涵远不限于此。下面,笔者拟通过对一个经典案例分析,就消极保险利益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三、对Technical Land, Inc. v. Firemen's Ins. Co.案 [9]的批判性分析
Technical Land, Inc. v. Firemen's Ins. Co.案本身是被当做法官运用实质性期待标准,通过确认投保人的期待利益与被投保财产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构造投保人对特定财产所具有的保险利益的经典判例。但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笔者发现,实际上本案法官并未对相关保险标的做出正确判断,因而造成了对保险利益性质的认识错误。事实上,本案真正的保险标的不应该是被投保的财产本身,而应当是投保人因期待利益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对特定财产保全的“事实负担”。这种“事实负担”为投保人带来的是一种消极保险利益,并且该消极保险利益的性质不是法律责任,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必需。
(一)基本案情介绍
1991年12月11日,合伙企业“Techniarts Engineering”(以下简称TE公司)起诉“1631 Kalorama”协会并胜诉,获得了金额为131,055.13美元的判决。次年9月30日,TE公司根据有关文件(a Marshal's Deed)取得了该组织位于科罗拉马路1631号的建筑的所有权,并依据该文件于12月10日将该建筑的所有权人替换为本案原告兼上诉人“Technical Land公司”(以下简称TL公司)。
1993年12月10,TL公司为前述建筑购买了财产保险,保险人即为被告兼被上诉人“Firemen's Insurance”公司,而TL公司是该保单上唯一署名的被保险人。同年4月1日,“1631 Kalorama”协会的债权人以TL公司为对象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质疑TL公司凭以获得相关财产权的文件的有效性。在TL公司申请破产之后,有关事项的审理被转移至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破产法庭。
1994年2月25日,虽然针对TL公司取得相关财产权的文件的合法性的审理仍悬而未决,“Techniarts Video International”公司(以下简称TV公司)向包含前述科罗拉马路1631号建筑在内的破产财团的托管人提议签署使用协议。为了使财产的价值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尽管该项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归属尚存争议,破产法庭于1994年3月16日批准了该项协议。
于是,根据协议托管人对建筑享有独占的控制权,其中包括出卖的权利。同时,TV公司享有使用该建筑内所有空间的权利,但作为对价,该建筑的维护、修缮、营运费用全部由TV公司承担。而直到相关所有权争议得到解决,该建筑将作为电影及电视节目制作设施使用。至于TL公司,其另外获得TV公司符合前述使用协议规定的许可(无合同的事实许可),占有使用该建筑,直到1995年8月TV公司与托管人之间的协议失效。
1994年2月28日,TL公司搬入位于科罗拉马路1631号的建筑后,立刻发现该建筑因水管爆裂遭到严重损害,便迅速联系保险人提出理赔。在与理算员会面之后,TL公司对建筑进行了紧急维修,共花费125,515.94美元。根据TL公司方的证言,由于当时公司已与MTV公司签订合同,预计将于1994年4月20日在该建筑内对克林顿总统进行电视采访,为避免违约,这笔维修花费是必要的。
同年6月1日,破产法庭宣布将所有权转移给TL公司的文件无效。
同年6月20日,第二次事故发生,由于空调系统水管阀门的爆裂,刚被修好的部分再次受损。而在接到第二次事故的通知后,保险人以TL公司对投保财产缺乏保险利益为由撤销了保险合同,并向TL公司退还了保费。随即TL公司以“违反保险合同约定,怠于及时补偿被保险人损失”为由,将保险人Firemen's Insurance告上法庭。
(二)两审法院意见
如果按照法定利益标准分析,投保人TL公司对位于科罗拉马路1631号的建筑并不享有财产权利、合同权利、法律责任这三种可以构成保险利益的标志中的任一项。
从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投保人对建筑的所有权因相关文件被判决无效而遭否定。投保人对此判决亦无异议,只是提出“对财产所享有的保险利益并不以有效的法定产权为决定性因素”。①需要补充的是,二审法院认为,由于上诉人并未主张“由于保单签发时有关所有权转移的文件未被判决无效,投保人基于善意合理相信自己拥有所有权因而享有保险利益”,所以二审法庭不会作这个角度的解释,于是回避了事后无效(after-the-fact invalidity)对保险利益的影响的问题。从合同权利的角度来看,有关标的物占有使用的协议的当事人是TV公司与破产财团托管人。投保人虽然获得使用许可,但依照协议,承担维护、修缮、营运费用的仍是TV公司,因此投保人仅凭占有使用事实不足以证明对财产本身的保险利益。而至于其他法律责任,更是无从说起。
但是实际上,即使是判决投保人败诉的一审法院,也并非严格依据法定利益标准。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破产法庭宣告了有关所有权转让的文件无效,但仅凭该事由并不能必然得出投保人对被投保财产无保险利益的结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投保人TL公司对被投保财产本身是否具有任何经济利益。诚然,“TL公司会因为无法使用遭到损坏的被投保财产而承受收入损失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TL公司所签订的保单所承保的对象是位于科罗拉马路1631号的建筑,不是公司将来的收入或者其在水灾中受损设备。而TL公司除了已被宣告无效的所有权转移文件之外,再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对该建筑本身存在任何经济利害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判定TL公司对被投保的建筑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
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存在对保险标的的认识错误。虽然它承认被投保财产的损毁与投保人的收入损失之间存在联系,但一审法院是将建筑因毁损无法使用这一事实,理解为以“收入”为保险标的的前提下的保险事故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投保人投保的标的是“建筑”不是“收入”,故无法证明对“建筑”存在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然而,二审法院却是将财产损毁与收入损失的关系反过来利用,认为正因为投保人对将来收入的期待(包括对避免违约的期待),被投保财产的保全、存续对投保人就具有了实质性的经济意义,然后以此来构造投保人对建筑本身的保险利益。
二审法院指出,依据判例法所确立的原则,“只有当投保人与被投保的标的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联系,使投保人可以因标的物的保全而获得金钱上的(pecuniary)利益或优势,或者因标的物的毁损而遭受金钱上的损失或损害时”[10],才能被判定保险利益的存在。同时法院也明确说明,“虽然TL公司能因(TV公司与‘1631 Kalorama’协会签订的)使用协议而受益,即事实上得以使用位于科罗拉马路1631号的建筑,但是光凭占有并不足以构成一项保险利益(occupancy alone is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an insurable interest )。”[11]因此,为了证明对建筑本身的保险利益的存在,TL公司需要向法庭展示,其因水管爆裂事故对被投保标的物(即该幢建筑本身)的损坏,将直接遭受财产上的损失。
二审法院参考由俄亥俄州上诉法院审理的Asmaro v. Jefferson Ins. Co.案[12]的判决,认为“使用人的经济损失与特定财产的特定属性(the unique traits of a particular property)密切联系这一事实,可以构成一种基本的保险利益”。而初审时的证据表明,位于科罗拉马路1631号的建筑内的工作室在整个华盛顿市区内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由于水管爆裂事故会导致该工作室无法使用,而投保人又无法再找到另一间拥有同样设备器材的工作室以及时履行自己节目制作的合同义务。因此,具有独特属性(unique traits)的被投保财产的损坏必然会对投保人造成财产损失。据此,二审法院认定,TL公司对位于科罗拉马路1631号的建筑本身享有保险利益。
(三)真正的保险标的——事实负担
二审法院判决的积极之处在于,它认识到了投保人对将来收入的期待,会使其在建筑(而非将来收入)之上产生新的独立的保险利益。但按照现代保险法理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在特定财产之上,可以因保险标的的不同而同时存在不同的保险利益。比如,特定物上,可以同时存在着以所有权、物上的抵押权或者合同产生的使用权等等为标的的多种截然不同的保险利益,并且不会被认定为重复保险或超额保险 。①2013年6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1条明确。可是,本案中投保人TL公司因期待利益是在建筑之上产生的新的保险利益,其保险标的为何,并非一目了然。
根据判决,二审法院是将这种新的保险利益的标的认定为建筑本身。理论上,由于“积极保险利益为一特定之人对某一特定积极财产或积极肯定有利之经济地位之关系”[2]86,而建筑是一种积极财产,故此时TL公司拥有的应是一项积极保险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积极保险利益之所以被称为“积极”,在于其强调“投保人在保险标的上享有的固有利益,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保有,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丧失”[13]42。换言之,积极保险利益的内容,就是投保人在保险标的上享有的固有利益。那么,本案中TL公司对建筑本身享有怎样的固有利益呢?显然,TL公司并不拥有任何法定的权利或承担法定的责任;而单凭事实上的占有与使用,也“并不足以构成一项保险利益”,继而无法确认其固有利益。然而,二审法院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即把特定财产的特殊属性以及对未来收入的合理期待,与对财产的占有、使用事实联系起来,进而将特定条件下的(不再是“单凭”)占有、使用的事实,确定为了投保人对财产所具有的固有利益。
但是,这种创造性见地也会直面一个新的问题。正如二审法院所援引的判例法原则所述:“只有当投保人与被投保的标的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联系,使投保人可以因标的物的保全而获得金钱上的(pecuniary)利益或优势,或者因标的物的毁损而遭受金钱上的损失或损害时,才能被判定保险利益的存在”;同样,根据传统保险法理论,“保险利益需为可以货币衡量的利益”[13]40。那么,二审法院所认定的,投保人因特定条件下的占有、使用事实而对建筑本身享有的保险利益,能够以货币衡量吗?为此,以下有必要展开一定的分析。
首先,当建筑保有时,投保人是不会因该建筑获得任何直接“金钱上的利益或优势”的。虽然其合理期待的未来收入与建筑存在密切联系,但联系仅仅是联系,该未来收入并非建筑本身直接产生的,因为建筑本身不会自动产生电影、电视节目制作的服务合同。其次,当建筑受损时,投保人也并没有承受由此带来的“直接金钱损失”。这里的直接金钱损失是指,例如所有权人因所有之物毁损所受之金钱(财产)损失,或者抵押权人因抵押权无法行使所受之金钱损失等等。
事实上,投保人只不过是因对未来收入的期待以及建筑的特定属性,在事故发生时不得不负担起维护、修缮建筑的职责,并因此发生金钱支出。换言之,期待利益、建筑物属性等前提条件为TL公司在建筑上形成的,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固有利益,而是一个消极的事实负担。具体地来讲,本案中虽然TL公司对于相关建筑的维护是没有任何法定、约定的责任的。但由于该建筑(工作室)所具有的特定属性,以及对利用该建筑制作电影、电视节目获得收入的期待,事实上使作为直接使用者的TL公司不得不负担起维护、修缮的责任。
在此不妨换个角度,我们来考察一下需要由主体承担法定责任时的情形。即当某事件发生后(该事件可能涉及当事人的主动行为,如侵权;也可能不涉及,如雇主责任的情形),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被强制要求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显而易见,这种需要由主体承担法定责任的情形,与前述TL公司不得不负担维护修缮责任的情形,在逻辑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迫使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原因一个是法律强制力,一个是经济利益刺激。而这两种原因,站在行为指引的角度来看,均属于外部刺激 ,体现的是主体的趋利避害,并没有本质区别。毋宁说,经济利益刺激的引导效果更胜于法律强制力。
众所周知,为分散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责任保险制度才得以产生。责任保险的功能在于“赔偿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因法律之规定而对他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时所产生之损害”。[2]108又“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之一种。惟其保险之标的,既非人身,亦非有形之动产或不动产,而是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负之赔偿责任”。[1]204
类推可得,本案中TL公司真正应该投保的,其实是一种以分散对非因法律规定、合同约定,而是由于实现经济利益的必要性而承受的事实负担的风险为目的的保险。这种保险的标的,在本案中,并非位于科罗拉马路1631号的建筑本身(与一审法院的观点契合),而是投保人对维护、修缮职责的事实上的负担。在这种“事实负担保险”中,投保人的保险利益是他与该事实负担之间的利害关系。由于这种事实负担是一种“不利”,因此按照本文文首所作的定义,这种保险利益就是一种不涉及法律责任的消极保险利益。
三、消极保险利益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一)保险利益作用的一般原理
根据保险法理论,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是避免赌博,其二是防范道德风险。[14]4那么保险利益是如何实现这两个目的的呢?按照定义,保险利益指的是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一种经济利害关系,而由于保险标的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必然会遭受某种损失,因此保险利益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投保人与特定损失之间的联系。换言之,保险利益确定了损失将由投保人承担(或者说风险由投保人承担)。于是,在存在保险利益的情况下,投保行为真正具有了分散未来损失(风险)的经济保障意义,因而区别于单纯的赌博行为;同时,正因为该损失被确定将由投保人承担,因此当可以获得的保险金金额小于或等于这个保险利益本身的经济价值(即损失)时,投保人便不大可能会去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换言之,道德风险得以避免。至此不难看出,确定投保人将承担损失,实际上是保险利益发挥作用的关键。那么,这种对损失承担的确定,在消极保险利益这种具体的保险利益类型中是如何实现的呢?
(二)消极保险利益中的损失承担
先来考察积极保险利益的情形。此时,保险标的为具有固有利益的积极财产,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固有利益无法实现,损失便会产生。而对于投保人来说,存在积极保险利益,意味着他的身份是积极财产所体现的那些被法律认可的权利的享有者。于是,自己享有的权利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当然应由权利人自己承担。从保险利益作用原理的角度来看,也就是积极保险利益确定了损失将由投保人承担,符合前文所述。因此我们可以确信,积极保险利益能够实现避免赌博、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
那么,消极保险利益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此时,保险标的变成了“不利益”,表现为对外给付金钱的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不利益”,与保险事故所生直接损失尚有不同。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保险事故的发生的确会造成某些损失,但在消极保险利益的情形下,该损失并非由投保人本身直接承受,而是由第三人充当了实际受害者,如交强险中的交通事故受害人、雇主责任险中的雇员等等。但对于投保人来说,存在消极保险利益,就意味着他与保险标的“不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害关系,换言之,投保人将不得不承担某种对外给付金钱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所针对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前述保险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于是,从保险利益作用原理的角度来看,消极保险利益实际上是将保险事故造成的他人损失,转化为了应由投保人承担的责任,最终也就确保了损失由投保人承担。
但是问题是这种转化是如何得以完成的?实际上,转化的机制在于,某种“强制”的存在迫使投保人在事故发生时不得不去负担受害人的损失。
(三)对消极保险利益中的“强制”的拓展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目前通说仅仅将消极保险利益与法律责任相联系,换言之,损失转化被认为仅能通过法律强制完成。具体地讲,对于传统的责任保险而言,投保人与作为保险标的的法律责任之间的利害关系(即消极保险利益本身),表现为法律规定所带来的强制力迫使具有某种身份的投保人在特定事故发生时必须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正是由于这种法律强制的存在,事故直接对他人造成的损失被转化成了需要由投保人承担的损失(法律责任),于是满足了保险利益作用原理的关键条件。因此,法律强制可以说是责任保险中使消极保险利益发挥作用的关键。
但是,正如前文对Technical Land, Inc. v. Firemen's Ins. Co.案的分析所显示的,在实际生活中,即使并不存在法律强制(即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的相关赔偿责任),当事人还是可能会因为某些事实因素而不得不去承担他人的直接损失。具体而言,投保人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愿意为他人所受损害“买单”,乃是因为存在效果与法律强制相类似的“事实强制”。所谓“事实强制”,笔者将其定义为由于经济利益的合理期待、特定财产的特殊属性以及特定人身关系等等,会对当事人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的存在,致使当事人在事故发生时不得不为有关损害“负责”的情形。而此种事实强制迫使当事人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就是该情形下的保险标的,作为与法律强制下的法律责任相对的概念,笔者称之为“事实负担”。
于是,在存在事实强制的情形下,投保人与事实负担之间同样也建立起了类似于法律强制所生的利害关系。正如在Technical Land案中,虽然TL公司对于相关建筑的维护是没有任何法定、约定的责任,但由于该建筑(工作室)所具有的特定属性,以及对利用该建筑制作电影、电视节目获得收入的期待,事实上使作为直接使用者的TL公司不得不负担起维护、修缮的责任。总而言之,事实强制也能够将事故直接受害者的损失转化为由投保人承担的损失(事实负担),从而保证了此种消极保险利益(由事实强制所生)能够像在责任保险中的(由法律强制所生)那样,实现避免赌博、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
(四)“强制”在医疗费用保险性质分析中的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扩展了消极保险利益中的“强制”概念之后,我们对某些传统保险性质的认识也将得到更新。下面,笔者将以医疗费用保险为例展开分析。
医疗费用保险,是指以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行为的发生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为被保险人接受诊疗期间的医疗费用支出提供保障的保险[15]。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医疗费用保险同时具有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是一种非传统的“中间性保险”[16]。据此,该险种方能纳入损害补偿原则及其超额保险、重复保险、保险代位权等诸项衍生规则的约束范围内[17]。但是,假如我们从消极保险利益的视角来考虑,似乎能得到一个更方便的结论。
具体而言,正如前文对消极保险利益中的损失承担的分析一样,在医疗费用保险的情形下,直接承受事故所生伤害(损失)的不是投保人,而是第三人 。但是,由于投保人与受害人之间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因此投保人将受到一种不得不去承担相关医疗费用支出的“强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由特定人身关系所产生的“强制”,既可能是法律强制,如亲属法中对家庭成员之间救助义务的规定;也可能是事实强制,即亲情伦理、良心道德的强大作用。但总而言之,基于此种强制,投保人不得不成为医疗费用支出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亦即与医疗费用支出责任产生利害关系,继而证明了一种消极保险利益的存在。并且,该消极保险利益能够确定受害人的直接损失转化为了投保人承担的损失,因而可以实现保险利益避免赌博、防止道德风险的功能。换言之,医疗费用保险,是一种保障消极保险利益的保险,其真正的保险标的,应该是投保人基于事实强制而对医疗费用支出的事实负担(当然,也可能是在法律强制下产生的救助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费用保险实际上是一种以投保人因特定人身关系而存在的对医疗费用的事实负担为保险标的的财产保险,因此,其当然适用损害补偿原则。
(五)消极保险利益理论新框架的总结
至此,我们可以对消极保险利益的相关问题做一个总结,并对原有的理论框架做出修正与扩展:
首先,从定义上看,与积极保险利益以各种有形、无形“财产”为标的相对,消极保险利益乃是以投保人因不同的强制所生的各种“负担”为标的的保险利益。从保险利益关系说的角度来定义的话,消极保险利益系指投保人与作为保险标的的“负担”之间,因某种强制的存在而产生的利害关系。这里之所以使用“负担”而不是“责任”,首先是因为“负担”一词在法学中本身表达了一种最广义的“承担某种义务”的内涵,如民法上的“负担行为”。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使用“负担”一词避免了让人产生一种消极保险利益的保险标的仅限于“法律责任”的误解,而同时将基于事实强制所产生的“事实负担”纳入进来。
其次,从内容上看,与积极保险利益以财产的固有利益为内容相对立,消极保险利益以负担的“不利益”为内容。这种“不利益”具体表现为承担由某种强制转化而来的他人损失。
再次,从类型上看,消极保险利益因“负担”产生的强制原因不同基本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基于法律强制产生的以“法律责任”为保险标的的消极保险利益;另一种则是基于事实强制产生的以“事实负担”为保险标的的消极保险利益。而根据具体的法律责任、事实负担的不同,消极保险利益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细更特定的类型。
当然,以上结论只是对消极保险利益理论框架的一种很基础、粗浅的重构,尚有许多细节问题值得我们去进一步仔细挖掘和研究。
五、结语
正如一切科学研究、工程建设都需要发达的数学理论作支撑一样,保险法制建设这一重要的社会工程,同样需要完善的保险法基础理论来指导。消极保险利益的相关理论,一直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对其认识也不够深刻,因此才会出现对现实存在的消极保险利益视而不见的情形。
综上所述,在认定消极保险利益时,我们不能仅局限于“以法律为准绳”这一点,而应该认识到,某些非法定的事实情况也会给当事人造成不亚于法律强制的事实强制。但无论是法律的强制还是事实的强制,都会使当事人与事故发生后的相关责任——负担——产生密切的利害关系,继而形成以该负担为标的的消极保险利益。
[1]梁宇贤.保险法新论[M].北京: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4.
[2]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樊启荣.保险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马宁.保险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5]覃有土,樊启荣.保险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任自力.保险法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7]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M]. 梁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8]小罗伯特·H. 杰瑞,道格拉斯·R. 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M].李之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Technical Land, Inc. v. Firemen's Ins. Co. , 756 A. 2d 439 (D.C. 2000).
[10] See, Lumbermens Mutual Ins. Co. v. Edmister, 412 F.2d at 353 (8th Cir.1969).
[11]See, Boston Ins. Co. v. Beckett, 91 Idaho 220, 419 P.2d 475, 479 (1966).
[12]See, Asmaro v. Jefferson Ins. Co., 62 Ohio App.3d 110, 574 N.E.2d 1118 (1980).
[13]韩长印.保险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14]杨芳.可保利益效力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5]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2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6年第8号[Z].2006-08-07.
[16]温世扬.中间性保险及其私法规制[J].北方法学,2013,(3).
[17]姚军,刘金玉.医疗费用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问题的探讨[J].科技与法律,2013,(2).
责任编辑:韩 静
The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of the Negative Insurable Interest Theory-On a kind of Negative Insurable Interest without the Legal Liability as the Insurance Object
Li Wei-qun Xia Ming-k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For a long time, when talking about the negative insurable interest, scholars often simply associate it with the concept of "legal liability" and it is easy to make us wonder if the negative insurable interest is equal to the "liability interest". Bu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Technical Land, Inc. v. Firemen's Ins. Co.", we can find that there is a new type of negative insurable interest which doesn't involve the legal liability but takes the burden of the relevant liabilities imposed by factual compelling force as the insurance subject. Therefore, after figuring out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s of the insurable interest and proving that besides the "legal compelling force", a "factual compelling force" can be found in the system of the "compelling force" of the negative insurable interest, a brand new system of the negative insurable interest theory can be set up.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is new theory, the medical fee insurance can be proved as a kind of property insurance involving a negative insurable interest. Thus, the puzzle that whether the medical fee insurance is a kind of personal insurance or property insurance can be finally solved.
negative insurable interest; burden; factual compelling force; medical insurance
2014-12-22
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法学)建设计划(经济法学科);2012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上海市特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研究一从保险视角探索巨灾风险转移的思路及对策》(IZZS155)
李伟群(1963-),男,上海人,华东政法学保险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法学博士,从事保险法研究;夏明轲,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D922.284
A
1009-3745(2015)02-007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