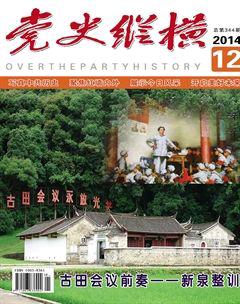改造康泽
葛美荣
康泽(1904-1967),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国民党特务系统大头目。在蒋介石统治集团中,康泽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深受蒋介石倚重,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
康泽是中华复兴社(中统和军统的前身)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名字就是他取的;康泽又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二人为刘健群、陈立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由他起的。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康泽仿效德国党卫队,成立了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别动队成立后,康泽在江西建立“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意在争取青年,断绝苏区兵源,消灭共产党。康泽的别动队对苏区的危害很大,曾杀害过不少共产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
1948年1月,康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防襄樊。虽是黄埔军校毕业,但他一直搞政工工作,根本不会指挥打仗。1948年7月初,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军区主力等部队发起襄樊战役。很快,康泽战败并被俘。
康泽被俘后,被解放军押送到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有一个收容所,专门看管和教育国民党被俘军官,也称第二野战军解放军官训练班。
在训练班里,康泽常常是一言不发,因为他的心情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中。他认为,这次失败有多种原因,责任不在自己。同时他一直在想,自已的被俘,没能“与城共存亡”,不知是否意味着对蒋介石的“不忠”。最让他担心的还是他的妻儿老小,他不知道蒋介石会怎样处置他们?
国民党的新闻媒体宣布康泽在襄樊作战中殉国后,中共新华社针对谣言,发表了“康泽就擒记”,公布了事情的真相。最初,康泽的妻子朱素怀不明真相,不知丈夫究竟是生是死,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人,哭诉他的丈夫为“党国牺牲”了。这在国民党上层掀起轩然大波,弄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蒋介石只得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马上给她送去金元券10万元,又答应为康泽召开追悼会。朱素怀这才稳定下来。
康泽还有一点担心,就是不知共产党会如何处置他。他知道自己对共产党犯下的罪恶太大了,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共产党能饶恕自己吗?对这个问题,他心里没有底,所以无心吃饭,也难以成眠。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在监狱里,他的伙食比看管人员还好;那些看管人员不拿薪水,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为他疗伤;审讯时也非他想象的那种严刑逼供,而是态度和蔼,令他不知所措。
同时,康泽在解放区看到的是,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官兵一致,深受老百姓爱戴。以前,他自以为对解放军十分了解,认为他们是”顽民“,是“洪水猛兽”,可是一经接触,才发现他们是那么善良、朴实,不像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了,为什么装备优良的国军会败在装备低劣的解放军手下。他感到,共产党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一两个人的魅力,而在于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的魅力。他决定再次研究共产党,于是向管理人员提出要看《资本论》、《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书。管理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
除了学习外,最吸引康泽的是新华社的新闻和《人民日报》,因为那里有国共交战的最新战况和南京方面的间接消息。在他被押解去解放区的途中,无意中听到广播里说国民党要为“以身殉国”的他开追悼会,急得他团团转,担心家中80多岁的老母经不起这致命的打击。为让老母亲知道自己还活着,他请求解放军允许他写封“现在解放区”的平安家信,托人送回四川老家去。新华社的广播成了他了解南京方面动态的重要途径。而当听到国军战场每况愈下,屡屡失败后,他开始有所反省。
1948年9月下旬,在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人谈话时,康泽说了下面这些话:
国民党是一个黑暗的封建的统治集团,丧失了三民主义的精神与原则,丧失了革命的理想,奖励贪污……说国民党不好怪下面,不怪蒋介石,这种论调现在已成过去。
蒋介石是地域主义、家族主义,信任浙江人,重用家庭,一切都是由蒋决定的,自然主要是他的责任。陈仪讲得好:“我们党的政策在哪里?政策在主席的脸上”。是的,大家一切都要看蒋的脸色行事。
蒋好用权术,制造矛盾,掌握矛盾,使部下各树一帜,互相牵制。今天的分崩离析一半也是他自已造成的……
从莫斯科回国算起,我为国民党工作20年,我为三青团工作7年,现在想来一切都是白费。现在我做了俘虏到解放区来,很惭愧,但将更加强我重新检讨重新认识的决心。
1948年底,康泽开始写“自省录”。在“自省录”里,康泽回忆,早年安岳家中每逢冬春青黄不接时,全家老小以无油无盐的青菜干萝卜叶为饭,最小的弟弟吃了这样的饭后,一滩一滩地口吐清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苦苦支撑,白天干活,夜晚纺纱;父亲为凑钱供他读书,四处奔走借得5元钱,此后贫病交加一病不起。年关更难熬,兄弟姐妹几个围在母亲和纺车周围望着别人家过年,还要面对要账的债主的欺辱。康泽谴责自已:“应当站在穷人的立场为穷人服务,使穷人翻身,而不应当跳到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阵营里,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服务,使穷者愈穷!”“自省录”是他人生第一次认真的反省,也是他转变认识的开始。
1949年5月初,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全体被俘国民党军官转押到北京功德林监狱。
到功德林后,康泽面对管理人员体贴入微的照顾,心平气和的说服,思想变化更大了。一次,黄维犯痔疮流血过多,手纸不够用,就拆开自费买来且已读完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本苏联名著,用作手纸以当急需。这在当时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同组人立即批评他“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黄维不服,与小组长争吵起来,说他这是废物利用,既已看完了,就可以发挥第二次作用。小组长请管理人员来解决“争端”。管理员不仅没有批评黄维,反而说出了一串极富人性味的话:黄维犯痔疮,应该要求多发手纸,他没有提出来,是他的不对,但是我没有发现,是我的失职。大家不要因为黄维处理得不恰当而同样也作出不恰当的结论。一场争端就这样平息了。
还有一次,康泽同前来功德林调查有关材料的人员发生口角,事后心中很是不安,担心会来一次疾风暴雨式的批评。然而令他不解却又十分感动的是,管理处领导在组长碰头会上宣布:今后接触调查材料的人,态度尽量好一些,对有些动辄拍桌子、打板凳者,可以不予理睬。又要人家讲,又要骂人家,真是岂有此理!今天康泽与外调人员吵架,责任不在他身上,他不用检讨。
1952年12月,康泽长达十多万字的反思性交待材料“我的再清算”完稿,其中对自己为国民党政权效忠的反共生涯进行了系统回顾。但由于他担心政府清算他的罪行,所以有关他的一些重大罪恶,他避重就轻、一带而过。比如对皖南事变后他充任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在重庆五云山、江西上饶等地均建立关押共产党员、新四军被俘人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尤其是江西上饶集中营残酷迫害和大批枪杀被关押者的罪恶行径轻描淡写。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重申共产党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他指出:“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毛主席这一段话决定了康泽的后半生命运。
在关押期间,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过功德林。他们带来了新的信息,党和政府希望这批人学习好,身体好,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今后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律妥善安排工作,愿意去台湾、海外的,政府也予以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改造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组织战犯参观学习。1957年,管理人员组织战犯去武汉等地参观。参观后康泽无限感慨!昔日国民党统治时期,城市、农村到处都奄奄一息,人民见了国民党官员,就像见到猛虎饿狼一样。今天的国家,到处井然有序,生机勃勃,工人农民情绪高涨,齐心建设。康泽对共产党又有了新的认识。
回到功德林,康泽对复兴社同僚“老大哥”曾扩情说:谁愿意吹捧共产党,为共产党说话呀,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
1959年9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战犯的消息。功德林简直像炸开了锅,一片沸腾。就连康泽这样谨小慎微,三天不说两句话的人,也一反常态,跟着欢呼。
1959年10月1日,中央安排战犯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让他们登上了观礼台。这次活动,使他们感受到一种庄严、一种震撼,回到功德林后还难以压住内心的激动。在学习委员会的组织下,他们向毛泽东主席表达了自已的心愿:
敬爱的毛主席:
在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到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的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利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已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敬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
1959年12月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首席法官郑重宣布,杜聿明等10名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这次特赦会,大多数人都大失所望。原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谁知只特赦了10个,战犯们普遍有不满情绪。
但康泽并没怎样发牢骚,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改造的行列里,他并不是个先进者。让他感到失落的是,接下来的两批特赦还是没有他。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名单公布时,他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但这次他听到了自已的名字,当时内心一阵激动。他走上台去,当接过那张16开的“特赦通知书”时,难以在他脸上见到的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他极力控制才使它不至滚落出来。
特赦后,康泽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先后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经历》等一系列以他亲身经历的事件为依据的回忆录。
出狱后的康泽深深地感到:共产党是宽宏的,也是伟大的,她能以她博大的胸怀包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难以容忍的昔日政敌,又能以她独有的魅力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他们改造成为全新的人。
康泽与妻子自从1948年南京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出狱后,他的儿子曾来大陆看望过他,他很高兴。“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受到冲击,红卫兵曾打伤过他一次。随后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秦城监狱,以监护的形式把他保护起来。1967年,康泽旧病复发,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