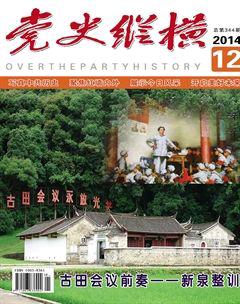毛泽东与王明迥异的利益着眼点
张家康
成长经历的不同
毛泽东长王明11岁,两人虽然都出身农家,可却有着不一样的父亲。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勤劳节俭的农民,靠着克勤克俭,使得毛家在小小的韶山冲算得上不大不小的财东。他对儿子没有过高的奢望,理想是儿子识字记账,再学会打官司就行了。因此,少年毛泽东被父亲当作“长工”一样使唤,因为读书,不知被父亲痛骂过多少次。在与父亲的争执中,他变得极为敏感且具叛逆个性。
王明原名陈绍禹,父亲陈聘之是读书人,私塾先生。毛泽东6岁就干农活,王明5岁则随父亲读书。与毛泽东9岁入私塾读书相比,王明早了4年。而更重要的是,有父母的期待和支持,王明的读书求学,根本用不着像毛泽东防范父亲那样小心翼翼。少年王明是个乖巧聪明的孩子,一手工整娟秀的楷书,每逢腊月,小小年纪的他都要给街坊邻居写春联,凡教过他的先生没有不欣赏他的。
生活在农村的少年毛泽东,天天和农民在一起,与农民有着最为亲近的情感联系,常常为他们的遭遇抱不平。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荒,粮价飞涨,民不聊生。饥民们去官府请愿,非但没有得到安抚,反而遭到镇压。消息传到韶山,毛泽东十分痛心,对官府的行径极为愤怒,几十年后还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而王明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他基本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在远离实际的私塾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入湘乡,进长沙,闯北京,纷繁多变的外部世界给予他极大的感官和精神冲击。他信过康有为、梁启超,信过孙中山,最后信过陈独秀,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政治有着一种莫名的冲动,这在他的《民众的大联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文章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种社会的担当,这种历史的责任,这种年青人一往无前的霸气,已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在他参与发起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中,他已成为风云人物,报刊上频频出现他的姓名,社会各界已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他。此时的他还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920年夏,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相会,陈独秀所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话,使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不久,陈独秀相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创建共产党,毛泽东成为湖南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6岁那年,王明考入设在六安县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钱杏村也即阿英是他的国文教员。1924年夏,王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到处都洋溢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热情,他亦为潮流所激荡,成为商大的积极分子。正是在商大,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和政治信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谓之“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耳目为之一新,思想为之一变。”1925年10月,王明在商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王明等60余人,由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
很快,王明被中大副校长米夫看中。米夫比王明大3岁,是个少年得志的布尔什维克,教授列宁主义课程,主要宣讲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他不重实际,讲课时很少理论联系实际,一味从概念到概念,一堂课下来,不知讲了多少政治术语。而这,正中喜欢死记硬背的王明的下怀。在课堂上,他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就这样引起米夫的重视和青睐。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与其由海参葳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期间,王明除充当翻译角色外,还帮助米夫作一些具体的工作。当时,共产国际六大通过了一个纲领,其中的精髓是:“保卫苏联已成为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王明多少也有些倚洋人而自重,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宋侃夫说:“王明这时活动多,到处讲话,做报告。”内容多与保卫苏联有关。
同时,王明还在《向导》发表文章,阐发共产国际纲领,提出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他把当时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看作是“武装进攻的第一个信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值得革命的中国民众注意;因为它直接关联着世界革命的命运。”这个“武装进攻苏联”,一直困扰着他,他为此而担惊受怕,为此而呕心沥血,这是他政治崛起的起始点和立脚点。
中央地位的升降
1927年的中国政坛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五大在广州召开,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列席会议,毛泽东则是会议的正式代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再强调农民运动、土地政纲等,王明对此应有印象和记忆。
毛泽东正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从长沙启程分赴宁乡等十余县考察党务,实际是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他看到,昔日被人欺的“泥腿子”,如今在乡村也挺直了腰杆说话,农民运动正以“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几乎一边倒的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责难声中,毛泽东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大声高呼农民运动“好得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其中,南昌起义为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帜。在运筹秋收暴动时,毛泽东响亮地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毛泽东成功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斗争。
会后王明回到莫斯科,正值中山大学内所谓“党务派”和“教务派”斗争激烈之时,王明看准机会向米夫献计,先争取超然于两派以外的力量,然后再向“党务派”靠拢,以此挫败“教务派”,进而控制“党务派”。王明的计策果然得逞,米夫当上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自此更视王明为难得人才,据曾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回忆:“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的‘无冠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
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无障碍地进行宗派活动,拉帮结派,罗织罪名,排除异己。有人对王明等行径的描述可谓深刻透彻:“他们这些人,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张口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不用翻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仗着能说会道,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王明,作风很不正派,善于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他又以此为资本,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
王明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完成学业毕业后成了米夫的忠实帮手,为了在中山大学脱颖而出,更因受苏共党内斗争的影响,制造了好几起冤案,后来又把矛头直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指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威信的瞿秋白、俞秀松等,以此显示自己更加布尔什维克。难怪中山大学的“多数同志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王明还写了多篇文章,鼓吹城市暴动,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中国大暴动”和“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即将实现。文章的理论基础和语言风格完全苏俄化。一个以苏俄模式为样板的中共未来领导人,已经在苏联产生了。1929年3月王明奉命回国,在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中,他借批判陈独秀之机,又把苏联摆到高于中国的位置,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他奉苏联为世界革命的圣地,称保卫苏联就是保卫世界革命,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保卫了本国的革命。
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包办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压制不同意见,硬是扶持王明上台,使王明一步一层天,由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再成为政治局常务,从而实际掌握中共中央实权达4年之久。而正是此时,毛泽东“运交华盖”,一直受临时中央局的排挤,先是宁都会议解除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继而开展实际针对他的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三十多年后毛泽东与外国朋友谈起这段经历时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统一战线的分歧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战线。根据这个精神,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在巴黎的《救国报》发表,后通称《八一宣言》。这是他在抗战中最为炫目的亮点,他也常常以此炫耀。而此时,他又由对国民党全面排斥改为一切服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
与此相反,毛泽东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用心,即将红军大批地开赴华北前线,借助日军的精锐消灭红军。所以,毛泽东一再坚持红军是“独立自主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正是在洛川会议后,王明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之命回国。行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特意接见了王明,让他作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回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之所以派王明回国,是担心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会得罪蒋介石,从而失去苏联的东面屏障,招致两面夹击。说穿了,斯大林担心苏联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威胁。
到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便急切地提议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声称所传达的都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系统地批评了洛川会议的方针,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些明显与洛川会议相左的意见,使与会者犯起迷惑。可是,由于王明手握“尚方宝剑”,大多数与会者都对他的意见采取了赞同的态度。彭德怀就感到为难起来,“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因此他自己也糊涂了,“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更使彭德怀感到困难的是,会议结束后如何传达贯彻。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在传达贯彻时,说“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是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高级指挥员如彭德怀都如此困惑,更甭说其他指战员了。而十二月会议所造成的后果,也正如彭德怀所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虽然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占了上风,可会议毕竟没有形成决议。所以,到了武汉后,王明未经中央允许,便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抗战路线的区别,并在中共中央已经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新的六大纲领,鼓吹“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蒋介石看到了王明的“价值”,更赏识他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讲话。当王明还在延安时,蒋介石就希望王明“来(武)汉相助”,共同商量解决两党关系的问题。在国民党一片“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鼓噪声中,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却附和这种声音,指出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
毛泽东看到了王明的问题,在决定王明是否还去武汉时,明确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上,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中央也作了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决定,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且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姗姗回到延安。而他自己也直言“不愿留在延安工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总得要受之约束。他在武汉可以避开延安,况且他的共产国际身份,在此可以充分展现其能量。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指示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此文。但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刊登。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理睬,就是不同意刊登,至于为什么,王明直到晚年才透露其心机:“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尽量忍让,却使王明产生错觉,以为他的钦差大臣地位本该如此,更是将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都是不请示汇报,先斩后奏,客观上已与中央闹起独立。这些被早已赋闲的共产国际前代表李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和很多人都已把长江局称作“第二政治局”,并说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连张国焘也说王明“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1938年7、8月间,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指示肯定朱、毛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大命题。
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为会议再作结论报告。他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六中全会对王明采取了温和式的批评。毛泽东根据王明“完全同意各报告”的态度,指出:“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王明则口服心不服,对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一直持抵触的情绪。他的“完全同意”,其实是敷衍过关,他仍然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
对美关系的分歧
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改变了对美方针,有着与美国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的良好期待。美国也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场上的突出作用,开始重视对中共的工作。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将之称为中共“外交的工作开始”。他亲自为《解放日报》修改社论,称美军观察组为“战友们”,指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大兴奋的一件大事”。他希望美军观察组的工作“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我们刚一到延安,毛泽东就在一天夜晚的联欢会上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当然,你们也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后来,在枣园,毛泽东曾与我进行过长谈。他直率地向我谈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中共的政策,解释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并展望了战后形势的发展。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为了进行中国的建设,确实希望同美国进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
这些信息很快便传至美国白宫。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谈,协调国共关系。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应赫尔利的请求,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但王明对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说毛泽东走得太远了,已经背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他在《中共五十年》中对此有如下叙述:
1944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约翰·谢伟思谈话时说,“我们不等待俄国的援助……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合作”。当时他甚至对美国记者格·福尔曼说,“我们并不追求苏维埃俄国那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宁肯这样认为: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林肯在国内革命时期为之奋斗的事情,这就是解放奴隶……”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宣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他肯定,“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胜利,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观点。
王明还说,在国共内战爆发时,毛泽东就“幻想由美国迫使蒋介石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有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参加的‘联合政府”;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不向美军开一枪一炮。政治上他沿袭‘门户开放的策略以期同美国合作。”朝鲜战争时,毛泽东犹豫一当中国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出兵后,当得知杜鲁门严禁麦克阿瑟下令轰炸中国东北时,毛泽东又懊悔中国不该出兵,寻求尽快地“结束战争”,以“逐步恢复中美友谊”。
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个“亲美狂”。为进一步论证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他甚至说:“1964年和1965年白宫先后把斯诺、李宗仁派往中国与毛泽东密切接触。”并说:“不言而喻,毛泽东和斯诺这样的老朋友无疑反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如何开展等问题,尽管斯诺没有写过与此有关的报道。”
毛泽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和远见卓识,基于坚定的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王明则带着有色眼镜,固守一成不变的东西方冷战思维,甚至憧憬着“使中国返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凡是与之相违,则都是“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王明所不能容忍的。这也难怪,因为在他70年的生命里,竟有最为关键的30年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思维乃至语言都与苏联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