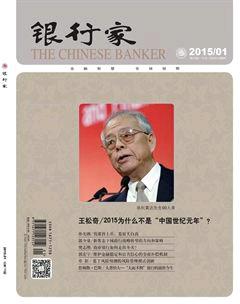金秋十月忆征程 (1)


编者按:2014年10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成立60周年。60年繁荣的背后,是建设银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土到“洋”的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个大行崛起甲子华诞之年,本刊推出一部60回的章回体“微小说”。
作者刘仁刚自1982年加入建行,至今已有32年从业经历,见证了建设银行从专业银行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从作者的言语与表达中,足以看出一名老员工对建设银行的赤诚和感恩之心。
而作者经历的这30余年同样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30年,作者在见证建行历史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本刊将分12期(每期5回)来推出这部“微小说”,让我们一同来品读一下建设银行以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发展纪实。
作者的话:
我们度过的一朝一夕,我们经历的一点一滴,我们发生的一事一幕,我们留下的一印一辙,组成了我们的历史;
这部历史没有粉饰,但生动感人;
这部历史看似平淡,但足够辉煌
第一回
刘姥姥,入驻神圣三里河 新市民,不解婉约南沙沟
话说1982年2月11日,春节刚过。我怀揣高校毕业生统分派遣单来到了北京三里河。一排排五十年代苏式建筑,门前高高悬挂的国字头牌号的高楼深院,荷枪实弹的哨兵,这一切告诉我三里河,牛!后来听说,中央部委集中在北京的二(二里沟),三(三里河),六(六铺炕),八(八里庄),尤以三里河为甚,20多个国家部委办局集于此地。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一机部,二机部,五机部,国统局,国税局,还有同在财政部楼内的建设银行总行。27岁的我,经过风雨,但没见过世面,尤其从一个知青经历了四年大学历练,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三里河的主人了?看着财政部蓝色工作证和刻有国徽的单位印章,总是透着一股神圣和神秘。南沙沟在三里河西端,紧靠钓鱼台国宾馆,它是当时的部长楼,在那个年代,这一栋栋不高但很考究的成排建筑一看就有些与众不同。原本就神秘的三里河,再加上更加神秘的南沙沟,就更令外人望而生畏了。三里河,一条看似很普通的街道,正在延续着它的神圣和庄严。不知是不是我这“刘姥姥”真的进了大观园,当时内心感受就是莫名的自豪。当然,我们这些小青年,也着实虚荣了好一阵子。
第二回
住单身,八人一室像校园 识新友,广州"老乡"名侯康
上回书说到,本人只身来京报到。其实我们同来总行的有20来人,辽财14人,湖财不到10位。因为新入行人数较多,所以行里特地与不远处的京沪食品商店联系,我们就住在7层。八人一室,上下铺,与学校一样的感觉,配了两个大号热水瓶,一个落地电风扇。还有一位老大妈作为管理员。京沪食品商店在当时绝对属于高大上层级的,一层专卖桂香村稻香村茯苓饼等北京名特食品,二层专卖上海食品,标志性的大白兔奶糖在其他商店很难买到。每逢上下班,楼道里充斥着诱人的糕点糖果的香味,有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进去闻闻香味。
侯康是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分到总行外事处当翻译。小我几岁的他一口地道的白话,但却长着一张地道的无法改变的北方脸。一问才知父母是沈阳,地道老乡。这层关系让我们接触多了些,对他的关注和了解也自然多了些。过年回家他总是带些广州人自制的油炸饺让我们分享。他同来自海南的另一位同学一样,三九天也提个水桶冲凉,那意志品质至今难忘。由于他的空姐女友出了意外,对他刺激很大。不久他就离开了。现在他定居在所罗门群岛,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但我心中一直印刻着这个广州老乡的轮廓,他是侯康。
第三回
罗道庄,办公场所像工地 养鸡场,总行机关全搬出
随着业务发展,总行内设机构也有了大规模扩张。特别是以中长期投资为主线的部门真的成了体系。投资一部,投资二部,投资调查部,建筑经济部,投资研究所,投资咨询公司等部门,兵强马壮,社会影响很大。财政部已经没有合适的空间满足总行办公了。出去我们认为是必然,但搬到罗道庄谁也没想到。罗道庄是北京量具刃具厂的一块空地,典型的临时工棚,夏不透风冬不保暖,办公用的是集团电话,一部话机铃声响起,其他人都可以接听,不管对方找谁,接错撂下就是了。罗道庄当时有个简易的食堂,在食堂旁边还有一副乒乓球台,有时中午休息大家还能活动活动。当时不仅办公用房十分简易,连道路都还是刮风就冒烟的土路,说句心里话,那条件真的与建行的地位不大相符,但大家都很乐呵,见面都很热情。程瑞华在投资研究所,陈勇鹏在投资调查部,前者现在是金融时报的首席记者,后者在厦门分行办公室,是著名摄影家和书法家。
大约过了一年多,建行的其他部门也都迁出了,但不是罗道庄,而是沙窝西,大致现在五棵松篮球馆的位置。这个时段是建行办公最分散的时期,大约七个地方,虽然很难见面,但当时民风淳朴加上人不多,所以彼此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第四回
守计划,六亲不认黑包拯 把口子,严守职能像审计
守计划,把口子,是建行的职能,也是建行的特色。深深记得刚刚入行时老同志经常讲的一句话,任何人找到建设银行说情要钱,回答“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四按”拨款原则更是耳熟能详,那就是“按计划、按预算、按程序、按进度”拨款,如果当时工程建设要是“逆程序”或“计划外”,那简直不可思议,所谓中央通报的违反财经纪律的事例基本上都与“四按”有关。说那时建行具有双重职能那是不准确的,就是单一财政职能。那时对上定期报《建设银行情况反映》,报到党中央国务院,对下定期发《建设银行简报》,对象是各级分支机构。那时要是有一篇情况反映是哪个人撰写,真的好像出了一部工具书,大伙儿会很羡慕的。情况反映,就是坚持原则,就是公开披露,就是向上“告状”。现在想想,像财政,更像审计,建行如果延续当时的职能,现在恐怕不少监管部门都不复存在了。
南京分行有个张杰,当年经办栖霞山化肥厂,这是一家国家重点工程。他对工程的一块砖瓦一分一毫都十分清楚,甚至单位库存还有多少都心知肚明。中央领导视察该厂都由他做讲解,厂党委破例让他列席党委会。当时建行系统北京分行的李厚峰,上海分行的沈纯二、湖南分行的李子祜都是全国劳动模范,名气很大。
第五回
南长街,建行领得参观票 社会路,红塔礼堂看大片
那时的建设银行名义上是银行,实质就是政府职能单位,它所享受的政治待遇一样不少。就拿参观中南海来说,中办每个月给国家部委发一定数量的票,固定时间,固定入口,一票一人,主要满足各部委招待本系统出差人员需求。当然,单位也要承担一定风险,每次发票都要反复叮嘱,一再强调。不知何故,这个待遇前后没持续多长时间就取消了,好在我有幸去了两次。
红塔礼堂似乎就是内部片的代名词,定期内部电影是我们当年享受的“特权”,过完周末,周一上班时常听到有的年轻人谈起他们到红塔礼堂看了什么影片,片子是什么情节。当然,我们这些年轻人主要精力是放在工作上,早来晚走那是常事,每天除了工作,要早上主动打开水,擦桌子,工间操那么短时间也只有打康乐棋等简易娱乐活动,老同志坚持的“拱猪”“钓鱼”似乎都要自己固定的牌友,年轻人也上不了台面。记得有天去化工部走访,回来晚了,食堂只剩下了冷却了的馒头,还有一块煮熟了的"猪肝",害得我这不吃羊肉的人,一不小心冷口吃了口羊肝。我当时饥饿难耐,吃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就问食堂卖饭窗口的同志:这肝是什么肝啊?对方回答:羊肝。我说:那小黑板上怎么只写了一个“肝”字啊?对方又说:羊肝不是肝吗?我无语。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机构业务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