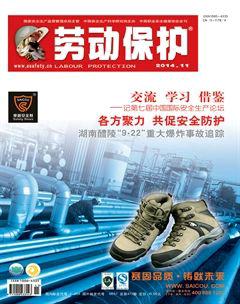工伤保险行政纠纷典型案例解读(下)
黄乐平+徐建军
判例三:何培祥诉江苏省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基本案情
原告何培祥系江苏省新沂市原北沟镇石涧小学教师,2006年12月22日上午,原告被石涧小学安排到新沂城西小学听课,中午在新沂市区就餐。因石涧小学及原告居住地到城西小学无直达公交车,原告采取骑摩托车、坐公交车、步行相结合方式往返。当日15时40分左右,石涧小学职工邢汉民、何继强、周恩宇等开车经过石涧村大陈庄水泥路时,发现何培祥骑摩托车摔倒在距离石涧小学约二三百米的水泥路旁,随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治疗。12月27日,原告所在单位就何培祥的此次伤害事故向被告江苏省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因故撤回。2007年6月,原告就此次事故伤害直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历了二次工伤认定、二次复议、二次诉讼后,被告于2009年12月26日作出《职工工伤认定》,认定:何培祥所受机动车事故伤害虽发生在上下班的合理路线上,但不是在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不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向新沂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之后,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裁判结果
经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一审,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是两种相互联系的认定,属于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事故伤害情形的必不可少的时空概念,不应割裂开来。结合本案,何培祥在上午听课及中午就餐结束后返校的途中骑摩托车摔伤,其返校上班目的明确,应认定为合理时间。故判决撤销被告新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职工工伤认定》;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就何培祥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
专家解读
关于上下班途中发生通勤事故受伤认定为工伤的规定,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也经历了多次的变动,核心在于如何理解“上下班途中”。
1996年实施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属于工伤。该规定将“上下班途中”限定为“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且限于机动车事故。从法规的规定来看,采取的是较为严格、保守的立法思路。这一规定导致在实务当中如何认定是否属于“必经路线”,以及起点至终点如何起算为“必经路线”产生了诸多的困难。
由于《试行办法》的规定在实务操作中引起诸多争议,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在《试行办法》的基础上,对于通勤事故导致的工伤在立法上作出了较大的调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大大拓宽了工伤认定的范围,体现在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删除了“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对“上下班途中”不再作时间与路线的限制;二是对机动车事故伤害不再限于“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只要发生机动车事故伤害即使本人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也可以认定为工伤。从这一规定来看,《工伤保险条例》大大放宽了对于“上下班途中”的理解,加大了保护劳动者工伤权益的力度。
2010年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沿袭了原版的立法思路,没有对“上下班途中”作范围限定,但对于通勤事故的类型作出了限制,即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
从立法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工伤保险立法理念的变化,进一步确立了保护劳动者权益、兼顾公平的核心原则。本案的处理,体现了司法对于立法原则的准确把握,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法原意。本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上下班途中”作出的规定,总结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争议性问题,对法规理解的误区进行明确,有利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促进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案虽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在裁判理由方面也并非无懈可击。何培祥在上午听课及中午就餐结束后返校的途中骑摩托车摔伤,固然可以认定为返校上班,是基于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内发生的工伤。对何培祥上午外出听课及返校上班的事实认定,如果认定为“因工外出”似乎更为恰当,倘能如此,那么判决认定为工伤的理由就要简单得多。
判例四:邹政贤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基本案情
宏达豪纺织公司系经依法核准登记设立的企业法人,其住所位于被告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辖区内。邓尚艳与宏达豪纺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06年4月24日,邓尚艳在宏达豪纺织公司擅自增设的经营场所内,操作机器时左手中指被机器压伤,经医院诊断为“左中指中节闭合性骨折、软组织挫伤、仲腱断裂”。2006年7月28日,邓尚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列“宏达豪纺织厂”(而不是“宏达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被告以“宏达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邓尚艳后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最终确认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宏达豪纺织公司”。2008年1月16日,邓尚艳以宏达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1月28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邓尚艳于2006年4月24日所受到的伤害为工伤。2008年3月24日,宏达豪纺织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邹政贤作为原宏达豪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09年3月10日收到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后不服,向佛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该工伤认定决定。邹政贤仍不服,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宣判后,邹政贤不服,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宏达豪纺织公司未经依法登记即擅自增设营业点从事经营活动,故2006年7月28日邓尚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禅城区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时,错列“宏达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并不存在主观过错。另外,邓尚艳在禅城区劳动局以“宏达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并建议邓尚艳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后,才由生效民事判决最终确认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宏达豪纺织公司。故禅城区劳动局2008年1月16日收到邓尚艳以宏达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从《工伤保险条例》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考量,认定邓尚艳已在1年的法定申请时效内提出过工伤认定申请,是因存在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原因而导致其维护合法权益的时间被拖长,受理其申请并作出是工伤的认定决定,程序并无不当。被告根据其认定的事实,适用法规正确。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
专家解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工伤认定申请时效问题。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规定,工伤保险立法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申请主体的变化,二是申请时效的变化。1996年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只规定了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即企业应当自工伤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职业病确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报告。而2004年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及之后修订的条例规定,工伤认定的申请主体为用人单位或工伤职工一方,前者的申请时效为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工伤职工一方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为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之内。
从表面上看,立法对于工伤认定申请主体及申请时效的放宽有利于保护工伤职工,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用人单位却往往借助时效的规定逃避责任,比如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职工申请工伤认定的必备材料,导致工伤职工无法自行申请认定,或者利用职工对法律的无知而拖过一年的申请时效。实践中的种种做法,不但没有减少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并导致了诸多恶性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立法本义而言,设立时效制度是为了敦促义务人及时履行义务、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但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反而起到了负面的效果,这也引发了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制度存废的争议。
关于时效制度的另一个争议,是时效的属性问题。有人认为“一年”是除斥期间,不得中断、中止;也有人认为“一年”是时效限制,可以适用中止、中断的情形。本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规定,重申了“一年”为时效期间,并列举了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将工伤职工通过民事求偿程序追索赔偿的行为排除在时效限制之外,充分体现了保护工伤职工的立法宗旨,对于工伤处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