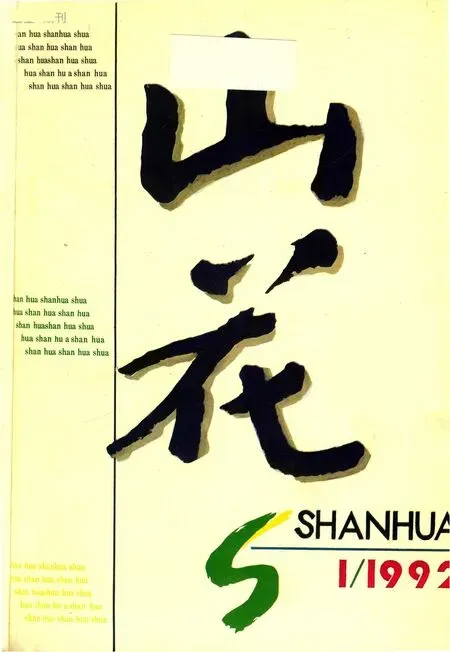乡村中国的寓言化书写
——论贾平凹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
康新慧
乡村中国的寓言化书写
——论贾平凹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
康新慧
早在1984年,贾平凹即敏锐地感到了社会转型期的来临,继而开始反思“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这些问题使我十分苦恼,同时也使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1]。在这一“兴趣”的诱使下,他开始了对家乡商州的持久关注和深入探究。二十多年来,贾平凹创作了从《商州三录》到《秦腔》等一系列文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在小说创作理念上转而追求“最大限度地回到生活本身,最逼真地呈露生活的原色原味”[2],贡献给我们的是一个个活色生香、充满世俗气息的民间世界。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贾平凹既不在文本里直接展示意识形态和倾向性很强的主观分析、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波澜起伏的悲欢离合、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不给人物清晰的道德评价,一切都通过貌似客观的书写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从实证层面来看,它们尽管无法等同于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的社会调查报告,但却是以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对当下乡村中国进行的寓言化书写。
被城市吞噬的仁厚村
仁厚村位于西京郊区,如今,随着西京城的扩张和周围村庄的陆续被侵占改造,仁厚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城中村,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困境。因此,围绕着仁厚村的保留与否所展开的抵抗斗争也就具有了相当的典型性。生性强悍、亦正亦邪的草莽英雄成义在生死存亡之际、去留危难之间被村民们推上了历史舞台,代替在征用土地上态度软弱的老村长而成为仁厚村的掌舵人。在成义和梅梅的带领下,村民们统一思想、同仇敌忾,为保卫家园进行着最后的抗争。但是,拼死一搏的仁厚村还是随着成义的离去最终化为一片废墟。“它的象征意义令人惊恐不已:谁也不曾料到,现代化作为百年中国的梦想,是以埋葬传统的‘仁’、‘义’形式实现的 。”[3]仁厚村的遭遇正是当下中国许多乡村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现实情形。贾平凹以作家的立场,表达了对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社会和广大农民的困境与出路的关注与思考。“城市化进程是大趋势,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中国在走这一步时,所发生的行为上的心理上的冲撞是世界少有的。……社会发生着变化,我们的思想上、心理上也发生着 ‘时间差’变化。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着‘土地、革命、人民’,坚守土地,保守而固执,向往的是桃花源和乌托邦,这种思想在城市文化进程中表现得很顽强,而在无法阻止的大趋势下走这一步时,又都是什么主义都产生的。”[4]贾平凹在为仁厚村的消亡悲悯叹息的同时,按照贴近原生态生活的散点透视的手法,以冷峻的笔触揭示出这个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中存在的愚昧和落后。村民们缺乏独立思考判断的习惯,他们崇尚权威,无条件服从成义的决策。人们在厕所的椿树上揩屎,闲暇时以“堆粮袋桩”的低级游戏娱乐消遣。男人们逢酒必醉,妇女们说长论短,吵架打架之事屡见不鲜。村里冬天烧煤取暖、污染环境,夏天蚊蝇横飞、瓜皮乱扔,路面凹凸不平、常年积水,这些都表现出村民生存空间的逼仄龌龊和自身素质的恶劣低下,喻示出仁厚村终将被改造的趋势与命运。
仁厚村必然被改造、吞噬的命运并不意味着贾平凹对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城市文明的全盘肯定。立足于时代发展和现实生活层面,作者虽然承认并认同这种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却也没有因此就对现代工业文明赞誉有加、顶礼膜拜。西京城中捕杀无证狗的警察冷静淡漠的神情,疯狂失控的球迷和混乱沸腾的球场,丧心病狂的凶杀灭门案和碎尸案,花枝招展的卖淫女子和从房地产中获利的公司,跪着擦鞋只为挣一元钱的女工昭示着这是一个嘈杂喧嚣、物欲横流的混乱世界。作者借范景全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城市和城市化的观点,“城里人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不厚道,排外,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自由散漫。……你们一味反对城市,守住你们村就是好的吗?国家工业化,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城市化,这一进程是大趋势啊,大趋势是能避免的?!”[5]贾平凹无疑有着对农业文化的天然亲近感,但他知道,城市文明才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最终方向,成义那种逆流而上、负隅顽抗的抗拒注定要失败,当下要做的是寻求城市文明健康良性的发展而不是丧失理性的反抗抵制。仁厚村居民抵抗城市侵蚀、保卫自己家园在动机上无可厚非,但仅仅因为住进高楼不方便下楼,打牌、说话没有同伴,习惯在老鼠吵闹声中入睡就坚决反对拆迁,靠延续了几千年的氏族宗法观念抵御现代文明,即使最终胜利了,又能将仁厚村引向哪里呢?
《土门》中,贾平凹并没有简单地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层面看待问题,而是全方位、多角度观察社会,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客观的审视与思考,在对行将消失的乡村文明伤感流连的同时,也冷静地发现了古老乡村存在的精神痼疾,而对现实病患的理性把握又使他对现代性的后果充满了反思和质疑。正如土狗阿冰尽管因为美丽两次死里逃生却终究难免一死一样,仁厚村的回光返照终究不能改写它被吞噬的命运。“狗是土命,见土就要复活”[6],“我们都是狗命,与狗结下不解之缘,或者说,我们的前世就是狗变的”[7]。是啊,人也是土命,像狗那样。被现代化进程连根拔起的农民如同丧家之犬恐惧惶惑。哪里才是他们的安身之地?失去家园的仁厚村居民果真能在母亲的子宫和兼有城乡之长的乌托邦——神禾塬找到自己的归宿吗?贾平凹的答案显得无力而苍白。
都市不仅是现代性的载体,也是其表征、内容和果实。城市作为权力和经济的中心,正在一步步地改变吞噬着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现代性侵占蚕食着前现代性,从外部形态到内部精神,古老的乡村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农民作为生活在其中的 “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注定要为历史的发展进步牺牲自己的利益。仁厚村的命运和处境无疑是当下乡土中国的反映和写照。
百丑丛生的高老庄世界
正如“对于神话主人公猪八戒而言,高老庄是一个阻挡取经志向的回家情结”[8],在农裔城籍的大学教授高子路心中,也时时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高老庄情结。然而,当他携着新婚妻子西夏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高老庄时,却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一个百丑丛生的混乱世界。高老庄的丑表现在以下方面:
1.相貌丑陋
从画像砖上显示,历史上的高老庄村民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还曾多次成功抵御过外族入侵。后来,为了保持血统纯正,他们不与外族通婚,近亲繁殖导致种族退化,现在的高老庄盛产身矮腿短的丑男丑女。除了高大英武的蔡老黑之外,其他人在西夏眼里都是“前额颅后马勺,歪瓜裂枣,鸡胸驼背,腰长腿短,矬子,矮子,半截子,猪八戒”[9],狗锁、鹿茂不仅个子矮小,而且是罗圈腿,背梁“个子极小,脖子和一个腮帮上白花花的,是白癜风”[10],石头“头颅长而扁,额角凸起,而耳朵明显高出眉目,且尖耸如小兽耳”[11]。女人除了菊娃等少数人有些姿色外,其余多无可观之处,三婶“胖得如菜瓮一样”,修子“头发稀黄,额颅光亮”[12],半香更是“肥胖而撅牙突嘴”[13],蔡老黑对这里“婆娘是墩墩,女子是黑黑”的评价几乎将所有女性“一网打尽”。尽管如此,高老庄从大人到小孩都十分反感别人说自己矮丑,就如同当年的阿Q忌讳头顶的赖疮疤。
2.行为丑陋
男人们喜欢请客喝酒、聚众赌博,推杯换盏之间,黄色笑话与猜拳劝酒齐飞,胡言乱语与觥筹交错一色,直到杯盘狼藉、酩酊大醉为止。女人们则习惯于乍手袒胸、咕咕涌涌地走路,平时脸面不洁、首如飞蓬,遇到客人来访,则用唾沫梳头聊以敷衍,撒泼哭闹时更是涕泗横流、到处乱抹。村民喜欢端着海碗蹴在离厕所不远的地方边吃边海阔天空地闲聊,间或说三道四,打情骂俏;饭后舔碗更是高老庄独具地方特色的一大景观;无论男女,都津津乐道于搬弄是非、散布谣言,三句话不离家长里短、桃色新闻;夫妻打架随处可见,俨然成为高老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3.生活作风丑陋
小小高老庄成了婚外性行为的高发地带,男女通奸在这里司空见惯。历史上 “村有村规,族有族长,公公不扒灰,母狗不跳墙,兄不与弟媳逗嘴,偷鸡摸狗要抽脚筋”[14]的良好人伦道德早已荡然无存,从官到民,多有此种爱好,有些甚至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供人们在茶余饭后闲聊逗趣。女人红杏出墙,招摇过市;男人四处粜粮,如鱼得水。蝎子南夹村的女人被苏红介绍到省城打工回来后,老公公对儿子说:“你媳妇回来了,你让她检查检查有没有性病,她是不能有病的,她有病了,我就有病,我有病,你娘就有病了,你娘有病了,全村人都要有病的。”[15]可见,高老庄两性关系已经开放、堕落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4.思想丑陋
高老庄是长舌妇和长舌男的集散地,村民妒富笑贫,嚼人舌头。地板厂打着“扶贫”旗号进驻高老庄,倚仗着领导的支持,肆无忌惮地掠夺本地木材和土地,引起本地村民的极度不满。他们既怨恨厂子压价收购木材,殴打卖原料给地板厂的白云寨村民,又痛恨地板厂不给高老庄修路带福。于是先匿名上书,再砍伐集体树林,到哄抢地板厂时,以王文龙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与以蔡老黑为代表的高老庄本土利益的冲突走向了最终的白热化。对眼前利益的极度贪求使人们丧失了理性,对现代性的狂热追求带来的是人性的堕落与良知的泯灭。恩格斯提出的历史进步发展与道德伦理规范之间的二律背反矛盾——人类在历史上的进步同时意味着道德的堕落——在高老庄又一次上演。
5.居住环境丑陋
在外来者西夏和返乡者子路眼中,高老庄氤氲着浓郁世俗色彩的日常生活场景足以粉碎人们关于乡村的一切美好遐想:马路上尘土飞扬,厕所大多建在路边,晴天臭气熏天、令人窒息,雨天尿窖漫溢、人粪漂浮。村民卫生观念淡漠,碗碟一律乌黑,油光可鉴,围绕着食物乱飞的苍蝇则被美其名曰“饭苍蝇”。
贾平凹反对在写作上的就事论事。他说“我无论写的什么题材,都是我营建我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16]。“作品必须形而下与形而上结合,无形而上不成艺术,但纯形而上则又成了哲学。作品的象征,我喜欢用整体象征和行文中不断的细节象征,这样,作品就产生多义性、说不尽”[17]。高老庄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庄,而是作家“营建”的“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才是他要传达的对于现实世界的感悟和评价。作为虚实结合的整体意象,高老庄实际上是整个乡土中国的象征。为了强化这一点,贾平凹还特地通过在省城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西夏收集散落在村中的残缺碑文回顾了高老庄的历史:那时的高老庄出英武男子、识文秀才。居民讲求大义、宁死不屈;心存仁孝,祭祀祖先;四时耕种,安居乐业;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男耕女织,家庭和睦。村规严明,禁止砍伐偷窃、放火烧山;严禁赌博、奸拐妇女;人们遵纪守法,孝敬双亲;尊师重道,善待朋友;扶危济困,买卖公平;戒杀放生,乐善好施。可是,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就像被冷落的石碑和画像砖,早已被人们抛到了九霄云外。面对商品经济的诱惑,乡土文化越发暴露出落后腐朽的一面,人性中贪婪、自私等负面成分被极大地刺激出来,于是,从基层干部到普通村民,几乎都成了拜金主义信徒。吃喝嫖赌的放纵、急功近利的浮躁、见死不救的冷漠在高老庄大行其道,这里已成为传统伦理观念坍塌、道德严重滑坡、村民愚昧依旧的百丑丛生之地。如果说,仁厚村的最终消失表现了古老的乡村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城市文明彻底击溃的一种现实处境,那么,高老庄在现代性侵入农村以后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生态环境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则是广大乡土中国当下遭遇的另一种处境的写照和缩影。
秦腔消散的清风街世界
长篇小说《秦腔》不仅是贾平凹为故乡树起的一块碑子,也是他为现代性进程中行将消散的乡土社会所唱的一曲挽歌。《秦腔》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文化变迁的书写可以说是中国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状况的缩影。
1.离开土地与打工求生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8]“农恒为农,世不徙业。”农民自古以来就取财于地,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人们获取生存所需的唯一途径和手段。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侵入与蔓延,土地对农民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村民们纷纷逃离土地,另谋生路,那种所谓男耕女织、质朴无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清风街,日子过得最舒心、自在的是那些彻底离开土地、摆脱了农民身份的农裔城籍者如夏风、雷庆等人,他们有固定收入,过着旱涝保收的安稳生活;其次是那些在种田之外(或者干脆将土地闲置)从事其他职业,并以此获取经济收入的人,如霸槽、三踅等,种地在他们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他们主要依靠第二职业维持生活;生活最为拮据的是那些固守、依附于土地,并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如狗剩、瞎瞎等。现实告诉人们,完全依靠土地谋生是一种既没出息、也没前途的工作。于是,乡村的男男女女开始前赴后继地涌向城市,在那里开拓新的生活。土地的衰败引发了打工潮的兴起,打工潮的兴起反过来又加剧了土地的衰败,二者相互作用,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乡村社会的萧条与破败。由于青壮年劳力大量外流,致使死了人将棺材抬到坟上去都困难。夏天智去世时,东街抬棺的劳力不够,还要从西街、中街借人。七里沟滑坡后,因为没有主要劳力,那些留守的老弱病残根本无法将夏天义从土石堆里挖出来,只得作罢,农村的凋敝由此可见一斑。而那些外出打工者,干着城里人不屑的最累最重的活,“除了在饭馆做饭当服务员外,大多是卖炭呀,捡破烂呀,贩药材呀,工地当小工呀,还有的谁知道都干了些啥,反正不回来。回来的,不是出了事故用白布裹了尸首,就是缺胳膊少腿儿”[19]。两个人因挣不到钱拦路抢劫而被抓坐牢;羊娃等三个打工者为挣钱过年而杀人抢钱;白路在建筑队当小工,出了事故丧命之后反复缴涉也才拿到六千元赔偿费;年轻女子通过向马大中的外出劳务公司缴纳二百元手续费,被组织介绍到外面卖淫。男性出卖体力、女性出卖肉体,进行着艰难的生存奋斗。在家种地没有收益,外出打工也绝非长远之计,那么,农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贾平凹对此充满了感伤和迷惘,“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20]
2.精神生活的贫瘠与传统伦理的破碎
与物质困窘相伴而生的是村民精神生活的平庸乏味;与精神荒芜相伴而生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在清风街,每天都有置气打架的,常常是父子们翻了脸,兄弟间成了仇人。”[21]夫妇邻里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架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其他人则煽风点火、乐此不疲,甚至起哄怂恿“吵熊哩,该打的事吵熊哩?!”[22]夏家作为清风街的大户旺族,是乡村伦理关系的表率。然而现在,夏家这种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且不说夏天礼自私吝啬、偷卖银元,并因此而不得善终,就是夏天义、夏天智在家族内部的权威也日益受到挑战。作为下台主任的夏天义在村人眼里早已失去了“父亲”的权威,只有当三踅、上善等人想达到个人目的时才会抬出他以自重。到了下一代,金玉满堂、瞎瞎五兄弟和媳妇们为赡养两位老人吵吵闹闹、纷争不断,“包谷”事件、“红木桌”事件、“碎碗”事件、“迁坟”事件、“打狗”事件和“树碑”事件无不反映出乡村道德伦理和亲情伦理崩毁的现实。夏天智作为清风街的道德楷模,在家族内部的约束力也日渐松弛。先是几个侄子对他的训诫心怀不满,打折执行;继而儿子夏风又不顾他的坚决反对,和白雪离了婚;而在一年一度的春节团圆饭上,晚辈们怪话连篇,搞得聚会不欢而散。在这里,大家族轮流吃喝所蕴蓄的情感内涵早已被剥除怠尽,沦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贸易市场的建立在推动清风街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瓦解了乡村传统的伦理观念,夏雨、丁霸槽在万宝酒楼公然设置三陪和暗娼,将支书君亭也拉下了水。之后便是年轻女子陆续外出、从事暧昧职业,甚至连翠翠也义无返顾地加入其中。随着传统伦理的瓦解,清风街已逐渐显露出精神上与文化上的衰败。
3.传统文化的衰败消散
秦腔作为一种草根艺术,在西北地区极受欢迎。早在1983年,贾平凹便在散文《秦腔》里,用文字把盛行于八百里秦川之上的秦腔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秦腔作为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作为一种地方戏曲、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秦腔也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县秦腔剧团振兴无望最终解散,秦腔演员四分五裂,有的改行经商另谋出路,更多的演员成了走乡串村为人们红白喜丧演唱的乐人,甚至像王老师这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也沦为搭班走穴的龟兹手。另外,与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的秦腔的衰落相伴而生的,是带有市民文化色彩的流行歌曲迅速赢得乡村青年的青睐。且不说夏风嫌秦腔聒噪不愿意听、外来户陈星惩罚弟弟陈亮的手段是要他听秦腔,就是秦腔演员白雪也被清风街流行歌手陈星的歌声所打动,夏天智的去世则标志着最后一个秦腔戏迷的终结。秦腔作为一种根植于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诉求,终于随着乡土社会的转型和农业文明的衰落走到了尽头。
《秦腔》写了一个村庄的人事变迁,展现的却是中国乡村在后改革时代的商品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的迷茫与困境和农民命运的困顿与无奈。
《土门》《高老庄》《秦腔》等作品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混乱不堪的当代乡村世界。现代化的侵入导致了乡村文化传统的断裂与消失、传统人伦关系的瓦解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在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矛盾冲突和相互撕扯中,乡村旧有的伦理秩序迸裂成块块碎片。
[1][2]孙见喜.神游人间[A].贾平凹前传(第3卷)[M].花城出版社,2001:459.
[3]孟繁华.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J].当代作家评论,1997(1):16.
[4][17]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4卷)[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439,463.
[5][6][7]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0卷)[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33,196,207.
[8]李裴.自述体民族志小说——从《高老庄》看中国小说新浪潮[J].民族艺术,1999(3):104.
[9][10][11][12][13][14][15][16]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5卷)[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336,48,112,48,169,267,315,408.
[18]费孝通.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08:62.
[19][20][21][22]贾平凹.秦腔[M].作家出版社,2005:496,561,138,83.
康新慧(1974— ),女,河南巩义人,文学博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