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恍惚(组诗)
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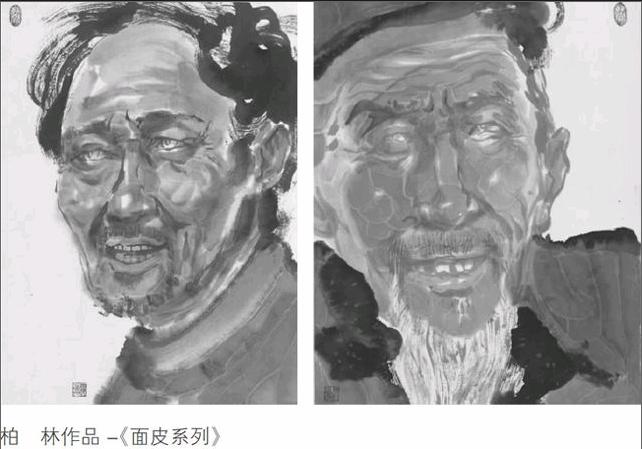
驱车看杏花
驱车去看杏花
那杏花分不清关内关外,它们攻破长城要塞
把中原和羌胡夷狄统一在这个春天
华北的天空在被杏花照亮之前,一直阴郁着
枝干是亚伦的杖,从睡眠中醒来
繁花轻摇在山崖黝黑的脸颊
朵朵纹饰印在空气中
青涩和微苦共同表达着甘甜,杏仁露是罐装的乡愁
花雾浮半空,在山坡和谷地拼了命开放
毗邻的密云县也嗅到了悲伤
除皇家行宫,或许还有晋太元中武陵人
时间恍惚,杏花自己不知开在哪朝哪代
坐在农家酒馆,望向起风的窗外
花瓣飘散,落进雪佛兰的辙印
河北滦平县衙的公章上
应刻有一枝斜倚的杏花图案,花瓣洁白清寒
底色青灰,用一块明长城方砖作背景
我的人生就是一次出游
是驱车迢迢千里去看野杏花
偶尔立在某条山路上,迎风哭泣
长城脚注
那在燕山上奔跑,分明在燕山山脊上奔跑着的
是长城么?
金山岭这一段,奔跑了四百多年,仍未移动丝毫
驮着它的山峦,该累了吧
风到这里总高亢,在垛口唱响历史
这堵厚墙原是国境线
是一个大国的院墙
站上墙头,想到南是故园,北即国外
而今没有通关文牒或签证
翻越自如,打个喷嚏就到外国
柯受良先生驾摩托车飞越这墙
以垂直的壮志征服了平行的雄心
从外邦到中原,其实只需一个飞跃动作
戚继光可曾料想过?
万里长城在金山岭确立王位,发表君主论
它不肯承认自己是恐惧的纪念碑
一直对着大地致辞:“我是东方的巴别塔,
只不过是横放着的。”
烽火台跟时间打赌,遂成废墟,颇具思想者之姿
喊声藏匿在巨石和青砖的缝隙
一枚埋了几百年的石镭,引信还在颤抖
使弥漫的野花香味感染上了惊恐
此段长城把华北穿在身上
牢记每座支峰的名字和高度
文字砖上,万历年间的笔划里生长着民国的苔藓
抬起头,一架去往京城的飞机正拖拽着一绺云在跑
如今内外都是疆土,院墙成了统一的房产
两边都是良善的国民
诗人骑在墙头,体内有朵朵镶边的云
加速的句子从前朝直冲进未来
杏花出墙,辨不清长在哪一边
一只蜜蜂在花蕊里迷路:哪里是祖国?
忘记还有这么好的阳光
这是长城外古道边
小餐馆背依一面山崖,上方有长城蜿蜒
崖根堆放一大堆圆木
在温暖的晌午,散发松树魂魄的清香
一生中很多时间都浪费在写诗和恋爱上
忘记了还有这么好的阳光
大家坐在圆木上闲聊
爱情在时间里发酵成绯闻
作为幸存者,我已忘记过去,即便有诗为证
伤痛也已忘记,只剩淡淡羞愧,亦可忽略不计
如果九年前来这里,女主角定会哭倒长城
美景即噩耗,在命运关隘
杏花短命凋零
而此时山野寂静,我有局外人的自由
一只蜡嘴雀从杨树枝间跃过,不知所终
一生中很多时间都浪费了,忘记还有这么好的阳光
抬起头来,长城作为山际线,对蓝天一无所求
整个华北正在春风里打开
文字砖
燕山统领华北
遗落山巅的这些砖上的汉字多么孤独
它们迥异于茫茫野地中的一切
古汉字刻进长城青砖
上面有不属于当今这个国家的部队的番号
代表浩荡的锐士,一个又一个征人
里面没准儿就有孟姜女的丈夫
刻字和烧制砖的手不见了
搬运并垒筑砖块的四肢不见了
而砖和文字还在,被太阳的拳头击打成铜褐色
久远得成了秘符,笔划紧绷
它们被我的手指抚摸
我的手鲜活,那些手已在史书里凝固
此刻我的手跟那些消失的手相接触
隔着时间这场盛大长眠
我的手连一块砖也无法留在世上
写下的诗,一行也不会被刻上砖瓦,当作文物保护
我的手消失时,无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
都不会被写进史书
蕨草在砖缝无为地生长
种子也来自遥远朝代
千年的风把字迹吹得模糊
其中两块砖想结伴逃离,携带汉字去往博物馆
在每一块砖的内心,都有偏旁部首沉没
都有北方的寒意
都有一道城门,一次凯旋,一支羌笛,一行归雁,一座青冢
我猜想
当UFO飞过这段长城时
外星人曾打算把这些砖上的文字破译
而当基督再来,在一个像现在这样的春天的早晨
这里很可能是他到达亚洲的
第一个落脚点
日 晷
我跟太阳签订了契约:它按光的几何来照耀我
我用它的影子表达时间的几何
我陷于孤立,精确计算那巨爪的角度
我是自身又不是自身
时间存于这里又不在这里
太阳摆脱星云,我放弃群山
请大地后退一下
一根针和一个圆面,我与宇宙的政权直接联系
分和秒以隐喻的方式袭击过来
我是本体的真像,太阳和时间的双重纪念碑
预感来自地平线第一缕曙光
正午盛大,全神贯注撑起光的拱廊
在黄昏哀歌里,镶边的云打着哈欠
即使在没有光和影的阴天和夜晚,我也要仰望
我相信太阳的存在
远远超过相信我自己的存在
比向日葵更爱太阳,颂赞并感恩全都默然无声
我是另一个西西弗斯,推动的是阳光这块亘古巨石
风从一棵小草上刮起,拂过时,我的指针颤抖了一下
后来从一位少女的脖颈上拐弯
吹向西周和巴比伦,吹向整个历史
迎面而来的灿烂,使虚无打开,谁正以光速
返回到无限的过往?
湾丘五七干校
那棵绿了二百年的黄葛树
请你告诉我:五七干校是一种什么学校?
课程是放猪、搬石头、担粪、砍柴、插秧打谷、收甘蔗
笔杆子变锄头
琴弦成扁担
面对正在开花的亲爱的木棉
不准抒情,只可检讨和揭发
谁在此地能过好日子?
绿瓦灰墙、木楼梯、五星天窗、粮仓、会台
民国建筑的校部,在口号、忠字舞和悔过书里沉浮
头顶上的那枚太阳不是全人类的
是中国人自己的
四川的古拉格群岛,或者动物庄园
主义被从书本里活活搬到大地上
苦和难,已成为最大污染
按照新颁十诫,乐园必建在废墟上
人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坪坝搂着满满一季的繁花
安宁河流走了岁月
龙肘山在末世依然屹立
火车在成昆线的桥梁和隧道赶路,来到二十一世纪
保存这里,不是为了记住苦难
而是为了想明白
怎样才能配得上我们所受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