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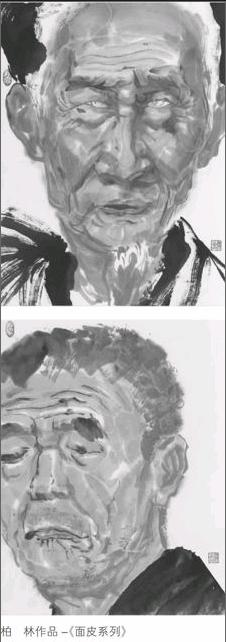
1
最近一次听到张金宝的名字是小七回到北京的两年后,一次朋友聚会上。老贺显出一副神叨的表情说:“你们听说了吗?玛丽张的本名叫张金宝!”在座的七八个朋友开始交头接耳,小七也装作一副好奇的样子参与其中,这个秘密她大概在十年前就知道了。尽管如此,她还是摆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老贺又说:“这名字土的哟,跟村姑儿似的。我还听说,这女的换过九次名字呢。”老贺其实并不认识玛丽张,他们未曾谋面过。可在纽约华人圈里,你有可能没听说过玛丽李、玛丽王、玛丽何,但绝不会没听说过玛丽张的。但实际上,张金宝只换过两次名字。脏小强操着一口福建口音说:“这人呀,不管到哪里都得靠口碑活着。她把一个名字用烂了,可不得换个名字么?”脏小强是福建人,二十年前偷渡到了他的梦之国——美国,几经周折后,又将自己渡到了梦之国的核心城市——纽约。他在一家广东人开的餐馆里打黑工,没人知道他真正叫什么,也没人关心。只是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脏小强,说是在纽约讨生活的福建人,都有像蟑螂小强一样顽强的生命力。
脏小强说的没错,饭馆儿需要口碑,足疗需要口碑,妓院也需要口碑,人更是要靠口碑活着的,尤其是在纽约的华人圈里。口碑和人是捆绑在一起的。当张金宝“火”起来的时候,正是用的玛丽张这个名字。
小七和玛丽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小七也记不清了,只是隐约记得那是一个较为温暖的冬天。和往常一样,小七晚上八点准时从学校图书馆里走出来,排队等待回家的60C路公交车。站在她前面的是一个金黄色长发披肩的女生。她穿了一件黑色呢子大衣,两条细长的腿就这么赤条条地露在冬日的夜里。小七把自己裹在一件白色羽绒大衣里,瑟瑟发抖。“怎么车还不来?”小七嘟囔句。赤腿女孩突然转过身来:“可能还要等个十分钟呢。”小七晃了一下神,连连点头。
十分钟过后,60C不慌不忙地驶来。她们并排坐在了一起。赤腿女孩开始和小七攀谈起来,姓名、年龄、籍贯、专业两人各交代一遍过后又不约而同地下了车。后来得知,赤腿女孩叫玛丽张,住小七的隔壁。
回到家后,小七正准备入睡,突然门铃响了。是玛丽张。她穿着一条红色蕾丝睡裙,手里端着一盘蛋糕和一瓶红酒。玛丽张对小七说:“我能进去坐坐么?”小七看着她这架势,哪里是坐坐这么简单。小七面有难色道:“我明天有早课,恐怕……”玛丽张垂下眼帘:“今晚是我生日。”
小七的房间是和别人合租的,室友是个香港人,她早已睡下。玛丽张踮起脚尖,兴奋地迅速冲进小七房间里,坐在床上,倒了两杯红酒。小七虽不讨厌玛丽张,可对她这种自来熟的行为实在感到不自在。
“二十八岁了,过得可真快。一转眼到这个城市也有十一年了。”玛丽张身姿妩媚,蕾丝裙挂在胸前,露出了半个乳房。她在胸前不停摇晃着手中的大肚红酒杯,红酒在玻璃杯里一圈圈地转悠着。小七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低头不做声。“你有男朋友么?”小七摇摇头:“交男朋友会影响学习。”玛丽张看着她,轻声一笑。“我得赶紧毕业然后找个正经工作。家里只供我读一年预科和三年大学的钱。”玛丽张又说:“你为什么叫小七?”“我脸上长了七颗痣,后来烧掉了两颗,一颗是眼角下面的,一颗是嘴边上的。因为姥姥说眼角长痣的姑娘容易哭,嘴角上长痣的姑娘爱贪嘴。姥姥不想让我变成爱哭鼻子的小胖妹,就点掉了这两颗。奶奶还说,其余的五颗痣不碍事儿。”
两人整晚只是随性聊天。小七心中一直想问玛丽张一句话——你没有其他的朋友么?可这句话却一直憋在心里,谁也没想到,这一憋就是永远。
玛丽张独自喝了一整瓶红酒,红酒把她的双唇染成了酱紫色。她就这样穿着红色蕾丝睡裙倒在了小七的床上,像只即将死去的吸血鬼。她的生日就这样在小七这样一个陌生女孩的屋中平静地度过了。小七站在床边看着她,莫名地对她起了怜悯之心。
第二天醒来,玛丽张早已离去。小七对妍姐讲述了昨天发生的事情,妍姐只是说让她远离玛丽张,这样的女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在妍姐心里,头发染成金色的都是坏女人。他给小七讲了一个四年前,在纽约发生的真实故事。
事情发生在一个圣诞夜的前夕,是个星期日的白天。教徒们在圣约翰教堂里做礼拜,这时候三辆警车呼啸而来。警察在教堂外面死守着,直到礼拜结束后,教徒纷纷走出教堂,四名警察冲进,把一个金色长发的中国女人给按在了地上。那个金色长发女人没有挣脱,老实地被警察带走了。可没过多久,就又被放出来了。逮捕她的原因是,警方怀疑她跟三天前的一起凶杀案有关系。死者死前,两人刚发生完性关系,可根据调查,两人并无直接关联。一个月后,这案子了结了,凶手找到了,果然跟这个金发女没有直接关系。后来才知道,这金发女名叫樱桃,本名是张金宝,说得好听点她是个援交妹,说得难听点就是个妓女。这新闻一曝光之后,就不得了了,关于她的小道新闻就像北京春天的杨絮一样飞满天。有人说樱桃被一个越南大佬给包起来了,也有人说她曾经进过三次戒毒所,每次都试图从中逃跑,未遂,更有人说她已经死了,被越南大佬给弄死了。她的事情被无数的华人盲流杜撰着。无论她是否已经死去,樱桃这名字就此消失了。那个时候,人们一度怀疑樱桃为什么会去圣约翰教堂里做礼拜。有人猜测,她此时正因宗教迫害的原由申请难民,谁知道呢。
小七却不以为然,她觉得玛丽张与她口中的樱桃相差甚远——怎么能把所有染成金发的女人都叫坏女人呢?
2
这一天,小七没有见到玛丽张,第三天没有见到,第四天也没有……她的莫名出现像是一场梦,唯有枕边那一根金发丝可以证明,玛丽张是真实存在的,她的确在小七的床上睡过一晚。
小七几次想去按响玛丽张的门铃,可每次都是在门外驻足,犹豫下还是退缩。仅仅一面之缘而已,何必再去打扰呢。可是她到底去了哪?纽约城中的普通公寓楼隔音效果极差,四面邻居家中的每一点噪音都可以听得清楚。就像上个星期,住在楼下的一对夫妇因在公共洗衣房中,丢失了两条裙子,三条裤子,五件衬衫以及丈夫一件风衣外套而大吵一架。最重要的是,丈夫的一只很贵重的钢笔落了外套的内侧兜里。夫妻二人的口音听上去不是纽约城的人,有点像印度或中东一代的。小七在家里听得津津有味,一清二楚。
这几日,她总是把耳朵贴到墙上,探听着隔壁——也就是玛丽张房间里的声响。可每次传来的,永远都是楼上或是楼下再或是隔壁的隔壁所传来的椅子挪动、咳嗽、打呼噜以及做爱的声音。
直到第八天,玛丽张的房间终于传来了动静。
晚上十点,邻居纷纷歇息,在夜晚的寂静中,不时传来楼上男人雷鸣般的酣睡声或是窗外警车的呼啸。小七在房中准备着期中考试,这时,玛丽张的房间里飘来了一阵对话,和一个男人。
男人说,下个月还是老地方见吧,钱已经打到你的账户里了,注意查收一下。这次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玛丽张没开口。关上了门,男人便出去了。小七立刻从大门的猫眼望向走廊,却只是隐约地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
“我一定是疯了。”小七倒头便睡下了。
夜晚某个时辰,小七被一阵硬物敲打墙壁的声音吵醒,她把头缩到被子里。
此时的玛丽张,正穿着一件吊带睡裙躺在床边。一个男人坐在床的边缘,一点一点褪去裤子。显然,这是他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他的动作笨拙、生硬、紧张,甚至显得有些龌龊。男人的举动让玛丽张想起了五年前的事情。
那是个秋天,玛丽张的男朋友莫小楠去上课了。玛丽张找到了一个兼职——教一个广东仔弹钢琴。上课地点是在这个广东仔家里的地下室。那时的玛丽张还不叫玛丽张,叫樱桃。广东仔带着樱桃走进地下室,按了开关,暗黄色的光在黑暗的房间逐渐晕散开来。地下室潮湿阴暗,有一股发霉的味道。这个地下室摆着一张单人床,床前有张书桌,桌子上躺着一架不是全键盘的电子琴。
地下室里,散发着死人般的味道。
樱桃站在门外,迟迟不敢踏入房门。广东仔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便开口说:“我们之前在网上已经说好了,给你的薪水是四十分钟五十美金。要不我给你再加一些。我给你七十美金怎么样?”樱桃答应了。她需要钱,她需要立刻从莫小楠的房子里搬出去。
她从未想到过自己经过十五年的严格训练后,会坐在一个散发着死人味道的地下室里,用一架简易电子琴教一个成年的广东仔弹钢琴。而这个广东仔却只想弹一首光良的《童话》。
广东仔坐在床的边缘,就像此时这个男人一样。他拍拍床边,示意她坐过来。他把电子琴的开关打开,这个举动让樱桃觉得无比可笑。她认为,这根本不能叫做琴,顶多算个玩具。
电子琴冒出了一阵高分贝刺耳的声音。樱桃慢慢把双手放到了键盘上:“我先给你弹一遍,然后在五线谱上标注上简谱的数字,简谱你认识么?哦,对了,差点忘记问你,你之前学过钢琴么?”广东仔摇摇头说:“我从来没学过,简谱也不认识。这是我第一次弹琴。”樱桃没再说话,照着谱子弹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在音符上标注了数字。
广东仔在樱桃边上如坐针毡,屁股在床上蠕动着。他微微起身,又坐下,就这样,起身再坐下。一只手慢慢拉下自己的运动裤。昏暗的灯光让樱桃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他的动作细小谨慎,樱桃并没有在意。“我先教你识五线谱,下加一线是Do,往上半个格子是Ri。”广东仔似听非听地点着头。他抬下屁股,又坐下,就这样一直重复着。樱桃终于看到了他的这一举动。在这封闭幽暗的地下室里,再无旁人。樱桃目光迅速转移到琴谱上,感到空前的恐惧。广东仔突然开口:“这是Do么?”他一手指着琴谱,一手便按下了琴键了。樱桃点点头,双手开始发抖,但又不能暴露出自己的恐惧。他已经把灰色的运动裤脱在了大腿跟的位置上,并且没穿内裤,他生殖器的上毛发就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面。他如此坦然地坐在床边上,双手接过樱桃递给他的琴谱:“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樱桃脑袋里像是被吸尘器吸空了般。她要保持镇静。樱桃说:“是简谱。”广东仔露着半个屁股坐在床上,认真地看着。
樱桃故作镇定地说:“我去一下洗手间。”广东仔微笑地对她点头示意。
她拿起包,缓慢起身,此时樱桃已经没有了呼吸。她快速地,几步冲出了地下室,推开大门跑了出去。她随便朝着一个方向拼命地跑,她已经很久没有跑得这么远,这么快了。她终于跑得没了力气,回头看看,广东仔并没有追上来。她瘫倒在一棵树下,把脸埋在了臂弯里,哭了。
现在,这个男人已经把自己脱得精光,他赤条条地坐在玛丽张身旁,伸手慢慢划下她身上的吊带裙。玛丽张慢慢躺下,面无表情地盯着天花板。
一阵床头木板不停敲打墙壁的声音,不断传进小七的房间里,这阵敲打声里又伴随着做爱发出的呻吟。小七仔细听着。男子说:“我要来了。”玛丽张声音有些不耐烦:“一定要拔出来,要是弄进去我们就不要再见了。”只听男人“啊!”的一声。世界安静了。
小七心里一阵恶心。过了会,一声关门声响。夜晚又恢复了原有的寂静。
小七睁大眼睛,凝视着万籁俱寂的黑夜。她继续聆听隔壁是否依然有动静,却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3
期中考试格外关键,如果有一门课没有考好,那么这门课就要重修。也就意味着,她要延迟一个学期毕业,住宿费、学费、餐费、电话费、交通费通通得增加,她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焦虑症就会发作。她的焦虑症是刚来纽约时患上的。那时候她只身一人,英语只停留在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水平上。家里给的费用只够她上一年预科以及三年大学的。小七父母认为,大学第四年的时候就应该有能力出去找工作,养活自己了。如果这一年预科不能顺利毕业,则就要卷铺盖打道回府了。在上预科的时候,她认识了妍姐。妍姐便给小七介绍了一个打散工的地方,可是那时候美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留学生是不可以打工的。但是妍姐介绍的这份工作是一个广东人开的中餐馆,老板为了偷税,在店里打工的人基本都是中国留学生,或是一些没有身份的难民。付给他们的薪水是政府规定的最低时薪的一半。小七没有打工经验,但样子却乖巧。老板就让她暂时到厨房里做洗碗和倒垃圾的工作。这时,她就认识了脏小强。脏小强当年从福建坐船偷渡到美国,在海上漂泊的数月里,有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死掉了,就死在脏小强的脚边。如今,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五年了。小七很好奇,像脏小强这样在美国没有身份,没有家,没有钱的人为什么偏要来美国讨生活。每当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脏小强总是笑嘻嘻地说:“美国哪里都好,连厕所的卫生纸都好。”
小七坐在三百人的教室里,忐忑不安。老师发下考卷。为了防止学生作弊,考卷分成了A、B、C、D四种题目不同的卷子。如果想抄袭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小七看着试卷,突然绝望了。题目与复习时的内容完全就是两回事。再环顾下班里的同学,大家都在奋笔疾书。尤其是坐在她左前方的那个黑人女孩,眨眼间卷子上已经书写了四行。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卷子,脑袋里并没有认真思考答案,而是在掂量着这次考试不及格的后果——回国还是再重读一个学期,想到这里就好像天塌下来了一般。八名监考老师像幽灵般在四周游荡。无奈下,小七只好硬着头皮填写答案。又一个小时过去,那个黑人女孩自信满满地站起来,走向前,交了考卷后离开了考场。逐渐地,同学们也都纷纷收拾起桌面,离开了考场。小七心急如焚,手心的汗把卷子浸得皱巴巴的。
她看了下自己的试卷,填写的答案似乎并没有错得离谱。每道题还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才作答的。一个小时地填写,卷子上也都是满满的字迹。她潦草检查一遍后,便交上了考卷。希望这次可以蒙混过关。
她急忙跑出校园,到了那个公寓后面的小花园里。一个人独自坐在一张木条凳上,发呆。
一个星期后,考试成绩下来了。小七看到成绩的那一刻,突然崩溃了。她把头埋进臂弯里哭了。这哭声是那么的绝望。走出公寓大门,人们脚步缓慢地走在街道上,享受着当下的阳光。
4
晚上,小七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看见一个身着黑色西装,年纪大概在五十岁上下的中国男人,手提公文包徘徊在玛丽张门口。男人见到小七后,尴尬地笑了下,便迅速低下头,把身体转向一边。小七不知那男人鬼鬼祟祟地在做些什么,她回到家,仔细盯着门上的猫眼,注视着那男人的行动。不一会,玛丽张给他开了门,男人进去了。小七又迅速把耳朵贴在墙上,听着动静。几分钟过去后,那声音又窜了出来。
小七心脏乱跳,屏住了呼吸。她多半已经猜到了什么。她后退几步,退到了窗子旁,她再也不想看见这个肮脏的女人。也许已经没有以后了,自己的路像是夜晚中的一片海,绝望得让人恐惧——是时候该回国了,可回国后就连个文凭也没有,这该怎么交代?这时候,玛丽张的房间里又传来了一阵对话。男人说:“这些给你,应该够你到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年初的生活费了,还有这个电话号码,我已经跟移民局那边的朋友打好招呼了。帮你办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可能有点困难,但是他们可以把你的签证再延续三年。我下个月就回国了,太太在杭州要生孩子了,我得回去。这次可能就不再回美国了。你以后好好照顾自己,钱攒得差不多了就别再干这个了。玛丽,我还是喜欢过你的,这个你是知道的吧?”从始至终,玛丽张没有说一个字。
男人走后,就连楼上那个胖白人的呼噜声也没有了。深夜,这座城市进入了睡眠。唯有小七和隔壁的玛丽张还醒着。她们就这样独自在漆黑的房间里,睁着眼睛,恐惧未来。
小七做了一个梦。
玛丽张多次打电话给小七,也曾按响过她的门铃。可她一概视而不见。可这么躲着也不是个办法,毕竟两人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一日,在公寓楼下的超市里,小七远处看到了玛丽张的背影,她在冷冻区的冰柜中挑选食物。小七立刻转身,躲在了一排货柜后面。她怀里抱着水果,心里仔细想着,她到底犯了什么错?自己与她其实不熟络,按道理来讲她的私生活与自己又有何关系?
小七决定大步走到收银台前去,即使碰巧遇到玛丽张也要坦然地面对她,可这时候,玛丽张突然叫住了她。小七却还是下意识地闪躲了下。“你是在躲着我么?”玛丽张开口直奔主题。小七用力摇摇头。“那为什么你明明在家,我按你门铃你却不回应?打你电话你又不接?刚才明明看到我却又躲起来了?”小七心里乱了,脸也感到一阵滚烫。
“那天,我看到有个男人在你家门口,然后……然后。”小七没有看玛丽张的眼睛,低着头小声说。“然后呢?你还看到,听到了什么?”玛丽张问。小七停顿了下:“你的私生活,和我无关。”说完便转身走掉了。玛丽张站在原地,看着逐渐走远的小七。身旁篮子里的冷冻番茄肉酱和意大利面条在慢慢往下滴水。她就这么一直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心拧成了一个畸形的疙瘩。
晚上,玛丽张在小七的门口来回踱步,几次想按响门铃,但又把手缩了回来。长长的走廊里空无一人,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隔壁家的那对夫妻又在吵架,好像是因为丈夫喝醉了,把车钥匙弄丢了。妻子气得在摔东西,因为那是他们家里唯一的一把车钥匙。今天玛丽张的房里不会出现任何男人,她把两个客人的预约都取消了。走廊里的灯灭了两次又亮了两次,她终于按响了小七的门铃。
门铃只响了两声,小七就开了门。玛丽张没有化妆,这是小七第一次见到最真实的她。她的皮肤黯淡无光,几条鱼尾纹浅浅地挂在眼角。去掉了黑色的眼线,眼神也显得那么沧桑,疲惫。这张脸在告诉着人们,青春已经在多年前就离她而去了。她把头发简单地绑在脑后,穿了一身淡橙色的运动服,她像一只快要干枯的橘子站在这里。
小七示意她进到屋里来。她知道玛丽张来的目的,待她们进到了卧室后,小七轻轻关上门,锁住了。她生怕那个香港室友会听到她们的对话。
玛丽张坐在了小七书桌前的一把椅子上,把身子挺得笔直。小七坐在床边,看着某处。她们都等着对方先开口。屋子里只有此起彼伏的呼吸声,还有从隔壁传来的吵架声。妻子愤愤地说:“车子的另一把钥匙就是你在去年喝醉的时候弄丢的!”丈夫终于忍不住了,夺门而出。
“原来这个房子这么不隔音。”玛丽张由于长时间没有说话,嗓子里卡了一口痰,她又清了下嗓子,终于把这第一句话讲了出来。
小七点点头,指着她睡觉的那面墙说:“我们就只有这一墙之隔。”
玛丽张说:“我刚搬来不久,房东说,这里的隔音效果很好的。每天躺在床上,我只想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死死睡去。有时候会失眠,失眠的时候会让我想起那些男人的口臭和肮脏的手在我身上胡乱地摸着。但这么多年倒也习惯了。我多次想自杀,我厌恶自己,觉得自己特别脏。可最后我发现,肮脏的不是我,是生活。”
“那为什么去做妓女?为了钱?”小七说。
玛丽张说起了五年前的事情。
5
她记得特别清楚,那是2008年的圣诞节。那时候的玛丽张还叫樱桃呢。圣诞节,原本基督徒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是家人团聚在一起,在家中吃饭、庆祝、一起拆礼物的日子。可对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只好凑在一起在酒吧喝酒或唱歌儿。他们不明白圣诞节的真正含义,也不明白圣诞节到底是在庆祝什么。只知道,圣诞节是一个大家必须都要喝得醉如烂泥的节日,像过生日一样。
就在平安夜这天晚上,樱桃的男友莫小楠告诉了她一件事情——他准备移民美国了,他的家人终于同意给他办投资移民。等他办好身份后,他们会立刻结婚,这样樱桃也就自然而然有美国身份。这个消息对樱桃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那时候的她并没有想要留在这个地方,她本想着毕业后,两人回国再共同发展,毕竟在美国他们什么也没有。五年里搬了快二十次家,这意味着什么?樱桃的行李箱永远会摆在房间里最显眼的位置,箱子里也永远备着日常生活用品。她说,这是为下一次搬家做准备。他们在这里永远都是漂泊的局外人,这些留学生就像北京四月的杨絮,纷纷扬扬地在空中飘呀飘,飘呀飘。
在美国的日子,他们相依为命。樱桃和莫小楠像是连体婴般的形影不离。之所以形影不离,不是他们对彼此的爱有多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两个孤寂的灵魂在陌生的城市,他们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最好可以合二为一,成为另一半的寄生虫,只有这样才会让他们安心,漂泊的肉体才会有依靠。樱桃没有朋友,他有莫小楠就足够了。她已经习惯了纽约这样畸形病态的生活方式。她盼望着莫小楠的身份可以快点办下来,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为续签、租房子这样的事情而烦恼了。樱桃认为,在美国只要有了身份,买了房子就可以变成真正的美国人了,一个可以永久居住在这片土地的本地人了。
玛丽张说:“日子就这么凑合过着,可谁知道,突然有一天莫小楠提出了分手。”
后来,我给自己写了一封信:
莫小楠,此时此刻,我在这家徒四壁,漆黑的夜里。我又开始想你了,每次想你时,我的四肢、心脏、大脑,甚至是脚趾间都在隐隐作痛。我觉得我病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我在记录这些的这一刻开始,我做了个重大决定,我要报复这个世界,报复这个无耻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报复你。
再后来,莫小楠又来找我了,他说他不爱那个女人。但那个女人可以帮助他,包括事业和生活。他又对我说,你知道么樱桃,其实我也挺不好受的。当和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步入婚礼殿堂的时候,当那个狗屁华人牧师问我是否愿意娶这个女人为妻我说“是”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难过么?我觉得自己特别失败,特别悲壮。
听完这话,我转身就走了。
那是玛丽张最后一次见到他。那个时候,她就知道人该现实一点,冷酷一点,健忘一点,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樱桃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对他说声谢谢,他让樱桃成长了,变得坚强了,同时也堕落了。”
小七说:“那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就像我的人生,没有了然后。”
6
“我要回国了,下个星期天的机票。这次的期中考试没有过。毕业的话,可能要再延期一年。家里没办法再为我承担费用了。你跟我一起回去吧。回到国内,我们一起重新开始。”
“说得容易,怎么重新开始?又不是打游戏,这条命死了可以重新复活的。也许你可以,但我是回不去了。回国的念头在五年前,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就已经打消了。来这里已经十一年了,这意味着什么?我的青春,我的爱情,生活上所有的辛酸全部献给了这里。回国我一无所有,就连朋友也没有。虽然我在美国同样孤独,但在这里每个像你我一样的中国人都孤独,这一点你敢否认么?我们大家都一样,所以就不觉得孤独了。我的父母认为我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他们以我为骄傲。我上一次回国时是在三年前,当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我哭了。我终于能回来了,回到爸妈身边了。我不再是玛丽张,不再是为了生活,为了那无谓的美国身份而出卖自己灵魂和肉体的玛丽张了。当变回张金宝的时候我居然哭了出来。可是一个星期后,我开始想念美国了。当然,在美国我依然一无所有,甚至美国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但相比之下,更令我恐惧的是北京的车水马龙。”
“回国吧,国内的机会还是多一点的。美国的生活就像是个大沼泽,现在唯一能救你出来的方法就是回国。你不必很快做决定,下个星期天我希望在机场看到你。”
玛丽张在曼哈顿最繁华的街道上,她走路的姿势从容不迫。她目视前方,眼神淡定,像是把耳朵关了起来。说唱艺人在路边手舞足蹈,最后摘下礼帽。路过行人偶尔将硬币投入礼帽中。她就这样在曼哈顿人生嘈杂中孤身自立,看不出她的幸福与悲戚。她孑然自处的身影逐渐被淹没。
星期六的晚上,小七的门口放了一盆花。花盆里塞了一张纸条:
它叫永生花,是经过复杂工序加工而成的。看得出来么,这永生花的前生是新鲜的玫瑰花和康乃馨。卖花的老板说它能活三年。我把它送给你,它能陪伴到你毕业的那天。珍重。
作者简介:
孟小书,198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多伦多约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