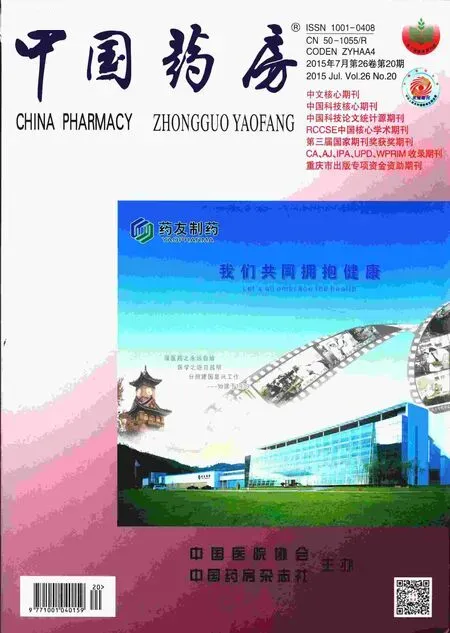慢性骨髓炎的病原学特点及抗菌药物治疗进展
王燕萍,陈 娅,武新安,赵 龙(.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兰州 730000;2.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岗院区,兰州 730000;3.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兰州 730000)
慢性骨髓炎的病原学特点及抗菌药物治疗进展
王燕萍1,2*,陈 娅1,武新安1,赵 龙2,3#(1.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兰州 730000;2.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岗院区,兰州 730000;3.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兰州 730000)
目的:了解慢性骨髓炎的病原学特点及抗菌药物应用的现状。方法:查阅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慢性骨髓炎的病原学特点及抗菌药物治疗进展进行归纳和总结。结果与结论:慢性骨髓炎感染致病菌具有复杂的特点,即混合性、多重性、交叉性,需氧菌、厌氧菌同时存在,甚至有真菌感染的存在。近年来阳性球菌感染率下降,阴性菌感染率上升。其抗感染治疗主要有全身治疗和局部治疗,其中抗菌药物的局部使用是目前研究的重点,抗感染骨材料在临床应用中逐渐广泛。但与此同时,抗菌药物的全身应用与局部应用是否容易诱导耐药等问题则是需要关注和研究解决的重点。
慢性骨髓炎;细菌学研究;抗菌药物;抗感染骨材料
*副主任药师,硕士。研究方向:临床药学。电话:0931-8357126。E-mail:wangyp317@sina.com
#通信作者: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方向:关节及创伤骨科。电话:0931-8357127。E-mail:zhao712@hotmail.com
慢性骨髓炎(Chronic osteomyelitis)是由化脓性细菌引起的骨膜、骨质和骨髓的慢性炎症,根据发病原因主要分为创伤性和血源性两种,以前者多见。慢性骨髓炎主要以骨组织的坏死、硬化、瘘管和窦道的形成以及长期流脓为特征,常反复发作,其基本治疗原则包括:彻底清除病灶、消灭残存细菌、积极适时骨组织重建修复骨缺损、皮肤组织缺损修复、局部及全身应用抗菌药物。慢性骨髓炎伴有无血运的坏死组织及对抗菌药物渗透有阻碍作用的细菌生物被膜,一般单独采用抗菌药物治疗很难达到痊愈,手术清创是治愈慢性骨髓炎必需的手段,而合理地联合全身或局部抗菌药物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慢性骨髓炎的治愈率。本文拟就慢性骨髓炎的病原学特点和抗菌药物应用作一综述。
1 慢性骨髓炎的病原学特点
慢性骨髓炎的抗感染治疗中,抗感染药的选择应参考病原学检查和药敏试验结果,临床标本的正确采集是得到准确检验结果的关键。其中,窦道分泌物培养是了解慢性骨髓炎病原菌的常用方法,也是应用抗菌药物的主要依据。窦道是慢性骨髓炎病灶向外环境排出坏死组织及脓液的通道,病灶中的病原菌将随着分泌物流出体外[1]。
慢性骨髓炎感染致病菌具有复杂的特点,即混合性、多重性、交叉性,需氧菌、厌氧菌同时存在,甚至有真菌感染的存在。如,尹秀云等[2]报道了1例黄曲霉菌引起的骨髓炎,叶嘉等[3]报道了1例新型隐球菌引起的肋骨骨髓炎。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肠杆菌属是引起慢性骨髓炎的主要致病菌,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为最常见的两种病原菌。迟涛胜等[4]对化脓性骨髓炎主要致病菌感染率进行了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溶血性链球菌、大肠埃希菌、普通变形杆菌、表皮葡萄球菌、枸橼酸杆菌、草绿色链球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慢性骨髓炎中阳性球菌感染率下降,阴性菌感染率上升,其中,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已经上升到第2位,说明骨髓炎的感染类型已发生较大变化。内源性的正常菌群或来自周围环境中的条件致病菌,已成为化脓性骨髓炎的主要致病菌,在近几年中细菌耐药发生了较大变化,菌种耐药率增加,给临床治疗骨髓炎带来新的难度。
苏建荣等[5]的研究特别指出厌氧菌在慢性骨髓炎中的重要性。慢性骨髓炎的感染常常是需氧菌、厌氧菌同时存在,经久不愈的慢性骨髓炎患者或有厌氧菌感染。厌氧菌感染常为多菌性,有细菌协同现象,厌氧菌中最多见的脆弱类杆菌能产生β-内酰胺酶,能显著降低病灶中青霉素的浓度并将其灭活,采用抗菌药物治疗时必须加以考虑。
近年来,肠球菌感染发生率逐渐升高,广谱抗菌药物应用日益广泛,肠球菌已发展成医院感染中重要的致病菌之一,关于肠球菌导致的慢性骨髓炎的临床报道也逐渐增多。时宁文等[6]报道了5例屎肠球菌所致的慢性骨髓炎的病例,对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青霉素、高浓度庆大霉素和链霉素均耐药,而对利福平和四环素表现出部分耐药,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对非抗万古霉素的肠球菌感染较敏感。
慢性骨髓炎的难治性除其疾病本身的解剖学和病理学特点决定外,还存在各种因素。近年来,研究较多的细菌生物膜(Bacterialbiofilm,BBF)理论认为,慢性骨髓炎BBF的形成是难治的主要原因之一。BBF是由细菌群体附着于有生命或无生命物体表面,分泌胞外大分子将自身包裹,具有特殊的内部生态环境和不同的细菌基因表达[7]。BBF可在坏死软组织、骨组织表面形成,对细菌具有保护作用,大大增强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抵抗力,导致细菌难以彻底清除,使慢性骨髓炎反复发作、感染。BBF的生长包括黏附、发展和成熟3个阶段。慢性骨髓炎的各种致病菌,在其形成BBF的过程中都有其独自特点,根据这些特点设计治疗方案可成为抗BBF感染慢性骨髓炎的治疗方法之一[8]。细菌L型的存在也是慢性骨髓炎难以治愈的原因之一。陈晓东等[9]从37例慢性骨髓炎患者标本中分离出细菌L型19例,显示细菌L型有较高的检出率,表明细菌L型存在于绝大部分的慢性化脓性骨髓炎感染灶内。结合慢性化脓性骨髓炎的发病特点,认为细菌L型感染与慢性化脓性骨髓炎的发生、发展具有相关性,可能是其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主要原因之一。临床对慢性骨髓炎患者除常规手术外,仅行普通细菌培养而忽视了细菌L型。因两者的药物敏感度不同,仅选用普通细菌敏感的抗菌药物,治疗后表面炎症消退,细菌L型得以保留,当机体抵抗力低下时,细菌L型成为致病菌,引起骨髓炎反复发作。目前,很多医院检验科室未开展细菌L型检测,故此方面研究资料较少。
2 抗菌药物的全身应用
治疗慢性骨髓炎的抗菌药物应在骨组织中具有较好的动力学分布。第1次清创后,在细菌培养的同时,医师可以根据临床经验使用抗菌药物,首选广谱抗菌药物。碳青霉烯类如亚胺培南、美洛培南,糖肽类如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四环素类药物敏感率较高,而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的敏感率在逐渐下降,不宜用于严重、化脓性、病程长的慢性骨髓炎的治疗,仅在轻症患者中经验性适当使用。《热病——抗微生物治疗指南(新译43版)》推荐,在微生物培养结果前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的可能性较大,经验性使用万古霉素进行治疗;若MRSA可能性较小,使用青霉素类药物,如萘夫西林、苯唑西林钠,或者第三代头孢类药物,如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并在治疗前先进行骨组织和血培养。当取得病原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应根据临床治疗效果和培养结果及时考虑是否更换敏感药物,并且要大剂量、足疗程、联合用药[10]。
Richter-Hintz D等[11]研究显示,对于革兰阳性菌感染可能性较大的难治性的慢性骨髓炎,利福平与抗菌药物联合应用,能有效提高抗菌药物的疗效。赵巍等[12]通过联合应用利福平与万古霉素,治愈了12例感染MRSA的创伤骨科患者,显示利福平与万古霉素联合应用对MRSA感染的慢性骨髓炎治疗效果较好,但在采用此治疗方案的同时,应警惕药物联合应用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
治疗慢性骨髓炎的全身给药途径有口服、静脉给药两种,临床常用的给药方法是在静脉用药1~3周后,改为口服给药4~6周,疗程较长。在完成慢性骨髓炎的清创、处置死腔、软组织覆盖后,可根据药敏结果短期静脉滴注抗菌药物和中长期口服抗菌药物。慢性骨髓炎的治疗疗程应到局部血运重建为止[13],其中儿童慢性骨髓炎的疗程可适当延长。Howard-JonesAR等[14]进行了一项系统评价,认为儿童慢性骨髓炎的抗感染疗程应达到3~6月。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抗菌药物的给药时间及给药方式并没有达成一致。Eyichukw GO等[15]的回顾性研究显示,慢性骨髓炎患者在充分的清创后,多采用敏感抗菌药物静脉给药48~72 h,口服给药48周。Howard-JonesAR等[14]研究表明,慢性骨髓炎患儿多先接受4~6周的静脉抗菌药物治疗,然后再口服抗菌药物2~3个月。有研究表明,短期的抗菌药物治疗对患者有一定的疗效,国内外学者开始思考慢性骨髓炎是否有长期使用抗菌药物的必要。Euba G等[16]进行了关于比较口服利福平-磺胺甲基异 唑与静脉使用氯唑西林治疗慢性骨髓炎的长期随访试验,两者的治疗结果相当。黄永栋[17]只在术后经静脉滴注抗菌药物,至体温正常后1周改用口服抗菌药物,总疗程6周,疗效满意。张杏泉等[18]的研究认为,关于抗感染的治疗时机和策略,术前2周必须停止一切口服或静脉滴注抗菌药物,治疗效果较好。因此,关于慢性骨髓炎的抗感染治疗疗程和方法,仍需要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来验证。
3 抗菌药物的局部应用
3.1 抗感染骨材料
慢性骨髓炎患者局部常有瘢痕形成或血管损伤,导致血液循环障碍,抗菌药物的全身应用很难在损伤局部达到有效的药物浓度。因此,抗菌药物的局部应用显得必要,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局部灌洗、高浓度滴注,还随着联合了抗菌药物的骨水泥、脂质体缓释系统等抗感染骨材料的逐步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广和应用。1970年,Buchholz HW等[19]首次应用庆大霉素联合骨水泥治疗骨感染,为抗菌药物在抗感染骨材料中的应用开启了新道路。此后,随着新材料的研发与抗菌药物品种的选择优化,越来越多的抗感染骨材料运用到临床治疗。
通常加入抗感染骨材料的抗菌药物要求为广谱抗菌药物,应具有耐热性、水溶性、低过敏性、无全身毒副作用、不影响伤口愈合等特性,应满足的基本条件为:(1)抗菌谱广,对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都有效;(2)在相对较低的药物浓度下有抗菌作用;(3)天然耐药菌株较少;(4)细菌较难抗药性;(5)与蛋白质结合较少;(6)潜在过敏性小;(7)对骨材料的机械性能影响不大;(8)具有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型;(9)具有良好的水溶性;(10)能从骨材料中较好地释放。
Joseph TN等[20]对多种抗菌药物混合骨材料后的变化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与骨水泥的混合。结果发现,可以与骨水泥混合的抗菌药物有丁胺卡那、阿莫西林、氨苄青霉素、杆菌肽、头孢孟多、先锋唑啉、头孢呋肟、头孢唑南、头孢噻吩、环丙沙星、克林霉素(注射用无菌粉末)、黏菌素、达托霉素、红霉素、庆大霉素(注射用无菌粉末)、洁霉素、甲氧苯青霉素、新生霉素、苯唑西林、青霉素、多黏菌素B、链霉素、替卡西林、妥布霉素、万古霉素等。
目前,应用较多的抗菌药物为万古霉素、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先锋唑啉、头孢呋辛、青霉素等。李有方等[21]在病变骨髓腔内放置1~2条先锋霉素珠链,同时全身应用敏感抗菌药物,明显提高了Ⅰ期手术植骨和组织瓣移位修复重建骨髓炎组织缺损的成功率。杨晓形等[22]根据院内微生物学分布和细菌耐药情况,选择了耐药率最低的妥布霉素加入骨水泥中进行慢性骨髓炎的治疗。牛慧云等[23]选择氨基糖苷类药物依替米星加入骨水泥中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其中,万古霉素因其满足热稳定性好、低过敏性、水溶性、抗菌谱广等基本要求,在抗感染骨材料中使用最广泛,对MRSA等革兰阳性菌的治疗效果明显,万古霉素和骨水泥的质量比一般为1∶20。治疗霉菌感染可以应用两性霉素B骨水泥。
陈红卫等[24]通过研究建议使用喹诺酮类、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喹诺酮类药物抗菌谱广、效力强而毒副作用小,应用于慢性骨髓炎的治疗能顺利地渗入到血管不丰富的感染部位,对可能引起慢性骨髓炎的病原体均有抗菌作用,少见严重不良反应。目前,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应用与抗感染骨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动物实验。KyriakiK等[25]评价了搭载有莫西沙星的一种新型的可降解可注射的碳酸钙骨水泥的体外研究,对葡萄球菌和肠杆菌属感染疗效最好,具有良好的体外释放度和洗脱浓度,用于治疗慢性骨髓炎有较好的发展前景。Efstathopoulos N等[26]进行了含格帕沙星骨水泥用于治疗新西兰大白兔诱导MRSA骨髓炎的动物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目前,鲜有证明抗感染骨材料全身毒性反应的案例,如Richte r-Hintz D等[27]报道的1例因置入庆大霉素骨水泥的患者发生Ⅳ型超敏反应的病例,但关于局部毒性反应的可能性应重视。目前,尚无局部低剂量抗菌药物系统毒性反应的报道,但有试验研究表明局部高浓度抗生素具有细胞毒性,主要对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功能产生影响。抗菌药物在抗感染材料中的局部应用虽然可减少全身不良反应,但是否会引起其他局部的毒性症状或局部过敏等,仍不可忽视。
市售或医院自制的抗感染骨材料中多只具有一种抗菌药物,刘涛[28]的研究报道了临床医师在自制的骨水泥中加入万古霉素、妥布霉素、泰能、头孢唑林等多种抗菌药物。覃开兵等[29]报道了在已经含有庆大霉素的市售骨水泥中加入根据药敏结果选择的敏感的混合抗菌药物粉末进行局部联合抗感染治疗。但是,多种类的抗菌药物的同时局部使用,是否会增大细菌耐药的可能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机会,值得商榷。抗感染骨材料中应单一使用抗菌药物还是联合使用抗菌药物而不会诱导耐药,将是抗感染骨材料应用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3.2 局部闭式灌洗
慢性骨髓炎在彻底清创后,可局部应用大量的敏感抗菌药物进行滴入灌洗,既可以在局部形成高浓度抑菌、杀菌,又可以通过高速的流动液体冲走病灶中坏死组织和炎性渗出物等。常用庆大霉素溶于生理盐水进行灌洗,浓度为每500m l生理盐水加入庆大霉素8~16 u,灌洗1~3周。其次,较常用的还有高浓度的克林霉素[30]、林可霉素和先锋霉素等,或可根据药敏结果选择用药。
局部闭式灌洗是在病灶清除后行持续灌洗引流,具有能在局部达到较高的抗菌浓度的优点,也存在缺点:(1)抗菌药物渗透力弱,很难渗入死腔和周围纤维瘢痕组织内发挥作用;(2)细菌长期接触抗菌药物后可发生变异,产生耐药性,冲洗过程中需要反复进行引流液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3)患者住院时间长、经济负担重;(4)引流管容易堵塞或发生脱管,创面渗液多,易感染,须多次更换敷料,加重患者痛苦;(5)肉芽生长缓慢,引流时间长,患者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重;(6)术后复发率高,创面不易愈合。
抗菌药物的局部滴注灌洗是治疗慢性骨髓炎较为传统的方法,然而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导致的耐药和存在的不足,使得其临床效果有所降低,近年来有学者不主张用灌注引流来治疗慢性骨髓炎。
3.3 其他局部给药方法
3.3.1 介入治疗给药 随着介入放射学科的发展,其治疗范围也被拓宽。刘碧波等[31]和付志明[32]报道应用介入性动脉内留置导管治疗慢性骨髓炎,采用Seldinger’s法动脉穿刺,将导管置于病变侧股动脉造影,查找病变局部供血动脉,在局部供血动脉内注入抗菌药物,取得了较好疗效。周志玲等[33]将介入治疗与中药相结合,将中药外敷联合导管介入局部给药治疗68例慢性骨髓炎患者,总有效率为88.24%。介入治疗抗菌药物的选择主要依据术前药敏试验,无法进行药敏试验则选用高效广谱抗菌药物。
介入治疗可明显地提高骨和软组织抗菌药物的药物浓度和作用时间,但其机制仍不清楚,可能与感染灶局部血液循环加快、局部组织血流增多和氧分压增高有关。结合慢性骨髓炎血运情况有不同程度损害的特点,可考虑在抗感染的同时,采用扩血管和疏通微循环的药物配合治疗。介入治疗中抗菌药物的用量尚待研究,现临床使用多为局部用量与全身用量相当,存在局部浓度较高、容易诱导产生耐药的问题。
3.3.2 直接放置法 将纱布条浸泡于抗菌药物溶液,或将抗菌药物溶液、干粉制剂放置局部病灶,抗菌药物的选择原则为经验用药或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
4 结语
慢性骨髓炎病程长、治疗困难、易复发,一直是外科医师面临的一大临床难题。临床治疗慢性骨髓炎时,抗感染的治疗必须掌握慢性骨髓炎的病原学特点和细菌耐药性。慢性骨髓炎的抗感染治疗是目前的研究重点,治疗过程中抗菌药物的全身使用和局部应用,怎样权衡利弊,把握好治疗效果和耐药性之间的关系是应该思考的问题。目前的治疗方案是口服或全身静脉使用抗菌药物的同时,提倡同时局部给药,已在各项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更多的研究还致力于抗感染骨材料的缓释或控释,以期达到更好的抗感染效果。但是否会加速诱导细菌耐药的产生,引发更多的潜在的不良反应,这是今后临床工作应关注的重点,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和循证药学的证据来解答。
[1] 陆维举,李斌,陈勇,等.慢性骨髓炎窦道分泌物与病灶组织的细菌学研究[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7,17(6):681.
[2] 尹秀云,陈建魁,曾利军,等.白血病患者化疗后多发性曲霉菌骨髓炎的诊治[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4,24(6):1 339.
[3] 叶嘉,林庆安,柳德灵,等.新型隐球菌感染所致肋骨骨髓炎1例报告[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3,33(11):902.
[4] 迟涛胜,吴红军,翟建国,等.创伤性骨髓炎细菌药敏及耐药分析[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14,22(2):52.
[5] 苏建荣,马纪平.开展厌养菌检查的重要性[J].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07,30(12):12.
[6] 时宁文,陆维举,邵海枫.屎肠球菌性骨髓炎的耐药特征及临床意义[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0,7(6):513.
[7] Sutherland IW.The biofilm matrix-an immobilized butdynam icm icrobial environment[J].Trends Microbiol,2001,9(5):222.
[8] 唐辉,徐永清.细菌生物膜与慢性骨髓炎[J].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2010,24(1):108.
[9] 陈晓东,周之德,胡汝麒,等.慢性化脓性骨髓炎与细菌L型感染的关系[J].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00,7(2):134、156.
[10] 魏亚恒,杨佐明,戴士峰,等.慢性骨髓炎的综合治疗及进展[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12,27(9):870.
[11] Richter-Hintz D,Rieker J,Rauch L,et al.Sensitivity to constituents of bone cement in a patientw ith jointprosthesis[J].Hautarzt,2004,55(10):987.
[12] 赵巍,邢进峰,陈中,等.骨科创伤中MRSA感染的治疗探讨[J].浙江创伤外科,2001,6(5):325.
[13] 张威,李琛琪,周明武.成人慢性骨髓炎的研究进展[J].实用医药杂志,2013,30(7):648.
[14] Howard-JonesAR,Isaacs D.Systematic review of system icantibiotic treatment for children w ith chronic and sub-acute pyogenic osteomyelitis[J].J Paediatr Child Health,2010,46(12):736.
[15] Eyichukwu GO,Anyaehie UE.Outcome of management of chronic osteomyelitis at national orthopaedic hospital,enugu[J].Niger JMed,2009,18(2):194.
[16] Euba G,Murillo O,Fernández-SabéN,etal.Long-term follow-up trial of oral rifampin-cotrimoxazole combination versus intravenous cloxacillin in treatmentof chronic staphylococcal osteomyelitis[J].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2009,53(6):2 672.
[17] 黄永栋.慢性化脓性骨髓炎23例的手术治疗[J].广西医学,2008,30(12);1 941.
[18] 张杏泉,陈刚,刘军,等.慢性骨髓炎的治疗[J].中国伤残医学,2012,20(2):8.
[19] Buchholz HW,Engelbrecht H.Depoteffects of various antibioticsmixed w ith Palacos resins[J].Chirurg,1970,41(11):511.
[20] Joseph TN,Chen AL,DiCesare PE.Use of antibiotic-impregnated cement in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J].JAm Acad Orthop Surg,2003,11(1):38.
[21] 李有方,郭亮,郭先礼,等.先锋霉素珠链结合组织瓣转位在合并溃疡的慢性骨髓炎中的应用[J].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2007,4(4):43、49.
[22] 杨晓形,吴波以,黄文铎.含硫酸妥布霉素的磷酸钙骨水泥对外伤性骨髓炎作用的观察[J].创伤外科杂志,2001(3):31.
[23] 牛慧云,康文磊,王瑞芳,等.临床药师参与1例化脓性骨髓炎患者的药学监护[J].中国药房,2013,24(42):4 031. [24] 陈红卫,赵钢生.病灶局部给药治疗慢性骨髓炎[J].中医正骨,2007,19(7):74.
[25] Kyriaki K,Thomas T,Kalomira A,et al.Comparative elution of moxifloxacin from Norian skeletal repair system and acrylic bone cement:an in vitro study[J].Int J Antimicrob Agents,2006,28(3):217.
[26] Efstathopoulos N,Giamarellos-Bourboulis E,Kanellakopoulou K,et al.Treatment of experimental osteomyelitis by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w ith bone cement system releasing grepafloxacin[J].Injury,2008,39(12):1 384.
[27] Richter-Hintz D,Rieker J,Rauch L,etal.Sensitivity to constituents of bone cement in a patientw ith jointprosthesis[J].Hautarzt,2004,55(10):987.
[28] 刘涛.多次清创抗生素骨水泥珠链置入治疗慢性骨髓炎[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1,22(1):97.
[29] 覃开兵,周树权.慢性骨髓炎行病灶清除后予抗菌药物骨水泥链置入处理后感染控制分析[J].北方药学,2012,9(2):53.
[30] 王晔.病灶区持续灌流及高浓度抗菌药物滴注治疗急慢性骨髓炎[J].局解手术学杂志,2006,15(2):108.
[31] 刘碧波,李凤英,文志广,等.介入性动脉内留置导管治疗慢性骨髓炎的观察与护理21例[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3,19(12):19.
[32] 付志明.慢性骨髓炎的介入治疗[J].中国医药导报,2008,5(24):242.
[33] 周志玲,袁进国,于爱国,等.中药外敷联合导管介入局部给药治疗慢性骨髓炎例临床观察[J].河北中医,2013,35(10):1 477.
(编辑:陶婷婷)
R979.4
A
1001-0408(2015)20-2867-04
DOI 10.6039/j.issn.1001-0408.2015.20.45
2014-12-26
2015-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