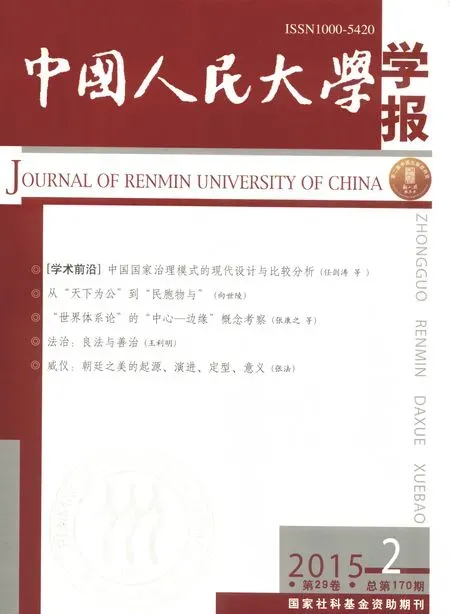“世界体系论”的“中心—边缘”概念考察
张康之 张 桐
“世界体系论”的“中心—边缘”概念考察
张康之 张 桐
20世纪70年代,依附论由盛转衰并迅速让位于一个受依附论影响很深的理论流派——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努力阐释世界体系得以产生、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原因,并对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对剩余价值如何向中心国汇集的问题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解释。世界体系论所使用的“中心—边缘”概念不同于普雷维什以及依附论所使用的这一概念,赋予它完全不同的性质,以至于这一概念失去了原有的批判力,表现为一组描述性的概念。
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中心—边缘;半边缘
20世纪中期,当普雷维什思考造成拉美经济困局的原因时,引入了“中心—边缘”概念。“中心—边缘”概念是一个解释框架,在这个解释框架中包含着如何去打破中心—边缘的追求。自普雷维什引入这一概念后,他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一直围绕着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去思考拉美经济脱困的策略,特别是经过了拉美经委会的一批学者的阐释,中心—边缘概念在拉丁美洲的思想界以及政策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下行的原因,普雷维什等人基于世界中心—边缘判断提出的拉美发展策略遭受重创。但是,作为一个解释框架的中心—边缘概念则被另一批学者继承了下来,并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分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思想流派——依附论(dependency approach)。依附论可以说是在20世纪有着广泛的世界影响的拉美本土学派,尽管依附论学派内部也存在诸多理论分歧,但他们都努力使用中心—边缘概念去分析问题,有着一种把拉美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认识问题的视野。所以,依附论突破了拉美的地理空间,使中心—边缘概念得到传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世界体系的视角。不过,到70年代后期,依附论开始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迹象。尽管直到今天依然有大批学者使用或借鉴依附论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成果,也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延续和发扬依附论学派的思想,但是,就全球影响力而言,依附论在70年代后就开始迅速地让位于另一个受到其思想影响的流派——世界体系论。作为一个思想流派,世界体系论不再是生长于拉丁美洲这样一个边缘地区的理论,而是诞生于美国这个世界中心国家中的,并具有(至少它号称具有)一种世界性的总体视角。世界体系论也广泛地使用了中心—边缘概念,用来描述世界体系的构成状况,并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解析世界体系中所存在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是,我们在对世界体系论所使用的中心—边缘概念进行仔细考察和分析后发现,它与依附论以及普雷维什所使用的中心—边缘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事实上,当中心—边缘概念从作为世界边缘地区的拉丁美洲移植到作为世界中心地区的美国时,其内涵中所蕴含的批判力和解释力就消退了。
一、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声称自己是致力于“一体化研究”的,并宣布其分析方法具有“长时段”、“大视野”和“世界体系视角”等特点。事实上,这是一个在理论来源和分析方法方面都极其混杂的思想流派。一般认为,世界体系论有着非常广泛的理论来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年鉴学派、发展理论,等等。但是,根据夏农(Thomas Richard Shannon)的意见,“与世界体系论联系最为直接的思想流派就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实际上就是依附论的直接衍生物”[1](P15)。许多评论者都断定世界体系论是依附论的翻版或再版。个中缘由就是,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都用中心—边缘概念去解读世界。世界体系论显然受到过依附论学派的巨大影响,但是,如果根据世界体系论也把中心—边缘概念作为解读世界的钥匙而加以利用这一点而断定其是依附论的衍生物或复制品的话,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观点。其实,它们是两个在理论性质上不同的思想流派,不仅分别产生于世界的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而且,它们的理论目标也是不同的。
20世纪60年代,在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理论与政策受到各方抨击的过程中,产生了依附论学派。这一学派运用了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但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并逐步形成了某种将政治社会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视角,目的是要弥补拉美经委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贸易条件恶化论”等政策策略在理论上的不足。依附论与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理论都有着明确的边缘国立场,都反对传统的、现代化的、从中心国出发的分析视角,并且希望通过中心—边缘概念对既存的国际格局进行重新解读,以求从中找到边缘地区为什么没有取得中心国所许诺的或者说中心国理论所预示的那种发展成就的原因。然而,在边缘国如何走出边缘地位的问题上,普雷维什以及拉美经委会给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拉美一体化”等政策建议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同样,依附论在对普雷维什及拉美经委会的政策实践进行激烈批评后也未找到出路。在某种意义上,依附论学派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批判方面,如果说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在使用中心—边缘概念而对世界体系的现状进行批判后提出了打破中心—边缘的一系列政策建议,那么,依附论只选取了可以作为批判武器的中心—边缘概念去开展更为激烈的批判,与此同时,也对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政策策略进行了批判,在如何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问题上则陷入了迷思。
到20世纪70年代,依附论学派的观点似乎出现了某些重心转移,从运用中心—边缘概念进行激烈批判转向了对边缘地区发展的关注,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要求从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走出来,即通过“脱钩”(delinking/break)而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另一种观点似乎是要在默认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前提下走一条“依附性发展”的道路。萨米尔·阿明是“脱钩”论的代表。阿明阐释说,“脱钩”旨在“拒绝使本国的发展战略听命于‘全球化’……‘脱钩’思想所给的含义完全不是‘闭关自守’的同义语……不是拒绝参与世界科学与思想潮流的同义语”[2]。但是,仅仅在科学和思想方面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脱离世界,又如何可能呢?所以,即使是在依附论内部,“脱钩”的主张也招致了许多批评。费尔南多·卡多佐和恩佐·法莱托等则属于“依附性发展”论的代表。虽然这一主张的持有者们对“依附性发展”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表现出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无奈和妥协倾向,希望在这一世界结构中谋求一种依附性的发展,而且认为边缘国在一体化的世界中也只能获得依附性的发展。的确,自工业化开始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成持续而稳定地走向世界一体化方向的过程,事实上,每过一段时间,世界一体化的程度都得到了大幅度增强,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变淡,人类再也无法复归于农业社会那种地域分离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边缘国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可能与一个互动的世界脱钩。相反,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也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但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又不是不可改变的现实,而是需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加以否定的。所以,默认这一现实而谋求依附性发展同样是错误的。总之,依附论学派的上述两种观点都是不可行和不能行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世界体系论的出场提供了表演空间。
夏农在综述世界体系论时指出:“世界体系论克服了依附理论的错误:持续地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将导致边缘社会一直维持在一个‘依附’的边缘地位;‘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发展’。这一观点暗示了成功工业化只能通过脱离世界体系而获得。”[3](P210-211)我们看到,“依附性发展”和通过“脱钩”求得发展实际上是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的,那就是认为中心与边缘的地位是固定的,而不是可以变动的。世界体系论正是要纠正这一错误,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南亚一些国家迅速崛起的条件下,说明一国在中心—边缘中的位置是可以改变的,也证明了依附论的解释框架已经丧失了解释力。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沃勒斯坦的写作动机得以提振,并以《现代世界体系》一书而宣布了“世界体系论”的诞生。
依附论学者所采用的是平面比较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到更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边缘地区落后的原因。与依附论不同,世界体系论要求对中心—边缘的差别做出历史解释,认为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是根源于较早的历史发展的。依附论学者们认为,边缘落后的原因并不是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源于某种内部发展的落后,边缘的不发达恰恰是中心的发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与中心的发达隶属于同一个历史进程。这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辩证思维的世界体系解读,可以说是非常深刻也非常准确的判断。但是,它毕竟是在一个平面或特定时段中来寻找边缘落后的原因的,而不是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去看问题。也就是说,依附论学者基本上没有对这个由中心和边缘构成的世界体系进行历时态的历史分析,没有去把中心与边缘在历史上的位移等当做一个重要议题加以探讨。所以,依附论学派面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而提出的各项策略都无法收到预期的成效。与依附论不同,世界体系论是倾向于对既定的社会现象进行历史分析的,这可能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中的一种回归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风气。所以,当美国学者遭遇了来自拉丁美洲的依附论时,立即就发现了其中缺乏历史分析的缺陷。但是,依附论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描述又包含着把整个世界看做是统一体系的内涵,正是这一点成了世界体系论赖以生成的生长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依附论传播到美国后促成了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是在对依附论的继承和改造中形成的。
1974年,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世界体系论”创立的标志。依附论对沃勒斯坦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2011年版序中,大致描述了他的思想演变过程。根据沃勒斯坦的描述,他在准备写作《现代世界体系》时仍然沉迷于现代化理论的魅惑之中,他的最初写作计划是想通过研究16世纪一些国家的兴起去理解20世纪另一些国家兴起的原因。显然,这是一种“所有国家都将遵从相似的演进路线”的假设,而基于这种假设的研究思路恰是现代化理论基本的和主要的形态。即使不是现代化理论的古典形态,也是现代化理论在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变体,而且在理论研究中已经占据了主流地位。沃勒斯坦认为,这种现代化理论是抽象的,要求跨越时间维度与历史背景而将不同国家强行拉入同一个假想的线性发展路径当中。沃勒斯坦承认,正是这种观念支配了他最初的研究思路,以至于他假设16世纪那些国家(后来的中心国)获得发展的原因是可以解释20世纪那些新兴国家的发展的。那样的话,就会努力去证明当前落后的国家也可以依据同样的路径在未来获得同样的发展。然而,正是依附论的理论观念和独特视角让沃勒斯坦在思想上发生了大转变,不仅放弃了最初的研究假设和思路,还向现代化理论发起了严厉而有效的批判;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依附论的观点,还在其影响下最终形成了世界体系的分析单位和研究方法。沃勒斯坦坦陈:“我赞同像萨米尔·阿明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等所谓依附论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与‘现代’二者同时产生。”[4](P xviii)的确,这是依附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那就是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并不是前后相继地存在于某一个线性发展道路上的,而是并存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从沃勒斯坦的这些描述中可以猜想到,他在接触了依附论后受到了震撼,从而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从逐一考察不同国家的最初设想转向了考察不同国家并存的世界,从而形成了世界体系论。
在依附论迈出拉丁美洲而走向世界的同时也走向了衰落;在它激荡了沃勒斯坦的头脑并催生了世界体系论之时,则把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力消耗掉了;在把世界中心—边缘概念传递给世界体系论的时候,也把自身的理论缺陷暴露在世界学术界面前。此后,尽管还不能说依附论走向了沉寂,但其理论影响力发挥作用的范围与持久度都让位给了世界体系论。一些早期的依附论学者(如弗兰克、阿明和多斯桑托斯)也自然或不自然地转向了世界体系分析,他们或者吸收了世界体系论的某些理论成果,或者接受了世界体系论的某些标志性概念,或者借鉴了世界体系论的某些研究方法。当然,在学术界存在着把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混同的做法。其实,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沃勒斯坦一再强调他的世界体系论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分析方法,但在那些采用了世界体系视角的依附论学者与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就中心—边缘概念及其解释框架的应用而言,事实上存在着从依附论向世界体系论转变的轨迹,可以说,世界体系论是继依附论而兴起的一种新的理论。在一段时间内,随着世界体系论的世界影响日益扩大,一些依附论学者出于维护依附论的需要而吸纳了世界体系论的某些理论元素,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的学术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依附论学者转而信奉世界体系论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发源于拉丁美洲(边缘地区)的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曾经的中心地区语言,通过殖民扩张成为殖民地的官方语言)为主要书写语言的依附论逐渐让位于兴起在美国(当前的世界中心)的以英语(世界的主导语言)为表达语言的世界体系论时,一些学者希望搭乘世界体系论的时髦快车,也是这个世界中非常自然的现象。所以,许多依附论学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学术声望而转投到了世界体系论的门下。这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可以用普雷维什以及部分依附论学者早已揭示的话语霸权或“智力依附”来做出解释。
二、世界体系论的中心、边缘与外围
依附论虽然是在世界体系中去把握中心—边缘结构的,但是,其分析单位则是民族国家,是先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确定民族国家的地位,然后再分析边缘国家落后的原因,并提出边缘国家的发展策略与路径。与依附论不同,世界体系论则努力把整个世界作为分析单位,是要在世界体系的历史中去寻找发展路径。所以,可以认为世界体系论弥补了包括依附论在内的各种理论关于发展问题的不足。但是,世界体系论又受到了依附论的影响,是在依附论所取得的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继起的理论,世界体系论努力去修补依附论,并在发展的问题上尝试进行理论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思想的进步。在沃勒斯坦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可见依附论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直扣住了“中心—边缘”的概念*沃勒斯坦也曾将“中心—边缘”概念的发明归功于普雷维什,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V: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1789—191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他在其中创造性地加入了“半边缘”概念和分类。不管“半边缘”这个新概念是否合理,都表明它是来自于依附论又发展了依附论的。参见《沃勒斯坦精粹》,1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而进行理论阐述。同时,沃勒斯坦在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等方面,也确实进一步丰富了中心—边缘概念的内涵。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阐述了中心与边缘之间在经济结构、劳动分工与劳动控制、国家力量、文化构成等多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其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关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不同位置的分析,他通过这种分析而对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做出了具有信服力的解释。沃勒斯坦将历史上的各种劳动控制形式铺展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指出“奴隶制和‘封建制’在边缘地带;工资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在中心地区;我们将看到的分成制佃农在半边缘地带”[5](P89)。沃勒斯坦还着力探讨不同地区采取特定劳动控制形式的复杂原因及其结果,尤其通过对不同的劳动分工与劳动控制形式的分析而弄清了剩余价值是如何向中心地区集中的问题。沃勒斯坦将视线集中在劳动控制方式上,他解释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上,在这个经济体系的不同地区(我们称之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分别被指派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了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采用了不同的劳动力控制模式,并且从这一体制的运作中获利是不平等的。”[6](P170)
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导致了不同地区间的不平等,致使边缘地区采用了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劳动控制形式。中心地区之所以能够采用相对自由的劳动方式,之所以既发展了畜牧业又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之所以货币租佃制和工资劳动制能够得到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在形成”[7](P101)。也就是说,由于中心地区建立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才能够在发展畜牧业以满足市场需求时不会遭遇粮食短缺的问题,那是因为边缘地区能够源源不断地为中心地区补充粮食。由于边缘地区承担了中心地区的部分农业劳动,从而使中心地区的一些劳动力从早先的农业活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地区所采用的不是边缘地区的那种需要大量监督人员的劳动控制方式,也使一部分劳动力得以解放出来,并成为中心地区发展工业的人力资源。相比之下,边缘地区的劳动控制形式则是“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不仅农业生产占用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劳动监督也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以至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处于劣势地位。
根据沃勒斯坦的考察,在16世纪的一些边缘地带(如东欧和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所实行的是“封建制”,但这种封建制与中世纪欧洲典型的封建制又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沃勒斯坦所说的“封建制劳动方式”就是指这种“强制性商业作物劳动制”(coerced cash-crop labor),这一制度中的农民是被法律强制劳作的,是为世界市场而非地方经济而从事生产的,制度的运作也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因此,这是一种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组织和劳动形式,是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是与典型的封建制不同的劳动方式。在对这种“封建制”劳动给出了定义后,沃勒斯坦指出,中心与边缘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共存的两类主体,他指出:“弗兰克在谈到现代世界时说:‘经济发达与不发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暂时表现和必然结果’。”[8](P94)正是因为中心与边缘同属于一个体系,所以,中心与边缘的发展同属一个历史进程,由边缘向中心的利益输送才成为可能。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利益传送机制,才造就了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如此一来,“剩余产品完全不成比例地流入中心地区,满足那里的人们的需要。企业的直接利润,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中心地区诸群体、国际贸易群体和地方当局官员(诸如波兰贵族和西班牙美洲的官吏及委托监护者)中瓜分。人民大众被迫从事劳动,而这种劳动制度又为国家及其司法机构所规定、限定和推行。当有利可图时,仍然使用奴隶制,但当这种靠极端严酷的法律来维持变得得不偿失时,一种表面自由但实际上法律强迫的劳动制,就在生产商品粮的领地上推行开来”[9](P96)。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正是这样在中心所安排的分工下“各司其职”的,并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运行着。
从沃勒斯坦对劳动控制形式所做的细致分析中可以看到,世界体系论在使用中心—边缘概念时,是努力将这一概念放置在更广泛、更细致的历史分析之中的。这种分析的细致性从沃勒斯坦如下的提问中可见一斑:“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心地带统治着边缘地区。但中心地带太大了。是热那亚的商人和银行家在利用西班牙呢,还是西班牙帝国主义者吞并了部分意大利?是佛罗伦萨支配里昂,还是法国统治伦巴底?或是二者兼而有之?”[10](P112)这正是沃勒斯坦所要探究的。尽管沃勒斯坦的分析方法和言辞表述常常让论题显得非常繁复,甚至有时前后矛盾,但是,对于中心剥削边缘、边缘依附中心、世界中心从荷兰移向英国再转到美国等等这样的简单化表述,沃勒斯坦显然是不满意的。在空间层面,他努力寻找并界定各历史时期的中心与边缘,希望确认究竟哪些区域是中心抑或边缘,而不是简单地以某个民族国家的名称来称呼。同时,沃勒斯坦还希望为包括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在内的世界体系确定边界,并试图对这些边界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动的情况进行确认。当然,这要回到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一词的界定中。沃勒斯坦一再强调,“世界体系”中的“世界”一词并不是“全球”的同义语,尽管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中的主导体系,在它之外,还有其他体系存在。另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又是逐步扩张的,不断地将外围地区纳入体系之中,并使它们成为围绕着中心的边缘。
沃勒斯坦认为,直到16世纪末,欧洲经济体系并不包括印度洋地区,也不包括远东地区(除了某一时期的菲律宾)和奥斯曼帝国,甚至可以说不包括俄罗斯。沃勒斯坦特别指出,并非与中心区有贸易往来的地区都能被归入体系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贸易的数量,也不在于贸易的构成,甚至不在于利润的获取,而在于贸易的性质以及这种贸易是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举例而言,尽管15世纪的日本与葡萄牙人之间也存在着贸易往来,尽管16世纪的俄罗斯也是用原材料去换取西方的制成品,尽管西欧在与亚洲的贸易往来中也攫取了大量利润,但是,并不能据此就认为这些地区已经在世界体系之内了。相反,它们仍处于体系之外,属于外围,而不在中心—边缘结构之中。沃勒斯坦的标准是,处于世界体系之内的中心与边缘之间所进行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而非奢侈品的贸易。这是因为,相对于消费奢侈品而言,作为生产剩余的必需品贸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贸易关系也相对稳定,这样的世界体系才可能是稳定的和长久的。至于原材料与制成品间的交换是否属于世界体系内的贸易,沃勒斯坦认为是不能做出简单化判断的。根据沃勒斯坦的意见,要将原材料与制成品的交换看做是发生在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还需要包括另外两个附加条件,即“保持原材料低价进口的政治经济能力及在中心国家的市场上与其他中心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11](P219),否则,英国也会因为曾作为其他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地而被称为边缘地区了。在利润方面,与中心剥削边缘相比,中心从外围区的获利既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关于赢利性的讨论还是清楚地表明在外部领域通过贸易获利的局限性。毕竟利润就是掠夺所得,经过一段时间掠夺就自我毁灭。而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体框架内的剥削却在自我加强”[12](P425)。
依附论学派在谈论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时,并未在“边缘”与“外围”之间做出区分,所以,我国学者在翻译依附论学派的相关著作时,时有将边缘译成外围的做法。但沃勒斯坦对边缘和外围予以明确区分,除了基于贸易的性质做出这种区分外,他还从国家机器和城市市民阶层等方面去考察边缘地区与外围地区的不同。比如,他认为俄罗斯尽管在16世纪与英国等中心国之间有着贸易关系,却属于世界体系的外围区。沃勒斯坦关于边缘地区(periphery)与外围地区(external arena)差异的特别关注和细致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说是沃勒斯坦对中心—边缘概念给出的新定义,也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正确解读。正是沃勒斯坦的这种解读,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世界体系不断扩张的特征。也就是说,由于沃勒斯坦对边缘和外围明确的区分,才让人们看到,中心并不满足于仅对边缘的剥削,而是不断地吞并外围地区,不断地将外围地区纳入世界体系之中,以扩大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区范围。就此而言,世界体系论要比依附论所呈现的世界体系更有层次感。
三、“中心—边缘”概念性质的变化
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从普雷维什和依附论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概念,并在理论建构和思想叙述中加以广泛应用,但是,综观世界体系论的文献,却很难说中心—边缘概念是它的核心概念,并不像在普雷维什和依附论中那样是作为一个基本解释框架而存在的。霍华德(Michael Charles Howard)在评价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时说:“‘不发达’和‘依附’在沃勒斯坦的书中并不占中心位置,而且由于他对世界经济中所有要素间普遍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视,‘不发达’和‘依附’已黯然失色。”[13](P176)关于“发达”、“不发达”、“依附”等概念在世界体系论中的应用状况也反映在“中心—边缘”概念上。虽然沃勒斯坦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在理论体系中所给予这个概念的地位则要比在普雷维什和依附论那里低得多。当然,在学术界,人们一提到中心—边缘概念总会首先想到沃勒斯坦,可以说沃勒斯坦对于中心—边缘概念在世界学术界传播发挥了远大于普雷维什和依附论的作用,但这是由话语的中心—边缘结构所决定的。因为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者大都来自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也决定了这些学者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往往会被严重低估。作为美国学者的沃勒斯坦则不同,虽然他更多的时候似乎是不经意地使用了中心—边缘概念,却赢得了世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其实,在沃勒斯坦的著作中,中心—边缘概念所发挥的主要是描述性功能,而且,在使用中心—边缘概念时有着泛历史主义的倾向。这是因为,沃勒斯坦在考察现代世界体系的生成过程时将其推到了前现代的历史阶段,即将现代世界体系的孕育期确定为“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之后来看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既然他也将中心—边缘的概念用来描述前现代历史阶段的世界体系,也就不可能真正看到前现代与现代社会在结构上的差别。比如,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的通货膨胀时说:“通货膨胀是重要的,这既是因为它是强迫人们储蓄的机制,进而也是积累资本的机制,也是因为它通过这一体系将利润进行了一种不平均的分配,使它们不成比例地集中于我们所说的正在形成中的世界经济中心地区,这些中心地区是从‘旧’发达地区(‘old’ developed areas)的边缘(its periphery)和半边缘(its semiperiphery)中分离出来的。”[14](P84)这说明,虽然沃勒斯坦要到历史上去寻觅现代世界体系的踪迹,却是缺乏历史观的,在研究以及理论叙事的方法上,不是去历史地看问题,而是对特定历史阶段中产生的现象做出了泛历史主义的理解。
其实,世界之所以呈现出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结果,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化中的市场开拓和殖民化,才造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在前现代的历史阶段中,地域性的社会在结构上是一种立体结构,而不是平面铺开的中心—边缘结构。由于各个地域性的社会分散地存在于不同的地方,而且它们之间很少联系,并没有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所以,当沃勒斯坦认为前现代也存在着“中心—半边缘—边缘”时,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前现代与现代的界限。正是因为他所持的是一种泛历史主义的观念,才会认为人类早在“延长的16世纪”就已经逐步进入了世界体系,并认为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中心与边缘不断变换位置的位移,把大国崛起和衰落的过程都强行地放置在世界体系之中去加以解读,把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事实解读成世界体系中的假象,从而认为:过去的中心可以转化为边缘,而过去的边缘则可以走进中心。如果我们不对世界体系的生成时间进行细致考察的话,可能会同意沃勒斯坦的解读,会相信原先的中心变成了边缘,或原先的边缘变成了中心,而且,欧洲与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变动也证明了沃勒斯坦的判断。正是因为世界体系本身的历史性没有得到定义,才使沃勒斯坦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被学者们普遍接受。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在资本主义世界化形成稳定结构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因而,也并不存在着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世界体系都未定型。也只是在这一条件下,某个国家才有崛起并领先建立世界体系的机遇,才能够把自己变成世界的中心而把其他国家变成层层分布开来的边缘。一旦世界体系定型并拥有了中心—边缘结构,一个或一些国家要想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是极其困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都说明那种试图成为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未能成功。
当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结构的概念进行泛历史主义解读后,就必然会把理论判断建立在一些历史假象的基础上,从而对人们造成误导,让一些国家以为可以在既定的世界体系中改变自己的位置,即跃迁到中心。如果这种认识转化为国家策略的话,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就中心—边缘概念来看,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都是作为批判工具而加以使用的,即用来揭示既存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并包含某种要求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追求。然而到了沃勒斯坦那里,中心—边缘概念的批判性消失了,被说成世界体系原本就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别,或者说世界体系本来就应当拥有中心—边缘结构。进而,世界体系又不是被界定为资本主义世界化的产物,而是认为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这样一来,沃勒斯坦似乎是给人提供了一条通过自我发展而竞逐中心的道路,让人们以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实现向中心的跃迁,或者可能被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再一次诠释了达尔文主义,至少可以说是准确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精神。
虽然很多人都用中心—边缘概念去描述世界体系的结构,但在普雷维什和依附论那里,这种描述是批判性的,从属于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目的,特别是在普雷维什以及拉美经委会那里,为了改变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困境,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依附论是在对普雷维什及拉美经委会的批评中成长起来的,但所批评的是普雷维什及拉美经委会的不彻底性,特别是对普雷维什及拉美经委会的那些政策措施没有在改变拉美国家边缘地位方面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这一点,给予了激烈的批评。在理论倾向上,应当说依附论在使用中心—边缘概念时表达了更为激进的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追求。在世界体系论中,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被默认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即便某个或某些国家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发生了位移,也没有使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一些依附论学者主张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来描述世界体系,反对用“发达”、“欠发达”、“不发达”、“发展中”等概念去描述世界体系的状况,认为这些概念会对边缘国的政策和策略造成误导。然而,在世界体系论这里,有时把中心与边缘还原成了发达、欠发达等。比如,蔡斯—邓思(Christopher Chase-Dunn)在简述现代世界体系时说:“在当前的体系中,所谓的‘先进’(advanced)国家或‘发达’(developed)国家组成了中心,而‘欠发达’(less developed)国家则处于边缘。”[15]这显然是与普雷维什和依附论所使用的中心—边缘概念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世界体系论在使用中心—边缘这个概念时,由于概念的批判力的丧失,虽然他们也向当前的世界体系发出了责难,但在事实上,却包含着某些维护这一体系的内涵。然而,学术界往往没有看到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之间的这种不同,而是根据它们都使用了中心—边缘概念而认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或者说,认为世界体系论只是依附论在美国的翻版或再版。这样一种评论可以说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看法:“由于世界体系论在大多数方面都只是依附论在北美的因地制宜/调整的产物(adaptation),所以在理论建构方面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16]
事实上,就理论可以成为话语的构成因素而言,也同样存在着中心与边缘。一般说来,产生于中心地区的某种理论是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边缘地区的,在话语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话语通过调整自身而去迎合和适应中心话语也是常见的。但是,边缘话语中心化的情况则是极少出现的,即使边缘话语中的一些因素引起了中心的关注,甚至加以采纳了,也会对它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只有在这些因素被改造得与中心话语的精神相一致时,才会得到应用。所以,当作为一个分析框架的中心—边缘概念从作为世界边缘地区的拉丁美洲迁移到作为世界超级中心的美国时,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如果它未被改造和不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也就不可能在美国存活下来,因为它必然会受到作为世界中心的主导性话语的封杀。所以,作为一个分析框架的中心—边缘结构概念在被世界体系论移植到美国时,就不再具有其原先的理论品质,而是成了一种能够适应美国话语的“因地制宜的产物”。简言之,当中心—边缘概念从边缘迁往中心,从边缘地区学者那里转移至中心地区学者的手中,其批判力的弱化甚至丧失,也是由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的。
在中心—边缘从富有批判力和解释力的概念转化为一种死板的和形式化的描述性词语后,原先在这一概念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理论目标也就丧失了,以至于世界体系论可以用来编造一个又一个大国如何崛起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一些国家或地区是如何在把其他国家打入边缘的过程中确立起自己的中心国地位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中心与边缘,边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成为中心的;中心如果处置不当,也可能会变成边缘。对中心与边缘的这种描述,一方面,激发了边缘国向中心跃迁的梦想,哪怕是采用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提醒中心国不要麻木,要时时刻刻地实现对边缘国和边缘地区的驾驭和控制,以保住自己的中心地位,尤其是要对半边缘地区给予充分的关注。“在经济的很多(但不是全部)方面,半边缘地区居于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这特别体现在经济体制的复杂性方面、经济收益的程度(既包括平均水平,也包括限度)方面,尤其是劳动控制形式方面。”[17](P97)所以,半边缘地区随时都有可能挤进中心区,而要维护中心国的地位不变以及中心地区的秩序不受挑战,即便不是将其打入边缘,也要尽力将其稳定在半边缘的位置上。
在沃勒斯坦的著作中,“半边缘”的概念应当说是他所发明的新提法,也正是这个概念的发明,使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性质变得清晰了。对于普雷维什、依附论而言,没有必要去考虑半边缘的问题,或者说,半边缘对于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没有可资考虑的作用。相反,对于世界体系论而言,半边缘的地位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如果说中心与边缘都是相对稳定的话,那么,半边缘则是处在变动中的。也就是说,半边缘既能够成为世界体系稳定的中坚力量,也可能成为世界体系动荡的根源,中心与边缘之间是否会发生位移,都会集中地反映在半边缘的变动之中。所以,沃勒斯坦需要发明“半边缘”这个概念,需要在理论上给予半边缘以充分的重视。沃勒斯坦肯定半边缘在中心与边缘之间起到连接作用,可以对世界体系的稳固性发挥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至于半边缘这一新分类,沃勒斯坦解释说:“半边缘地区不是一种统计学上划分点的技巧,也不是一个剩余下来的类别。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必需的结构因素,这些地区起着类似于中间商群体在一个帝国起的作用。”[18](P423)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则提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来划分“中心”、“半边缘”和“边缘”。总的说来,沃勒斯坦不甚喜欢量化标准,对同为世界体系论者的阿瑞吉的这种划分标准也是不同意的。沃勒斯坦更强调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质性区分。但是,20世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较为推崇量化的方法,既然沃勒斯坦提出了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区分,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阿瑞吉的量化区分。这样一来,就等于是以量化的经济标准去划分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了。这肯定是与世界体系论的奠立者沃勒斯坦的观点不同的,却又是根源于沃勒斯坦的半边缘概念的。
半边缘概念的提出不仅包含着想对世界体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层的要求,而且直接导向了对量化方法的应用。这样一来,中心—边缘结构中所存在着的中心国(地区)对边缘国(地区)的剥削、掠夺和压制也就被完全掩盖了。正是掩盖了这一点,才能够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边缘向中心跃迁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考虑到中心对边缘的剥削、掠夺和压制的话,那么,就不再会相信边缘能够向中心跃迁了。
对于沃勒斯坦从边缘中区分出边缘和半边缘,依附论学派的著名代表萨米尔·阿明从现象上给予了准确的揭示。阿明指出:“边缘在世界体系中所担负的职责的多样化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多样化的特点使人们总是特别想对边缘加以分类。”[19](P72)沃勒斯坦的“半边缘”概念就是这种分类的表现,根据阿明的意见,“我看不到阿里奇提出的分成三类的主张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我宁愿在两极化的单义项中去分析世界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这一整体理论化相联系,对具体情况(而不是人为分组)的具体分析提供了建立抽象的一般理论的基础”[20](P74)。也就是说,边缘显然会有着多样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这种多样性不仅仅是由于边缘地区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数量众多而引起的多样性形式,而是中心采用多样性的剥削、掠夺和控制手段造成的。无论边缘在表现形式上如何具有多样性,但与中心的关系却是单一性的,它们之间所构成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即便存在着半边缘的经验事实,那么,在时间的维度中,半边缘总会被打入边缘,而不是向中心跃迁。即使经济发展以及GDP超过了中心国(地区),而在政治和话语方面,依然受制于中心国(地区);无论表面上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而实际上依然是承认和接受中心国(地区)的霸权,甚至会出于一时的利益考虑而为中心国(地区)的霸权鸣锣开道。
总之,尽管中心与边缘是互动的,但这种互动并不会表现为相互向对方转化。在此意义上,沃勒斯坦的半边缘概念其实是模糊了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属于维护当今世界体系需要的。这一点也许是潜藏于所有中心国学者的意识深处的,即使他们在研究中努力表现出某种所谓的“客观”或“中立”,但透过他们的文字,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种维护当今世界体系的潜意识无处不在。至少可以说,即使沃勒斯坦本人声称是在批判当今世界体系,并进而提出了对未来的某种模糊想象,但就其理论结果而言,他的半边缘概念则会(事实上已经)被他人用于对既存世界体系的维护,或者说去替中心—边缘结构作辩护,而不是提出打破这一结构的要求。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理论倾向是极其有害的,会将中心与边缘引入更强烈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从而加重全球风险。
[1] Thomas R.Shannon.AnIntroductiontotheWorld-SystemPerspective.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
[2] 萨米尔·阿明:《论脱钩》,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4);Amin,Samir.“A Note on the Concept of Delinking”.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1987,10(3):435-444.
[3] Thomas R.Shannon.AnIntroductiontotheWorld-SystemPerspective(Second Edi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6.
[4] Immanuel Wallerstein.TheModernWorld-systemI:CapitalistAgricultureandtheOriginsoftheEuropeanWorld-economyintheSixteenthCentury,WithaNewPrologu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5][6][7][8][9][10][11][12][17][1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3] 霍华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4] Immanuel Wallerstein.TheModernWorldSystem:CapitalistAgricultureandtheOriginsoftheEuropeanWorldEconomyintheSixteenthCentu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15] Christopher Chase-Dunn,Peter Grimes.“World-Systems Analysis”.AnnualReviewofSociology,1995(21):387-417.
[16] Daniel Chirot,Thomas D.Hall.“World-System Theory”.AnnualReviewofSociology,1982(8):81-106.
[19][20] 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林 间)
The Concept of Core-Periphery in the World-System Analysis
ZHANG Kang-zhi,ZHANG T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In the late 1970s,the dependency theory began to decline,giving its way to another school of thought named the world-system analysis. The world-system analysis inherited the concept of core-periphery from Prebisch and dependencies,put it into a more detailed historical analysis,and even remold this phrase by creating a new term of semi-periphery. The world-system analysis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origin,consolid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system and to explain how and why the surplus value had flowed into the core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However,core-periphery in world-system analysis is only a descriptive term with a lack of criticism,which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analysis of Prebisch and dependencies. In other words,though the world-system analysis originating from the core and the dependency theory from the periphery have used the same concept,they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concept. Specifically,the dependency theory had raised a claim of breaking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through explaining the concept,while the world-system analysis used the concept only for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dependency;world-system analysis;core-periphery;semi-periphery
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
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