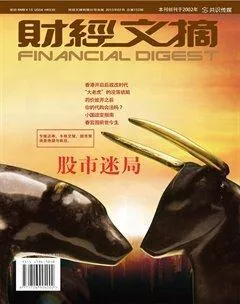伫立溪畔,任感官奔走
苏洁
在经历了一场几乎致命的肺炎之后,27岁的安妮·迪拉德在弗吉尼亚州的听客溪旁生活了一年。与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经历类似,安妮把在听客溪独自探索的这一过程称为“朝圣之旅”。一年的时间里,她是自然的观看者,也是一位完全的融入者。
在安妮笔下,大自然是丰沛而美丽的,如她的文字,随意,却充满了精细的美感:
“有一天我去察看那喧哗;我走向一棵树,一棵桑橘,结果上百只鸟飞了开去。就那样突然从树里面冒出来。我走近一些,又有上百只鸟飞走。……我再看那棵树,叶子又都聚拢一起,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我直接走到樹干旁,最后的一百只顽抗的鸟出现,散开,而后消失。怎么会有那许多鸟躲在树上,而我却没发现?那棵桑橘一叶不乱,与我在屋中所见未有不同,而那时其实正有三百只红翼燕八哥在树梢叫着。”
而大自然并不只有美好。《听客溪的朝圣》的后半部分,安妮转而开始阐释自然的残酷:寄生物将宿主从肚子里吃空,生命的传承基于这样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浪费,那些朝生暮死的虫子,产下成千上万的卵,死掉无数,单单靠其中的硕果仅存者,便成活了一个物种。她也因此发问:“神啊,看你把这个生命弄成什么样……难道这样荒谬地,真的是为了这个,我才在这个无意识的星球上,和我那些无辜的同类玩垒球玩上一整个春天?”
在十五个章节中,安妮其实在通过听客溪边一切动植物,消化那些她从书本上读来的和文明社会中得来的知识与受到的教育。她希望能解释这个自然界的真实面目。对寸步未离听客溪的安妮来说,朝圣并非以双脚步向圣地,更像是在思索的旅程中朝圣。
安妮开始“醒来”。比如在寻找麝香鼠时:“这世界上有野生动物存在,此事本身就令人为之大声欢呼,真正看到它们的那一刹那也令人大声欢呼。因为它们有美好的尊严,宁愿不要和我扯上什么关联,甚至不愿成为我观看的对象。它们以其谨慎之道来告诉我,光是张开眼睛观看,就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我从前也受此干扰:就是没法儿忍受如此之丧失尊严,为了一只麝香鼠竟然会完全改变整个生存的方式。因此我会移动身体或四处张望或抓抓鼻子,麝香鼠则一只也不出来,只剩我独自一个,带着我的尊严。连续好几天,直到我决定学习潜行——直接向麝香鼠学习——是值得的。”
当懂得沉浸在当下、忘我,学会真正的“看”,终于,在一开始就借经文的发问“天与地与其间万物,汝以为吾戏作乎?”得以解答,“阻隔在创造者和我们之间的,即我执……创造本身因为其自由的本性而无可怪咎,只有人类的感受乖离地出了错”。
安妮·迪拉德朝圣的意义在于此,而对打开《听客溪的朝圣》的人来说,一切似乎简单,如译者余幼珊在译后记中所言:“无论大自然是美丽还是残酷,无论神是善是恶,迪拉德以这本书,以她细腻而又活泼大胆的文字,带我们一同前往听客溪朝圣,‘从上游到下游,欢欣鼓舞,头晕目眩,跳着舞,和着那一堆赞美的银色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