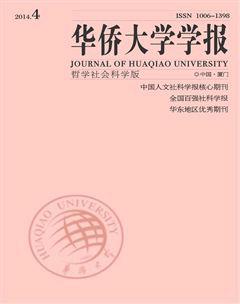福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模式、机制及其适应性研究
和红
摘要:
依据“养老服务供给来源”可将福建现行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划分为集中居住服务、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和互助养老服务三种模式。每种模式有其独特的运作机制和建立及普及的适应性条件。处于起步阶段的福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不可避免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服务供需不匹配、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和专业服务人员缺乏等共性问题,须因地制宜地选择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开办形式,规范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运行,转变养老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格局,加强专业养老服务队伍建设,以构建福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关键词:福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运行机制;适应性条件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4) 03-0134-07
福建省人口老龄化和空巢化都出现较为严重的城乡倒置。2013年全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76万,占总人口的12.61%;其中,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21.4万,占全省老年人口总数的67.52%;农村老龄化率为21.7%,高出城乡平均水平9.09个百分点数据来源于《2013年福建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未富先老”的困境在农村表现更为突出,农村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不仅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承受着体力上的考验,相当一部分老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等重体力劳动,更面临着严重的情感与精神危机。长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又造成农村养老保障能力明显弱于城市,做好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尤为紧迫。
一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一)农村养老服务模式
养老服务模式指动用社会化的资源和设施,利用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等多方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健康等必要的养老服务的稳定方式。学界关于养老服务模式的分类以及分类标准尚存在分歧。例如,在资源筹集方式上,养老服务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运作型、民间互助型和混合型模式;在服务提供方式上,养老服务可分为政府运作型、非营利组织运作型和混合型模式;在服务享受条件上,养老服务可分为无偿服务型、低偿服务型和有偿服务型模式;在居住方式上,养老服务可分为机构养老型、集中居住型、居家养老型、社区养老型模式。实际上,上述划分标准内部存在交叉,例如居家养老服务在服务享受方式上既可以是有偿、也可以是低偿甚至无偿;集中居住在资金筹集上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实践中的每一个具体模式的运行机制包括资源筹集、服务供给方式、服务享受条件、居住方式等方面,上述划分标准仅从一个侧面反映服务模式的运行机制,难以反映养老服务模式的全貌。本文借鉴穆光宗的“养老支持力来源”[1]54概念,提出“养老服务供给来源”标准来划分养老服务模式,一种养老服务模式可能有多种的养老服务供给来源,那么主要的养老服务供给来源就决定了这种养老服务模式的特征。
1.集中居住服务模式
集中居住模式是指老年人入住本村的“敬老院”、“颐老乐园”和“慈善幸福院”等老年人的集中居住点,采取“离家不离村、村中享天伦”的方式安度晚年。这种模式是将机构养老和社区照顾这两种方式的优点集于一体的社会化养老方式,类似一个服务全面的小型养老院。集中居住点建设的初衷是解决空巢、特困高龄老人的“吃饭难”和居住环境差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晋江大浦村敬老院。村敬老院向全村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开放,现已有近200位老人入住。每月举办一次老人生日宴会;挂钩卫生院每星期两天入院义诊,小病由敬老院免费提供日常药品。晋江现已建成16所村级敬老院,计划每年将新建或改建20所综合性村级敬老院。二是永安吴坊村“颐老乐园”。“颐老乐园”配有专门床位供空巢老人入住,通过开办老年互助食堂,解决了空巢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在总结“颐老乐园”经验基础上,永安提炼出空巢老人“三助康乐点”的建设。“三助康乐点”主要采取“三助”的服务形式,自助即依托家庭成员的赡养义务,空巢老人尽其所能解决自己生活起居问题;互助即开展搭伙入住共同生活,空巢老人各尽所长互相帮助解决生活照料问题;帮助即组织社会资源和志愿者帮助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采取“三自”原则规范运作,自愿即老年人自愿申请搭伙入住共同生活;自费即老年人搭伙入住生活费用自理;自负即搭伙入住的老年人风险责任自行承担。永安已建成41所“三助康乐点”。三是蕉城黄田村慈善幸福院。蕉城黄田村慈善幸福院已入住16名老人,幸福院在当地人气相当高,附近村庄共有60多名老人报名申请入住,现已进入扩建阶段。蕉城区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建设30所农村慈善幸福院,涉及50个行政村,拟容纳580个五保户和孤寡老人,总投资2000万元。
2.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养老服务由社会提供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模式。就制度定位而言,居家养老服务是“福利多元主义”在老年人福利领域的体现,社区通过整合社区资源,联系基层政府组织,协调家庭与社区之关系,为社区内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一系列养老服务[2]117、[3]184-187。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南安珠渊村的“老年人之家”。“老年人之家”设有便民餐厅,凡是年龄70岁以上老年人均可报名参加,其中,70岁至79岁每月缴纳90元,80岁至89岁60元,90岁以上老年人以及计生“二女户”、“五保户”、“低保户”的老年人全免。“老年人之家”还设置老年人宿舍,目前提供给80岁以上的老年人午休使用。二是石狮灵秀镇塔前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中心设施配套十分齐全,拥有老年学校、图书阅览室、日间照料室、养生保健室、健身室、棋牌室和厨房等设施,为本村老年人提供一处集居家、养老、娱乐、保健、健身、养生于一体的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三是武平七坊村“农民之家”。成立医疗、低保、青年等多支义工服务队,上门为结对帮扶的老年人打扫卫生、清洗衣被、买菜、做饭、代购物品、送煤气等。组织村民家庭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明确规定赡养人对被赡养人关于生活照料、疾病医护、经济供养、农田耕作、精神慰藉、财产监护、寿寝安葬等10多项赡养义务。武平已签订农村“家庭赡养协议书”6300余份。
3.互助养老服务模式
“互助养老”模式自发在基层产生,是老年人基于友爱互助、相互信任的基本原则在基层社区实现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该模式符合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文化中老年人对家庭、朋友和社区邻里的依恋,顺应了居家养老制度对家庭和社区养老资源的高效利用,在政府和相关专业组织的正式社会支持体系下,是增强家庭和社区养老功能的重要尝试[4]36-42。“互助养老”作为一种互助共济的养老观念和实践在福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目前发展的比较好的有三种形式:一是农村老人间的互助。德化探索出“党支部+老年协会+互助组+志愿者”关爱留守老人机制,目前共有187个村(社区)建立该机制,组建互助组465个、成员6052人,建立留守老人服务站109个,建立老年人档案12315份;设立村(社区)“关爱老年人幸福基金”83个计487.52万元。承泽村组建理发、刮痧服务、生产互帮等三大互帮组,共有30名成员,又按角落分成三个互帮小组开展“生产互帮、生活互帮、经济互帮、精神互帮”等四互帮活动。二是志愿者互助。尤溪西城镇老人互助会创办于1987年,目前共有3831名会员,不仅为会员提供养老服务还为1808名老人送终。镇政府将“卢家大院”(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委托给互助会管理使用;将大院里部分房屋出租,租金作为互助会开展活动的补贴经费。三是以“时间储蓄”为载体的轻老互助。连城溪尾村早在2008年成立了全省首个农村居家养老的服务机构——照料储蓄社,以妇女为主要成员。社员自愿为老年人提供护理、照料、家务、耕作、寻医、聊天等生产生活方面的服务,并将帮扶照料的内容、时间记录下来,到自己需要照顾帮助时,根据各自储蓄的服务时间和内容,可优先享受到其他社员的帮助。以“时间储蓄”为载体的“互助”,以基层社区为依托,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实现了老年人间的友情互助资源的流动,并对老年人需求和老年服务的累积有专业的评估指标和计量方法。
(二)农村养老服务运行机制比较
集中居住模式的服务对象具有较强的社区和公益属性,服务对象为本村的五保、低保、孤寡和空巢老人。从资金筹集方式上看,主要有两种类型,主要是采用村集体筹资兴建集中居住点, 大埔村敬老院是村集体筹资兴建的典型。而农村慈善幸福院的建设主要依靠省慈善总会和区政府出资,建设完成后,区政府将按入住人数的情况分别给予每所慈善幸福院专项管理经费,乡镇每年也配套一定的经费。从服务供给方式上看,集中居住点对大多数老年人提供免费入住,只对少数经济条件好的老年人象征性地收取一定费用。黄田村五保户老人由政府财政供养,如果空巢老人想入住每月只需交300元。从管理模式上看,集中居住点一般设有服务管理部,聘请专职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三明“三助康乐点”的日常管理主要由村“两委”委员和老党员、低龄志愿者承担。
居家养老服务站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五保、低保、重点优抚、“五老”等特殊群体,更覆盖了有需要的全体老年人,特别是一些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在服务站的建设上,各地充分利用老年活动室、文化室以及闲置办公服务设施进行改建。服务站的运行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补贴、村集体经济、企业捐赠和个人缴费。例如泉州市为每个服务站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各负担50%。武平已建成的38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中,已有10个村发动本村经济能人和乡贤捐赠成立助老基金或慈善基金,金额达600多万元,将基金投资收益用于老年服务活动。有些村还划出固定资产,用租金收益扶持居家养老服务。服务站的服务供给方式以无偿服务为主,政府购买服务为辅。服务站的组织实施大多由村委会承担,村两委干部和团支部书记、妇代会主任等组成专兼职助老服务队,指定人员负责服务站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农村互助社的运行和管理权完全交由互助社承担,互助社是由低龄、健康老人等志愿者组成,会长由老人协会会长或者村支书(村主任)兼任。基层党政部门和村委会主要承担资源提供、宏观指导的职责,主要包括给予一定资助、制定优惠政策、组织开展培训、进行管理服务指导等。虽然基层党委不直接参与互助社的日常管理,但是在起步阶段基层党委动员、组织作用必不可缺。互助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接纳政府资助和社会公众捐赠。互助社的服务群体多为农村空巢和留守老人。互助社的服务供给方式主要是开展定期聚餐、相互照料、协助处理老人日常家务和生产劳动、协助联系子女等服务(见表1)。
表1三种养老服务模式的运行机制比较
集中居住服务模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互助养老服务模式
服务对象具有较强的社区和公益属性,服务对象为本村的五保、低保、孤寡和空巢老人。不仅包括五保、低保、重点优抚、“五老”等特殊群体,更覆盖了有需要的全体老年人,特别是一些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多为农村空巢和留守老人。
资金筹集主要有两种类型,主要是采用村集体筹资兴建集中居住点;但农村幸福院是由省慈善总会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出资兴建。运行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补贴、村集体经济、企业捐赠和个人缴费;有些村还划出固定资产,用租金收益扶持居家养老服务。主要是接纳政府资助和社会公众捐赠。
服务方式大多数为老年人提供免费入住,一些地区只对少数经济条件好的老年人象征性地收取一定费用。以无偿服务为主,政府购买服务为辅。免费向困难老人提供定期聚餐、相互照料、协助处理老人日常家务和生产劳动、协助联系子女等服务。
管理模式一般设有服务管理部,聘请专职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也有部分村庄将日常管理主要由村“两委”委员和老党员、低龄志愿者承担。组织实施大多由村委会承担,村两委干部和团支部书记、妇代会主任等组成专兼职助老服务队,指定人员负责服务站日常管理服务工作。运行和管理权完全交由互助社承担,互助社是由低龄、健康老人等志愿者组成,会长由老人协会会长或者村支书(村主任)兼任。
设施建设多为新建居中居住点。利用老年活动室、文化室及闲置办公服务设施进行改建。对服务设施的建设没有太多要求
二农村养老服务模式的适应性条件
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家庭关系、社会基本网络的特点以及社区组织形态密切相关[5]66-70,短期内建立“普适性”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农村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实施必须遵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权衡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区域差异和城乡差距的存在决定了农村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应有所侧重,在构建过程中应体现农村养老服务模式的“适应性条件”。
村级敬老院对入住的服务群体有较强的选择,基本上是接纳健康的、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生活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被拒绝在外,这主要是因为村级敬老院依靠现有服务条件和医疗资源还无法实现对失能老人的护理和照料。越来越多的失能的空巢老人正在考验着农村养老体系的建设。一些发展较好的村级敬老院正在探索如何实现“医养结合”、“护养结合”的模式,希望未来能够实现对健康老人和失能老人的共同接纳。以上三种形式的集中居住模式都在所属县域(城区)内得到了积极的推广。然而,落实到具体每个行政村的建设实施上,资金和土地往往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制约因素。因而,在农村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还不可能完全普及这种集中居住模式,所以现阶段政府需要支持和引导经济发达村庄改建或新建集中居住点。
居家养老服务站具有建设成本低、布局设点灵活的优势。对于村财较小的地区也能承受。经济发达地区更是有能力超前完成居家养老服务覆盖大多数村的任务。例如,石狮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正进入高峰期,至2015年底将实现全市农村全覆盖。农村开展居家服务的真正困难不是建站设站,而是如何持续运营和管理。乡村极少有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组织化或市场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在农村基本上处在空白状态。如果采取市场化运作,要考虑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付能力、思想观念、及是否愿意自掏腰包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因而,在农村发展相对滞后、有效需求少、集居化程度低的背景下,开展居家养老服务难度很大,将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搬到农村是不合适的。
互助模式变“弱势群体”为“参与主体”,引导老人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生活、生产、经济、精神互助和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帮助老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实现从被别人照顾到帮助别人的转变。在村落财力不足、养老服务资源短缺和养老服务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互助社可以有效地缓解农村养老压力。然而,互助模式本身存在着较强的不确定性,带有一定风险。一方面低龄老年人是互助社的主要参与者,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好,尚能从事一些田间劳动或者一些非农业生产,实现自我照料并开展帮扶。但是随着人口高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村的老龄人口结构将进入深度高龄化阶段,而一旦农村高龄老年人口占绝大多数,其自我照料和帮扶他人能力必然不断降低,这种互助养老模式也将失去重要的支撑条件。另一方面互助模式在为脆弱老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由于低龄老人缺乏专业培训难免有服务不到位的情况,粗放式的服务甚至可能出现事故;农村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参加群体也多为轻老,老人年的互助链条也就容易受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影响而中断。
三养老服务模式及运行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地在发展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上进行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和有益的探索。然而,由于受到原有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生产生活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根据调研资料,对现阶段福建省农村各种养老服务模式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在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中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从全省范围来看,农村养老服务发展起步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较落后,因此各地级市在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大都将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作为最重要的事项。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的整体水平,为满足农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硬件基础。但是,有了硬件设施不等于就有软件的养老服务,如果没有对养老服务设施和场所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养老服务设施就会成为“空壳”或“摆设”,更加谈不上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真正亟需的服务。一些农村老年日托站由于缺乏规范的管理机制,最终只是成为健康老年人的娱乐场所,没有真正起到日间照料的作用,甚至有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更是沦为年轻人打麻将的场所。
第二,“计划性的服务导向”引致农村养老服务供需失衡。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财政支持格局基本决定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市级财政的资助比例较大,基本上决定了全市统一的工作流程和方法,各区(县)根据财力及实际情况在“市级大纲”的范围内进行适当配套补贴。基于此,各级民政部门按照确定的规划来考核下级,如果没有达到上级布置的任务,可能会减少对农村养老服务站的后续财政支持,这样,各养老服务站首要的工作就是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有时也可能忽视了老人们的真正需要。养老服务供需不匹配既造成养老公共服务资源的浪费,又不能有效满足农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6]22-23。
第三,地方政府执政理念加深农村养老公共服务的区域不均衡。经济发达的县(市)乃至村落的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很大程度得益于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也印证了农村养老保障作为一种再分配政策,其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是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的唯一决定因素。例如德化山区和尤溪县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创新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决定一个地区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绩效,同时,经济发展水平高也并不意味着当地政府就会给予农村地区更多的公共养老资源。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影响农村养老保障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7]15-21。基于政绩的考虑,市县两级财政都倾向于支持补贴原有基础设施条件好或者已经发展较好的服务站,真正有需要建站的贫困地区很难得到补贴,造成许多贫困的村落开展养老服务“先天缺失,后天不足”。
第四,农村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缺乏。大部分居家养老服务站由村干部或老人协会理事负责,无论是从专业素质上还是从时间精力上都难以保证农村老年人口服务质量。因待遇较低,各服务站甚至无法聘请到相应数量的工作人员,使得整个为老服务队伍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服务质量始终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只有个别服务站已能提供相对较为全面的居家养老服务,大多数服务站的服务内容只能停留在简单的家政服务上,像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项目都无从谈起,更谈不上提供文体娱乐、精神慰藉等服务。其次,农村社区志愿服务人员少,而且主要以轻老和妇女为主,致使现有志愿服务活动具有阶段性、临时性的特点,缺乏长期运行的机制保证。
四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首先,因地制宜地选择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开办形式。经济条件优越的村,可通过对废弃的医院、学校、办公场所等进行改造装修,或在有土地资源的地区新建农村幸福院、村级敬老院等集中式居家养老设施;经济较好的拆迁村,可按照“集体建设、无偿居住、旧宅收回、配套服务”的模式建设老年公寓,鼓励村民在农村幸福院、村级敬老院、老年公寓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现有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为基础,整合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场地改造成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尚不具备条件建设农村幸福院(老年公寓)和照料中心的自然村,可选择村里闲置或废弃的房子,进行简单改造、装修,建成农村互助服务点,作为老年人日间休息、聊天、娱乐的场所,以解决偏远山区老年人生活照料、心理慰藉等问题。
其次,规范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运行。一是市级层面应尽快制定出台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统一化标准,从性质定位、发展模式、资金来源、运营管理、政府职能和机构主体的法律责任等角度对其进行统一规范,以改变当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不规范、难以评估和监督的格局,从而切实维护农村老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充分发挥县、镇(乡)级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推动、资金扶持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农村社区和村级组织在设施建设、服务管理、长效运行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形成合力,以建立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具体运行方式。
再次,转变养老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格局。各级政府明确公共财政向农村养老服务等涉及民生的社会建设项目倾斜,逐步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事业的投入;并建立按占当地一般预算收入适当比例设置养老服务事业发展专项经费的长效财政投入机制,规范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加强监督检查。在具体补贴发放时,将“锦上添花”式的发放形式转变为“雪中送炭”式,适度加大贫困地区申请开办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一次性开办补贴标准,有效缓解贫困地区开办阶段遇到的资金困境。
最后,加强专业养老服务队伍建设。一是依托市人社部门和各级民政系统的定点培训机构对养老服务人员实行免费培训,提高其服务技能,今后要加快推行居家养老服务持证上岗制度;二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为各个农村养老服务站配备专职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人员,专职工作人员应签订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并经有关部门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该岗位可以参照事业单位待遇。三是在本市职业技术学校中开设养老服务方面的新专业,保障专业人才供应。
参考文献:
[1]穆光宗.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及社会对策问题:中国的养老之路[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8.
[2]李明,李士雪.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老年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的构建[J].东岳论丛,2013,(10).
[3]吉鹏.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关系解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13,(6).
[4]陈静,江海霞.“互助”与“自助”:老年社会工作视角下“互助养老”模式探析[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4).
[5]林卡,朱浩.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目标定位的演化[J].山东社会科学,2014,(2).
[6]王莉莉. 基于"服务链"理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供给与利用研究[J].人口学刊,2013,(2).
[7]黄俊辉,李放.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绩效考察——基于27个省域的宏观数据[J].人口学刊,2013,(1).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n Fujian
HE Ho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In Fujian, the present rural social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is divided into three modes of centralized residence service, home-based care and mutual care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supply of service. Each mode has its uniqu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daptive condition of establishment and generaliz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rural social service, the common problem is highlighting construction and ignoring management, mismatch of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staff, so we need to choose the suitable rural service form, regular the operation of facility, change the pattern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team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wa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Key words:
villages in Fujian; social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operation mechanism; adaptive conditions
【责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