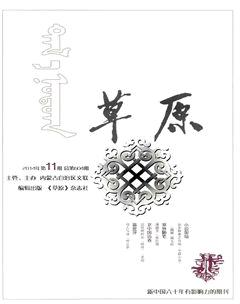记忆中的麦田
张文彪
在我住处的西边,是大片的麦田。每天回家时,我会穿行在麦田中的小道上,从春天到夏天。我看到麦田就格外有感觉,格外有诗意,我觉得,麦田就是我们的粮食,就是我们生存的保障,就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未来。一个生长于城市的人,或者生长于80后的青年,我想一定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只有经历过贫困岁月的人,才会知道麦田里蕴藏的更深层的生命含义。
从我开始记事起,我记得妈妈就开始去割麦子。早晨天一亮就起床,吃罢酸粥或酸焖饭,晾好酸米汤,就与队里的人下地割麦子,割麦子是农活中最苦最累的活,早晨,天不热,但麦子秸秆湿,不好割;中午,秸秆脆了,好割,又是烈日当头,汗流浃背。麦芒扎人,麦尘呛人,弯着腰一镰一镰割下去,腰疼腿肿,俗语说:“男人怕割麦子,女人怕坐月子。”没有亲临割麦子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份艰辛的。妈妈下地割麦子,我会和村里的伙伴一起玩耍,玩到半前晌,想妈妈了,就与伙伴们跑到地里看妈妈,在地里捉蚂蚱玩,或者到麦田附近的草滩捡鸟蛋,快中午时分,队里会派人用铁桶送来有一股烧糊味的谷米稀粥,让社员解渴,我们也跟上喝几口,然后再回家等妈妈,妈妈回来时,腋下总会夹一把芦草,那是晒干后煮饭用的,当妈妈迈着疲惫的步子,衣衫湿透,沾满麦芒,头上顶一块擦汗用的蓝手绢回到家中,喝上一口早晨晾好的酸米汤,赶快烙烙饼,再熬酸稀粥,盛夏时的酸饭,解渴解暑,委实是河套农民的佳饮。匆匆吃完饭,略展展腰,下午两点,又下地了。
当我能入学时,割麦时节,就跟着姐姐在收割后的麦田里拾麦穗了。拾麦穗是一个快乐的营生,全村所有的小孩,就跟在拉麦捆的大胶车后面,大车拉空一块麦田,我们被放入一块麦田。捡拾遗漏的麦穗,真正是颗粒无遗。其时的麦子产量很低,顶好的土地亩产也就三百多斤,均产也就二百多斤。虽然每个社里种植了大片大片的麦田,但是粮食短缺仍然困扰着人们。温饱始终是一个解决不好的大问题。麦子种的多,产的少,收割时劳力又少,割麦拖的时间也长,大约需要一月之余。每年我们姐弟三人可捡麦穗打粮60余斤,这足够一个人两月的口粮。那时,我们的家境与同村相比算好的,起码全年细粮够吃,不用吞咽口感粗糙,吃多了呕心的玉米窝头。但是对粮食的珍爱根本无需去进行“粒粒皆辛苦的教育”。
当小麦打场,全社喜交公粮后,交出去的是喜,留下来的是愁,小麦每人每年也就能分一百多斤,剩余的口粮主要是秋后的糜子,补充口粮来自于自留地,分到新粮后,虽然少,但渴望了许久的人们仍然是欢天喜地,排队日夜加工,然后烙成碱串大烙饼,吃西瓜泡烙饼,烙饼香酥,西瓜沙甜,整个村子里有一种节日般的喜悦荡漾开来,人们的笑容添了许多,话语添了许多,在艰难的岁月里有了一段难得的释然与开怀。
一直到三中全会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这一切才永远结束。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每家每户焕发出空前的劳动热情,过去割一月之久的小麦,承包后,每家的麦田最多一星期就割完了。而且大家也再无闲暇去拾麦穗了。品种的改良,科技种植的推广,不知不觉中,小麦每亩达千斤了,粮食问题不再困扰饥饿了太久的农民,一切都好了起来。
我们的生活是愈来愈好,好得不少人都忘却了其实过去并不是很久的苦难,虽然从幼儿园就开始背诵“锄禾日当午”,但是已经没人在意粮食的珍贵了,在学校食堂,整个的馒头,整个的包子当垃圾扔掉,一位老太太在忙不迭地捡拾,她用这些扔掉的“垃圾”喂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肥猪,被纳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并被上海电视台报道。各个家庭与饭店的浪费触目惊心,正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没有人在意节俭,追求的目标是奢华。关于饥饿,我们有太多的记载和伤痛,历史上的大饥荒,人民都到了“易子而食”的程度。新中国建立后六十年代的饥荒全国饿死三千万人,三千万人呢!内蒙古有多少人?巴彦淖尔有多少人呢?在浪费的同时,麦田也在大片大片地消失。今年夏天,我家西边的麦田消失了,一千多亩的一级良田,变成了住宅楼、办公楼,我们发展的欲望,享受的欲望,消灭了麦田。尽管我们有许多离城不是很远的碱地,但是我们仍然占用了良田大兴土木。或许三十年后,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每户将拥有三套到五套的大面积住宅,而我们整个民族,还能拥有多少绿油油的麦田,闪烁着金光的麦田,给生命以无尽滋养的麦田呢?endprint
——烙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