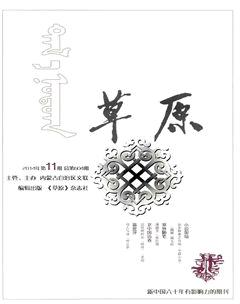二舅家的热炕头
张铁良
二舅的四儿子要给女儿办十二岁的“圆生”庆典,打电话邀我参加,我才知道这“圆生”的节目又搬到乡下演出了。出于“不将精力做人情”的想法,我对这般多如牛毛的礼数一向有抵触情绪。国人倡导“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结果,误导着世道人情的泛滥。四姑舅和媳妇离异得早,襁褓中的女儿是二舅和二妗帮他一起带大的,至今尚未再娶的他,要为没有好好享受过母爱的女儿举办一个生日“party”,我就痛快地接受了,并且要提前去“宴(夜)坐”,这样,我就理由十足地回到了常常牵挂的生我养我的小村庄。
那天傍晚,正是小村掌灯时分,我和四弟金良驾车经过一番颠簸到了村子,直抵二舅家。小院灯火通明,灶房香气扑鼻,出出进进的人们说笑着,彼此打着招呼。“宴坐”的时候,二舅的老屋也摆了酒席,我们几个晚辈陪着三位舅舅围着炕桌盘腿而坐。席间的二舅依然寡言少语,即使外甥和他多时不见,他也不会主动问我什么,最多说上一句:“你吃了哇!”
我注意到,晚上二舅家来的人不少,便对二舅说:“今晚我就睡在炕上了!”此话出口,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饭少先吃饱,炕小先睡倒”那种意思了。
土炕硬邦邦的有些硌腰,我睡在炕上很不适应。有几次想睡二舅家的土炕没有睡成,原因是条件好的亲戚硬是热情地拉我上他家住,反倒弄得自己不好意思坚持。自己要找的那种感觉别人怎么会有兴趣。
其实,我和二舅是理想与现实的两头。炕在我的眼里,是我生命最初的摇篮,我在炕上牙牙学语,摸爬翻滚,乃至摔在地下,所谓“三翻六坐九爬爬,十个月上个扎扎”的系列动作便是在炕头上完成的。炕上贪睡,常常梦中尿炕,尿渍如地图一般,母亲责备后常把褥子放在院子里晾晒,左邻右舍的伙伴故意捂着鼻子说:“羞,羞,尿炕猴!”臊得我好几天都不敢出门耍玩。
农家的土炕啊,上演了一个孩儿最初的童年故事。
后来,我走出了村庄,告别了土炕,多少年后,再睡到炕头上,便觉得心中有太多的话要说。要知道我家和二舅家是房前房后的关系,两家的房子也是前后建起的,而最关键的是我家的土屋早不复存在。我深情地与炕对话的同时,躲不开眼前的现实,炕,日复一日地承载着二舅的生活,他对炕的厮守竟成了一辈子的事情,我不敢说那是二舅对炕的“守望”,其中的无奈又怎好说清楚呢?
躺在二舅家的炕上,盯着屋顶上裸露着的被陈年的烟气熏得漆黑锃亮的木椽和筢子,再瞧瞧那斑驳陆离的墙帷子,上面有陈旧的报纸残片,我就断定农耕时代的土屋会很快风化在风中。灯灭了,我的心思漫无边际地游走着,炕的温度让我感觉到了舒服,灶坑里余火的光朦胧地照在墙壁上,幻化出一幅画面:母亲正拿着菜刀切剁猪菜,身边的哥哥们耷拉着脑袋不愿看风箱一眼,大姐坐在板凳上带头拉起了风箱,声音快一下慢一下的,一点儿都不好听。不久,铁锅沸腾起来,白色的气体渐渐挤满了屋子,吻润着泥巴墙,母亲的面孔也模糊不清了……
隔壁四姑舅家传来酒客的说话声,院子里的狗也不甘寂寞,乡村的夜晚,一切有生命的无疑都有话语权。窗户上半部分的窗格贴着的塑料薄膜被外面的风吹得“呜呜”地响,单调的没有一点倦意,感觉这风像从好远好远的地方刮来,我碰到灵魂回家,而找到根的灵魂都睡着了。二舅均匀的呼吸和偶尔的咳嗽,让我进入了“姨姨怀里闻娘香”的梦境中。
冬日黎明的鸡、狗变得迟钝,但靠窗户睡着的我还是早早地醒了,趴在被窝里透过窗子下半部的两块玻璃,读着四姑舅家的柴火园子(曾是我家的菜园),简易的草棚子下面,拴着的那匹骡子静静地站立在原地动也不动,难道骡子是站着睡觉的牲畜?倒是那头毛驴安静地卧着,天开始亮了,它也站了起来,腹下吊着一根器物。园子的东边和南边仍然被树包围着,种树的主人早已长眠地下,但树还长得那么茂盛。我索性悄悄地穿了衣服,盘腿坐在炕头上继续读着窗外的景物。我惊奇地发现,东边出现了淡淡的霞光,不远不近的树木,还有一些房子慢慢地明朗起来,起先这些参照物的背景是淡妆,眨眼功夫就绚烂起来,日头红彤彤的摆出一副磅礴欲出的架势,简直就是一幅即将出炉的乡村油画!
我急忙下炕穿鞋,提着相机疾步开门跨出屋子。
乡村的天地通透而又高阔,空气中没有任何杂质。凭借那副破烂的梯子,我摇晃着爬上了二舅家的凉房顶,顶子的松软让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选择下脚的地方。昔日的菜园、老树、断墙在初日的烘托下组合在了一起。
一张,两张……我拍着。
二舅起来了,我看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抱着柴草喂羊、喂驴、喂骡,他的背驼得上身与下身几乎形成直角,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脑海,心里酸溜溜的。
太阳每天照进屋里,照在炕上,然后悄无声息地消逝了,二舅就这样在炕上从年轻睡到年老。据说掏炕洞是人对炕的维修和养护,炕洞的通风和供暖功能足以让墙体保持干燥和坚挺,也使房主人免受潮湿和寒气之苦。还听说“人是房楦儿”,意思说房子有人住就烂得慢。可是,岁月的剥蚀让墙体的泥巴如同秋叶落地,裂痕凸现,即便及时修补也挡不住乡村最后的风景放入相册里。
此行不虚,二舅家的热炕头还能有几次睡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