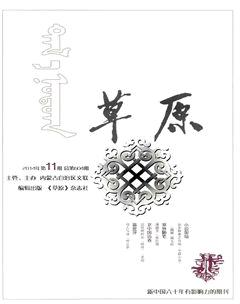马兰花开
河套叶子
迁徙
这是一株野花和一个西域古国的传说。
一个久远的故国,远走了千年,却总也没有走出人们的追忆,甚至被编织得愈发神秘和美丽。而在她的身旁还能牵扯出一连串的西域古国,不过唯有她是人们念念不忘的那一个,究竟是她曾经的华彩遗珠令人叹惋,还是仅仅因为她诗意的名字?
楼兰,谜一样的故国,谜一样消失。
我宁愿相信只有一株野花知晓其中的一切悲喜,这株花也有一个“兰”字。
故国的精魂不死,汇聚所有的悲歌、希冀和复活的渴望在一株花的茎叶、根须和花瓣上,种子椭圆,外壳坚硬,落地即裂,抛出籽粒去寻觅生根的土壤,寻觅被风刮走得到落脚的机会,寻觅被一只鸟的胃馕带着远走高飞得以落地繁衍,因而生生不息,开辟出子孙可以安身立命的一方水土。
兰花,追随一株花的踪迹,我顿悟了一件事情,很久以来困扰着我,豁然间开朗。1947年的仲秋,我的祖父赶着一辆牛车,牛和车是邻居们凑钱买来的,几家人星夜逃荒,丢下成熟在望的谷穗,远离了世代守望的村庄,简车而行,拖儿带女,除了人,还带着足够的水,充饥的干粮,粮食籽种,豆种,一捧故土。路漫漫,前程未卜,何处落脚,只听说过一个叫河套的地方土肥水美,但是此去是逃荒,不是去朝觐,一群落荒而逃的人,人家会收留吗?
人们除去身上褴褛的衣衫,除去牛皮壶里的水,除去一头老牛一辆花轱辘高车,除去逃离的热望和无着的前路,没剩下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作为礼物,赠予异乡的土地。
兰花,就在人们踯躅在村庄最后一寸土地之际,抬眼一瞥,一株马兰花在路旁的沟谷静静地吐艳,穷乡僻壤的一隅,竟然开出了如此惊艳的芬芳,围拢,跪下,双手剥离了一株花和故土的深厚情意,一株野花携着故土的暖意伴随人们远走他乡,而且将作为一份礼物移栽新的故乡,是荣耀,更是慰藉。从此,对故土的眷恋和遥思就在一株花的四季里安顿了下来。
古凉州往东北走2000多里,河套地,就在黄河边上,一株马兰花繁育播撒,我故土的第一株野花从一个新的村庄起步,或远或近迁徙,蔓延,跟随风的翅羽,跟随水的歌谣,跟随云的游踪,扎根在沙漠、草原、旷野,甚至盐碱滩上。
这株野花的河套来历,母亲曾经提起过一次,仅仅一次却根植在我的记忆里。而她仅仅说过的是在武威民勤的一洼野地里,春天开满遍野的马莲花,她和伙伴们兴奋地采摘,成筐成筐,镰刀割走了野地里的芬芳,野蜂野蝴蝶跟着孩子们走,水嫩嫩的马莲花,水嫩嫩的幽香,水嫩嫩的伙伴们,水嫩嫩的故土,水嫩嫩的春。可是那片故土越来越干旱,一连几个年头滴雨未降,只有马莲花还在一年又一年抽芽、长叶、开花,像是祈祷,像是安慰。
我似乎有了一点证据,楼兰故国曾经是马兰花最繁盛的故乡,只为一条河流的干涸,马兰花往东迁徙落脚在了古凉州城。
孔雀河畔,楼兰古城宫阙绵延望巍峨,八方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四方商贾往来络绎,丝绸锦缎绚烂华美,茶叶瓷器堆积如山,异域风情歌舞升平,一切都在繁华的激流中涌动。
如此顺畅,如此自然,没有丝毫的征兆,殊不知一场浩劫的帷幕已经徐徐开启,曾经渔歌互答,碧波涟漪,野鸟起落的罗布泊,一夜之间如繁星陨落,天外来客斩落了一朵繁花的头颅,罗布泊一片荒漠、盐渍,孔雀河铩羽而去,楼兰古城落寞残破,就像一首华丽的乐曲永久落幕,只留下空空的座位上的无限幽暗,和人们心底剪不断的一卷留恋、叹惋。
究竟也不是天外来客摧残了一个珠玉故国,仅仅四字足以概括,是天灾人祸。
就以兵燹而言,仅仅唐诗里要结果楼兰性命的出塞诗就可轻易翻出几首,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岑参“浑取大宛马,击取楼兰王”,曹唐“分明会得将军意,不斩楼兰不拟回”,就算此楼兰非彼楼兰,楼兰的强悍和繁盛已经引起中原王朝深深的忧虑,必欲去之而后快,故而渗透进了文字和文学,一说报国志必言斩楼兰。
楼兰死于一场与中原文明的较量,而楼兰遗存的精魂化作了一株野花,却被中原接纳,毕竟一株野花被轻视了,而一株野花将在中原文学的典籍史册里要安身立命,要在中原的医药行列中堂堂有名,要吸纳中原水土的养分开花结籽,至此一来,这株野花也就有了返回故土的夙愿,至少也要认祖归宗。
这是一株野花的身世,也是一个西域古国的往事,她一路跋涉,在不同的土壤上落脚,又一次次地辗转迁徙,千里万里流浪,故乡异乡,日暮乡关何处是,一株野花被人认识被人取名:马莲花、马莲草、马兰花、紫蓝草、兰花草、箭秆风、山必博、蠡实、旱蒲,既有人们迥异的喜好,也透露出一株野花随遇而安的精神境界,还有比她更顽强的花卉吗?
我坚信,马兰,是一种韧劲十足的花草,这样一种植物既有美丽和芬芳,更有千年遗传的生生不息的基因,而马兰,或许是马群可以食用的芳草,她的花朵、茎叶给一匹马驰骋的养料,至此,马和兰在一株野花上结了姻缘,人们才肯说这是最为完美、妥帖的命名,实至而名归。
深情
一个女子的传奇,一株野花的流落。
一往情深。一个唯一可选的词汇。
如果一个人活了一世,不曾一往情深过,那样的一本人生志总是略显单薄,底色也不够深沉。请别误解,难道不可以对一个人情深吗?除了一个人,不可以对一朵花卉,或者对一处山水,哪怕是对一间老屋怀着深情呢?
兰,简单单纯,单纯生可爱。我曾解密过一个男孩的心结,我告诉他,他所暗恋女孩的缘故,正是那女孩简单单纯,没被世俗过重地污染。他说她的眼眸纯澈似湖水,又如一株野地的兰花,叫人怜爱不舍。
我只说一个女子,她在一个传说里活着,一千五百多年,往事尘封,星辰变幻,河流改道,而一个名字却鲜活如初,除了“一往情深”没有别的可以守护得住。endprint
木兰,一个勇毅又圣洁的字眼。是一株乔木,高枝藏着花,不肯轻易示人?还是一株野花,肆意而舒心地开着?木兰是野性的,骨子里的野。
我喜欢野,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命特质,野性子,直性子,不遮掩不矫情,端起碗喝酒,放下碗唱歌,来者都是客,跨上马背一路冲杀,血肉之躯灌注着贲张的血脉。人们丧失“野性”已经太久了,繁缛的礼法戕害人们于无意识的麻木之中。
很久了,礼法的另一侧刀刃削平了流淌在人们血液里的野性,之后暗藏着的污垢滋养出蝇营狗苟的嗜好,光鲜的面子包裹着肮脏的交易,被丢弃的是坦诚和真挚。温良恭俭让的顺从,骨子里却是扭曲和暗算,伺机报复,嗜血成性。
借野性的直率和坦荡改良卑劣的血脉。
我想到一株野花,她来自北方的漠野,她和一个千年前的女子是孪生姊妹。
就像我喜欢一株野花,她微笑的花瓣,还没被世俗污染;她裸露的脊背,还未被贪婪猥亵;她放肆的奔走,还不曾受绳索捆缚;她透亮的歌喉,叫雪峰的苍鹰敛羽;她芬芳的气息,唤醒夜晚的星空。
人们是一往情深的,美丽的名字接二连三赠予一株野花:蝴蝶兰,蝴蝶花。一株脱俗的花卉和一种美丽的昆虫联名,在北中国的土地上吐露芳香,同蓝天白云应和,与山川河流齐寿。
蓝、白、黄、雪青,矮株、中株、高株,马兰花,花期长,喜阳光,最宜背风向阳的砂质土壤,同样耐盐碱,耐干旱,是改良水土的优良植被,是街衢美化的优选花卉。园艺家,植被学,授予一株野花的桂冠。足矣。
还是来说说她的孪生姊妹木兰吧。
人们是一往情深的,一个女子能活在一首民歌里,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千里奔驰,星夜兼程,越过大漠、荒野、河湖、山岭,只为止兵戈,为生灵的休养生息存一方安宁的水土。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面对荣誉和财富,木兰没有动心,她毅然转身,回归故里。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木兰不爱武装爱红妆,她真心想要的是女子美丽、安静的生活。这是世俗百姓的真切心意,争斗杀伐从来只源于达官贵人们的狂热贪欲。
人们把自己的朴素意愿留存在一首北朝民歌里,也为木兰寻得了一处可以千年安居的书页。
送走了木兰,我侧身走入黑夜,和马兰相对而坐,隔着一张窄窄的木桌,饮茶,聊天——说江南,说波斯,说宋瓷,也说民国;说祁连雪,说鸵鸟蛋,说胡杨林,说丝绸衣,也说傣族舞。不经意间,夜雨飘来。
一场夜雨,一株野花的天地沐浴,水珠混合着清脆的笑声,扑打着,洋溢着,追赶着。清新的雨雾里,我走过北中国土地,木兰已经告别远去,而她的妹妹,马兰骑着马儿在旷野上疯跑,从楼兰古城抵达古凉州,马不停蹄一路风尘直达河套平原。
我知道她内心的秘密,她的远祖逐水草而居,逐水而生,她的血脉里最动人的情愫也是逐水而走,是黄河的男子汉气概招引她远道而来,不辞辛劳,而她的四色花朵和内心芬芳也将魅惑黄河的视野。
她的别名寓意“宿世的情人”,也就是“祝英台花”。而我多不情愿使用情人这个被玷污过亿万次的词汇,那就以“恋人”取代吧。
马兰花开,岁月不老,木兰远走,传奇不止。
一株北国野花和一个北国女子,一对孪生姊妹分别太久,就让我做一回信使,为她们的往来鸿雁传书吧。
寻找
阴历三月二十五,从河西走廊直至河套平原,阴山南北,大河东西,飞扬起弥漫的一场雨夹雪。人们诅咒、谩骂、臆测、唏嘘,也有欢欣、喜悦、寻味、品咂,谁能公允评判一场雨雪呢?
天公的性情已经被人类的狂妄肆意篡改,被激怒的何止天公?一群栖居屋檐的鸟儿,如今也是四处流落,它们不愿竭力飞上高厦筑巢,它们悲伤地飞离了人们的睡梦,就连乡村的屋瓦也没留下一丝可藏身的缝隙,乡村的老树林在萎缩,它们的生存只靠着一双翅膀,在雾霾风尘暴雪冻雨里尖厉地鸣叫。
一群麻雀,我熟识的雀儿,最平常的生灵,它们被迫丢失了故乡,人们啊,你们的故乡又能幸免吗?那些悠闲、琐碎、安静,甚至贫穷不堪的时光被谁贩卖掉了。
食物填饱了人们的肚皮,却挖掘了更深的欲望之壑。精神的空壳,是缺少亮光的深渊,一旦坍塌将万劫不复。故乡被埋葬,人们失掉了精神的根须,回归之路被截断,迷惘的情绪是心头不散的阴霾。
我将带着一株野花,沿着长河溯源,寻找我精神的故土。
长河流过历史的村庄,河水浑浊,乱石嶙峋,林木森森,长风浩浩,人烟不绝。
收买,恫吓,淫威,杀戮,毒酒,美色,绑架,威逼利诱,刀山火海,合纵连横,魔鬼成群,野兽出没,告密,一把屠刀刺穿,一支飞箭呼啸,监牢和酷刑,围追堵截,水漫金山,法西斯枭首,切·格瓦拉战友,蒙古族呼麦,吉卜赛女郎,哥萨克雇佣军,锦衣卫,末日王朝,克格勃,东条英机,丰臣秀吉,刺探,暗杀,出卖,贵族被绞刑,野兽被供奉,历史的全部剩余,无非是一条词语铺就的荆棘之途,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的千堆雪,也终将被岁月的风吹散,踪影全无。
而,人心和传说从不停步。
我踏着历史堆积的乱石,沿河溯源,寻找精神的土壤。
是一株野花,昭示我必须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
马兰花的颜色渗透着夺目的血色,和太阳结为一体。
马兰花的根须蔓延扎入泥土,和大地结为一体。
马兰花的叶片十二分柔韧,和平民结为一体。
马兰花的种子可以深藏千年,不腐,不裂,不眠,和岁月结为一体。
在茫茫戈壁,我和马兰花相依为命,我要拜谒民族的灵魂,找到民族的宗教情怀。何处曾记录?
一路跋涉,风雨兼程,四顾茫然,我疲乏地倒下,我匍匐爬行,我血迹斑斑,我骨瘦如柴,我形单影只,我绝望万分,我昏迷不醒,我沉沉睡去,我惊醒过来,我在民族文学的长河之畔苏醒。我惊喜地狂呼,向着四野和星空,喜极而泣。endprint
我翻阅着民族的心灵史,隐约感觉是一条文学的河流,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个民族的文学史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史,文学情怀就是这个民族的宗教情怀,一点也不说教,一点也不虚蹈,一点一滴渗透进了血脉。
我彻底安静下来,我能做的事情很简单——找到民族文学里的“兰词”“兰诗”,为开悟我的那株野花寻到“根”,一株野花只有获得了文学的认可,它才回到了自己的家走进了自己的门。
千首咏兰诗,万首咏兰词,我只说屈原、司马迁、鲁迅是民族文学史的三瓣“兰瓷”——烈焰燃烧中生成的最坚硬、馥郁、华美的兰之瓷,花色,根须,茎叶,种子,一致的精神,生生不息。
呵,丢失的故乡必要化为文字,在一行一行的文字里永生,鸟雀们也在文字里安巢,一声一声清脆地叫喊,精神的曙光必要从文字里射出,照亮天空和土地,驱散雾霾和阴暗,而历史的谎话必要被文学的真诚戳穿,马兰花痴情追随长河的步伐,也不曾停歇一刻。
徘徊
花语,是谁命名了花之语?是花神,还是俗人?就像抢注商标一样,以贴标签的手法殖民,占有欲是生物的一个特性。
马兰花的花语被指认为“神秘”。那就由我来解说她身上的神秘吧,如果她不怪罪于我的话。
她翩跹的手指美妙地弹出一朵悦目的花型,青紫色的火焰,左右两瓣略低垂,像虔诚的双手托举中央三瓣,主角呢,英姿飒爽,透着争高直指的劲头儿。我惊叹于高低错落的搭配,这是自然的秩序啊,妙不可言。
我呢,一下子想到了敦煌里的飞天,身姿曼妙舞姿翩翩,在高耸的墙壁上飞动出内心的情绪,而一朵马兰花却静若处子,她静默不语表情神秘,四方野风躁动,也揭不开她严整的装束,这是一种矜持和庄重,不似那些轻浮的花瓣,追风而落,逐水而去,只落得颜色零落染污秽,马兰花内心藏着独有的芬芳,不肯随随便便掏出来示人。
由此而观,“神秘”是有一些合适马兰花的。
我的外祖母可不操心什么花语不花语,她弯腰割下一铺一铺的马莲叶子,那些叶子柔韧,新鲜,滴着汁液,被结结实实捆起来,整捆整捆地码放在车厢里,暮色初上,打着响鼻的黑骡子拉起车离开野地,向着村庄深处走去。
在银色的月光里,外祖母卸下车上成捆的马莲叶子,她跪在地上双手均匀地铺开叶子,平坦坦的场面上一圈一圈的马莲叶子沉沉地睡去,外祖母的衣襟被汗水和叶子的汁液浸湿,她顾不得擦汗水,手就把每一处叶子都摊出一样的薄厚,就像对待所有的子女一样只一个心思。
她在心里默念着一句话,“三两天都出太阳,晒葇(失掉一些水分)我的马莲叶子,我好搓绳线”。
她每天到场面去翻晒马莲叶子,用手抚摸用心琢磨什么水分正适合搓绳,绳子的结实程度全在水分的掌握上。
趁着好月色,蔫巴的马莲叶子被粗糙的手用力地搓在一起,一条长绳在月光里渐渐出现,我恍惚地感觉到是银色的月亮被搓成了一条长绳,或者那根长绳上结满青紫色的花瓣,马兰花的叶子被编进了一根绳子的沧桑岁月里。
夜深了,我困倦,仍旧不肯去睡,我要看见一根长绳完全的模样。徘徊,徘徊,我顺着场面的外圈来回走动,眼睛盯着长绳一点一点蠕动,一点一点的月光也在蠕动。
月色很好,外祖母搓好了一圈又一圈的长绳,长绳被盘成一圈又一圈的圆,一层一层堆叠起来,像一轮圆月堆放在场面,外祖母逐渐隐去了身影。我还在徘徊,徘徊,我的外祖母哪去了?
我惶恐,我四下里找寻,长绳依旧叠放如初,外祖母不见了身影。我在月下,愈长愈高,我能望见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人们走过告诉我,外祖母去了很远的地方,很远,也许就在月亮的背面,可是人们有些伤心地说,谁也看不见月亮的背面,孩子,你还是回家去睡觉吧,也许明天一早醒来,外祖母就回家来了。
我不肯,我宁愿在场面上等,外祖母答应我忙完了搓绳,就给我摊金黄濡软的鸡蛋摊饼。
月亮也在徘徊,在或薄或厚的云层里出出进进。我想野地里那些一望无际的马莲也会徘徊,往年外祖母会好多次去割下马莲叶子,秋天割走春天才会顺利长出新一茬马莲。
岁月流逝,赶上月夜独处,我多少次回到那时的月色里,在场面上徘徊,守望着祖母的归来。不远处,野地里的马莲已经没人去割,疯狂地一年又一年生长,鲜嫩,水灵,柔韧,暗暗的芬芳,还是最初的样子。
我暗自思忖,生命轮替,但是总有一些生命的菌丝亘古不变,它们隐藏在一个人的记忆里,遇到适宜的雨热就会萌芽膨胀扩散,传下去,不断地吸纳新的记忆,为下一茬生命配给更好的养料。
今晚我独自徘徊,马莲花在高楼脚下的园圃里静默着,月色不明,搅拌机轰鸣。
被囚禁在城市夜色里的马莲花,内心也在徘徊吗?
我无意诅咒城市文明,但是我要领着一株马兰花私奔,从城市喧嚣的旋涡里逃离,回到山坡,回到宽阔的野地,在幽寂的月色里坐下来,或者在郊外的阳光里徘徊,一株花需要自由自在地呼喊和奔跑,它的肉体和精神需要开阔,需要野地的风吹霜打,城市的园圃终究不是它安顿身心的地方。
马兰花,曾经追逐大河,曾经被移植园圃,在城市的深处扎根,繁衍,却失去了天然的心性,逃离是它唯一的出路。
我赶着车在城阙的一隅等候一株私奔的马兰花到来。我必得隐身,我懂得潜伏在城市角角落落的杀手,随时都会放箭,带毒的箭头会一击致命,它们受命来阻止这次逃离。
月升月落,失约的马兰花不知去向。她一定被内心的绳索捆缚,她一定在庭院里徘徊,她一定在拆掉一件罗衫,她一定吮吸指尖上殷红的血滴,她一定折断了海棠的花枝,她一定呼唤天上的云彩捎走她的愁绪,她一定跑进潇潇秋雨无绪地奔跑着,她一定撕碎了纸上的签约撒在长街,她一定无数次地徘徊在月色里,她一定会向着城阙约定的方向默默流泪。
我坐在野地的高坡上,吹一枝长长的紫箫:飞雪,薄衫,残云凝滞,大河冰封,有商旅驼队路过,有沽酒小贩路过,有欢庆的歌舞路过,有飞驰的野马路过,也有岁月的尘埃路过,一切独来又独往,交替与轮回,生死与祸福,剪断的与新续的,欢颜与泪眼,丑陋与美艳,黑与白,永不停顿,一株马兰花追逐着大河之水,芬芳遍野,气贯如虹。
往昔已落幕,逃离已无望,前路仍杳杳。
我还在徘徊,一株野地的马兰花正吐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