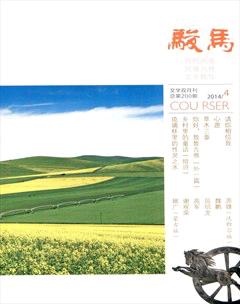那些岁月那些歌
孟彤
当我迈开一双稚嫩的小腿,刚开始蹒跚学步之时,就随父母下放到苏北一个偏僻的乡村。那个落后贫穷的村庄,在记忆中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数年后便随着父母,辗转落脚在洪泽县城的一座大院里。
院子里有好几只高音喇叭,家里还装上有线小广播。这些大大小小的喇叭,成天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诸如此类激昂慷慨的革命歌曲。刚听时还有些激动,可怎敌得成年累月狂轰烂炸,而终于日渐麻木。在幼小的心灵中,这些革命的歌,就成为一切音乐的总和。
大约九岁时,又随父母迁回省城南京。在举家搬迁之前,父亲几度去南京,历经数月奔走才有幸与另一家“下放户”同栖身于一套单元房内。那是幢通体灰暗的四层楼房,我们住顶楼,没有客厅,只有个很短的过道,连接三间不大的房间,一个狭小的厨房,以及更狭窄的厕所。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内,却如沙丁鱼罐头一般,挤住着两家九口人。几乎单元内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到淋漓尽致。这还是因“下放干部”,方才得到如此优待,其他更多“下放户”,只能在马路边搭个棚子,一家老小只能挤住在芦席与油毛毡搭建的陋室中苦度日月。
对过单元住着一对教师,夫妻二人年纪轻轻,就拥有一套独立的单元房,大门一关便自成一统,这些都令我羡慕不已。一来二去熟悉了一些,当我第一次踏入陌生的门内,第一个就直奔朝南的阳台而去。我们那套房有阳台的那间房稍大,同厨房一起就分给另一家。我家住两个小间,一间稍大父母住,堆放着家中许多杂物,另一小间则成为厨房,兼我和哥哥的寝室。
那时阳台对我而言,是由家中伸向外部的地方,连接着日月星辰和广阔的大千世界,是与天堂最接近的处所。可偏偏被人家占据了,阳台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在这之前我从没住过楼房。
当兴冲冲的我来到向往已久的阳台左顾右盼,只见脚下几排错落的破败屋脊,和远处一些灰暗的楼房,再就是灰蒙蒙的一片天空,并未获得期待中的新奇与满足。正失魂落魄之际,男主人却问我:“毛毛,你会不会吹口琴、吹笛子之类乐器?”
这一问犹如“天问”,令我一时瞠目结舌。从未有人问过我类似问题,也从没有料到自己会遭遇这样的问题。这就好像在问:“昨天,你见到过外星人吗?”吃饭、睡觉、上学、放学,难道这些还不足够?要口琴、笛子之类的玩意有屁用?能当饭吃?能当衣穿?还是能当被子盖?
那时我虽才刚有十岁,却也学会了些世故人情,我用委婉的口气,表达了自己的疑问。他却轻叹了一声说:“现在你还不明白,等以后遇到了忧愁,一时难以排解,弄个笛子或是二胡,吹一吹拉一拉,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这一番高论,再次令我疑惑不已。这辈子我怎么可能遇到什么忧和愁?那些小资情调,以前我没有,现在也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这位老师真有点莫明其妙……
其实那时我刚刚回城,是班上唯一的“下放户”,学习成绩自然不能与城里同学相提并论。常因土里土气的穿着、笨头笨脑的举止而倍受讥讽和白眼,甚至辱骂。昔日的同伴全留在县城大院里,回到家中没有一个伙伴,别说电视、音响之类,连个收音机也没有。除了课本和练习本,只有几本《毛主席语录》,其他书籍一概全无。不仅没有娱乐,对“娱乐”这个名词也一无所知。其愚昧、空虚和寂寞程度,可想而知。其实当时已处于寂寞之中,只是年少的我对此浑然不觉罢了!
转眼之间到了初三,却依然懵懵懂懂。当时我只知道有小提琴,不知还有中提琴和大提琴。有一天班长对一大群男女同学故作深沉地说:“我最喜欢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之死》……”不知哪来一股义愤,我当即理直气壮地反驳道:“世上只有小提琴,哪有什么中提琴?既然有中的,那还得有大的不成?”
话音还未落,立时招来一片奚落和嘲讽。在四起的鄙夷与笑骂声中,我见班长并没加入嘲笑,只是故作大度,不屑地发出一声冷笑,那鄙夷的笑容至今历历在目。面对讥笑我却无半点还手之力,因为无知又出了一回丑!我无地自容,脸一直红到了脖根,可一言也不敢发。只能深深低下头,想找到个地缝一头钻进去。少年人的虚荣之心,又一次被击得支离破碎……
这时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紧闭已久的国门刚刚打开,港台流行音乐如一股股暗流,在神州大地四处涌动,搅动着一颗颗处于花季的心——当时流行音乐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普遍的贫穷,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家里有收录机。
谁能拥有台收录机,是很值得炫耀的事。当时热闹的街头时常有一两个留着长头发身穿喇叭裤,手提着个收录机的时髦人物,大声播放着流行歌曲,一路招摇过市,引来无数羡慕的眼神……此现象可称为当时的一种独特景观,那种景象过去没有,估计将来也不再会有。但不管怎样收录机是当时时尚人物追逐的对象,对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件奢侈品。
有个同学,他个头矮小,其貌不扬,因打架背上记大过处分,又因成绩欠佳而留级到我们班。但他待人却有些侠义之气,他的一个哥们儿家中有收录机,还有好几盘港台歌星磁带。他学会了十几首流行歌曲,并据歌声记录下歌词。那歌词如今看来漏洞百出,有些只是同音字,词意却风马牛不相及。
当老师不在时,他就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歌声不仅令自己沉醉,也让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个个心动不已。一有机会纷纷凑上去,聆听他“婉转”的歌喉,瞅准他心情好时,就进一步索要歌词。他理所当然成为全班的中心,相比之下成绩很好,长得又很帅的班长,一时之间竟黯然失色。
在回家路上,我边走边手捧着他的“墨宝”,将美好的心情与“美丽”的歌声,飘洒一路……那时在班上我依旧是样样都不起眼的“丑小鸭”,可他却并没鄙夷我,同样也赐予了我两首歌词,我因此对他感激万分,唱起歌来格外带劲,歌声之中似乎又增添了另一些情愫。在他影响之下,我将罗大佑的《童年》,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何日君再来》等几首歌反复吟唱——唱得如醉如痴,大有“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之感。
最令我着迷的还是歌星张帝,他在现场顺口胡诌的那些歌,被我奉为经典。时常一路走一路直着脖子乱喊,心中感叹道:原来歌和词,竟有这种唱法和写法!直唱得摇头摆尾得意忘形,似乎词曲皆出之于自己手笔……涌动着类似“阿Q式革命”的畅快和兴奋——如此的感受可谓空前绝后,它帮我打发了许多寂寞的日子。
有一次放学后,我说了许多好话,他终于答应将我带到那个哥们儿家里。这是我期待已久的,当时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就像一首诗中所说,“这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当录音机打开时,我不禁凝神屏息,如同正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紧接着,邓丽君那甜美的歌声,从四个喇叭的收录机中,缓缓地流淌而出,顺着耳朵直往心里钻。我如闻仙乐,只觉得股股暖流在胸口涌动,全身如同沐浴在热水中,每一个毛孔都十分舒服,皮肤上还不时起一层鸡皮疙瘩……那一刻我因为幸福而战栗,我忘记了身外的一切,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歌声中,一颗心随着旋律而不停地上下起伏……
可正如歌中所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不久全国上下掀起一场强劲的“扫黄”之风。港台流行音乐被斥之为“靡靡之音”,因流毒甚广而首当其冲。随着运动不断深入,一个多月之后,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被请到学校来讲演。他的头衔已记不太清,似乎是某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
我们几个班被招到一起,坐在全校最大一间教室里,当面聆听教授的教诲。其他同学只能通过校内有线广播在教室中接受教育。教授引经据典,用渊博的音乐知识,系统全面地阐释了靡靡之音对处于成长发育之中青少年的毒害性。将懵懂无知的我们说得个个瞠目结舌惊骇不已。看反应似还不够热烈,他又反复劝导和启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竭力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对这些坑人的洪水猛兽产生出刻骨仇恨。说到高潮处,又从包里拿出磁带来,播放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然后集中对其进行了犀利的剖析和批判。接着又再次循循善诱,以激发出我们心底的愤恨之情。
不知别人感受怎样,在他反复论述之下,反正我越来越惊骇。这样貌似悦耳动听的“靡靡之音”,竟全是恐怖的糖衣炮弹,犹如当今“毒品”一样可怕。要不是学校及时遏制,或许不久就会被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想想还觉后怕!脊梁沟不禁冒出了冷汗。
回到教室之后,班主任却认为说得还不够,又大发了一番议论。她比划着,慷慨地说道:“在讲演之中他就不该在学生的面前播放‘靡靡之音,岂不让流毒得以进一步传播?只要尽力批判,将这些害人不浅的东西批倒批臭就行了,何必再拿出来展览!这些精神上的臭狗屎,就应该永远待在茅厕里!只有那些不知好丑的野狗,才会跑去闻一闻、舔一舔……”
听了班主任的言论,更觉得毛骨悚然,手不禁伸进裤口袋,摸到那两张皱巴巴的歌纸,就这样紧紧捏住,直到手心渗出汗……不知怎的,就是舍不得拿出来将它窝成一团或干脆撕碎。明知窝赃的行为极为不妥,但就是不舍得,也许其中寄托了太多的欢乐和憧憬……
我又感到一丝庆幸,当得意忘形地唱着“海龙王的女儿,世上无人可以比……”之时,那种丑态幸亏没让班主任撞见,否则这时就要成为最好的反面典型!简直不堪设想。
回家后我将两张纸片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仔细地看了一番,才夹入到一个笔记本中,将它们放到抽屉最里面。对苦心孤诣才学会的几首港台歌曲,再也不敢引吭高歌了,只是偶尔在心底里默唱一段,或在左右无人时轻哼上三两句。在偷食禁果的快慰之中,又含有了一种罪恶之感。
好在后来家中添置了收音机,一有机会就将它抱在怀中,摆弄着旋钮搜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如《乡恋》《军港之夜》《请到天涯海角来》等等,只要它们一露头,往往就被一一捕获。当悠扬的歌曲声传来,我就全神贯注地聆听,听过两三遍之后,词曲也就能大概记住。其后就放开歌喉,如留声机一般反复吟唱……
有时歌唱只是为了歌唱,有时又开始默默品味,品味苍白的岁月和幼稚的青春。歌喉并不优美,却浸透一种难以复制的真切。这一份真切之情,只属于那花一般的年华,如今已再难拥有。在美妙的旋律中,未来似一幅美丽的画,缥缥缈缈地缓缓展开,如海市蜃楼……一个无知少年,有权去幻想与憧憬,可如今却再不能如此痴狂,真是可悲可叹!
有一次搜到《海的女儿》,还作了简短的评论,接着又介绍了作者生平与文学成就。统统听完了,已开始播别的节目,我却依旧沉浸在震惊之中,那一刻似乎摆脱了简陋的现实,心神恍惚,似乎飘入一个更高更美的地方。一个女人,不,一条美人鱼,为了深爱的人,竟如此无怨无悔,甚至不惜生命,这是怎样崇高的情怀啊!世上还有这一类人……
写出这个童话的作家,又何等的了不起,脑中所思所想同普通的人是多么截然不同。这才第一次感受到,文学星空是如此灿烂和神奇。真切体味到还有一种叫“文学”的东西存在!作家真是个神圣的职业,他们或许并不富有,却拥有高尚的精神,这才是我的同类。要有可能的话,定要与这样的人成为朋友。世界简直太大、太奇妙了,神奇到我一时竟无法理解……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所有篱栅已拆除,各类流行音乐大行其道,数字电视、音响、电脑、卡拉OK、CD、MP3等等,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可是我却不再年轻。面对流派纷呈的各类音乐,现在人们神经却日渐麻木,出现了审美疲劳,可见好东西太多,并非一定就是什么好事。现代人面对不断的冲突与竞争,个个皆身经百战,早修炼成了铜筋铁骨,只有利益受侵害时,他们才会呐喊。这或许就是进化的成果,其中却夹杂几许无奈与悲哀。
当前各种信息以爆炸的姿态肆无忌惮地释放,激动人心的事变得极为稀有。面对日益麻木的神经,迫切需要的是震撼!可这期待往往要落空。如今的我偶尔从网络上下载几首歌,只是为解闷而已,音乐沦为生活里可有可无的点缀。曾经的那种痴迷,如黄鹤西去渺无踪影,我早已同流合污,也是个不能免俗之人。
可有时如一个游魂孤鬼,游荡在人来人往而冰冷荒凉的街头,当偶尔从敞开的窗口中飘来一段熟悉的旋律,曾经飘然而逝的岁月又蓦然重现于眼前……那些美妙无比的旋律已浸透入青春,与生命融为一体。歌声曼妙如旧,而心却已满目疮痍。这些深爱过的老歌,令我恍然忆起昔日那些健康活泼的岁月。青春,如青涩却华丽的梦,可梦一旦醒来再也回不去了!
好音乐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涓涓细流,帮我们冲刷掉心灵的尘垢。我苍白的青春,被那些优美的旋律镀上了一些亮色。由衷地感谢那些为音乐而献身的音乐家们,他们的辛勤耕耘,丰富了我的生活,也丰富了我的灵魂……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