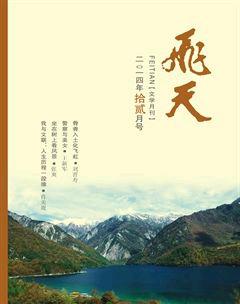坐在树上看风景
张爽,本名付文顺,北京平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民刊《天天》主编。2010年开始发表小说,中短篇小说散见于《雨花》、《星火》、《山花》、《青年文学》、《鸭绿江》、《上海文学》、《芒种》、《清明》、《文学港》等多种期刊。有小说被选刊选载。
我老叔死之前是四顷地最温柔的一个酒鬼,他一生未娶,连个到女人家入赘的机会也没捞到。他除了是个酒鬼外,还是个拐子,不走路时还好,一走路,尤其一快走的时候,就成了个前后左右相当招摇的残疾。
老叔是个拐子,穷,又没有女人,却是个快乐的穷光蛋和光棍,老叔的家是四顷地一帮小光棍的大本营。我们没事了就都约好了似地出现在他家里。我们通常是这样几个人:我、双岁、四条、二小,还有东来,有时东来的弟弟春来也来。
我们在四顷地坏事干尽,把偷回来的鸡和狗拿到老叔家让他做给我们吃,老叔明知原委,也睁只眼闭只眼。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个高尚的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没有鸡狗可吃,我们就吃老叔的豆腐菜。老叔自己是不做豆腐的,他的豆腐都是用玉米或黄豆换来的,他能把豆腐做出很多花样:熬、炖、煎、炸,哪怕就是用水煮过就盐水吃,在我们眼里都是一顿丰盛大餐。
老叔不是个小气的人,在我们没法偷鸡摸狗的日子,也照吃老叔的豆腐,他非但没流露出不满,每天还乐呵呵的。老叔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没有女人却交了你们这帮四顷地的小混蛋,我死而无憾。
我们在老叔家吃饱喝足后,会先后离去。那时候老叔家的小院子一下子会变得鸦雀无声,夏天的阳光懒洋洋地透过老叔家低矮的门窗,照到他家的瓦灶绳床和漆黑的屋顶。老叔此刻会安静下来,脸上还挂着他招牌一样的温柔笑脸,他正背着手在他的小屋里逡巡,样子像个微服私访的大员。在他频频颔首、色胆昭昭的时刻,他的小屋正蓬荜生辉,贴满了明星画报的一周墙裙,全是女人袒胸露乳放荡淫邪的召唤。
老叔不知道,这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此刻,我正躲在一棵高大榆树的顶端,把老叔的样子看了个正着。我生下来就暴露出猴子一样擅于攀爬、瞭望和机警的天性。我白天大部分时间藏身在一棵树上,梨树、苹果树、杨树或者榆树,我对树的热爱,让我疑心自己是树的儿子,而不是老海的儿子。我心中是看不起老海的,他除了会下窑挖煤,除了会喝酒、做一锅东北乱炖,简直一无是处。好吧,我们不提老海,还是说说我。我叫树生,这是我母亲给我起的名字,这名字和我对树的依恋有着某种遥远隐秘的关联。我疑心自己的母亲前生就是一棵树。但我没法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她,因为,说后注定要遭到一顿暗无天日的毒打。我的母亲像个歇斯底里症患者,有关她打人的经典场景在四顷地流传甚广。
我有时会爬上老叔家前面的老榆树,那树恐怕只有我一个人敢爬上去,那树就长在老叔家的祖坟的中央,我在上面向下看的时候,会看到那些年轻女人乳房一样的土堆,那里生活着一些被我们称之为鬼的祖先。但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谁,姓甚名谁或年龄几何。别人都不敢爬的老榆树我敢爬,而且我爬上去就不想下来了。我在老榆树上看到温柔的老叔陷入一群不要脸的女人的包围之中,我看到老叔鬼鬼祟祟地看了眼门口,然后把手放到裤裆里。
我看到了王斌,没错,这个四顷地著名的杀猪匠人,如今已混到批发站,当副站长了,他身材不算魁梧,眼神凶凶的像个煞神。我很少听到王斌说话,更很少看他笑,我看到他出现在我们四顷地场院那里,他没有走大路回家,却顺着一条小路奔了另外一个院落。我听到那个院落的门吱呀一下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露了半个粉白的脸,王斌机警地往身后看了看,闪身进了小院。小院的门很快关上了,小院里的房门也关上了,然后,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没办法,即使我在全村最高大的榆树上面也有看不到的风景。
我在树上差不多待到黄昏,我发现我的手一直在裤子里放着,那里的坚硬凸起早已不在,我的胡思乱想消耗了我少小的欲望。我手搭凉棚看着老叔家,老叔这时正躺在他的炕上酣睡,他有二两酒就可以美美地睡上半天。有时候我很羡慕老叔,我甚至想过,自己长大了最好也变成老叔那样,有酒喝,有温柔的脾性,有满屋的女人和做一手好豆腐菜的本领。
王斌此刻已经从小院子出来了,他重又回到了大路上,他在大路上又迈开了方步,他脸上依然杀气腾腾,一副吃饱喝足后的杀气腾腾。他顺大路拐来拐去,走到一个大院子前面去了,那才是他的家。此刻他的女人正忙里忙外地抱柴、烧火、做饭、熬猪食,她矮小的身影沉默着,转动得像个陀螺。
我刚要从老榆树上下来,就听到二小家里传出杀猪一样的叫声,那叫声凄厉、悠远,如同旷野狼嗥。此刻,王开肯定已经把二小吊在门框之上,他正在从腰间往下抽皮带。王开的腰很神奇,他即使把皮带完全抽下来,也不用担心裤子会掉下去,那么他系裤带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是为了打儿子二小?十岁的王二小已经长得豹头环眼,老叔说过,现在的王二小和当年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王开长得一模一样,过去王开偷他父亲的烟叶卷了抽,而现在王二小偷了王开的烟叶卷了抽,不同的是过去王开是被父亲抽嘴巴,现在王开却要把二小挂到门框上用皮带抽。
看你还偷我的烟叶,看你还偷我的烟叶?王开的皮带抽到二小身上,噼啪作响。他抽二小一下,问二小一句。二小呢,在皮带落到身上后,反而不哭了,皮带在他身上像祖父的耳光抽到王开脸上一样响亮。有那么一刻,他好像已经进入了某种冥想的境界,好像在温习着祖父抽打父亲耳光的美好时光,那是他不曾见过的美好时光,他的脸上漾出一种幸福混杂着痛苦的享受。王开却因为二小的这个样子而越发恼怒了,他的皮带抽得更狠。我让你美,我让你美!二小终于从遥远的冥想中清醒过来,他的哭声如石破天惊的狼嗥。然后,几乎所有的四顷地人都听到了他的叫骂:
我操你妈王开,我操你八辈祖宗王开!
我笑了,开始从榆树上迅速滑落。此刻王开也笑了,他把二小从门框上卸下来,就像卸下一头待宰的猪,王开把皮带重新系回腰间,他抬脚踹了一脚二小,说,王八犊子,你有种,是我王开的种!
二小一直没掉眼泪,此刻他的眼泪却像雨天房檐下的滴水一样扯不断了,他还在骂着,我操你妈王开!王开,我操你八辈祖宗!
王开说,混蛋小子,再骂我还抽你,我妈是你奶奶,我八辈祖宗是你九辈祖宗。
黄昏的四顷地到处弥漫着一种酒香,那酒就是普通的高粱酒,散装的,被马车拉来存放在四顷地小学前面的供销店里,那里有几个硕大的黑漆大缸,那些酒就储存在那几个大缸中,四顷地的人谁想喝了,就会拿着空瓶子或塑料桶过来,喊过那个脸上的肉像沙皮狗一样垂到脖子上的瘦子售货员。来打酒的一般都是孩子,比如我、二小、双岁、四条、东来,有时候东来的姐姐英子也来。我是个早熟的孩子,比如我会常常想到英子,想到英子静静地坐在她家窗前。她那么小,却能做很多针线活,给两个弟弟缝补衣服,给父亲王宝贵画鞋样、纳鞋底。英子有个针线笸箩,笸箩里有各种颜色的线和针,笸箩里还有个颜色金黄的铜顶针,那顶针过去戴在母亲的手指上,现在戴在英子的手指上,母亲的手指粗,英子的手指细,英子戴上顶针,顶针会显得更大,也就更衬得英子的手纤细和苍白。我发现,自己看到英子戴着顶针做针线时心会疼,就像一个男人心疼他的女人。
我有时候会借着找东来、春来玩的机会去英子家。我不知道为什么经常看不到王宝贵,王宝贵自从自己的女人死了后,就好像是一棵树长在了外面,长在了别人家,只有在黄昏后,他这棵树才会回家,而那时的他通常是喝醉了酒。你也不知道他是在谁家喝的酒,不知道他怎么就醉成了那样。那时候,我会趁人不注意,悄悄爬到他家门前的那棵大梨树上去。那棵梨树真的是又高又大,春天开满雪白的繁花,夏天浓阴匝地,秋天金黄的梨子挂满枝头,冬天树上就只剩下了苍黑的枝干。有时,枝干上挂着白雪或冰凌。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四顷地有个著名人物吴志军把自己挂在那棵大梨树上,伸出后来被冻得僵硬的舌头,成了个吊死鬼。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拐子老叔的亲哥,也是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那个吊死鬼,就没有我。吴志军吊死了,我父亲老海才有机会结束自己旷日持久的光棍生涯,也才有我的出生。我出生时就耳聪目明,机敏得像个猴子,但却羞于讲话,五岁前除了哭,一个字都讲不出来。这一点不妨碍自己日后迅速成为一个攀岩爬树的高手。
我喜欢待在树上,就像英子喜欢待在家里一样。自从英子的母亲过世以后,英子就很少出现在外面了,把自己的影子深深埋藏到自己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像旧社会待字闺中的贤良姑娘。这时候,王宝贵踩着凌乱的脚步顺着大路回来了,嘴里骂着一连串的人,他的骂声和他的意识一样混沌不清。
此刻,英子像她的母亲一样叫着已经被吓傻的两个弟弟东来、春来,到院外迎接他们的酒鬼父亲。王宝贵说,我操你妈王东来,我操你妈王春来!他说英子你把老子要喝的酒打来了吗?老子要喝酒,还要喝酒。英子就说:爸,你醉了。爸你别喝了。
东来说:爸你醉了。
春来说:爸你别喝了。
王宝贵说:我操你妈王东来,我操你妈王春来!儿子管起老子来了?
王宝贵是真醉了,几次摇晃着差点倒在门前,英子就叫东来过去扶住他。
王宝贵看着最小的儿子春来说,你盯着老子干什么?
春来就赶紧把眼睛低下来,去看院子里新鲜的泥土。
王宝贵说,你看那土干什么?那土是你爹还是你妈?
春来的眼泪就下来了。春来长着一双和英子一样好看的眼睛,睫毛很长,眼睛很大。春来的眼泪像珠子一样掉下来,啪嗒一个,啪嗒又一个,砸在土地里,那被太阳晒了一天的土地就一砸一个坑,一砸冒出一股烟尘。
王宝贵说,去,拿铁锨去!
春来到窗下取了铁锨,又站回原来的地方。
王宝贵说,我操你妈王春来,你给我装傻是吧?挖坑,给我挖坑!
春来没动。春来不知道爸爸让他挖坑干什么。春来也就六七岁吧,铁锨沉沉的,几乎带歪了他的身子。
王宝贵看春来没动,想像过去那样,走过去一个耳光,再踹一脚,耳光会打春来一个趔趄,那一脚会让春来一下跌倒在几米之外。王宝贵大概想到了自己无数次对春来干过的事,那事他都已经上瘾了。可今天他实在醉深了,他的手伸出来软绵绵的,离儿子很远,他的脚伸出来也软绵绵的,不像踢人,倒像做一种奇怪的广播体操,而且,那脚伸出后好久不知怎么收回来,就那样晃荡着,晃荡着。等收回来时,那脚就像在为自己画圈了,多亏有英子和东来扶着,不然是必倒无疑了。
狗日的,看什么看?挖,给我挖,挖个坑,把自己埋了!王宝贵下达着他不可一世的命令。
春来眼泪掉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偷眼看了一眼哥哥东来,又看了一眼英子。
春来说:姐!
英子说:听爸的,挖吧。
英子的语气越来越像她母亲。
春来就吭哧吭哧挖起来。
王宝贵被英子和东来架着往屋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脑袋歪过来看春来。王宝贵说:春来,你好好挖,挖个大大的坑,挖好,把自己埋了,把你哥你姐也埋了,把王八蛋们统统都埋了。
我有时候会爬到杨树上去,爬得比喜鹊窝还高,我甚至想像喜鹊一样,躲进它们的窝里,或者像喜鹊一样,衔来树枝,给自己筑一个巢,生活在树上。
我不怕住在老叔家的祖坟中间的榆树上,也不怕住在高大的杨树上,只是怕住在大梨树上。我还怕看到喝醉了的王宝贵,怕看到吭哧吭哧挖坑的王春来。春来这孩子也怪,如果没有父亲的命令,他是不会停下挖坑的铁锨的,东来和英子在王宝贵睡着了以后,已经出来“命令”春来“别挖了”,可春来就是不听,还在一直挖,好看的眼睛掉着眼泪,粗大的铁锨把儿已经把手磨出血泡,可他的劲儿实在太小了,他什么时候才能挖出一个足够把自己埋进去的坑呢?王宝贵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呢?只有王宝贵清醒过来,才会止住春来不停为自己挖坑的铁锨。
我在大杨树上如鱼得水,我在大杨树上会忘记春来和他的眼泪,会暂时忘记英子愁眉不展的面容。四顷地的黄昏太可怕了,一股股不安分的酒气四处游荡,很多人都喝醉了。我爸爸老海喝醉了,正骂着姐姐,他骂我姐姐给他脸色看,欺负他这个后爹。我老叔也醉了,他正绕着那圈浪荡的美女在唱情歌,他哼哼唧唧,手上还打着拍子,有毛病的脚一点一点地点着地,倒也跟得上那歌的节拍。好像他那脚是故意那样走,那样走才合辙押韵,才会使他的情歌更动听一样。四条和他爸爸王贵也喝醉了,四条和他爸在划拳。王贵说,四条啊四条,你牛逼,你是我爸爸行了吧?四条就说爸啊,谁不知道你牛逼?吐个唾沫成个钉,脚一动,四顷地就要晃一晃的。王开也醉了,他抽下皮带,在打他的儿子王二小。王二小是自己把自己吊在门框上的,王开打一下骂一句,看你还偷我的酒喝,看你还偷我的酒喝!打到高兴处,王二小就骂,我操你妈王开,我操你八辈祖宗王开……
整个四顷地一到黄昏就像演一出生旦净末丑全五行的热闹戏。
只有王斌家是安静的。王斌当然也醉了,不过他醉得安静,他醉后就躺在他家东屋的炕上,一脸餍足,不停地吹着酒气,打着酒嗝。他很快睡着了,确实是睡着了,睡得就像死去了一样安静。
四顷地的天黑下来了。四周群山像一群蜂拥而至的怪兽,而笼罩在四顷地上空的天空则像这群怪兽拉扯过来的一张网,那些星星就像是漏洞百出的网眼。我在夜里的杨树上开始有了恐惧,我的恐惧就像与生俱来的一样,但不久,我的恐惧就消失了,因为我看到了双岁,这个和我同岁的王斌的儿子,正从他家院子里走出来,走过大路,走到场院那里,然后拐进了那条小路,在一家院门前,他谨慎地站住,然后大胆推门进去。在里屋那里,他的手没有推开门,门被人从里面插上了。
他敲门。
谁啊?里面灯影一闪。
我,双岁。
是双岁啊,你干什么?
你开门!双岁说。
又过了会,女人把门开了,双岁闪身进了门。
女人开门的时候,正在扣着自己衣服的扣子,那扣子刚好扣到乳房那里,好像是她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也好像是刚刚给孩子喂过奶。
双岁进去后,里面的灯就关掉了,我看到了一扇漆黑的小窗,就像黑夜里的一只眼。
我在高高的白杨树上看到我的拐子老叔,他在那天夜里也来到那个小院门前,我看到他敲门,听到女人在屋里问谁,老叔没吭气,女人说,是王斌他叔么?是双岁他哥么?是王贵他爷么?是王开?女人问出了一连串的名字,那些名字在女人嘴里如数家珍。老叔吭吭哧哧,老叔说我是吴志斌啊!女人说,是志彬老哥啊,你有什么事吗?老叔说,你开门,我进去说。女人说,我已经睡了,有事明天说。女人屋里的灯却关掉了,老叔愣了愣,摇晃着走掉了。
我在大杨树上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我就在杨树的枝杈间睡着了,流着口水,打着莫名其妙的呼噜,脑袋里带着一连串的问号,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睡着了,就像树上栖息的一只猴子。
我还是喜欢爬到大梨树上去,那通常是白天或者黄昏,我在那里更多的时候是想看看英子,看春来的坑挖得有多深了。春来几乎每天都在黄昏中挖坑,因为王宝贵几乎每天都会醉着回来。后来,春来一听见王宝贵摇晃的脚步声就拿起沉重的铁锨。有时候王宝贵还会夸他几句,说春来你这个龟儿子,快点挖,就这样挖,再挖几天就可以把你自己埋进去了。王宝贵还会问英子,给他买酒了没有,如果没买,王宝贵就会抽她一个耳光,踹她一脚,像过去打春来一样。东来却不知跑哪里去了,王宝贵酒醉的时候,他会失踪,那时候整个四顷地的人都不知道他藏在哪里。
王宝贵开始打英子了。我在大梨树上咬牙切齿,像一只真正的猴子一样抓耳挠腮。可我又毫无办法。英子也毫无办法。春来也毫无办法。春来只好更卖力地在那里挖坑。我后来发现,春来挖的坑竟然方方正正的,像是一个小型的墓地的地基。春来的坑已经挖得越来越像样了。他的姐姐挨打的时候,他正在挖坑,那坑已经深过了他的小腿,新鲜的泥土被他扬在四周,堆得越来越高。英子在王宝贵打她的时候,咬着失血的嘴唇,漆黑的睫毛沾着滚烫的泪珠。英子在挨打的时候想到什么呢?在想她刚刚过世两年的母亲?还是在想自己和弟弟为何这么命苦?
英子掉泪的时候,我也要陪着英子一起掉泪。我希望英子不要看见我掉泪,我把自己隐在梨树的绿阴中间,像一颗青涩的梨子隐身在苍翠的树叶中间。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眼泪掉在胳膊上,我发现连我的眼泪都是青涩的绿。
我老叔被女人拒绝后不久出门打工了,在一家砖厂替人看大门,他在那里依然热爱喝酒、女人和吃豆腐。他挣的钱不多,他那些钱都花在了离砖厂不远的两个小卖部里。那时候,我只有爬在四顷地的最高峰卧龙脊上的松树之上,才能隐约看见老叔的样子。没有了老叔的豆腐滋润,我很快变得苍老枯干和忧郁起来。我希望老叔这个温柔的酒鬼能很快回到四顷地,可是他却越走越远,因为他欠下小卖部的账越来越多,而黑心的砖厂老板又处处克扣着他的工资,他就只好远走高飞。
我在树上的岁月越来越单调,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长在树上的一枚叶片,经风历雨,正在逐渐凋零。四顷地黄昏的大戏正在变味。王开突然有一天不再把王二小吊在门框上用皮带抽打了,而二小已经不满足偷他的烟偷他的酒,二小从四顷地消失了,据说加入了营子镇的流氓队,他开始在偷火车了。王开虽然每顿仍然借酒浇愁,对王二小却鞭长莫及,皮带抽不到儿子身上,因此,他的酒就喝得有些寂寞。王斌和双岁仍然去女人家,王斌大都是在白天,是他从批发站回来的时候,而双岁则是在晚上。女人的丈夫也是个挖煤的矿工,不知为什么,那男人很少回来,女人的家里因此成了很多四顷地男人向往的地方。
王宝贵的酒已经醉得不成样子,他成了四顷地最不受欢迎的酒鬼,因为他酒后把四顷地的人都骂遍了,春来和英子更是被他打得鼻青脸肿。春来还在愤怒地给自己挖着坑,而英子已经很少坐到玻璃窗前为她的爸爸纳鞋垫儿了,她的一双大眼变得越来越无神。
半年后发生的那次离奇事件,至今在四顷地被人津津乐道。那时候春来已经把那个坑挖得高过了他的人头,他正在等待着王宝贵的一声令下,然后,他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把自己埋掉,小小的春来早已视死如归,似乎谁也挡不住他把自己埋了的意愿。然而,他不知道,这个坑最终埋了的不是自己,而是他爸爸王宝贵。
那天黄昏,或许不是黄昏,也许是黑夜吧,谁能真正把黄昏和黑夜的边界分得那么清楚?总之,在那个黄昏或黑夜时分,王宝贵醉着回来,不知怎么就冲着春来挖好的那个坑过来了,那个坑并不深,也就到他的腰际吧,可就是那么一个坑,他把自己埋进去了。可能,他进去后还有过挣扎,因为他的爪子缝里全是新鲜的泥土,他把那些浮土全都刨到坑里,然后把自己埋了,窒息而死。
四顷地没多少人为这个结局感到悲伤,这个结局甚至带了些喜剧的成分,被四处流传。然而,这毕竟是个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快公安上的人来了,在勘察了一番现场、捂着鼻子把浑身酒气的王宝贵挖出来后,在询问了一番已经被吓傻了的春来、英子和不知从哪里赶回来的东来后,这个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我想说的是几年之后,几年之后,英子在她十七岁的时候,把自己嫁掉了,她下嫁的人家不详,地址不详,因为在她嫁走之前,我的父亲老海已经死亡,我的母亲带着我远嫁京东,我到那里不久,就彻底丧失了之前机敏的攀爬、瞭望本性,平原沉闷的生活让我变成了一只标准的室内动物。我的名字还叫树生,可我已无树可爬,我像一个废物一样生活着,用一些枯燥的方块字打发漫长的岁月。
后来有一天,我碰到了远道而来的双岁,因为要做倒煤的生意而来找我,他对我说起了他的第一个情人,如我所料,双岁的第一个情人,正是他父亲的情人。我奇怪的只是双岁的说法,他说,他那样做,仅仅是为了报复自己的父亲。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他就说到了我老叔的死。他说我老叔有一天在老家再也混不下去了,他欠下的酒债不多,但那些酒债就像陈年的渔网,漏洞百出,让他狼狈不堪,他最后无处可去,就想到要到京东找我讨生活,因为他听别人说,我已经在京东成了个名人,好像本事大得不得了。然后他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当时已经弹尽粮绝,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最后是二小帮了他,请他吃了最后一餐饭,喝了最后一口酒,临走时又给了他五十元钱。当年加入流氓队的二小如今已成了四顷地最富有的人,在营子镇开了好几家饭馆。二小给老叔买了一张到西厢县城的班车票,让老叔到京东后给我带个好,问问我当年攀岩爬树的本领还在不在。我老叔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他到了西厢县城,结果那五十元钱还没被他捂热,就被一个进行残疾表演的坏小子给抢走了,当时那个坏小子是以一个傻子的名义出现的,他卖力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套取旁观者的怜悯的纸币。
老叔看到傻子伸开的手掌心里有人给了他五角钱,他掏了半天口袋,只掏出那张五十的。那是二小给他的仅有的一张纸币。他该怎么办呢?他是告诉这个坏小子用拳头那么猛烈地打自己脑袋是会把脑袋打坏的,那样人就会更傻,人更傻了之后就更不好赚钱养活自己了。他还想告诉那个坏小子,他只有这一张五十块钱,但他不能都给他,他只能给他五角,或五块,因为他还要用这钱坐车去京东来找他的侄儿树生——也就是我。
然而,还没等他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那个正进行暴力表演的小子就劈手夺过老叔仅有的五十块钱,迅速穿过人群跑了。我老叔愣了一下,开始追,但他怎么能追得上那个坏小子呢?那个坏小子像知道老叔是个拐子一样,他跑得就像一支火箭,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两天后,有人在班车站的大桥头发现了他被冻僵了的尸体,当时出现场的警察为此询问了不少附近的生意人,他们中有很多人记住了老叔的样子,说他在他们那里打过求援的电话,还说他几次迈上开往京东或回四顷地的班车,但几次都被售票员痛骂一番后,给踹了下来。他被踹下去后,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那两个肥得像头猪一样的女售票员恶劣的大叫:臭拐子,没钱坐什么车,滚下去,去死吧!
然后,老叔就真的死了。
还是说双岁,这个和我同龄、却敢用同样方法报复自己的父亲的坏小子,像当着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在讲一个毫不相干的故事一样,说着老叔悲惨的故事,然后,他在喝掉三大扎扎啤、抽掉我一整包烟后,突然对我说起了另一件事:你还记得王宝贵的死吗?
我说,记得。
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知道王宝贵是怎么死的吗?
难道这也算个秘密?我说,王宝贵不是醉酒后被自己埋掉的吗?
双岁说,我也以为王宝贵是醉酒后自己把自己闷死的,可后来才知道上当了,咱们都上东来的当了。王宝贵不是自己死坑里的,是被他儿子东来推到坑里埋掉的。东来才是杀了他父亲王宝贵的凶手。
双岁说,要不是东来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把这事说了出去,恐怕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他都没事人一样过来了,现在却说了出去,不光说了出去,还自己到公安局自首了。你说他傻不傻?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