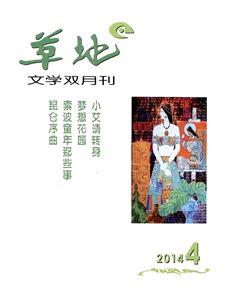草木素描(组章选二)
江剑鸣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韦应物把野草写得很凄美。实际上,野生草木难入人眼,文人画士不屑一顾。草木一秋,人生一世。人世无情,草木有意。再怎么低微卑贱的野花野草,也会有它们的春夏秋冬。
——是为题记
丝茅草
丝茅草,恐怕是野草族群里地位最卑微的一种了哦。
丝茅草,也叫白茅,茅草的一种。不像长在磨刀河岸边的巴茅,长两人高,像甘蔗林,开出灰白的茅花,满河沟里飘荡。也不像长在青冈林边上的红茅草,长出一米多长的红色草苔,我们叫它虹子草,可以割来盖房,房子叫茅草房,有别于谷草盖的房子。
丝茅草的丝字,是有来历的。把丝茅草叶子对折压平,再平拉,拉断后,就会发现压在下边那半截断叶的创口,有白色的丝绒,像杜仲皮那样的丝绒。这是其他的野草没有的现象。
观音寺四周的荒山坡上或者庄稼地的地盖上多有此物。我家自留地地盖上就有很多,经常铲除,都不能根绝。其生命力之旺盛,可见一斑,真实草贱命强啊。
丝茅草尤其喜欢生长在贫瘠的黄泥巴(粘土)里。开春时候,稍微下点细雨,它就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从黄泥巴里钻出个头来,深红色,尖尖的,有点像麦颖,但那半寸深的茅草尖尖比麦颖尖锐坚硬,草鞋踩上去,能够锥透鞋底,甚至锥伤脚板。而后,慢慢长出来嫩叶来。嫩叶初像麦苗,之后像水稻秧苗,但叶片一直朝上长,不弯曲,不倒伏。叶子呈青绿色,叶边呈微红色,叶面有纹槽,叶柄呈暗红色,每只叶子独立,只在根部分蘖,不在干上分支发芽。丝茅草一般长一两尺高,最茂盛的高可达一米,少数太长的叶片稍微弯曲,更多的叶子笔直朝上,显得特有精神的样子。仲夏时节,每茎草都孕育出一个草胎,肥鼓鼓的,几天后,从草心生长出来,开始拔节,像水稻拔节一样,但没有水稻有气势。香签棍大的暗红色花梗茎上端寸多长的花朵,开出淡白色草花,白色的毛绒状,在叶子顶上举着,像是它们的旗帜,又像是长满白毛的蜡烛,狗尾巴状的微微弯——所有的都朝一个方向。
秋风刮过,丝茅草就开始变黄,先是淡黄,后是深黄,叶子开始弯曲。打上几场霜,或者下上一场雪,它的叶子就开始大量倒伏,只有极少数仍然挺立,叶片颜色全部变成白色,惨白的那种。我常常在暖暖的冬阳下,躺在干燥的茅草丛里晒太阳。有时和周大爷一起。我们都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砍柴或者扯猪草累了,躺在丝茅草丛里晒太阳是一种很美的享受。那时候还不懂得晒内心晒思想,只是晒晒身体。虽然肚子饥饿,但身上暖和些,心里也就满足了。
于人类的生活,丝茅草似乎没啥用处。
长在山坡上的虹子草可以割来盖房子,据说除了防火性能差些,住在里边,人会感觉到冬暖夏凉。长在河沟边的巴茅草,拇指般粗大,可以砍来编住房的篱笆茅厕的篱笆或者盖猪圈的棚子。我们生产队在磨刀河岸边的水磨坊,就是用巴茅杆盖顶巴茅杆编篱笆的。我问,咋不用丝茅草盖房子?大人回答说丝茅草太硬,太滑,不易捆扎,盖在房背上容易梭落。小学生初学算术,老师就叫我们折些巴茅杆做计数的“小棒”。连大人们逗小孩玩,都折狗尾巴草,又叫猫猫草,编成狗狗猫猫的形状,毛茸茸的,在手臂上划过,逗得小孩子哈哈笑。可是,丝茅草,割来喂牛,牛都不喜欢吃。羊子对它更是不屑一顾的。女人或者孩子们扯猪草,更加不会与它沾边。遇着雨天,我们给公社兽医站那头秦川牛割草喂,一般都选玉米地里的一种巴地草,叫做“熟草”,牛特喜欢吃,同时也算给玉米地除草。到初秋季节,生产队要组织劳力割草垫圈,猪圈或者牛圈,为下一季庄稼积肥。社员们喜欢割各种蒿草,青蒿,黄蒿,艾蒿,或者干脆去玉米地里扯熟草,也算给玉米除草。都不割丝茅草,说那种草沤不烂,不肥地。
出于保护庄稼生长,野草总是在铲除之列,只是有些野草尚可以喂猪喂牛羊或者垫圈积肥,派上有益的用场,可丝茅草连这些用场也派不上呀,悲乎!
丝茅草如此不被人待见,在本来就低下卑微的野草族群里,其身份居然如此另类,其地位居然如此低下,实在出我意料啊!
但我个人还是不讨厌丝茅草。春上,我们跟周大爷去观音寺后面玉米地边扯猪草,累了时,坐在地边玩玩。当然,无法与如今的孩子比玩具和玩法了。我学着他玩丝茅草射箭,聊以打发那些孤独寂寞的日子。我们掐来丝茅草叶子,从中间撕两个不断离的口子,用指头在中间快速划过,丝茅草中间的叶茎就嗖地一下像箭一般飞了出去,飞几米远。我们寻找嫩实的茅草苔,拔出来,剥离开,把嫩芯放在嘴里咀嚼,略有点毛绒的感觉,也有点清香,有点微甜。有时我们也用镰刀尖啄出丝茅草根来。粗壮的丝茅草根,像则耳根那么粗。遇着嫩实的,就在裤腿上擦去泥土,放进嘴里咀嚼,比草苔有味,甘甜,像嚼甘蔗,只是水分较少,草茎的细丝常常卡进牙缝里,要使劲掏才掏得出来。周大爷拔出丝茅草花的梗柄,拔一大把,编织成一个花环帽子,戴在他家林娃子头上。挺洋盘的。周大爷还说,丝茅草可以做草药,能够止鼻血。后来我在药书上也看到丝茅草能够止血的说法,但不知道具体怎样使用。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丝茅草总会给世界留下点什么吧?
拔丝茅草的时候,我的手被叶边割破了。直流血。周大爷说,叶边那齿齿叫做锯子齿,快得很——我们把锋利叫做快,割你这种嫩肉肉有个稳当。他还说。鲁班当年发明锯子,就是被丝茅草割了手指才发明的。我马上想到了我家墙壁上挂的那把木工锯子。
哦,大自然给人类这样的启发,如同苹果之于牛顿,是无意和有心的一念之距啊!锯子的发明,推动了人类的工业革命。如此说来,丝茅草也算这种革命的功臣呢!
后来读到《诗经》,发现《诗经》里多次提到茅草这种古老的植物。如静女等待的小伙子放牧归来,小伙子便有“自牧归荑,洵美且异”的吟诵。那“荑”,便是嫩茅草,相当于采摘的花朵野果一类,作为礼品赠送给心上人的,异常珍贵啊!在《召南》里边,还有“野有死盾,白茅包之”“白茅纯束,有女如玉”的描写,意思是说在野外,一个小伙子将自己打到的一头野鹿用具有特别含义的白茅草捆束起来,放到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面前,向她求爱。可见茅草在上古的诗经时代还是一种至雅之物,象征美好爱情。
这么卑微的野草,居然象征爱情!
而美好淳朴的爱情是不讲尊阜的!
哦,当时的大自然和社会没有被污染,当时的爱情更没有被污染,爱情是那么真挚,那么纯洁,那么淳朴——不论我们今天爱情充满铜臭的人们多么瞧不起这卑微的丝茅草啊!
野棉花
磨刀河两岸的山坡上水沟边小路旁田埂地头,到处都生长有野棉花。尤其是从观音寺去高村街上上学的小路两旁,野棉花春夏秋三季都陪伴我来回往返,像我的小伙伴一样。
春天刚到,各类野草从泥土里相继钻出头来。野棉花的嫩叶卷曲着拱出泥土,抖抖身子,舒展开第一片青紫色的叶子,有小巴掌那么大,三个桃形的椭圆叶尖,还略略带一点毛绒。经过日晒雨淋,叶子长老些,毛绒就消失了。随着第一片叶子长出,便相继生长出四五片来,每片叶子都长一根三四十公分长的青紫色柄梗,小筷子那么粗。到了夏天,在几只叶梗簇拥着的根部,生长出一两枝花苔,筷子粗,慢慢长高,高到半米以上甚至一米。花苔上端分两三个叉,每个叉枝约两寸长,顶端结一个花蕾。花蕾起先只有米粒大,青色,慢慢长到黄豆大,拇指头大,李子般大,像算盘珠那样扁平,颜色也就慢慢变成青里透白。我们小孩子喜欢摘下这种果子状的花蕾打仗,互相往头上掷,看谁掷得准。那东西打在头上,还很疼。立秋一十八,寸草都开花。到了初秋,野棉花的花蕾开始绽放,像荷花一样的粉红色花瓣,次第绽开,花瓣大的有李子大,小的也有指头大,简直就是袖珍版的荷花瓣。花瓣比较厚实,有点肉感。每朵野棉花一般五个花瓣,如同一朵袖珍荷花。整个花朵就像一个佛教图画里的观音的微型莲台。花瓣的粉红色,点缀在荒凉萧索色彩单调的小山路上,略带些暧昧,也带些热情。在日渐寒冷的秋风里,给人温暖的感觉。不像学校花园里的藏菊花和棋盘花那么张扬色彩的斑斓和炫耀花朵的雍容,却只能让人敬而远之。在野棉花花骨朵萼盘上面,花瓣围绕的中央,是一盘黄色的花蕊,又像是一朵微型的向日葵朵盘。一只只蝴蝶在花朵上翩翩舞蹈,流连忘返,一只只蜜蜂在花蕊里爬来爬去,周身裹满厚厚一层黄色的花粉,懒洋洋地飞走。虽然是野花野草,照样能够招蜂引蝶,看来爱美之心,及至昆虫。
初秋,一场大风或者一场细雨,野棉花花瓣纷纷掉落。那些粉红色立刻枯黄,变黑,腐烂在泥土里。若干年后学到一句描写落梅的诗,说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我以为用着此时的野棉花身上,也很贴切,只是野棉花没有梅花那样的清香气味。
野棉花的花瓣掉尽,便结出一个比拇指头略大一些的棉花桃子,由青紫色慢慢变成黑黄色。待天气放晴,秋阳如虎,棉桃便沐着目光的暴晒,吸纳阳光的温暖,越长越大,大到李子一般。野棉花叶柄被风折断,耷拉到地上,叶子早在秋风里卷曲,枯黄,灰黑,慢慢掉落,腐烂了。再有秋风刮过,棉桃就呲地一声,裂开一条口子,哗啦,野棉花从里面爆挤出来,白花花地绽开酒杯大的一团。那新绽出的棉花,白白净净,几天后,就被灰尘雨水污染成灰不溜秋了。那些被晒干了的棉花,随着秋风向着远处飘散,轻轻地飘散而去。偶有几株没有被吹散尽的茎杆,高高地擎着日渐变枯变黑的花枝,在秋霜冬雪里摇曳着,坚韧地摇曳着,似乎是在尽情地挥洒生命,又似乎在百般无奈地抗议世界。
大人们常常采摘一些干净的野棉花收拾着,冬天烧火烧馍的时候。揣进玉米面里边。后来我才明白,玉米面粘合性差,做馍馍时把面粉揣不到一起。人们利用野棉花的纤维拉扯,烧出的火烧馍才不致开裂。这同时说明,野棉花可以吃,不毒人。于是,我放学回来的路上。就采撷一大捧交给大人。但那时候我家很少烧火烧馍,因为常常是连稀饭填充肚皮都成问题,哪里能有玉米面烧馍吃那样的奢侈享受哦!
记得我在生产队当赤脚医生学医时,草药书上说,野棉花具有去除风火,解毒,治疗牙痛的功能。听草药先生说,还可以消化积食。我终于没有学成救死扶伤的医生。至于野棉花的前几种功效,我没有见过。倒是最后一种消化积食的功效,我亲眼所见。我们把那叫做“打饮食”。我家孩子当年在外婆家,逢着特别喜欢的食物,吃了个没饱局。饮食隔在肚子中间没法消化,上吐下泻,外婆家住在高山,也没法立即上医院。孩子外婆去房子背后地盖边扯回来一把野棉花,再加上些茴香藿香的叶子茎杆之类,洗尽,熬一罐子,滤出一碗水来,香喷喷的,再放一点糖,凉温,让孩子几口喝下去。过一个时辰,孩子的病就好了,欢快地去与其他孩子玩去了。这野棉花还真是有疗效。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缺医少药是普遍现象,于是,农村草药先生和他们的土法子土方子就自然多些。在他们眼睛里,百草都能够入药。我想,这也该是成就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之伟大的历史基础吧。
但野棉花很不受待见。那叶子,牛羊都不吃。春天,叶子很嫩的时候,偶尔有实在扯不到猪草的女人或者小孩子,割几把塞进其他猪草里面凑数。七八月份,生产队组织社员割草垫圈给小春庄稼积肥。人们在田埂地头割草,野棉花跟其他杂草一同做了镰刀下的尸体,填进猪圈牛圈,被沤成种小麦种玉米的肥料。冬月间,生产队组织社员铲除地盖,免得来年野草疯长袭住了庄稼。野棉花跟其他野草一样,倒毙在锄头下,被铲除精光。野棉花的根茎粗壮,肉头厚实,在锄头钢铁的重创下,筋皮分离,露出白生生的骨肉。但野棉花是多年生植物,哪怕只有一点点根须留在土壤深处,第二年也会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说到野棉花,就不能绕开家棉花——我姑且用一个“家”字,以示区别。我小时候就知道,川东一带出产棉花。我的同学李福昌是遂宁人,每次从老家遂宁走亲戚回来,都背回几床棉絮,几斤做袄子的棉花。生产队曾经在平地里和沟坝里几块大田里种过棉花。浸种,播种,反复几次地施肥,薅草,打芽,治虫,而且要求挺高,活儿挺麻烦,结果,秋天摘不回几斤棉花。因为磨刀河一带空气湿度重,日照不够充足,不适合棉花生长,家棉花靠长时间日照吸纳热量而成熟。再后来,我才知道,西北地区才是我国的主要产棉区。听说,在棉花成熟收摘季节,广袤的新疆大地,一片白花花的世界。近些年里,每年秋天,磨刀河畔高村乡就有不少农民工,在火车上颠簸几千里。去新疆采摘棉花,俩月时间,可以挣回万把块钞票。
古代人就能用棉花纺纱织布,裹体御寒。当然,富翁们还有丝绸罗缎穿。上世纪七十年代,突然时兴穿化纤产品的确良一类,伸抖,好洗,但二十年后,人们又推崇其自然环保的棉麻衣料了。除了棉花的用途广泛,棉籽还可榨油。不过,后来有专家又说棉籽油有“计划生育”的功能,人们就不敢买来吃了。
起初,我想,既然名字中都有“棉花”二字,它们总该有点亲戚关系吧——不论是堂亲还是表亲。当然,有家和野之分,就肯定有诸多区别。植株不同,家棉花是独立成株,单苗生长。叶子不同,家棉花叶子淡黄,叶柄和株杆成淡红色。花瓣不同,家棉花花瓣大些,白色居多,但没有野棉花的花瓣艳丽诱人。棉桃子不同,家棉花桃子一般都有水蜜桃那么大。当然,棉花更不同。家棉花的产量和用途不言而喻,而没有谁用野棉花缝制棉袄。我问过小学教我自然课的雍老师,他说,野棉花其实算不得棉花,只是样子略像罢了。野棉花纤维太短,没法纺线织布,缝进袄子,也不热和。
其实,我认为,最大的不同,还在于身份。家棉花那么娇贵,那么难于伺候,但它出身高贵的世家。野棉花再怎么说,一个“野”字的出身,决定了其低微卑贱的生命历程。
后来,我明白,它们应该没有亲戚关系。即使有,恐怕也出了“五服”。除了一个身价高贵一个身价低微外,就凭着野棉花是多年生植物,家棉花每年要浸种播植这一点,就足够证明。所以,我更理解,北方许多地方,不叫它野棉花,而把它叫做打破碗碗花——尽管我还不知道起打破碗碗花这名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