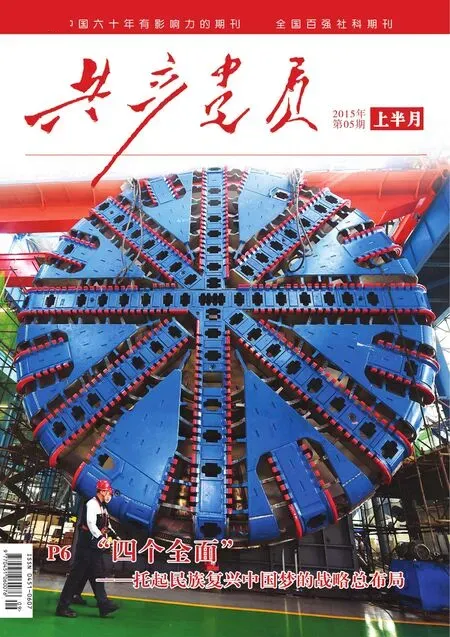左手理论右手舆论的侵华教父(下)——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家福泽谕吉
文/周力
如今,福泽谕吉仍然被日本右翼势力奉为“灵魂导师”和“精神教父”。谁能相信一个有着300年侵华之梦,行70载侵华之实,此后又70载高调反华的东洋邻国,会在一夜之间就改弦更张,铸剑为犁,变成一个福泽谕吉自诩的“文明之邦”“日新之国”呢?

福泽谕吉的头像被印在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上
领衔学术团体,手握自办媒体,依托庆应义塾阵地,
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时期名副其实的知识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要人。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到1902年去世,他以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发表一篇社论、评论、随笔的持续节奏,议论政治,臧否时事,阐述观点,影响政府和社会。
脱亚论恶邻国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抛出著名的《脱亚论》,否定和抨击中国,阐述他关于亚洲的外交观、战略观,引起强烈反响。
福泽谕吉在文中叫嚣,“支那朝鲜实行古老专制”“不知科学为何物”“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朝鲜行刑场面残酷”等等,都会被西方误解为日本也是这样,这就“间接地成为我外交的障碍,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解决的对策就是“脱亚入欧”,“与西洋文明共进退”,而且态度要坚决鲜明,“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它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
这些论点,是福泽谕吉“智慧”的“结晶”。
《脱亚论》问世三年前,朝鲜发生了动乱,清政府应朝鲜请求,派兵前去平定。福泽谕吉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支韩三国的关系》的文章,认为日本应乘机干预,将朝鲜由中国藩属改为日本控制,甚至不惜一战。
《脱亚论》问世两年前,福泽谕吉发表了《到支那去应奖励》和《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两篇文章。前者鼓励日本人把“支那的四百余州”当作闯荡事业的地方,“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都可以“积极进取”,表现出日本扩张主义者共有的贪婪。后者则诋毁中国为“一潭死水”,“支那人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开始从国格和文化的角度否定中国。
《脱亚论》问世前一年,福泽谕吉又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认为中国对西方“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没有进步的希望”,因此“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另一篇题为《东洋的波兰》,认为尚在进行中的中法战争“是支那灭亡的伏线”,预言中国会像波兰一样被西方列强瓜分。他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张来路不明,用汉字标注的《支那帝国未来分割之图》,叫嚣日本应乘势“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在故地(明末倭寇骚乱中国之福建、浙江沿海地区)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
福泽谕吉对中国资源的觊觎窥伺,对自己得以教益的儒学文化的否定诋毁,对中国应对西方文明举措的歪曲和中国与西方列强军事冲突中意欲分肥的贪婪,已凶相毕露。他在伪善的假文明外衣下,包裹着一颗思虑臻熟的军国主义扩张野心。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观点,对历史上藤田信渊和吉田松阴的侵华设计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如果说,藤田信渊和吉田松阴尚局限于领土资源上的贪欲、侵略路线的规划、“失之欧美,取之中国”的卑鄙,福泽谕吉则通过对中国、对东亚的国别歧视、文化诋毁和全民族的否定,增加了日本社会蔑视亚洲的盲目自信和侵华侵朝的“合理性”,以至后来日本侵略军一直自欺欺人地以占领邻国、解救亚洲的“远东宪兵”的姿态实施侵略。正是由于“脱亚”的国策,促使日本踏入太平洋战场后加入德意日二战轴心国,在狂妄中走向彻底失败。
“脱亚论”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日本近代中国观的分野,是日本与中国断交的另一种方式的声明。从那一刻起,它的巨大影响,使日本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战争前的非常时期。
主侵华 鼓与呼
福泽谕吉信奉强权武力,视其为日本的生存之道。他认为,“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箱弹药”,各国交往的途径只有两个,“或灭亡他国或被他国所灭”,因此日本要与“禽兽世界”看齐,走一条“内安外竞”、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国家之路,即法西斯军国主义扩张之路。而他谋求消灭并借此保存自己的对象,则是近邻中国和朝鲜。为此,他不仅在理论阐述上不遗余力,还通过具体规划、直接指导和社会发动等方式,冲到侵华一线直接作战。
福泽谕吉别有用心地美化战争,著文宣传“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随后,他又著文告诉日本社会,战争的目光要聚焦中国,因为“日本在东洋立国,与支那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必须高度予以注意”,方法是借机下手,趁火打劫。
——1882年朝鲜内乱,福泽谕吉蛊惑日本政府派兵干预,遭到中朝联合抵制,没能如愿。此后的几年里,他屡屡煽动日本政府对两个国家作战,并规划出一个详细的侵华路线:
首先应该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京城与支那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的要求。同时,我军从陆海大举进攻支那,直捣北京,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到热河。
这条侵华路线,与吉田松阴当年规划的思路如出一辙,一脉相承。福泽谕吉疯狂地为日本政府打气:“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愿全部充作军费……日本必然胜利。”为了让日本绷紧对华战争的弦儿,他撰文呼吁,与谈判的准备相比,日本“更应该作开战的准备”,甚至“希望的是御驾亲征”——天皇亲自率军侵华!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福泽谕吉更是密切关注,随时煽风点火。战前,他就对李鸿章与朝鲜政府往来电文中,斥责日本干预朝鲜内政的语句不满,呼吁日本政府“一刻也不要犹豫,要与支那为敌,断然开战”,同时不放过朝鲜这个与中国“同一个洞的狐狸”。
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著文疾呼:“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活到今天,才看到如此光荣的事”。他给日本国民和军队鼓气说,“我军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锐的武器,打他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结果本是明明白白的”,而“野蛮不开化的中国人”,“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拜九叩,感谢其恩”。战争中,他建议日本政府驱兵“直入北京可也”,让中国承认日本“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甘心俯首于文明的脚下”。他在1894年8月11日至16日接连发表文章,呼吁日本军队“赶快攻略满洲(中国东北)三省”,灭亡中国,否则,“旷日持久,会上支那人的当”。他还著文《支那庞大,但不足惧》,进一步分析日本打败中国的理由:中国政府腐败,人民不团结,中国人“喜欢虚张声势……出动一两万的兵力就声称几十万,古来笔法即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痛哭流涕,组织了“报国会”,带头募捐,支援战争。仅他自己就捐出名列全国第二的1万元巨款(这也是后来他的头像被印在1万元面值日元上的原因之一)。他不仅要求日军疯狂掠夺,还再次鼓吹天皇御驾亲征:“越遥远之大海,大纛(天皇旗)迎韩山之风飘扬之事,亦可考虑。”他建议,在靖国神社,由天皇“亲任祭主……招待全国战死者之遗族,使其得到临场之荣誉”,借以鼓舞士气。
日本兵攻占中国旅顺后,疯狂屠城,造成6万多人被杀害。当这一兽行被国际社会谴责时,福泽谕吉一反以“文明人”自居的虚伪,狡辩说“不能把这些人当普通人看待”,因为中国人“不讲信义”,“这些人是军人伪装成市民的”云云,虚伪的面孔不攻自破。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后,他积极建议内阁借谈判之机逼迫清政府将旅顺、威海、盛京、山东和台湾等地割让给日本。一时间,福泽谕吉的侵华表演甚嚣尘上,影响巨大!
——1900年,在福泽谕吉的生命降下帷幕的前一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福泽谕吉立即建议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国联军,在英美不能派大量军队来华的情况下,借机进军中国,进一步获取领土和权益要求。结果,在32000人的八国联军中,竟出现12000人的日本军队。作为主力,日军不仅打到北京,获得赔款,还一度进兵厦门,企图单独占领福建。自此,日本把自己定位在“远东宪兵”的强权位置上,不断战争,不断侵略,直至1945年在二战中举国惨败。
往事并不如烟。回首当年,由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国权扩张论”和“武力侵华论”在“倡导文明进化”的外衣下流毒甚广,不仅对当时的日本社会舆论具有极大的偏激误导,也在庆应义塾的课堂上不断植入学生的头脑之中。他所谓“文明”和“野蛮”之分的地域文化歧视,日渐成为日本蔑视邻国、武力称霸世界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他集路线设计、理论舆论和教育于一身的文人侵华模式,更加强化了日本侵华的内在理念和外在成效。
如今,卷帙浩繁的福泽谕吉全集仍大行于世,庆应大学的“杰出校友”小泉纯一郎之辈在日本右翼势力中的影响与福泽谕吉的侵华设计还在遥相呼应,福泽谕吉仍然被日本右翼势力奉为“灵魂导师”和“精神教父”。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日本,知晓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掌握日本侵华的理论脉络,仍是今天国人的必修课。谁能相信一个有着300年侵华之梦,行70载侵华之实,此后又70载高调反华的东洋邻国,会在一夜之间就改弦更张,铸剑为犁,变成一个福泽谕吉自诩的“文明之邦”“日新之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