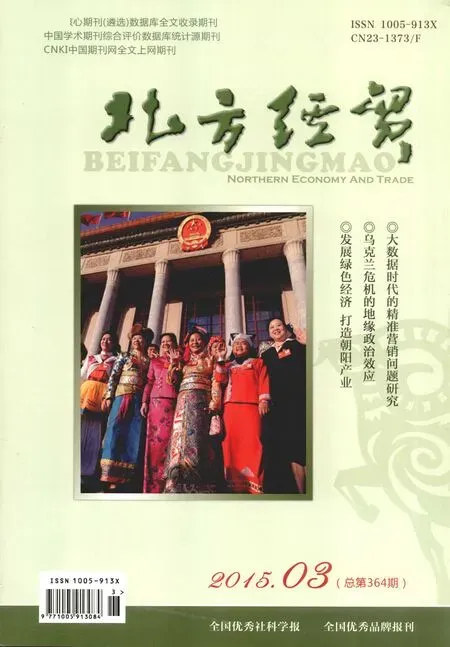法律手段还是经济手段让年轻人“常回家看看”
周维良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珠海519090)
法律手段还是经济手段让年轻人“常回家看看”
周维良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珠海519090)
老龄化背景下社会转型期如何保障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和亲情赡养是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国家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款的修订内容,从社会伦理上角度看,本质是用法律保障子女对父母尽孝的社会道德,维护儒家传统的家文化价值观和孝道文化。从经济学视角上看,传统家庭兼具有经济功能和亲情功能,现代家庭中经济功能衰退后亲情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倡导子女行孝、弘扬孝道文化仅通过法律手段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政府应设计一套包括住房、税收、补贴、社保在内的经济机制激励公民行孝、企业支持行孝。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家庭经济功能和亲情功能;经济手段行孝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人口计生委的资料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我国在1999年就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一方面,由于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4-2-1”结构和“4-2-2”的家庭日渐增多,家庭趋于小型化,并且三代直系家庭中老年人的数量构成不断下降,[1]年轻人的赡养负担加重;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引起工作机会的地区间差异,人口流动越来越普遍,城乡“空巢家庭”和“留守老人”大幅增加。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空巢老人家庭占家庭户总数的31.77%。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空巢比例上升了8.94%。两方面的作用下老年人的经济扶养和亲情赡养在家庭内部得不到充分实现。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同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却建设滞后,老年医疗和老年社保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水平尚未到达足以取代家庭养老的程度。这种背景下,2013年7月我国修改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新法”)。
新法第13条将以前的“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老年人养老依靠“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前者即为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模式,老年人住在自己或子女的家里,自我照顾或由子女赡养服侍,安度晚年,这种家庭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和精神慰藉自然可以兼顾;后者即社区养老模式,可能会扩大了老年人和子女的地理距离和情感距离。新法第14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这一条对赡养人既提出了经济供养要求,又提出了精神慰藉要求。为了防止今后社区养老扩大了老年人和子女的地理距离和情感距离,新法第18条中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第14条和第18条都强调了子女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义务,即俗话所说的“常回家看看”。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新法颁布的目的在于保护老年人在经济和亲情两个方面得到充足赡养,法律强制性规定自然有一定的效果,但难以完全保障老年人得到家庭的精神慰藉和情感关怀。“你可以把牛牵到河边,但不一定能让牛喝水”,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赡养目的,除了法律手段外,还得依靠经济手段,两者相互补充。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社会伦理分析
二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奉行“家天下”的治国理念,皇帝视自己为君父,向子民倡行忠孝节义,把维护家长制的社会等级秩序作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手段。在历代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地的鼓吹下,家族伦理主义成为儒家传统价值观之一。例如,孔子认为搞好家庭内的“孝”“友”关系就是搞好了政治。“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孟子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篓上》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在理论上明确了以建设家族伦理作为王道政治的基石,建立在这种伦理思想上的社会等级秩序,也就成为了封建礼教。为了保证家庭伦理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基础地位,儒家学者不惜借助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引礼入法。一方面用礼来对法律施加影响,如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就是用儒家经典《春秋》的经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实践。《后汉书·应邵传》中记载“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2]另一方面用孝道来调节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等级关系,如《孝经》由东汉至明清均被规定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历代儒家思想渲染下,尽孝道成为中华民族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除了思想上宣扬孝道敬老外,历代王朝还颁布实施了许多养老法令,用法律来保证礼教秩序,“礼法并用,德刑为辅”,使得法律儒学化,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在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养老难题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历代法律条文中,不孝是十恶之—,父母若向官府控告,子女要受到严厉惩处。如《唐律疏议》明确规定,无论是子孙本人或者他人等,只要触犯了封建统治者认定的孝行为,一律加以严惩,轻则处以笞、杖,重则处以绞、斩。如规定:“‘恶逆’者,常赦不免,决不待时”。“闻父母丧,匿不举哀,流;告祖父母、父母者绞,从者流;祝诅祖父母、父母者,流。”[3]
在依法治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用法律的强制手段规定子女“常回家看看”,以尽孝道,体现了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用法律保障孝道伦理的实现,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在社会转型期维护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不得不用的手段。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家庭的养老功能,除了法律的强制性义务要求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外,还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能使公民有能力和有意愿践行孝道。
三、传统孝道伦理的经济学分析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个人和家庭的生存经常处于风险之中。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收成可以规避未来生存风险,但传统中国社会科技进步缓慢,特别是由元到明清,人均收入水平长期陷入增长停滞(麦迪逊,2003);[4]通过个人之间的经济交易与精神交换实现互相帮助与资源共享,也可以提升家庭和社会的风险规避能力。[6]后者发生的个人间经济交易需要契约制度做为保障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和交通技术设施尚不发达,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的地域范围有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纵向的关系为主,社会横向的关系的程度处于不发达状态(金日坤,1991),[5]与陌生人的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使得交易成本太高以致交易无法达成。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风险,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主要在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家庭内部和家族内部进行,交易的进行不需要今天的合同法等调整横向社会关系的法律来调整,而需要伦理秩序等调整社会纵向关系的道德来规范,保证交易在家庭和家庭内部顺利进行的契约制度正是传统的封建宗法伦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成年人为幼年子女提供生存的物质保障,幼年子女成年后则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为了防止幼年子女长大成人后违约不赡养老人和虐待老人,家族内部有族长运用家法主持家庭伦理秩序,家族外部有州县官府运用国家机器维护宗法制度。所以说,传统农业社会里家庭的功能首先是经济互助,其次才是精神互助,家庭内父母和子女缔结了隐性的社会伦理契约。
在这样的隐性契约关系下,养儿防老就成为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6]相匹配的文化和制度则被先儒们设计出来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7]孝文化的首要作用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其次才是亲情功能。[6]在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社会里,为了实现“家”的这个交易制度下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利益交换,子女的孝顺排在第一,而当一个社会的温饱问题退居次要地位的时候,家的经济功能将由该社会的其他制度安排所接替,家的亲情功能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目前我国的人均收入已达中等发达国家程度,但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比较大。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整体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年数在增加,从2002年的城乡人均差距4年达到2010年的城乡差距11年,而各省内的城乡差距,GDP大于3万亿元的京津沪苏浙蒙地区是7-9年,GDP小于2万亿元的藏陇云黔是14-15年。[8]沿海地区和城市的收入水平较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较高,家庭的经济功能已经退化,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血缘关系纽带下的亲情功能。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和社会的收入水平比较低,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够大,家庭仍然是老年人获得供养、子女获得投资的地方。在这些地区,家庭既具有情感慰藉功能,又残留有风险共担、利益交换的经济功能。考虑到我国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国家规在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在第2章第14条既规定了家庭的经济功能,又在第18条专门强调了家庭的亲情功能,规定了年轻人有“常回家看看”的法律义务,否则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然而,用立法的手段强制年轻人履行对长辈的亲情义务,延续中国的孝文化传统,能达到目的么?
四、“常回家看看”的现实困境
我国人口分布已不同于三十多年前,年轻人为了工作四处流动,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人口流动常态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己达到26139万,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11700万,十年间增幅达到81.03%。[9]精神赡养对于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人自然比较容易解决,对于远离父母为生活和前程奔忙的年轻人来讲,实现“常回家看看”的愿望却存在诸多困境。
困境之一是收入对于年轻人“回家看看”的制约。年轻人从参加工作到安身立命,需要经历较长时间。因为工作的绝大部分收入用来支付住房、医疗、应酬交际、个人娱乐后,可支配收入所剩无几,对一部分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不断增长的交通费用使得跨越遥远的距离从工作地返回家乡探望父母是一笔比较沉重的经济负担。虽然说孝道与亲情无价,但收入水平不高确是活生生的现实,即使有心尽孝,也无力返乡。而对于另一部人来说,由于出外打拼多在工作机会比较多及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大中城市,即使有把父母接来身边照顾的想法,面对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也只能望而却步,遑论那些身体不好不能长途旅行的年迈老人,他们的亲情家园也只能是梦里落花而已。
为了支持子女对父母的尽孝行为,国家于1981年公布了《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明确了“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与配偶或父母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体假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探亲待遇。根据实际需要,单位还应当提供路程假,而且职工探望配偶和未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由所在单位负担。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在本人月标准工资30%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所在单位负担。除此之外,职工在规定的探亲假期和路程假期内,单位还应当按照本人的标准工资发给工资。”然而,这一规定不适用于非公有制企业。当前我国的企业所有制结构与三十多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公有企业占据绝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公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从2008年到2012年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在75.51%-78.53%之间[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年鉴的就业基本情况表计算],但这部分劳动者并不在1981年《规定》的受益范围内,探亲费用由个人支出。
困境之二是闲暇时间对于年轻人“回家看看”的制约。虽然国家早在2008年颁布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但这一法律上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却遇到软约束的困境。例如第五条中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这条规定并不具有强制性,留给用人单位灵活调整的余地比较大,而用人单位又往往把薪资奖金、晋升考核与休假时间挂钩,导致一方不愿放年假,一方不敢请年假。此外,2008年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在第17条中只是规定了劳动合同要有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条款,对于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如何计算则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在年假的执行上,企业握有主动权,条例的约束对企业来说是软的,而软的约束在现实中是效果有限的。这样,由于年轻人得不到年假时间,法律上的“常回家看看”只能变成现实中的“想回家看看”。那么企业为什么不愿意主动安排职工的年休假呢,原因自然在于职工离岗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产生经济损失。
五、解决“常回家看看”困境的经济手段
怎样才能把“常回家看看”的愿景变成现实呢?造成年轻人“不回家看看”的两个原因都与经济有关,如果纯粹依靠法律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尽孝的道德问题。法律自然有维护道德的功用,所以先儒们将法律儒学化,德刑相辅,但如果只依赖法律来解决道德问题,那就会变成“法律万能主义”。[1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维护和弘扬儒家传统的孝道文化,还需借助经济手段。
孝道文化的维护、家文化价值观的宣扬,不仅是公民个人的道德义务,也是政府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公民个人是尽孝的行为主体,也是尽孝行为的受益人;政府是公权机构,负有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倡行传统孝道的责任;企业是社会的经济单位,是大家庭文化的受益者,也应负有社会责任。政府应建立一套维护孝道亲情文化的经济机制,将劳动者个人、政府及企业纳入其中,保证劳动者有能力尽孝心、企业有意愿帮助劳动者行孝,引导尽孝的道德风尚。在这种机制下,老年人权益也能得到维护与尊重。目前我国尚没有成熟的经济机制支持鼓励尽孝行为,但可以借鉴儒家文化圈内其他国家的做法由政府设计出一套中国特色的尽孝机制,这套机制的根本原则应该是让利于民。具体来讲,政府可以利用财政税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在住房方面为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共同生活提供方便。[11]在现在廉租房和保障房供给政策的基础上作适当调整,增加保证三代人共同居住的大面积房屋的供给,并优先分配给与老人共同生活的被保障家庭。在购买大面积的商品房而申请银行贷款时,如商品房用来与老人共同生活,政府提供贷款利息补贴。如遇有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持购房贷款但又愿意与老人共同生活的,政府担保机构可以考虑其他贷款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安排贷款担保。
二是所得税方面的调整。现在的个人所税以个人收入为基础进行征税已经不能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形势,随着人口老年化趋势加剧,税基人口比例越来越少,税源也就越来越枯竭,应该改为以家庭收入为基础进行征税。家庭收入以共同生活的整个家庭三代几口人的平均收入来计算,这样那些与父母共同生活而父母又无社会保障基金可以领取的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负会大幅下降,等于间接提高其可支配收入。销售旧有住房购买新住房是为了与老人共同生活的,则免除旧住房的营业税与个人所得税。对于积极安排职工休探亲假的企业,政府可以安排一定额度的企业所得税收减免。对于与父母共同生活的赡养者,继承父母遗产时应予以减免遗产税。
三是补贴措施。对于与老人共同生活但家庭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当地一定程度的,政府可以每年提供一定金额的补贴,缓解赡养者的经济负担。当前的地区经济差异使得大多数老年人居住地与子女工作地相隔遥远,对于想回家探望父母又囊中羞涩的年轻人,政府可以提供路费补贴,哪怕是单程的路费补贴也能减轻劳动者的交通费用负担。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与老人共同生活,或居住地不超过“一碗热汤”的地理距离的还应该给予老人护理补贴费用,用于居家养老所需。
四是社保覆盖对象调整。社保基金的缴纳应以三代同堂的家庭收入水平为计算基准,但社保户头分立,有工作收入的子女应该为无工作收入的父母填补社保公积金空额,家庭成员之间负连带缴纳责任。当赡养者失业时可按大家庭生活所需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标准,或延长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时间。
以上四种手段运用得当,都能有效地激励年轻人对老人进行经济赡养和亲情赡养,达到政府尊老敬老的公共政策目标,维护老龄化社会的和谐稳定。但要完成孝道文化的宣扬和家文化价值观的继承推广,最根本的还是破除现有的城乡壁垒,消除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使为当地经济建设贡献力量的家庭融入当地社会,使年轻人在当地工作照顾父母而不用背井离乡,子女才有能力和意愿“常回家看看”。
六、结语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改变,社会日益老龄化,家庭的经济交换功能和亲情功能日益弱化,儒家传统的家文化价值观和孝道文化正面临嬗变和解体,为维护传统文化,增强家庭凝聚力,政府应担负起责任,鼓励引导公民尽孝、企业支持职工行孝,维护家庭情感功能的完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用立法手段将孝道入法倡导行孝外,还应采取相配套的经济手段激励公民尽孝,在住房、税收、补贴、社保方面提供优惠与减免,缓解劳动者在行孝方面有心无力的困境,引导公民践行“百善孝为先”的价值理念,使《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所追求的亲情孝道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
[1]王跃生.三代直系家庭最新变动分析—以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J].人口研究,2014(1):58.
[2]转引自俞根荣.俺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140-141.
[3] 转引自徐慧娟.《唐律疏议》中的孝伦理思想[J].湖南社会科学,2011(6):43.
[4]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M].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
[5]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 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7(1):1-17.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3.
[8]杨华磊,周晓波.中国城乡及省际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数据中凸显的唯象法则[J].经济研究,2012(s1):47.
[9]邹湘江.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流动与分布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1(6):24-26.
[10]范传贵.误读“常回家看看”淹没立法真实价值[N].法制日报,2013-07-04.
[11]刘云香.儒家文化圈背景下的家庭价值观与社会保障制度[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55-58.
[责任编辑:兰欣卉]
Legal means or economic means let the Young always Go Home for Parents?
Zhou Wei-liang
(Zhuhai Polytechnic College,Zhuhai Guangdong 519090)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how to safeguard the economic support and the affection support of old people is a challenging problem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the state revises the old’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law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ual purpose.This law’s partial revised clauses aim a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ethical essence,using legal weapons to keep the social morality of children treating parents with filial duty,maintaining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 family culture values and culture of filial piety.Looking from the economics perspective,the traditional family has both the function of the economy and the affection,in the modern family economic function recesses while affection function dominates.Advocating children’s filial piety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are not enough only through legal means,must be supplemented by economic means.The government should design a set of social economic mechanism with housing,taxes,subsidies, social security inside to initiate citizen’s filial piety,enterprise’s support to filial piety.
the protection law of the old’s rights and interests;family;economic means
F063.4
A
1005-913X(2015)03-0047-04
2014-12-10
周维良(1972-),男,湖北应城人,经济师,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