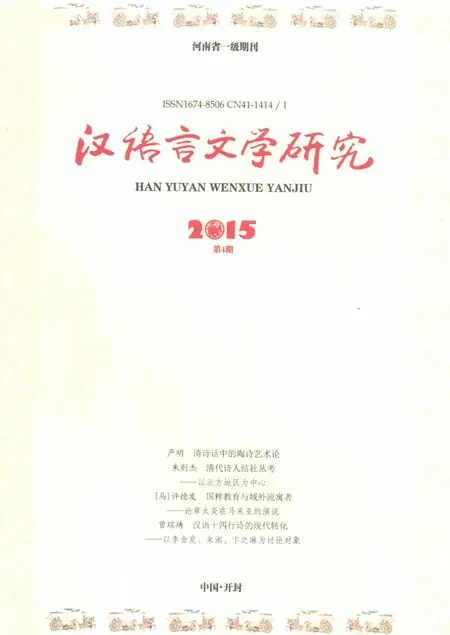论《修道士》的反讽叙事艺术
王晴阳
作为西方文艺理论中历史悠久的诗学概念之一,反讽被不断地应用于文学和哲学的理论领域。尤其是20世纪以来,历史剧烈动荡,语言学深刻转向,现代人在生存困境中感受到断裂和破碎,诗学不再具有阐释和照亮人生存在的寓意,而是倾向于一种迷宫式的高智商搏斗。反讽就是这种智力游戏的典型代表,它将各种语言学、叙事学要素加以整合,呈现出各因素既有交织又有悖立的局面,应该说,它是最丰富厚重,也最轻巧空灵的诗学概念之一。反讽在概念上具有拓殖性,意义边界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而拓展,形成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概念的未定性带来理论应用的滞后性,但同时表征着反讽叙事具有深度挖掘的潜力。纵观世界小说评论史,汉斯·罗伯特·耀斯(Hans Robert Jauss)曾有论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的作品。”①[德]汉斯·罗伯特·耀斯著,顾建光等译:《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可见反讽策略的运用是衡量一部小说成就的重要标准,基于此,本文希望对《修道士》独特的反讽叙事艺术作出深层次的解析。
《修道士》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成为18世纪最受欢迎、最畅销的经典性哥特式小说之一,“它的‘哥特式’特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恶魔式修道士的形象塑造;(2)对情节结构的设置与营造;(3)对心理世界描写的拓展和挖掘”②李伟昉:《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这三个方面对我们解读文本具有指引作用,笔者以此为基础,以反讽叙事为理论工具,结合《修道士》的成书背景、文体对话、整体结构、情感类型、表达模式、宗教内涵、人道主义思想等诸多方面,分析小说叙事话语中反讽策略的介入与渗透,以期揭示反讽与叙事紧密结合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设置、心理世界描写等方面的艺术魅力。正是反讽叙事铸就了《修道士》的经典性和生命力,使之在揭示荒诞世界和复杂人性时更加深刻,也极大调动了读者参与情节解密的兴趣,并使之警醒和沉思。
一、语词反讽:似是而非的人物形象
反讽源自希腊语eironeia,意指对某一事件或某个人物的陈述或描绘包含着与阅读所感知到的表层寓意相左的含义,真相与表象之间形成干扰和冲突。在修辞学范畴,反讽即反用法,是一种词义的逆转,常常涉及修辞、叙述、风格等艺术领域。反讽还要承受语境的压力,语词反讽蕴藏在叙事文本里,就是利用语词之间的确定性进行相互消解的过程。若要解析《修道士》中的反讽、虚构、显谎等手法,符号学家格雷马斯 (A.J.Greimas)和库尔泰(Joseph Coutes)所建立的“述真方阵”(carré-véridictoire) 对文本分析大有裨益。此方阵把“是”(être)与“似”(parat^ire)作为“真”的两极,那么,与之相对立的就是“非是”(non-être)与“非似”(non-para^itre),这个符号方阵有四种可能:
1.真(le vrai):即“是”又“似”;
2.假(le faux):即“非是”又“似”;
3.幻觉(l’illusoire)或想象(le mensonge):“非是”但“似”;
4.保密(le secret)或伪装(la dissimulation):“是”但“非似”。①述真方阵的具体内容详参 A.J.Greimas and Joseph Coutes,Semiotics and Language—An Analytical Dictionary,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82, p.312.
刘易斯在小说第一章就开始使用这种方阵,别有用心地揭示出部分真相:
利奥娜拉和安东尼娅连忙从座位上站起,伸着头,细细地打量这位修道士。
他,一副贵族派头,身体高大,相貌不凡,英俊倜傥,长着一个鹰钩鼻,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两道黑黑的眉毛几乎连在一起。他皮肤黝黑;学习和祈祷已完全使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他的光滑的无皱纹的前额透着宁静和安详,他面貌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满足感,似乎在显示着他是一个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人。他向听众谦卑地鞠了一躬,但在他的面容上和举止上仍有些足以让听众敬畏的严厉。他就是卡普琴斯教堂的安布罗斯院长,被人誉为“圣人”。②[英]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著,李伟昉译:《修道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这段引文呈现出意蕴深厚的双层叙述,法国修辞学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对叙述层次做过如下表述:“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下面紧接着产生该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故事层。”③[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他把起始的层次称为故事外层或超故事层。在《修道士》中,全知叙事讲述安布罗斯与安东尼娅的故事,可称作故事外层。引文是通过利奥娜拉和安东尼娅的眼睛打量,是深入故事人物心理的第一人称视角。但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利用全知视角进行干预,每句的前后描述都相互抵消、彼此对立:“贵族派头”和“鹰钩鼻”表现出高贵与阴鸷的相互冲突;“皮肤黝黑”与“学习和祈祷使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又在暗示着安布罗斯先天本性与后天修养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似乎”使“宁静”“安详”“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等褒义词都耐人寻味;举止的“谦卑”与面容上呈现的“严厉”产生显在的龃龉……几组悖立的形容词对举出现,提示读者穿透其表象,领会深层意蕴。两位女性观察到的修道院院长是高尚圣洁甚至是完美无瑕的,但是操纵文本的叙述者的声音却不断地质疑,他嘲弄进而直接诋毁安布罗斯,后者对前者进行顽强的否定和拆台,破坏了言意固有的对应结构,最大限度地扭曲言意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呈现出复杂难解的对立局面。“他就是”一句明确了主人公的神职身份,是所谓的宗教化身,“被人誉为”还是间接转述,修道院院长一职看似和“圣人”挂钩,实则全是讥嘲。此句意在说明,这一形象除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外,还蕴藏着典型而深刻的社会意义,上述这些不确定性大大激活了阅读兴趣,召唤读者的心智活动。
加拿大文艺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从语义特征方面扩展了反讽界限:“第一,反讽具有关联性,是一种所言与未言意义的交流过程;第二,反讽具有包容性,两种意义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第三种意义;第三,明言与未言之意两者之间只是差别,但并不冲突,反讽意义同时存在于两种或多种意义的交流过程之中。”④参见 Linda Hutcheon, 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Oxon: Routledge, 1994, p.66.反讽策略为这一段文字增添了含蓄的魅力,女性声音明言了部分现实,男性声音则吐露剩下的信息,小说人物被叙述者操纵着又时时有游离的危险,二者在进行深层次交流时,反讽意味就生成了。反讽手段亦为文本带来意义的多元性和内容的复杂性,含而不露的微妙描写,恭维的言辞下表达出莫大的轻蔑,都让读者心存疑窦,猜想这位院长的身世背景及后续故事,并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后续情节的解密。
综上,“述真方阵”里的“真”在“是”和“似”的两极之间纵横摆荡,蕴含诸多潜台词。“‘是’可以理解为发送者的诚信意图,‘非是’就是意图不诚信;‘似’可以理解为文本忠实地表达了(无论诚信与否的)意图……幻觉是接受者幻觉,保密是对接受者保密”①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0页。。换言之,发送者假装真诚,利用伪装叙述和描写让读者尽情想象,却无法把握修道院院长的真实性格,从而增添了形象的丰厚性。这些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的语词暗示却强烈地表征了叙述者的在场,充分展现了语词的歧义性:他时时压抑着要一语道破的冲动,使用反讽言辞使真相更加意味深长,又巧妙提醒思维敏锐的读者挖掘字词下的幽深含义,不要被表象误导。
同时,反讽借助白昼和黑夜无情地揭露了修道士,故事情节常常被安排在夜晚,夜晚的行动具有不可告人的隐匿性,与白天道貌岸然的形象形成尖锐对立。反讽还涉及了其他人物形象,雷德蒙的叙述里有年轻英俊又阴险歹毒的奥托,阿格尼丝视角下的圣克莱尔修道院院长多米娜竟然是凶狠残忍的。
《修道士》以主人公身份命名,安布罗斯是宗教清规戒律的受害者,又是人性中固有的情欲的施暴者,双重角色可以相互对调。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orge Frazer)曾总结过评价文学人物形象时的标准和角度:
喧闹的历史舞台上所成就的每一个大人物都是五颜六色的角色,他的色彩斑驳的服装根据你从正面还是反面、从右面还是左面来观察他而有所不同。他的朋友和敌人从对立的方面观察他,他们当然只看到其外套上正好朝向他们的那种特殊颜色。②[英]弗雷泽著,童炜钢译:《〈旧约〉中的民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页。
在塑造安布罗斯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既不一味地否定丑化,又不固执地为其开脱罪责,一方面表现他虔诚可敬、正直善良的理性光芒,一方面又揭示出他道貌岸然、情欲膨胀的可憎面目。小说中,安布罗斯自我评价十分良好,甚至妄称:“宗教又怎么能和我安布罗斯相比呢?”③[英]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著,李伟昉译:《修道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其他角色对该人物的看法也是多姿多彩:安东尼娅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洛伦佐却认为他不一定能在充满诱惑的考验中凯旋而归;利奥娜拉则直言再也不想看到那副阴森森的铁板面孔。自我形象与他者眼中的形象进行潜在的交流与对话,多种视角在差异中相互斗争,誓约与毁约、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兽欲错综杂陈,在放射状的描绘中使形象呈现出丰满而矛盾的真实性。刘易斯利用反讽叙事模式对修道士形象进行别样塑造,正是尊重原型、尊重艺术的有益尝试,对如何全面塑造和阐释文学形象的立体复杂性有深远的示范意义。
《修道士》是英国哥特小说中富有韧性和阐释空间的文本,作者拥有独特的小说叙述意识和叙事技巧,采用非直陈式的修辞介入,智慧地将观点藏匿在曲径通幽的反讽叙事中,首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修道士形象,彻底颠覆了之前文学史中该类人物的正面形象,犀利又深刻地揭示出修道士乃至人性中最本质的真相。作者对叙述视角的控制极为妥帖,既点明了两位女性的立场,又将叙述者的态度泄露几分,深度契合了小说作为“一个既未解释也未隐藏的符号”④[美]希利斯·米勒著,申丹译:《解读叙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的评价标准。
二、情节反讽:言此意彼的斑斓文本
反讽叙事普遍存在于文学艺术中,已经成为一种颇具研究价值的文学现象,甚至可以由此观照文本生成背后的文化环境。反讽叙事对小说内在价值的构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作品意义生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刘易斯将反讽作为哥特式小说叙事的核心手段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厚复杂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语境。反讽可以表达深藏在内心无尽的焦虑和失望,展现人类在现实中无法如愿的欲望,故而,反讽是我们阅读和阐释某一时代和文学文本的关系时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刘易斯以16世纪西班牙的一所修道院为背景,融合超自然性、恐怖性和情欲等哥特式因素,展现了灵与肉不可调和时内心搏杀的惊心过程。归根结底,哥特小说和感伤主义小说、墓园诗歌一样,都是当时社会精神状态的曲折反映。
反讽是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因其不确定性,极易被宽泛地划分为修辞学意义上的形式因素。但事实上,反讽文学“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既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①[英]D·C·米克著,周发祥译:《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修道士》的故事情节虽然恐怖,但是在形式上可谓诗意葱茏。《修道士》采用戏仿的叙事模式进行创作,通过对古典诗歌、民间史诗等体裁进行有意模仿,不动声色地进入反讽佳境。《修道士》诗文并茂的显著特色来源于对诗歌的灵活运用,刘易斯本人嗜好诗歌创作,曾出版过《诗集》,这在小说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个人特色。
《修道士》分三卷共12章节,每章起始部分都摘引一段诗歌,它们绝非形式主义的摆设,而是为了营造氛围、补充情节或揭示人物心理。部分诗歌还在赞美背后隐藏了讥讽,以悖逆双方的并举实现反讽意图,内容与形式的对立越尖锐,反衬就越强烈,讥诮之意就越明显。刘易斯洞察了小说内容与形式两种因素的悖逆生成状态,为了维系其间的平衡,便采用了暗含挖苦、否定和抨击的修辞策略。比如,修道士的神职身份埋葬了安布罗斯本能的情感渴求,他陶醉在自负虚荣的世界里,在回想布道时的慷慨陈词以及听众满含崇敬的目光中得到强烈的幸福感受。
英国学者威廉·赫士列特(William Hazllit)对《修道士》有过如下评价:“点缀在这声名远扬的小说中的一些诗篇,特别像‘朗斯萨拉斯的战斗’与‘流亡’,有一种浪漫而欢乐的和谐,那情调像月夜行走的朝圣者唱出的歌声,或者说像使夏天海上的水手入梦的催眠曲。”②[英]威廉·赫士列特:《论英国小说家》,转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0页。诗歌已然成为描摹人物、揭示主题的手段,这就提醒我们注意《修道士》中诗歌的有意设置。《流放者》③该诗篇幅较长,此处不便引用,原诗见[英]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著,李伟昉译:《修道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 189-193 页。(即上文提及的《流亡》)一诗出现的客观目的是埃尔维拉以此来劝慰洛伦佐,提醒他尽早切断与女儿门第不对等的感情,以免日后跌入更煎熬的痛悔之境。这种点拨不是棒打鸳鸯,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劝谏当事人避免重蹈覆辙。因为当年埃尔维拉就有过相似而惨痛的经历:出身卑微的她与来自名门望族的格瑟尔沃相互爱慕并暗结连理,但男方家庭的否认逼迫二人流落海外,在异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后来,格瑟尔沃客死他乡,埃尔维拉只好带着女儿回到祖国,却发现年轻的贵族洛伦佐已经爱上女儿并企图私奔。《流放者》表面上只是流放者的哀歌,是男女萌生爱慕之意后的续篇。其实不然,深沉的反讽力量却在于它能够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人类生活中的某种社会现象,描写社会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从中揭示道德问题,在特定的情景下爆发威力,以文学形式对社会生活提供诚挚而有分寸的道德引导。
此诗在补充故事情节、渲染背井离乡的苦楚等方面功不可没,它详尽地宣泄了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凄惨情绪,把思念故土、渴望团聚的悲戚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用故国之思的宏大题材去反映微不足道的男女之情,构成了形式与内容的不对等,这样琐屑的小情意在爱国思乡的庄严情感下经不起衡量或比照,刘易斯戏仿技巧的圆熟敏锐之处就在于此。他也以此劝诫痴情小儿女以理智的目光处理情感,用更端正的态度对待人生。“仿英雄体史诗的作用就在于将一个人物、或场景、或语句对应、或对比于另一个人物、场景或语句,以使我们体会到一种既相似又有区别的感受”①David Fairer, The Poetry of Alexander Pope.London:Penguin Books Ltd, 1989, p.146.。此诗的戏仿功能也可以由此阐发,在相似又不叠合的相互交融中,诗歌获得了普适性的恒久意义,种种因素的交流碰撞下生命力得到新的萌发与繁衍。从文体设计上看,作为诗歌的《流放者》也具有回环往复、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浓郁的抒情乐章冲淡了小说里的压抑世界,舒张了读者紧绷的神经,叙事节奏被处理得有急有缓,张弛有度。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诗歌的艺术形式进行嘲笑,提示读者在适当的距离从道德、审美角度重审情感生活,赞颂了真正爱情力量的感天动地,讽刺了当时社会(如格瑟尔沃家族)门当户对的陈腐的嫁娶观念。他以嘲弄、讽刺的手段纠正庸俗、虚假的社会风气,试图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拨正偏离人性轨道的社会行为,反映出刘易斯本身追求中正和谐的社会理想。
与诗歌一样,情节中的直接反讽和远距离对照比比皆是。雷德蒙自述在客栈遭劫遇险的情节是一处微观对比,他表明留宿意愿后,女主人的不快和烦躁使读者对其产生厌恶之情,男主人的豪爽和殷勤令人尊敬和信任,然而,雷德蒙上楼时看到床单上的深红血迹才疑窦洞开,这是一次颠覆性的嘲弄:憨厚友好的男主人是杀人强盗,女主人的简慢冷漠都是为了提醒他、拯救他。亲历者的叙述增添了情节的悬念意味,烘托了气氛,也通过反讽对雷德蒙和读者的自作聪明进行了一次教育。作为凡人和幽灵打交道的典型事例,雷德蒙与滴血修女的交往离奇却充满了巧合。虽然令人毛骨悚然,但是这段经历里的滴血修女死而复活,对爱情执着真诚的态度却令人唏嘘,尤其体现在她三次的喃喃自语中:“雷德蒙!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你的身体、你的灵魂都属于我!”②[英]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著,李伟昉译:《修道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142页。这是对雷德蒙感情忠贞程度的捉弄,也是一次考验,与修道士只重感官享受而轻视精神领域的行径构成远距离的反讽对照。此外,洛伦佐和阿格尼丝真挚的感情也潜在讽刺了安布罗斯与马蒂尔德的肉体接触。
反讽的矛头直指违反人性、荼毒生灵的宗教法规,修道院的教育和生活破坏并扭曲了安布罗斯良好的天性。他有进取心、有魄力、无所畏惧,而且思维敏捷、判断果敢稳健,但是修道士的教员们竭力压抑他的原始美德,使他不得同情他人的错误,拒绝人世间的仁慈,把自私视为圭臬,受到冒犯时绝不宽容而是要残酷报复。因而,修道院忙于根除他的善德,禁锢他正常情感的同时,也使各种罪恶在他身上达到了极限。值得一提的是,刘易斯对人性的认识完满而深刻,他没有囿于叙述者对修道士的理解和惋惜,也没有故意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是如实展现一个在毁灭性因素中挣扎的心灵。
三、结构反讽:多元纵横的叙事框架
作为英国哥特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修道士》体现了这类小说情节上的典型特征——怪诞和恐怖。怪诞风格的典型特征是“把人和非人的东西怪异的结合”③[德]沃尔夫冈·凯泽尔著,曾忠禄等译:《美人与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怪诞的标志是有意识地将幻想与现实融合;恐怖与哥特小说的“黑色”性质密切相关,表现为暴力凶杀、非常环境、时间选择、体验痛苦和死亡等各方面的恐怖。作为一个拓展性概念,它的内涵不断被挖掘,意义边界也不断延伸。刘易斯似乎更在意于情节中不动声色地揶揄,热衷于呈现表现对象的悖立状态。文学视阈内的反讽叙事包含修辞中的暗讽语调,也指人物塑造、场面编排、情节设置等处理技巧,还融会在整部作品的宏观构思中,展现为主题意蕴的展示上。
场面是小说中的基本单元,《修道士》对巫术魔法的场面渲染可谓绘声绘色,尤其是马蒂尔德在墓地密室实施魔法的描绘。她召唤幽灵取得神木,喃喃的模糊咒语中,苍白的硫磺火焰让屋子充满颤巍巍的蓝色火光,她用匕首刺破胳膊滴血,黑云升起,大地震颤……一系列的巫术仪式相当神秘而离奇,借助安布罗斯的视角所看到的非常态的场面,引起了读者强烈的恐怖感。正是叙事结构借助了暗道和密室,暗示了安布罗斯暗无天日的坟墓般的生活。
从故事结构的角度上来考察反讽策略,也就是在总体结构的高度对“结构反讽”(structural irony)进行综合分析。这依赖于读者能够对角色和情景的细微变化进行敏锐感知,读者的感知跨越障碍、识破迷局后和无所不知的叙事者在叙事文本上达到最大程度的接近,获得终极的阅读审美享受。换言之,反讽艺术通常表现为一种整体结构,统领叙事内容和形式,作者以此传递意图。《修道士》在整体结构上应用了“苏格拉底式的反讽”,真正的作者从不露面,读者无从得知他的真实意图,叙事主体的隐蔽消融在第三人称客观冷静的叙事里,文本看似只是呈现故事情节,实则不然,作者就是“佯装无知者”。他的叙述态度委婉又微妙,而且多从其他角色口中说出,如直到最后,魔鬼将魔爪插入修道士的头顶,在修道士凄厉的叫声中飞翔并扔下他,我们才读出作者的情感倾向。安布罗斯经历了高空摔落、昆虫噬咬、鹰隼啄食、口渴难耐等炼狱般的痛苦,并且在这种惨痛严酷的折磨中煎熬了六天才最终死去。这和小说开头盛况空前、听众云集的布道场面相照应,尤其是与安布罗斯雄辩的口才形成对照:“每个人都在回想着自己过去的罪过,并颤栗不已:仿佛末日审判就要到来,天主挟着雷电就要把他击成粉尘,他即将坠入永久毁灭的深渊。”①[英]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著,李伟昉译:《修道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这样的伏笔使反讽叙事变得畅快淋漓,圣洁高贵又清心寡欲的修道院院长最后竟然成为狡诈狠毒的杀人狂魔。在肉体的有限性和欢乐的暂时性面前,安布罗斯也像常人一样渴望精神领域的慰藉,诱惑与苦难考验之间归根结底也就是上帝与恶魔之间永恒的冲突。
最后情节的编排本身就是犀利而明快的直接嘲讽,有一处对比颇耐人玩味,我们可以从中对作者的心理探幽抉微。“他还试图挣扎着站起来,然后已不可能再站起来了。这时,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温暖的阳光照射在安布罗斯身上。”②同上,第384页。站是一个人基本的行动能力,也是存在的象征。按照一以贯之的反讽叙事策略,此时已经血肉模糊、气息奄奄的安布罗斯象征着黑暗、丑恶势力的彻底衰落,太阳升起寓意光明与正义对世界的重新主宰。然而作者却动了恻隐之心,想在悲惨情境下增添一抹温暖的色彩吗?行文至此,真理显现出了逃逸性吗?F.施莱格尔的反讽定义或可成为这个疑问的答案:“反讽是对于世界在本质上即为矛盾、唯有爱恨交织的态度方可把握其矛盾整体的事实的认可。”③转自[英]D·C·米克著,周发祥译:《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那么,我们可以从此处感知作者跳动的创作脉搏和抑制下的情感潮汐,刘易斯设定这个场景,就是在用反讽策略表达出对安布罗斯哀其不幸、恨其放纵的复杂态度。文字符号的表征层面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欺骗性,但置于整体情境中,就显示出颠覆性的反讽效果,构建了一个包含喜剧性、悲剧性和哲理性的多元空间。恶势力的陨落呈现出喜剧色彩,人性中的固有缺陷带来无尽的悲凉之感,坚守誓约与满足情欲之间惊心动魄的撕咬斗争留下耐人寻味的思考。安布罗斯的堕落是被魔鬼引诱,他的死亡结局是向命运臣服,个人悲剧的典型性也是人类在理智与情感搏斗时牺牲的概述。显然,《修道士》提供了一个世界荒诞性和人类复杂性的真实范例,刘易斯拥有俯视并理解人性本质的慈悲胸怀,达到了人类终极关怀的高度。
根据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修道士》的反讽不止停留在文字游戏中,而且超越文本,投射到读者身上。“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生活起始于反讽。”④[丹]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著,汤晨溪译:《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从小说的开篇,读者追随叙述者的指引,在阅读中保持理智和清醒,尽情嘲笑着书中各类人物,自以为高明,洞彻世事,但是随着细致而深入的阅读,安布罗斯的心理世界被开掘得透彻淋漓,人物性格在内外双重冲突的挤压下不断变形。在生存还是毁灭这样惊心动魄的搏杀中,投射到主人公身上的反讽色彩有逐渐强化的趋势,这是安布罗斯自我意识的退让与存在于主人公外围的社会性的进攻所导致的命运结局。同时,读者不由得以此反观自我,这样的搏杀不是自己也每每经历吗?在此基础上反观社会,对恶人的惩治不也是如此吗?
概述之,《修道士》的结构反讽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它决定了小说在形式上高于一切的原则。从纵向上看,从开端、发展、高潮直至结局,每个环节都有反讽迹象;几个故事的情节之间又构成层层推进、相互照应的反讽叙事。从横向上看,反讽如同一个聚集中心,投射到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上,结成一张密集聚合的关系网络。
结语
众所周知,哥特小说最鲜明独特的审美特征是恐怖、惊险、痛苦和罪恶,专注于不寻常的、极端事件的描写,追求强烈的文学效果。反讽是颠覆现实、揭示本质的主要叙事方式,它采用一种幽隐的嘲讽手段,以漫不经心、戏谑玩弄甚至是否定的修辞技巧推动叙事,耐人寻味。在紧张有序的道德探索中,小说散发着惩恶扬善、向善向美的理性光辉,其成功不仅在于思想层面,从微观的文本语词层面到宏观的整体结构也都贯穿着反讽的修辞策略,呈现出严肃性、对话性、开放性等特质。暗香浮动的叙事姿态表现出写作对象的分裂的内心本质,增强了文本的叙事张力,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之间得到审美愉悦。可以说,《修道士》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无害而且易于接受的阅读途径:在由怪诞和恐怖激发的震惊和怜悯中重新发现了自我,认识了自身的有限存在,进而深刻完满地理解人性,对人生的航行有着更准确的掌舵。
- 汉语言文学研究的其它文章
- 无政府、女权和清末小说
- 陈衡哲与《西洋史》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