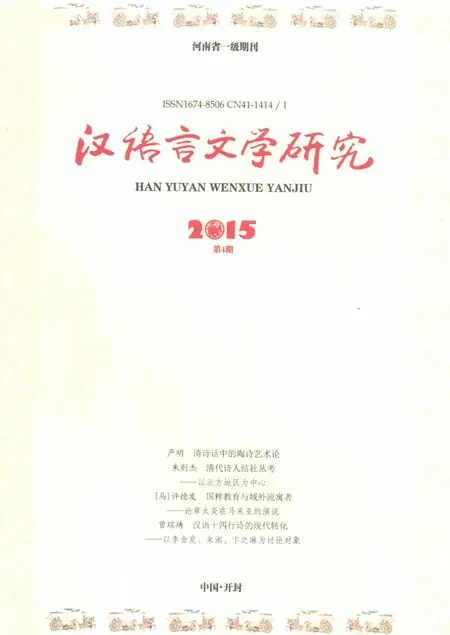陈衡哲与《西洋史》的写作
黄 华
陈衡哲(1890—1976),原名陈燕,笔名莎菲(Sophia Hung-che Chen), 是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女学者。国内熟悉陈衡哲大多是因其在新文学运动中的突出贡献,但其实对陈衡哲而言,文学只是副业,西洋史才是主业。1914年陈衡哲考取清华学堂公费留美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公费女留学生,赴美国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专业,兼修西洋文学。1917年因投稿到《留美学生季报》,开始发表白话文学作品。1918年陈衡哲获学士学位后,又到芝加哥大学深造。1920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教授西洋史,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但目前文学研究者只关注陈衡哲的文学作品,却没有充分注意其史学著作;历史研究者尽管注意到陈衡哲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但因其史学著作不多而未给予充分重视。这就造成了国内陈衡哲研究相对冷落,究其原因,学科局限和研究者的固步自封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也许有人认为陈衡哲的史学著作与文学创作关系不大,但我认为二者存在密切的关系,一来陈衡哲的文学成就和她的求学、治学经历分不开;二来陈衡哲的史学素养对她创作风格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其作品大气洒脱、与众不同①的主要原因。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陈衡哲有着骄人的成绩,她是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女诗人。1917年,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初具小说雏形的白话作品《一日》,比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早一年。她最早的诗歌《人家说我发了痴》刊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她的童话《小雨点》刊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比叶绍钧的童话处女作《小白船》早了一年。可见,在新文学运动中,特别是白话文的使用和推广方面,陈衡哲走在前列。虽然拔得头筹,但陈衡哲的主要精力显然没有放在文学上,她的作品数量不多,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文集《小雨点》1928年才结集出版。人们不禁要问: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转做什么去了?如果读了她两册① 阿英评价陈衡哲:“她的取材也不像一般女性作家的狭小,她是跳出了自己的周圈在从事创作。”见黄英:《现代中国女作家》,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陈敬之评价陈衡哲:“她之所以显然与一般女作家有所不同者,就是她却能进一步的把这一股炽烈的感情,透过严肃的理智,冷静而客观的描写社会和反映人生。她的写作题材,能够扩展到各方面,而不以身边人物与日常琐事为限;而且还能以其卓越的构想,优美的文笔,运用她的类似象征派的手法与接近理想主义的作风,藉以表现她在文艺创作上的独特风格。”见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本的《西洋史》,问题便有了答案。
《西洋史》一般被认为是陈衡哲的史学代表作。它一扫童话《小雨点》给人留下的文笔清新稚嫩的印象,代之以成熟睿智而不乏风趣、优美清丽而不乏深刻的文风,很符合朱维之“文笔清新而时有凌厉峻峭的风格”①朱维之:《陈衡哲散文选集·序言》,朱维之编:《陈衡哲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的评价。如果不读《西洋史》,就无法体会陈衡哲笔下“凌厉峻峭”的一面。1930年代陈衡哲以写作散文为主,鲜有诗歌和小说,文风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更关注现实民生。这不能不说与1920年代《西洋史》的写作(1922-1926)有关,在梳理西方历史的过程中,陈衡哲的创作风格和文类都发生了转变,更注重文章的实用性,突出论述部分。朱维之曾摘录《西洋史》部分章节作成历史小品十则,收入《陈衡哲散文选集》。由此可见,《西洋史》是陈衡哲用散文的笔触来写历史著作的典范,将知识性与文学性融为一体,堪称学术散文。
《西洋史》发表至今已近90年,有关该书的好评不少。从发表伊始被胡适赞为“一部开山的作品”②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1页。,到2008年在北大执教的陈乐民向学生推荐:“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写的《西洋史》当中,我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③陈乐民:《陈衡哲和她的〈西洋史〉》,《南方周末》2008年6月12日,第23版。一部中学教科书仍被列为大学课程的参考书目,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并不多见。那么,该书是如何写成的?究竟好在哪里?
1921年,陈衡哲因身怀六甲而辞去北大教职,次年应邀进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举家迁至上海,期间主要撰写了《西洋史》。这部应王云五先生约稿为新学制高中生撰写的中学历史教材,结合了作者多年求学所得以及在北大教书的体会,有感于当时西洋史方面中文参考书籍的匮乏而撰写。陈衡哲直言“要使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者的心中”。为此,她力求将“活的历史”与“幻想之神”相结合,以引起少年朋友们对于历史的兴趣。因而,该书并未局限于教科书的体例,而是要为一般读者提供“西洋历史的常识”。④陈衡哲:《西洋史·原例言》,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这也就难怪一部诞生于20年代枪声炮影中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能够长期受到读者的追捧和青睐。
作者深厚的西洋史专业素养和出众的文笔,不拘泥教科书体例的限制,使这部教材全然没有教科书的呆板和书卷气,而成为一部颇受欢迎的介绍和评述西方历史的普及性读物。《西洋史》上册1924年出版,下册1926年出版,出版后销路一直很好。短短三年内即重印六版,后共印制九版。之后,《西洋史》伴随陈衡哲一道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直到近年来,大陆的出版社纷纷重印《西洋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工人出版社(2007年)和东方出版社(2007年)先后推出了《西洋史》的再版本,使《西洋史》在阔别70年后重新回到读者中间。下面分别从语言风格、文化史观和写作立场三方面分析这本教材的特色。
一、白话教材的典范
陈衡哲的《西洋史》用优美流畅的白话文写作,全然不落旧教材的文言窠臼,文笔酣畅,气势磅礴,标志着陈衡哲20年代写作的高峰。
用白话文编写教材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并非易事。因为尽管“五四”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但在当时教材中使用文言文或文白夹杂的情形仍较为普遍。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就存在上述情况,例如书中叙述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的剧情:“七子之役,二子骈陨,新王Kreon礼葬Eteokles,独以Polyneikes叛国,故暴其骸,敢葬者死。其女弟Antigone收瘞之,鞠之不屈,Kreon子Haimon营救不许,遂闭之墓穴。而先知预言神怒,将降大疫,Kreon父子亟往启穴,已死矣。”⑤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8页。教材中不仅文白杂糅,而且夹杂西文。相较而言,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对语言的处理要成熟得多,例如同样谈古希腊戏剧,“在文学方面,此时最发达的,乃是那个最能表示深切感情的戏剧。而此时雅典又适产生了三个大悲剧家,和一个大喜剧家,所以他的戏剧也就由简陋的赛会式的歌舞,进为有动作有结构的真正戏剧了。三位悲剧家的名字是爱司凯拉(Eschylus)、索福克(Sophocles)和幼利披笛(Euripides)”①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陈衡哲全部采用白话叙述,对于外国人名、地名、专有名词、术语等,译成中文,另标注英文原文。因为叙述外国历史,文字是否流畅,注释是否清晰,决定了读者阅读是否方便以及对内容理解的程度。对比上述两本教材的语言风格,并无一较高下之意,只是让读者感受当时用白话教材的稀少,且两本教材出版时间有先后。比较旨在说明因无先例可循,用白话文撰写教材只能单凭自己的语感把握,实属不易。
有关自己使用白话文的经历,陈衡哲在她的英文自传《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中特别提及幼时用白话文写家信获得父母首肯的事,指出:“从这件小事我懂得不少道理。首先,它告诉我,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寻找有创意的表达方式并非可望而不可及。第二,它使我后来很同情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学倡导用中国的白话取代文言,并以白话作为国民文学之本的努力。当其他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反对他这种文学革命的设想时,只有我给予这个孤独的斗士以道义上的支持。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这场论争中支持他的原因:童年时代用白话写信是我早年教育中唯一觉得有趣生动的经历。……而用白话写信则是积极又有创意的。第三点……我教会了我的孩子不但要用白话,而且要通过写信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感情,结果再令我满意不过了。”②陈衡哲著,冯进译:《陈衡哲早年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3页。陈衡哲自传里提到“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学”便是胡适,她“很同情”并“支持”胡适的文学革命。有关这场发生在域外的白话与文言的论争,胡适在为《小雨点》作的序中进行了更详细的叙述:“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光迪)、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③胡适:《小雨点·胡序》,陈衡哲:《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6页。“莎菲”即陈衡哲,她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不俗表现,《一日》《鸟》等白话小说和新诗的发表,验证了胡适称其为“一个最早的同志”的说法。
除了创作上的实绩,更重要的是,陈衡哲借着史学家的眼光注意到了语言变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陈衡哲对但丁的文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尤其是但丁在语言上的突出贡献。她指出,但丁诗歌写作的成功也是意大利方言的成功:“但丁之前,也有用意大利方言做诗的。但第一等的出品很少,第一等的长诗更是没有。但丁凭着他的文艺的天才和纯挚的情感,把那块方言的生铁打成一片柔美的钢;使后来的人见了,不但可以得到他的用处,并且还可以学着一点制钢的方法。”④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接着,陈衡哲指出语言变革对于文化的意义:“方言的成为文字,也是文艺复兴中的一件大事。……但丁不但是第一个运用这个方言而得胜利的;并且他能用了他的文艺的甘露,去把那棵憔悴枯瘦的树,灌培滋养,使它开出鲜明美丽的花朵来。”⑤同上,第166页。文艺复兴部分,陈衡哲专门谈到“方言文学的产生”,列举了意大利但丁(Dante)的《神曲》、英国绰塞(Chancer,指乔叟)的《坎特布里古事》、西班牙塞文蒂(Cervantes,指塞万提斯)的 《吉诃德先生》、法国的拉勃雷(Rabelais,指拉伯雷)等,作为欧洲各民族国家文学诞生的标志。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陈衡哲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方言文学的产生与“我国近日的白话文学运动有点相像”。⑥同上,第186页。尽管只是点到即止,但这一比较背后隐藏的意义并不小,暗指诞生不久的白话文学代表了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故而,在这部教材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陈衡哲身体力行推行运用白话文的苦心。
二、多元的文化史观
陈衡哲将历史看作“人类全体的传记”,研究历史之目的在于“说明各种史迹的背景”,即史迹的因果关系及彼此的相互影响,借以“培养读者分析现代社会各种现象的能力”。①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这种重视历史实用价值的做法,使《西洋史》一书在叙述西洋各国历史的同时,并未忽略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北非、亚洲和中国等,从而具有多元的文化史眼光。
首先,何谓“文化史”?这关系到历史写作的范围和史料的选择。陈衡哲在《西洋史·导言》中写道:“历史既是全体人类的传记,他的范围当然很广。拿破仑的事业固然是历史;法兰西乡下一个穷妇人的生活状况,也何尝不是历史。……有些历史家,以为历史便是以往的政治,他们所取的史材就一定是偏于政府的文牍公案了。……我们深信,历史不是片面的,乃是全体的;选择历史材料的标准,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换一句话说,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凡是助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的价值。这是这本历史取材的标准。”②同上,第10页。陈衡哲将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没有把政权更迭、武力征伐作为叙述的重点,而是着重梳理欧美历史中的文化脉络。《西洋史》全书20章,有6章专论文化,约占三分之一篇幅。尤其是上古史,6章中有4章记述文化历史,占了三分之二的比重,由此可见陈衡哲对文化的重视。
作者不仅在单列的章节中论述文化,而且在书中处处可见文化的踪迹。例如下册第5章《地理上的大发见及殖民地的竞争》谈到哥伦布远行的动机来自《马可·波罗游记》,“这部游记是欧洲有史以来第一本对于东亚诸国的确实记载,他的影响的伟大,但观哥仑布的成绩便可以明白。因为哥仑布若不是受了这本游记的深刻的激刺,他的‘西行达东’的伟大梦想是不会成熟的”③同上,第253页。。其实,不仅哥仑布,13世纪之后的欧洲人在数百年内都主要通过 《马可·波罗游记》了解亚洲和中国。又如,陈衡哲指出,近代以来欧洲各国争夺殖民地的结果之一是将欧洲文化被及全世界,“欧洲文化浸荡全世界的工具也不止一个,其中有的是武士政客,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传教士或教育家。凡以上各类人物势力所到之处,那里便不免成为白人的属地。……现在地球上的各处,无论是自由的或是欧洲的殖民地,他们是没有不在承受欧洲文化的了”④同上,第260页。。全书俯拾即是的文化叙述让读者深切体会西洋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脉络。
其次,文化有何作用?读者也许要问:陈衡哲为何如此重视文化?因为在陈衡哲看来,文化具有反战争、谋求和平的重要作用。陈衡哲撰写《西洋史》时正值军阀混战,她在1924年11月15日给胡适的信中对时局表示了深切的担忧:“我以为中国现在已自civil war(内战,注者加)时代而进入anarchy(混乱、无政府状态,注者加)时代,如不幸,或至沦入巴尔干的地位,为世界各国的大战场。所以我总觉得前途茫茫,如随盲人瞎马之后,不知要陷入什么深渊里去。我天天编书,但天天觉得所编的稿子,一定要被焚成灰烬,或撕成条子的。我真不能乐观,我眼见虎狼水火的侵犯全国人民而绝不能救助,我觉得惭愧而羞耻。”⑤陈衡哲:《西洋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历史书不可能避开反帝国主义、反对战争的现实需求和愿望。陈衡哲在初版《原序》中明确指出:“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的一个。运用这个方法的工具,当以历史为最有功效了。”⑥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战争与文化的对立,让书中的反战思想随处可见,作者常常从文化的角度来解构统治者的武力战功。比如,“亚历山大的十万刀兵,却比不上小小的二十四个希腊字母。兵亡刃销之后,而希腊的字母不但巍然独存,并且已经成为上古世界的普通语了。所以亚历山大东征的结果,虽是东西文化的相互吸引,而因为希腊文字优胜之故,所有上古各种文化的遗产,此时也就都归了希腊人的看管”①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显然,在文化史学者眼中,穷兵黩武的结果不是疆域的开拓和帝国的建立,而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书中最能表现武力与文化关系的,莫过于展示土著部落和游牧部落关系的一个圆形示意图,游牧部落通常会先通过武力取胜,土著部落虽然战败被征服,但会在文化方面后来居上,形成新的土著文化,新土著又与新的外来游牧民族发生斗争……如此循环往复。作者又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意大利衰弱致使其不断受到异族蹂躏,但意大利文化却为近代文艺复兴奠定了不朽功绩的史实,得出“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②同上,第200页。的结论。可见,文化史研究者不以武力的胜败来论英雄,而是具有更长远的发展眼光。
第三,陈衡哲的多元文化史观从何而来?留美归来的陈衡哲明显受到1920年代欧美 “新史学”思想的影响。新史学以法国的米希勒、美国的鲁滨逊等人为代表,他们拒绝传统的政治史,表现出追求总体史的倾向,主张用综合的、多因素的眼光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③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在美国,以鲁滨逊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为大本营,形成了一个带有共同治学取向的史学派别,时称“鲁滨逊先生派”“哥伦比亚史学派”,今多称 “鲁滨逊新史学派”。 《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912)是鲁滨逊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1924年由何炳松翻译的中文译本出版,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五四”时期史学界正是除旧布新的年代,“新史学派”因其叛逆的姿态而深得中国学界的好感,加之大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归国执教,例如何炳松、陈衡哲、蒋廷黻、徐则陵、李飞生等,他们纷纷采用“鲁滨逊新史学派”编著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的影响。1920年执教于北大历史系的陈衡哲指定预科学生阅读的历史参考书籍中,即有鲁滨逊的《欧洲的历史读物》(Readings in European History), 鲁滨逊和比尔德合著的 《现代欧洲的历史读物》(Reading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现代欧洲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海斯的《现代欧洲政治社会史》(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④《图书部典书课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6日,转自李孝迁:《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上)》,《东方论坛》2005 年第 6 期。可见她对“新史学”的重视。
其实,不止“新史学”,“五四”前后,唯物史观、进化史观、实用主义史观、民族主义史观等诸多西方史学理论陆续进入中国,对当时的历史研究和教科书编纂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陈衡哲曾在致胡适的信中明确表示:“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 《西洋史》,便可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影响的一个人。但我确不承认,历史的解释是unitary(一元的)的;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他的唯一工具。”⑤《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2页。这表明陈衡哲在叙述西洋史的同时,并未忽略与欧洲文明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文化,借以表达多元的文化史观。
陈衡哲多元的文化史观体现了她鲜明的“国际主义”立场与对和平的向往。在《西洋史·序言》中,陈衡哲称该书在于帮助青年“发达他们的国际观念,俾人类误解的机会可以减少,人类谅解和同情也可以日增一日”。⑥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国际主义”是20世纪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超越于国家主义及民主主义之上”,国际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有海牙的和平会和欧洲的国际联盟,在社会上的表现有各种国际学术和慈善事业,如洛氏基金团、卡诺基基金会、诺贝尔奖等。陈衡哲满怀希望地指出,虽然这些国际主义运动“尚处在萌芽时代,但他们实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最大希望,也即是二十世纪历史上一件最足自荣之事”。①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②同上,第364页。。可见,陈衡哲将国际主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通向世界和平梦想的途径,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正义感。
三、鲜明的主体立场
《西洋史》最突出的特点是个性化的叙述和阐释,如果放置在中西方文化互为参照系的前提下来看,便是作者带有鲜明主体意识、立足自身文化立场的叙述和阐释。这对今天的中国文坛和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胡适在1926年《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一文中,对陈衡哲的《西洋史》给予高度评价:“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倚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③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1页。这一评价虽然因胡适与陈衡哲私交甚厚而有过誉之嫌,但的确指出了该书的最大特色——立足于自身文化的立场和勇气。胡适认为,《西洋史》最大的贡献是突破了“以西洋人眼光看西洋史”的局限,实现了“以中国人眼光看西洋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学界大多唯西方马首是瞻,缺乏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自我参照系的缺席使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变了味,成为无根之浮萍。例如,陈衡哲撰写《西洋史》的192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刚刚起步,资料十分匮乏,当时国内的西方历史教材以译编、改编国外教材为主,不仅史料来自西方,甚至观点也照搬西方教材。1933年,何炳松在为商务印书馆编著的《高中外国史》所写的序言中称:“关于亚洲民族的史迹竟不能不取材于英国学者所编的《大英百科全书》,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林生的《古代东方五大帝国史》和派克的《一千年间鞑靼史》”“所有对于这许多民族在文化贡献上的价值的话,又十九采取前三书著者的意见。这是我们亚洲人的‘数典忘祖’呢?还是‘礼失而求诸野’?”④何成刚、张安利:《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历史教科书——陈衡哲著述〈西洋史〉教科书特色述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1期。反映了当时世界史教材普遍存在的弊病。陈衡哲在为何炳松《中古欧洲史》撰写的序言中也指出:“欧美人所著的历史,在我们东方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来,有许多是累赘可删的,有许多是应当增加材料的。但这一件事更不易做,更非素无历史研究,或乏世界眼光者,所能下笔了。”⑤陈衡哲:《中古欧洲史·序》,《何炳松文集》(卷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
《西洋史》的贡献在于摆脱了转述、翻译西方教材的窠臼,开始探索以中国人的眼光审视西方历史的新模式。
陈衡哲编写《西洋史》时,注重将历史的真实性与教材的趣味性、审美性结合在一起,同时秉承“历史是要人明白”⑥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的宗旨,用极具个性化的叙述和阐释来撰写西方历史。陈衡哲常常将西方的历史人物、掌故与中国作比较,便于读者理解。比如谈苏格拉底,陈衡哲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和中国儒家的学说有相似之处,“他的哲学是入世的;是采取中庸态度的;是以国家的幸福为人生努力的标鹄的;是以修身致知为达此目的的手段的”⑦同上,第70页。。陈衡哲还善于用中国的成语、古典诗词帮助读者理解西方历史的变迁,例如总结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作者发出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感慨①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彼得拉克“常怀那‘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慨”。②同上,第183页。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陈衡哲充分发挥文学才华,注重将历史的真实性与教材的趣味性、审美性结合在一起,将《西洋史》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成为中国人治西洋史的典范之作。
陈衡哲从总体史的眼光出发平等对待各民族文化。《西洋史》没有局限于“地理欧洲”,而采用“文化欧洲”的视角。以上古史为例,陈衡哲认为不能忽略与欧洲文明有紧密关系的埃及和西亚两河流域文化,她打了个比方:“因为在这两个地方所开的文明之花,后来有许多果子落到欧洲的地上去,发育生长起来,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历史,有同等的价值。”③同上,第27页。故而,西洋文化便有四个来源——希腊、罗马、希伯来、埃及或两河流域文化,四种文化的火焰在西洋文明中不绝地燃烧,久已融合为一。对于西洋文化中的东方因素,陈衡哲认为,“公元前三世纪之后的二三百年,与其说是希腊文化传布于东方的时期,不如说他是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影响的时期”,因为“文化是一件有机的东西,他是生生不息的,是‘铜山西倒,洛钟东应’的”。④同上,第76页。这体现了陈衡哲平等的文化观,不以民族的大小、强弱论,注重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
在谈西洋史的同时,陈衡哲不忘与中国现实的联系,即在叙述“他者”时没有忘记“自我”,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陈衡哲指出研究西洋史之目的:“虽然只以西洋各国为限,但无论那一部分人类的历史,都具有普通和特别的两个性质……所以我们研究了人类一部分的历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类,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⑤同上,第10页。这表明作者撰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为我所用。因为对文化的重视和对现实的关注,《西洋史》中陈衡哲多次谈到“帝国主义”的“反文化性”,并以反讽的语气指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之目的:“新帝国主义最大的目的物,既是大宗的原料,投资的机会,及消耗盈余出品的商场,于是我们中国便成为他们最好的目的物了。原来我国的原料是最为丰富的,投资机会是最为广大的,人民是不但繁庶,而且又是最能消耗‘洋货’的,这岂不是列强资本家的乌托邦吗?”⑥同上,第354页。陈衡哲又探讨了中国面对列强瓜分的自救问题,认为亚洲国家有三条出路:以日本为代表效法列强的武备以自救;以印度为代表沦为列强附庸;而中国徘徊于两条道路之间,作者希望中国能够自创出第三条出路。这代表了当时民族危亡之际一部分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期许,也反映了作者深切的民族责任心和忧患意识。
陈衡哲写作《西洋史》时的主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因为作者的女性身份,《西洋史》比较关注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尽管着墨不多,但总能让人在历史的缝隙中不时窥到女性的身影,而先前的历史书很少见到女性的踪迹。因此有人评价,从民国时期出版的全部历史教科书看,陈衡哲是唯一从女性的角度、女性的立场去论述历史进程的人。⑦何成刚、张安利:《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历史教科书——陈衡哲著述〈西洋史〉教科书特色述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1期。这一评价恰如其分,作者的女性身份和价值观直接影响到她对于史料的阐释和理解。比如,陈衡哲谈到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时,注意到其中妇女的地位很高,她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⑧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作者评价中古时代的骑士制度,指出“义侠骑士制度”是对“混乱社会的一种反抗”,它的价值“是在保护弱者——尤其是妇女——为一般人民打抱不平”,因为在封建社会“强者即是合理者”的逻辑支配下,妇女的地位是最危险的。从这个角度看,骑士制度立了大功。①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又如,陈衡哲叙述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影响时,提到其中一点就是“女学者的兴起”。她指出:“威尼司的佳姗特拉和佛罗稜司的亚历山特拉,是十五六世纪时期女学者的两个代表。她们颇能与男子自由交际,自由讲学,但同时又都是品洁行高,为一般人士所景仰的。这些女学者实是近代女子解放的先锋。尤可贵的,是她们的解放方法。她们的解放,是由内而外的,是以解放自己的理智为起点的,她们并不曾以解放的责任推到男子的身上去。”②同上,第185页。对照同时期的中外历史教材,鲜见能够在古史的断片中挖掘妇女的史料,这在当时难能可贵。
陈衡哲特别注意到近代西方妇女运动的兴起,并对此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她指出:“妇女运动的原动力也是从民主主义得来的,他也是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③同上,第360页。在阐述工业革命的结果和影响时,她认为:“靠了工厂制度的兴起,妇女已能获得经济的独立,靠了教育的普及,妇女的智识与能力也日益增加了,所以女子在教育方面、经济方面、职业方面、政事方面确已与男子争到了平等的地位。而其中尤以女子参政权运动及获得为妇女运动得胜的最明显的标志。”④同上,第360-361页。虽然陈衡哲对英美妇女参政运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她不拘泥于当时的情势,而是前瞻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人们常有把女子参政运动视为妇女运动的唯一事业者,这是一个大错误。女子参政固是妇女运动的一件事,但他绝不足以代表妇女运动的全部。”因为政治上的活动只是人生活动的一部分,而且参政权的获得只是肤浅的平等,陈衡哲指出:“妇女们如欲与男子们争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智识的解放、能力的修养及人格的提高为最重要。”⑤同上,第361页。陈衡哲指出的妇女运动未来的发展方向,被后来的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所证实,这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衡哲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可见陈衡哲作为历史学者的远见卓识。当然,这种主张是基于对历史上妇女地位的客观分析,同时也结合了陈衡哲自己的人生经历。在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纪念一位老姑母》等自传性散文中,我们看到一位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形象,陈衡哲以自身求学奋斗的经历印证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路径。
《西洋史》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秉承了陈衡哲优美清新的文笔和个性化的叙述风格。比较《一日》《小雨点》等陈衡哲前期的作品,《西洋史》堪称一部更成熟的白话文作品,可以作为陈衡哲文风成熟的标志之作。当然,这里讨论《西洋史》与当代教育界和学术界兴起的 “民国怀旧风”不无关系,重读“民国老课本”成为反思今天教育弊端的一个契机,但本文的意图旨在借重读《西洋史》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在全球化和民族化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提供借鉴,即思考研究者采取怎样的立场和观点来审视西方文化。总的来说,在研究西方文化时,首先要反对不加反省地承袭外来的概念和理论,因为没有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参照,“西方”就不复存在。同时要警惕“西方主义”的倾向,即以一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抵制西方的一切文化元素。其实,无论日本、印度,还是近现代中国,“西方主义”都构成了深入认识西方的障碍。如果不认清楚对方,就不能很好地认清自我,当然也就不会对东西双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有所建树。
【责任编辑 孙彩霞】
- 汉语言文学研究的其它文章
- 无政府、女权和清末小说
- 论《修道士》的反讽叙事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