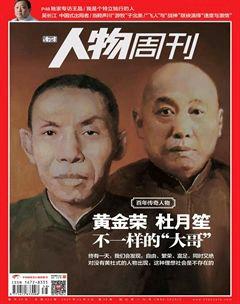奶奶
2008年,奶奶88周岁。过完春节,她有半个月茶水不进,睡在堂屋中间的床上,一口气没上来,走了。奶奶活到近九十岁,农村叫喜丧,识字的人叫寿终正寝,乃有福之人。
奶奶这辈子吃尽苦头,9岁时父母双亡,和一个弟弟相依为命,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野菜、树皮、花生壳,能吃的都吃过。父母双亡留给奶奶的是犟脾气,爱吵闹、较真,十几岁“上婆家”,成了董庙村董彪的媳妇。她和董彪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董彪勤劳肯干,农闲时推小货车溜村串巷买个针头线脑,贴补家用。一日董彪黑夜赶路被匪徒一棍子打死,抢走货物和零钱。匪徒们将董彪的尸体扔在芦苇荡里。那个年代还叫解放前,人命如草芥,死了就死了。这可苦了奶奶,奶奶这个刚性子很难向困难低头,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她拎了一包家什,嫁给了濠城镇的鳏夫丁玉平——一个专做棺材的木匠,也就是我爷爷。翌年,奶奶生下了我父亲。

我父亲八九岁时,又逢上了“戒年”(1960年大饥荒),淮北平原每家每户都饿死人,人没有吃的,就吃秫秸、花生壳等,吃了这些东西肚子胀,拉不下来屎,用手抠,喝水更胀,最后只有死路一条,人死了拖到湖里埋了(湖:田地)。奶奶只顾自己和儿子,根本不顾爷爷的死活(当然那年头也顾不了)。爷爷没撑几天就饿死了。几个庄邻有气无力地用门板钉了口棺材,找牛车拖出去埋了。奶奶中年再次丧夫又成了寡妇,和儿子相依为命。奶奶的弟弟,我的舅姥爷,跑反跑到东北混穷,居然侥幸参了军,部队安排识了些字的舅姥爷当了军医。
在农村,娘俩过日子,少不了被人欺负。有次,我家的石磙子被村人王树金强行拉走,不还了。奶奶跑到王树金家索要,被树金妈扯掉几缕头发,回家恼得睡了几天,石磙子还是被霸占了。奶奶气得扎了一个胸插尖刀的草人,放在十字路口,诅咒王树金。还有一次,我家的鸡跑到华维国家的草屋顶,华的大儿子新华在屋顶撒了药,小鸡们吃了毒药浸过的玉米粒,纷纷从屋顶滚了下来,奶奶在华维国家门口蹦了几天大骂不休。在生产队每年都透支,拿不到平均工分,还要交点钱给生产队。奶奶养鸡卖鸡蛋,在自留地里,想办法种菜、种瓜,补上生产队的钱。1960年后,生活突然改善了,一日三餐虽然吃的是红薯、高粱、玉米等粗粮,但是可以糊饱肚子。父亲告诉我,“老天救人啊,天无绝人之路。1961年春天,房前屋后都长满了灰灰菜,那是救命的野菜。”
父亲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生产队当会计,因为本分老实,和大队书记关系又好,被推荐到宿县地区“五七”大学读农机专业。当时是“社来社去”不包分配,父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农机维修上学有专长,“五七大学”毕业后没去拖拉机站工作,而是回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奶奶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到处夸儿子有出息。
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我家分到7亩责任田,一季小麦、一季黄豆,还养了一窝肥肥的猪崽,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得到根本改善,再也不为饿肚子发愁。可是,奶奶有个业余爱好:讨饭。她有十年光景冬闲时和一帮人到广东讨饭。在我小时,就听说她到过肇庆、茂名,也到过广西梧州、玉林等地。她把讨来的米零存整取换成钱,再从邮局把钱打回家。奶奶春暖时从“客居地”带回年糕、腐竹、糍粑之类,有时也分给邻居品尝。奶奶年年出去讨饭,晚辈们觉得挺没面子,又不是遇到旱涝灾害,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干嘛出去讨饭?可是,没一个人敢阻止奶奶去两广讨饭。我父亲背了很重的思想包袱,作为小学校长,是村里的“脸朝外的人”,老娘出去讨饭,丢脸呐。但奶奶“油盐不进”,我行我素。每年大雁南飞时,她便和搭档们大包小行李扒火车向岭南迤逦而去。
1996年,奶奶76岁。父亲在那年秋天遽然去世。奶奶这次又是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悲伤至极。奶奶心硬挺了过来,很快摆脱了丧子的痛苦。腰板硬朗地忙这忙那了。
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三件事都被奶奶碰上了。人总是要死的,这世界哪有不死的人?从无疾而终、寿终正寝这个角度来讲,奶奶是有福之人。奶奶是体面死去的——让村里老人们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