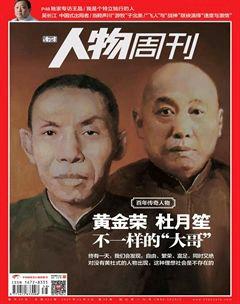杭州一怪陈立
《舌尖上的中国》热映时,我就在想,央视真应该去找陈立当顾问。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真能说得一口好菜的大概也只有陈立兄了。后来听说他果然是此片的幕后顾问之一。再拍《舌尖2》,他又是美食顾问。陈立被称为“杭州七大怪”之一。也许是因为这个浙江大学的教授,却偏以美食家闻名。有报道称,“陈立在被媒体打捞出来作为美食家之前,是专攻情感性精神疾病的教授”,而我正是当年打捞陈立的媒体人。
15年前,在南怀瑾先生的香港饭桌上,第一次认识陈立兄。怀师介绍说,他是杭州大学教授,国民党元老陈仪的后人。陈立长得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口才便给,谈吐不俗,虽说是浙江人,但操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攀谈之下,知道他早年在杭州学医行医。80年代中期到香港大学社会系攻读社会心理学专业,毕业后回杭州大学心理系教精神分析学,后来又在历史系研究心理考古学。陈立兄还有一个学术兴趣是研究台港澳问题和两岸关系。他从90年代起就先后出任杭大和浙大台港澳研究机构的负责人。陈立那时候每月都会来香港盘桓几天。因此,我们经常能在怀师的饭桌上见面。陈立兄见多识广,知识渊博,说话机智幽默,同桌的人都喜欢听他聊天。因为是同乡,开始时我和他的话题多半围绕着浙江的风土人情。比如外人大多只知道绍兴黄酒有花雕和女儿红,殊不知绍兴酒的品种有数十种之多。有一次,我和他说起,离乡多年,很久没有喝到太雕酒了。此后,陈立每次来香港都会给我带上一罈太雕。他还说,二次酿的黄酒,太雕之上还有金雕和仙雕。仙雕最为上品,其色泽澄黄透明,香气浓郁芬芳,入口绵软、甘甜醇厚,已不易寻觅。几年后,陈立兄觅得一罈仙雕酒,居然还不忘当年承诺,特地托人捎来给我解馋。

由谈酒而论及菜肴,发现我俩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多。我们这一代人能通晓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之精髓者已寥寥无几。一般号称美食家流也是泛泛而谈。真正的美食家不仅要懂一道名菜的烹制方法,还要说得出这道菜的来历和源流,更要知道这道菜所取食材最合适的产地和时令。陈立曾说:“美食不在厨房在菜场。杭州的一些餐馆起伏太大,跟厨师无关,跟食材有关。一个餐馆的味道百分之三十由厨师掌握,百分之七十则掌握在采买的那个人手里。”此语一出,我立刻断定:这才是真正懂吃之人。于是我们成了惺惺相惜的“酒肉”朋友。当时我正在香港亚洲电视当新闻总监。亚视的深夜节目始终是个大难题,既不能花高成本制作,又要有一定的收视率。有一次,在怀师的饭桌上,我向陈立提议:何不为我们亚视做一档美食节目。他欣然答允,在场的亚视总裁封小平先生也乐观其成,于是就有了《越食越疯狂》。这个美食节目每天深夜播出,在香港红火一时。后来香港的茶餐厅还按照他的创意,在咖啡里加姜汁,发明了一款“陈立咖啡”。陈立之后,两岸三地的电视美食节目才开始方兴未艾。
本世纪初,怀师从香港移居上海后,我和陈立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有一天,突然听到他病危的消息,令我十分震惊,立刻打电话去询问,知道他已经转危为安,我才松了一口气。此后,陈立的健康状况一直时好时坏,但他始终保持坚毅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与病魔搏斗。他不仅坚持工作,而且照吃照喝,和朋友们一起享受他的美食人生。2009年春,我去杭州看望他。他带我穿街走巷寻找当令的时鲜菜肴。对美食家来说,没有什么是最好吃的菜,只有在什么时候该吃什么菜的问题。一家路边的无名小店,味道却非同寻常。这家餐馆每天花最多的精力在买鱼买菜上,自己家里又有承包的山地,养猪养鸡,难怪能迷倒我这个老饕。陈立兄还陪我去探访灵隐寺旁的法云安缦酒店。我们坐在村落深处的“和茶馆”品茗闲聊。茶馆老板娘庞颖小姐是陈立的朋友,拿出珍藏的极品龙井茶飨客。陈立幽默地说:“龙井茶就像江南女子,第一是矜贵,没有好水不出味;第二是薄情,水泡三遍就无味;第三是难伺候,保管不当就走味。”我笑言:“你毕竟是专攻情感性精神疾病的教授,三句话不离老本行啊!”
前不久,陈立兄来电话邀我去杭州参加两岸关系的研讨会。因为我早就退出江湖,不再涉足这一领域,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我心里仍很想再游西湖,再会会我的这位老友。愿陈立兄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