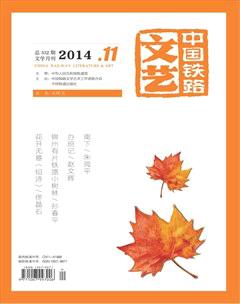故园靓影四题
山泉
三伏雨趣
乡愁难以割舍。每当入伏以后大雨连绵,我总会触景生情,悠悠思绪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雷雨大多在中午下,天气闷热,好不腌臜,空气湿漉漉的,攥一把能拧出水来。天地间犹如一个偌大的蒸笼,芸芸众生都在体验“桑拿浴”。我天生怕热,身上就起了痱子,越烦躁越难受,真渴望下一场大雨,以便凉快凉快。心诚则灵,天随人意。不经意间,西北面的大山后面会冒出一团乌云,迅速变幻升腾,不大一会儿就遮住了太阳弄黑了天幕。苍穹低垂,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蒙古包。闪电交加,如同天神手持狼毫蘸着金水在练习狂草;雷声隆隆,俨然一群巨兽趴在云层后面歇斯底里地哮吼。天色骤然变暗,一阵凉风刮来,挟带着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一万只山羊贴村跑过;“鞭杆子雨”接踵而来,天地间挂起了亮亮的雨帘,满世界全是哗哗的雨声。
庄稼人巴不得有这样的天气,权当是天公垂青给放假,便坐在家中饶有兴致地端详雨中的景致。
屋檐滴水成线,如同一排银色的流苏。水滴敲打着水筲、陶罐、脸盆,音色有别,叮咚悦耳,仿佛有一位隐形的音乐家在演奏古筝。院子里积水盈尺,形如方塘,雨点落在上面,溅起朵朵水花,瞬间绽放,霎时凋谢,此开彼落,经久不息,又如一个缀满银花的神奇地毯。
下大雨的天气是蛤蟆和青蛙的节日,是它们的盛会,在纵情对歌,或排练庆丰的鼓乐。它们的叫声在村庄里、原野上荡漾,成了最好的催眠曲,庄稼人听着听着就美美地进入了梦乡。
倘若遇上东北风,大雨会不歇台地下上两三天。这期间,有的人家草垛没苫好,柴草被雨淋湿了,不能生火做饭,没法子,只好将柴草放在锅上,再找点干柴,将其略烘一番,不然的话,势必断顿。
大雨将土壤泡酥了,街旁一棵榆树被大风刮趄了,树上一窝小雀被摔落下来,它们的羽毛都长齐了,眼见就要出窝了,真可谓功亏一篑;一对老雀束手无策,急得围着小雀直叫唤。有人想把小雀拿回家给孩子玩。后街孙奶奶心地善良,闻讯赶来,说:“人和雀儿没甚两样,都是个命心,风雨将它们的家毁坏了,你们不救助它们,反而趁火打劫作践它们,还有人性么?”说着把几只小雀兜在衣襟里,回家找出一个旧笊篱,把小雀们放在里面,然后用小米精心喂养。待到遇过天晴,人们将那棵被刮倒的榆树扶正加固,孙奶奶让他们将笊篱和小雀搁在枝杈上。那对老雀紧跟而来,落在笊篱上朝孙奶奶和其他人欢快的叫着,分明在表达感激之情呢。
大雨滂沱,街道成了溪流,水中竟然有泥鳅,毋庸置疑,这是龙卷风旋来的,偶尔被鸭子碰上尝到了美味,它们以为还能遇到,便嘎嘎地叫着沿街寻觅。
大雨刚刚过去,我便到西河观看山洪暴发。出门西去不远,就见河畔的粮田全被水淹,麦收后抢种的玉米只露出个梢儿。我发现路边水沟的积水里有两条大泥鳅麻花样扭在一起,不免顿生疑窦,从未见过泥鳅相互缠绕,莫非是两条小水蛇?正待定神凝视,怎奈它们瞬间即逝,再没露面。这情景让我感到缠绵,感到惆怅。未到河边,就感到大地在微微震颤,此乃山洪争泻撞击所致。前行几步举目观望,但见浑浊的洪水如同一群强悍的野牛竖着犄角狂奔而来,相互抵顶,夺路而去,那场面十分凶险,慑人魂魄!乡亲们不约而同地赶来,有人手持长杆将水中漂浮的花生、瓜果等打捞上来,竞相品尝。嗬,不知谁家的麦穰垛被山洪囫囵个驮来,颤巍巍地顺流而下,仿佛河神娶媳的轿子。河床落差大,再猛的山洪不用一锅烟的工夫就流势锐减,即便河水齐腰,涉水也无危险。
未等雨霁天开,我和伙伴们便沿着山道捉“水牛”。“水牛”并非南方耕田的水牛,而是一种鞘翅目昆虫,因它总是在雨中出来,名字缘此而得。牛把粪便屙在山道上,那粪便经雨水浸泡,养分渗入地下,致使路边的野草长得特别茂盛。这种野草生命力相当顽强,长得匝密,高约一拃,就像驴毛,乡亲们管它叫“驴皮芽”。“水牛”喜欢在“驴皮芽”里产卵,卵变成幼虫俗称“地蝗”,“地蝗”几经嬗变而成蛹,再由蛹蜕化为“水牛”,生命正好做了一个轮回。那时,故乡的牛多,路边的“驴皮芽”长得旺,下大雨时山道上的“水牛”特多,让你捉不迭。“水牛”有一对锐利的大牙,一旦被它咬住手指,非咬出血不可,然而它不会转动脖颈,你捏住它的背部足可安然无恙。“水牛”的生命很暂短,仅仅一两天的光景,鉴于这个缘故,它们出来后就忙着寻找配偶传宗接代,往往成双成对,一捉就是俩,好不过瘾。将“水牛”上锅佐油炒着吃可香哩。
大雨接近尾声,我和伙伴们时常冒着蒙蒙细雨到山里捡“雀菜”和“粘莴”,它们都是大雨的杰作,是大雨对人类的慷慨馈赠。“雀菜”洗净可馇渣吃,鲜美爽口,只有山里人才有这份口福。“粘莴”晒干后可卖钱,是我们勤工俭学的主要进项。
待到山洪消退河水变清后,我们成天泡在河里捉鱼摸虾。捉鱼特有瘾,时常乐不思归。
啊,三伏的雨,给山里的孩子带来多少乐趣!
而今,我住在县城,生活环境相当优越,然而再美也有欠缺——雨下的再大,也无法看到山洪暴发时的情景,享受不到雨后的种种乐趣。蓦然惊觉,疲惫的灵魂已与灵性的山水大为疏远了!我真想趁下大雨时回到故乡,重温少年时代的生活情趣,为躯体增加一些勃勃活力。
故乡的野菜
春风解冻,春阳和煦,春雨轻洒,山里的野菜就开始登台亮相了。
最先上场的是蒲公英。前一年初秋,它们手持妈妈制作的精致小伞,随风飘啊飘啊,最后撒落在山道边、河畔上,经过秋雨滋润,雪花呵护,现已生根发芽,并率先开花了。那花儿金灿灿的,俨然用赤金打制而成,星罗棋布,分外耀眼。少年时代,我和伙伴们时常提着小篮子,拿着小铲子,沿着河畔剜蒲公英。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剜满了篮子,拿回家让妈妈用开水焯一焯,用它包包子,味道略苦,但却好吃。尤其蒲公英有消炎祛火的功能,逢上伤风感冒头痛脑热,用它烧水喝,挺管用哩。
苦丁子和苦苦菜紧随蒲公英而露面。这两种野菜不喜欢择水而居,而喜欢向阳的山洼和地堰,往往是一片一片的,有的地方拥挤不堪。苦丁子和苦苦菜好像命运很苦的孪生姐妹,相依为命,密不可分。尤其那些小小的苦菜花,脸庞瘦削,迎风瑟瑟,总让人联想到那些风鬟雨鬓、胼手胝足的村姑,顿生怜悯之情。我和伙伴们星期天到山里剜些苦丁子和苦苦菜回来,将它们择好洗净蘸酱吃,头两口觉得很苦,再吃就觉得清香可口,越吃越爱吃。将它们焯好浸好熥虾酱,味道特鲜,百吃不厌。它们的根和老叶,鸡和鸭子最爱吃,往往是你争我抢毫不相让。倘若分一些给猪,猪会高兴得不得了,风卷残云般连泥吃掉,然后前腿搭在圈沿上,朝你哼哼,分明在问,还有没有,要是有再给点。这家伙见了野菜饕餮无度,即便给它一篮子,也不够它吃的。
在春风频频呼唤下,生长在麦田里的荠菜已长得绿莹莹的,那叶儿长得纤巧,细细端详,跟雪花的图案极为相似,莫非是雪花眷恋大地幻化而成?还有一种野菜,俗称“米溜菜”,叶子很小,没有火柴头大,但是叶子紧紧箍在一起,重重叠叠,凝碧聚翠,赫然醒目。它伴随荠菜登场。我和伙伴经常剜一些回来,用它包饺子,满口清香,食欲大增。还有“麦粒蒿”、“胡黍布墩”等野菜,都可食用。
这时节,深山里的薇菜和蕨菜也从石缝里长了出来。嫩芽破土时,状如鸡爪,绿莹莹紫蒙蒙的,采回来略微一焯,佐以蒜泥凉拌着吃,味道独特。如果将其晒干,冬天用它炖野兔,堪称山珍。
香椿俗称樗芽,喜欢生长在石堰下,繁殖力特强。那嫩芽紫莹莹的,囫囵个儿扳下来,佐以面团和鸡蛋,上锅炸着吃,奇香无比。将其腌于坛中,可作为小菜终年品啜。
谷雨前后,山蚂蛛菜就发芽了,长到一寸多长时,我和伙伴们便上山掐。山上有的是,不大一会儿就掐满了篮子。大山距村子远,来一趟不容易,索性脱下衣服再包一些。山蚂蛛菜味道纯净,佐以“五花肉”包包子,挺顺口的,远比大白菜和萝卜丝好吃得多。
有一次,我和伙伴们上山掐山蚂蛛菜,突然在一簇草丛中发现了一条1米长的小花蛇。它通体呈褐黄色,点缀着一些米粒大的黑斑,盘在那里,朝我昂起脑袋,眼露冷光,信子直吐啦,分明嫌我打扰它,便攻击我。我天生怕蛇,不免尖叫一声,大呼有蛇,招呼伙伴快跑!伙伴们都扔下篮子,屁滚尿流地四散逃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如履薄冰般靠上前拿篮子。我心有余悸,再掐山蚂蛛菜时,总会细细打量一番,然后再掐。
地堰上、山坡上有一种俗称“老母鸡肉”的植物,根儿酷似桔梗,刨出来刮去皮即可生吃,味道又甜又香,果然名副其实。还有两种植物,分别叫“鸭肉”、“鹅肉”,与“老母鸡肉”大同小异。据说,这三种植物都属沙参家庭中的成员,常食对人体极为有益,难怪它们这么好吃。
当山桃花盛开的时候,榆树也开花了。那花儿黄绿相间,如同古钱,鉴于这个缘故,乡亲们管它叫榆钱儿。这名字取得有学问。榆钱儿没有歪味,摘一些揞在嘴里,细细咀嚼,甜兮兮的。采一些拿回家让母亲馇渣吃,香甜可口,会吃得饱饱的。
母亲深知前街刘奶奶爱吃榆钱渣,做好后总让我送一碗给她尝鲜。刘奶奶接过榆钱渣,满脸会笑成一朵“金钩菊”,不无感激地说:“你妈心眼儿真好,你呢,手脚又勤快,长大后保准会有出息的。”举手之劳,就受到刘奶奶这等夸赞,我听了心里也感到美滋滋的。
立夏以后,刺槐又开花了,一串一串的,满树皆是,往往是满坡满谷,白茫茫的,如降瑞雪,芬芳馥郁,蜜蜂们赶来采粉,嗡嗡声不绝于耳。我和伙伴们会趁花儿含苞欲绽时赶来采,左手拢枝,右手摘花,转眼工夫就会摘满篮子。回家用开水一焯,佐以小许白面蒸着吃,白爽爽粉嘟嘟的,既保持了花的原貌,有增强了美感,满盘满碟,楚楚动人,真个是春色可餐哩!
刺槐花馨香扑鼻,一些草蜂也会捷足先登,就势在树上做窝,往往一窝有五六十只。有一次我上树采槐花,不慎惊动了草蜂,它们视我为打家劫舍之徒,竟对我大动干戈,有三四只箍在我头上,每只蜇了我一下,我猝不及防,被蜇得呲牙咧嘴,从树上摔了下来,跌的屁股好痛。
春风梳理着河边的柳树,梳的柳树好不舒服,不出几天,枝条上就鼓起了芽胞,一串一串的,好像爬满了一树绿蝌蚪。再过几天,“绿蝌蚪”就长出了小翅膀。这时采下来食用,可好吃哩。
当山楂花和梨花刚开时,采一些回家馇渣吃,味道与刺槐花相似,既节省了粮食,又领略了山野情趣,可谓地地道道的原汁原味的绿色食品。
芨芨菜虽然浑身长刺,但是却有止血的功能,小孩子鼻子动辄出血,用它烧水喝准好;倘若割草不慎割破手了,可采几棵揉细,将汁液滴在创口上,稍停就好了。芨芨菜喜欢粘性土壤,在未播种之前,往往会长出一大片。为防它扎手,可捏住其基部拔出来。芨芨菜一入开水,刺儿就没了。芨芨菜无论怎没做都好吃。
蚂蚱菜与芨芨菜截然相反,通体光滑,庄稼地里比比皆是。薅些回家,专掐嫩芽吃,剩下的喂猪,猪特爱吃。人们上山干活总会顺便薅一些,这样可节省好多粮食。
河边的河蓼子和一种俗称“王八叉”的植物也长出来了,它们的嫩芽也可食用。
地榆是一味中药材,有止血、疗疮、除渴、明目的功能。将其嫩叶采回家,掺和玉米面烀饼子,黄绿相间,味道独特。
胡枝子的花紫莹莹的,采回家蒸渣或烀饼子,烧好火一揭锅盖,立马香味四溢,令人满口生津。
当进入夏天,连下大雨,山上会长出“雀菜”。“雀菜”学名地衣,是菌和藻的共同体,由腐殖质滋生而出,平日里销声匿迹,只有在下雨天才出来。我和伙伴们总愿趁雨后上山捡“雀菜”,将其洗净馇渣或包包子,吃到嘴里滑滑的,不用细嚼就如小孩子坐滑梯,一下子就滑到肚子里,好不受用。“雀菜”是稀有之物,何况时间又短,唯有山里人有这份口福,外人是尝不到的。
有一次,有个伙伴发现了一簇稠密的“雀菜”,忙着用手往篮子里捧,不巧把一只癞蛤蟆捧在手里,他觉得软古唧的,以为是盘蛇,吓得魂飞魄散,等看清是癞蛤蟆时,就不怎么害怕了,随手扔到一边。癞蛤蟆朝他直瞪眼,肚子气得鼓鼓的,分明是嫌伙伴对它不友好,不该这么鲁莽地对待它。
进入三伏,草坡上的黄花就开了。那花形如同长号,好像在合奏《生命畅想曲》。采些黄花炒着吃,那可是一道味道鲜美的下酒佳肴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遇上了所谓的三年国内困难时期,乡亲们把树叶都撸下来吃了,至于上述那些野菜早就不见踪影,我和伙伴们好几次到山上剜野菜,无不大失所望,空手而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有几个小孩子,饿得实在没有法子,只好上山挖黄花的根儿吃,他们压根儿就不晓得,那根儿有毒,结果导致双目失明,终生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之中。这确实是挖野菜中的悲剧!有的山坡上还出现了几丘新坟,毋庸置疑,他们是被饿死的。
我是吃故乡的野菜长大的,因此对故乡的野菜特有感情,也有深深的记忆,述说起来如数家珍。至今,我的唇齿之间仍有悠悠的野菜清香。
蝉韵蝉趣
在胶东半岛,每当割完小麦,芙蓉花开的时候,树林中就会传出蝉的叫声, 这就意味着蝉们开始在这绿意氤氲的夏之歌坛登台亮相尽情演唱了。
古书上称蝉为蜩,称较小的蝉为螗。它们既然是遐迩闻名的歌手,理所当然都有学名和艺名。
首先上场的是蟪蛄,俗称麦吱儿。它体形小,仅有手指顶那么大,腹部发白,背涂斑点,贴在树皮上,让你看不出来。其声为“唧唧唧,唧唧唧”,因了这个缘故,人们管它叫“小唧唧”,有的地方美其名曰:“小嗓子”。这名字起的有学问。蟪蛄的叫声单调而凄然,仿佛一个羸弱的小女人面对隐隐青山,在诉说悠悠哀怨。
与蟪蛄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小蝉,俗称“记帐哥,”其体形和肤色与蟪蛄一般无二,只是发声有别:“记——住 ,记——住”。韵调清晰而宏亮,打老远儿就能听见。它就像柜台里面的一个小记账员,在掌柜的吩咐下,把流水账一笔笔记清楚。
盛夏之际,马蜩露面了。马蜩又名蚱蝉、黑蚱,因个头大,通体黢黑,俗称大马猴和大马知了,是蝉之家族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它叫声洪亮,底气十足,就像京戏中的黑头花脸,“哇呀呀呀、咋咋咋……”声震河谷,唱彻酷暑,风靡三夏。
接下来是蛁蟟亮相,它比蟪蛄略微大些,全身绿莹莹的,腹部白如粉,背部有黑斑,叫声独特:“富得喽——富得喽——”因此俗称“富得喽”。它长得极潇洒,只是数量不多。
鸣鸣蝉俗称“唔悠哇”,与蛁蟟相差无几,其声为“唔悠唔悠哇——唔悠唔悠哇——”,重复4次即停,倘若没有什么危险,就接着尾音继续吟唱:“哇唔——唔悠唔悠哇……”顶多重复两番,等叫完“哇唔”就飞到另一棵树上,再老调重弹,可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小家伙真乖!
寒蝉作为压轴戏上演。它的长相与蟪蛄极相似,其声亦为“唧——唧——”。不过腔调更为悲切,让人生发怜悯之情。,其时已是暮秋,秋气肃杀,山荒树老,景象萧瑟,若遇北风劲吹,树叶飒飒,寒蝉疑为危险将至,紧贴树干,不敢吱声,故有“噤若寒蝉”之说。
有人把上述6种蝉编为一个故事。说是蟪蛄的父母包办婚姻,要将她嫁给大马猴。她一见大马猴长的又笨又黑,打心眼里不愿意,就掩面哭泣:“唧唧唧,唧唧唧”。“记帐哥”劝解道:“我——看,可——以”。 蟪蛄不予理睬。蛁蟟很同情蟪蛄,二人一见钟情,蟪蛄转悲为喜,跟着它私奔了。蛁蟟高兴地唱道:“可得啦,可得啦”。大马猴见媳妇让人拐走了,就大放悲声:“妈呀妈呀……”寒蝉也替大马猴惋惜,不停地啜泣:“唧——唧——”鸣鸣蝉赶来安慰:“不要不要吧,不要不要吧。”
蝉的幼虫又称若虫,俗称知了猴或蝉龟,是由蝉卵埋入泥土中嬗变而成的。在地下一般为十二三年,甚至长达十七八年之久,靠吸食树根之汁而生活,先后蜕皮5次而渐次成熟。若虫于雨后之黄昏,用一对利爪凿洞爬出地面,本能地攀援树木枝头,于午夜时分背裂蜕皮。初时,那薄而透明的蝉翼如绢丝皱缩,身躯白嫩如玉,经晨露浸润,晓风吹拂,于清晨双翼舒展变硬,肤色由白转黑开始飞行自如。
古人云:“蝉有五德,头上有帻,文也;含气吸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处不巢居,俭也;应侯守常,信也。”细细琢磨,所云精妙,可谓无以复加。
捕蝉有好多方法,乡间儿童爱用面胶黏蝉,蝉翼一旦挂上面胶,就难逃厄运了,一边挣扎一边尖叫,弄得细竿颤颤,黏者收竿捉蝉乐不可支。《庄子》上有“佝偻承蜩”一节,说的是一位驮背者擅长黏蝉,百发百中,究其奥秘,乃屡经实践、技艺娴熟所致。有些儿童则用马尾勒,蝉的两眼横生额外,一俟勒上,越挣越紧,只好乖乖就范。捕蝉的最佳方法是在漆黑的夜晚,于林中生起一堆篝火,然后脚踹手摇树干,蝉们以为世界末日来临,弃树惶遽逃蹿,“飞蛾扑灯”般纷纷落于火堆,这时只管往桶里捡就行了,最好就势烧着吃,自会猎趣横生,别有味道。
蝉不但是一种野味,还可为人疗疾。蚱蝉主治小儿惊痫夜啼,癫病寒热,又治惊悸、妇人乳、胎衣不出,能堕胎。蝉蜕主治惊痫,妇人生子不下。《本草纲目》载,蝉在壳中不出而化为花,称为蝉花。主治小儿天吊,惊痫瘛疭,夜啼心悸。功同蝉蜕,又止疟。如此看来,蝉浑身是宝。
蝉的寿命一般在60至70天之间,靠的是紧贴胸前的针状长喙刺进树木中吮吸汁液而生存。雌蝉尾部有产卵器,用以刺破细枝末稍产卵,往往会在一个枝梢上产五六十粒卵,致使枝稍枯干,风折落地,再作生命的轮回。
凡是有树林的地方,都是蝉的家园,蝉的歌坛。据说全世界约有1600余种蝉。夏日听蝉音,能让人充分领略其幽美的天籁,体验这浓浓的乡情和野趣。
故乡的蚂蚱
在我的儿童时代,故乡的生态环境可谓大自然的原创版,鱼鸟虫兽特多,触目皆是。若论家族庞大、数量又多、引人注目的,当首推蚂蚱。
说起蚂蚱,必定让人联想到蝗虫。蝗虫口器坚硬,前翅狭窄而坚韧,后翅宽大而柔软,善于飞行,后肢很发达,善于跳跃。蝗虫由若虫蝗蝻蜕变而成。蝗蝻形如蝗虫,翅膀很短,体小头大,也善跳跃,因此也叫跳蝻。我没经历过蝗灾,听村老们讲,蝗虫袭来时,形如怪云,遮天蔽日,沙沙作响,令人震慑。落在庄稼地里,密密匝匝,伸手能抓七八只;若用扫帚扫,很快能装半袋子。蝗虫吃庄稼特快,转眼工夫,庄稼的叶子会被洗劫一空,惟剩一片光秃秃的秸秆,农民的汗水为之白流,满腔希望化为泡影。由此可见,蝗灾对农业生产有极大的危害,确实令人惊骇。
距故乡不很远有个村子,早年遭过一次蝗灾,当蝗群飞走之后,人们发现有一大片庄稼和草地安然无恙,揣摩此处有神灵,便纷纷捐款,在此处建了一个小庙,内塑一个老大的蚂蚱,谓之蚂蚱神,并对其顶礼膜拜,祈祷它法外开恩,严管部下,不要祸害黎民百姓。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它一个雕塑的大蚂蚱,有何法术能化解蝗灾,此举纯属荒唐,十足的愚昧!
除了蝗虫,没见其他蚂蚱对庄稼造成什么危害,即便吃点庄稼叶子也无大碍。倒是众多的蚂蚱为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提供了许多乐趣,伴我们度过了儿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