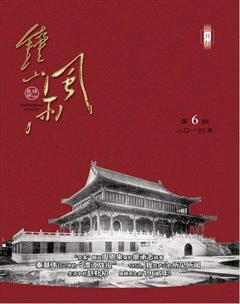文革破“四旧” 专家救国宝
金宝山



“文革”是一场浩劫。它不仅践踏人权,残害生命,也殃及文物。在高压的氛围中,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郑为、承名世、钟银兰等国家级鉴定家,以拳拳爱国之心,顶住恶浪,甘冒风险,保护了8万多件古代和近代的书画珍品,被人们誉为“国宝保护神”。
众专家甘冒风险 抢救珍品八万件
自1966年夏天起,造反派日夜出动,闯进所谓“牛鬼蛇神”的家里,横扫“四旧”,将抄来的贵重物品放进仓库,或交给文物商店和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准备廉价外销。
1970年,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负责人郑为、承名世听说上海一家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准备将60多万件书画作品按件计价外销,平均每件仅售人民币10元。他们立即赶赴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要求鉴定“出口”书画,留下文物。在得到该组负责人谢稚柳的支持后,两人与钟银兰、朱恒蔚、万育仁和裱画师黄桂芝、华启明组成鉴定小组,兵分两路,一路赴浙江慈城,清理上海存放在此地的书画作品。而此时,外商们正在香港举杯畅饮,庆贺捡了大便宜。一件书画进价10元,今后名画出手拍卖,拍价可能翻几百倍乃至上万倍!一家外商还请到侨居海外的中国书画鉴定专家,每日报酬8000美元,并承诺可携家属任选一处世界名胜游览一次。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郑为、承名世、钟银兰等人,在慈城清理出6万多件明清和近代的名家作品,定为“不能外流之文物”!造反派竭力阻挠,百般刁难,振振有词地说:“书画属‘四旧处理品,外销能换取数百万元外汇,不是很好吗?”郑为、承名世等据理力争,说:“外汇可从别处赚,文物不能再生,外流一件少一件,太可惜了!”造反派依然不服气,郑为他们引用周总理的指示与其辩论:“周总理作过指示,书画文物是国之瑰宝,不准出口。否则我们要愧对党和国家,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最后经过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裁定:留下6万件书画精品,入库封存!
郑为又率领另一路人马,来到上海玉佛寺一座佛殿。刚推门而入,就一脚踩在一捆书画作品上。那里有数万件书画,20件一捆,像是垃圾一样堆放着,其中有些已经发霉、损坏。郑为从中取出一件鉴别,不禁大叫一声:“这是八大山人朱耷用小楷写《蔡邕赋》的书画作品,标价人民币1元,糊涂透顶!上海博物馆才存一件八大山人作品呀!这些人是败家子,决不能让他们做主卖文物。”而后郑为转道乌鲁木齐路,进入一座仓库,只见库内铁架上堆满了书画。郑为取出一批书画,打开细读,发现有一幅绫本书卷,长一丈二,是明代董其昌临唐代大书家颜真卿的《裴将军》帖,每个字大于三寸,系董书的精品之作。郑为对承名世等说:“这么好的古代书法,价值连城,竟成了垃圾,束之高阁,真惨呀!”最后,经过几人共同鉴定,留下2万多件文物级书画和近代一批书画珍品,全部由上海博物馆保管。
历时两年,郑为、承名世等共鉴定了60多万件书画作品,将其中的8万件国家级文物保留在了国内,免遭流失之痛。
空四军借宝不还 挺身而出追不停
1968年,从“牛棚”放出来的郑为得知,上博珍藏的十多件元明时代的书画作品被空四军美术小组以临摹为名借走了,郑为闻言大吃一惊,问:“谁批准出借的?”听说是军宣队、工宣队头头批准的。他们现在是“上博”的太上皇,谁敢不听他们的!
郑为想到自己曾是书画研究部负责人,有责任把古代书画追回。他不顾个人安危,前去对驻本馆军宣队、工宣队头头说,元明作品属国家保护的文物,不能出借,别说借了,就是在本馆临摹也是不允许的。两队头头自知理亏,未置可否,阴阳怪气地敷衍道:“调查一下再说。”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是林彪的死党,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权倾沪上,“上博”军宣队便是他派驻的。谁敢去摸这个“老虎屁股”?一天,军宣队、工宣队头头在大会上说:“有人反映空四军借走了元明时代的书画作品,要求追回。人家是工作需要,借用一下嘛,不必大惊小怪。此事到此为止!”郑为性情耿直,散会后又去找两队头头据理力争,要求归还书画文物。两队头头把脸一沉,冷冷地说:“文物让空四军保存,比放在上海博物馆更加安全,这件事我们做主,你不必管了。”郑为怒火顶撞:“那还要上海博物馆干什么!”话毕,气呼呼离去。有人劝说郑为:“你管这种事,得罪了空四军,要担很大的风险。算了吧,别自找麻烦。”郑为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为国家利益考虑,我不怕,哪怕重进‘牛棚或坐牢,我也要管到底!”当晚,郑为奋笔疾书,将此事反映给了专管全国文物工作的王冶秋。那时林彪的势力横行天下,王冶秋也爱莫能助。几年后,“林彪叛逃事件”爆发,王维国在上海被捕。郑为此时重提“上博”文物被空四军借走一事,再次致函王冶秋。王冶秋在回信中告知:那十多件元明书画作品已在北京查出,后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原来,空四军美术小组借画是假,实为奉王维国之命,将书画送给林彪、叶群,借以讨好他们。郑为得悉文物已归还国家,庆幸国家文物得到了保护,自己的努力并未白费,分外欣喜。
连夜抄家斗巨商 偷护文物入“上博”
“文革”之初,造反派疯狂“打、砸、抢”,到处抄家,毁坏文物。国务院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及时发出通知:文物与字画是国之瑰宝,各地必须采取措施,竭力保护……上海文物部门据此告知上海博物馆派人参加清理古物与字画;凡是清乾隆以上年代的字画,更要封存、保管好。
造反派抄出的字画成千上万件,分别堆放在仓库、庙宇或教堂里,等待处理。老专家们几乎都已“靠边”站,谁来鉴定?情急之中,“上博”鉴定专家、时年34岁的钟银兰被调入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有关方面命令她每天24小时值勤,随叫随到。白天,她将上缴的数万件字画逐件登记入册、编目,列出清单,复写一式5份,分送上级主管部门与有关单位,手指都磨出了茧子。夜晚,她睡在办公室沙发上,不论夜多深,只要电话铃一响,她就要奉命出发。
1967年的一个夏夜,纺织系统造反派闯进江宁路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住宅抄家。钟银兰接到通知,火速前往。刘靖基先生是纺织、水泥业巨商,购藏字画多年,家藏颇丰。那晚,年逾花甲的刘靖基穿着短袖汗衫、短裤,颈上挂着“打倒反动资本家”的木牌子,站在庭院中,接受批斗,被折腾了整整一夜。天亮后,造反派都跑到外面去吃早点了。这时,刘靖基看到钟银兰独自一人坐在红木桌旁,正在一边鉴别抄出的古字画,一边将字画名称、创作者姓名和创作年代、收藏主人等内容登记入册。他惊喜地说:“看不出,你还懂行呀!你也是造反派吗?”钟银兰摇摇头,答:“我是‘上博的。”刘靖基喜出望外,悄声说:“原来你是‘上博的人,那我就放心了。我相信你,你不会胡来。橱顶上还藏着不少古字画,他们没发现,一起交给你,我一百二十个放心!”这批古字画交由上海博物馆保藏,得以幸免于难。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落实政策,抄家物品归还原主。许多被抄文物的原主人感激地说:“幸亏‘上博替我们保存,一件不少,物归原主。如果古物落入造反派之手,只能当作废品处理,或毁于一炬!”他们纷纷表示想捐赠一部分给国家。刘靖基老人带了头,他对上海博物馆领导说:“我愿捐出40件古字画,任凭你们挑选!我留一部分准备公开展览,让外国人知道,共产党保护文物,我的收藏品一件也不少!‘四人帮及其爪牙搞打砸抢,他们并不代表共产党!”上海博物馆委派钟银兰等鉴定专家,逐一挑选刘老收藏的古字画。钟银兰他们慧眼识宝,从中挑选了40件传世之作,其中有“元四家”之一倪瓒(云林子)画作《六君子图》轴、南宋张即之《行书待漏院记卷》等珍稀的国宝,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刘靖基对钟银兰说:“小钟,你挖掉我的眼珠子啦!”钟银兰抿嘴一笑:“刘老,这可是你让我们选的呀!怎么,你心疼反悔了?”刘靖基连连摆手:“不,不,永不反悔!古字画交给‘上博保存珍藏,比放在我家里安全。古字画本是过眼烟云之物,本来也应该属于国家,交博物馆珍藏,能一代一代相传,其意义更大。”
刘靖基与钟银兰在抄家时相识,成了莫逆之交。1997年,刘靖基在沪病逝,享年95岁。弥留之际,他对家人说:“‘文革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我最喜爱的古字画虽然被全部抄走,幸亏遇见了‘上博的钟银兰,将全部古字画保存下来,一件不损,并且交还给我们,她是好人啊!”
继郑为、承名世之后,钟银兰成为又一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她也是上海地区目前返聘上岗的唯一国家级鉴定家,在全国同级别的鉴定人员中也是唯一的女性。
(责任编辑:武学沪)
——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将于 4 月 29 日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