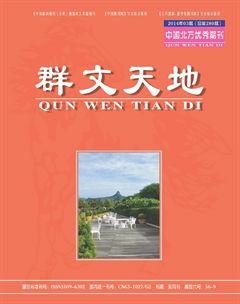草原王国吐谷浑(二)
任玉贵+解生才
丝绸之路
提起古路,历史上的唐蕃之路是民族和睦之路;茶马之路是互通有无之路,惟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之路,遐迩闻名。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名著《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原指汉代中国穿过西域腹地与中亚和中东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通过对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资料的进一步考察,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东岸和小亚细亚,从而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中国古代横穿亚欧大陆的贸易交往的通道。“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并非是固定的一条线路,而是随着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政治形势的演变而不断调整。道路的选择一般要依据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选择最平坦、安全、近捷的途径。据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藏高原文化研究所教授丁柏峰撰文:
据考证,我国从上古到先秦逐步形成的通往西方(中亚洲、欧洲、印度北部等地)的陆路通道的东段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从关中或今河南北上经漠南阴山山脉至居延海绿洲,趋向天山南北麓至西域,即所谓的“居延道”或“草原路”;二是从关中过陇山,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所谓“河西路”;三是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由柴达木盆地而到达今新疆若羌的古“青海路”。
丝绸之路并非由于政治意念的干预而于一夜之间突然形成的。依据现有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该道是在许多相当古老的区域交通道路的基础上,经过无数磨合和探索而最后形成的。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形成也是如此,可以说先后生存在这一地域的许多民族都为这条道路的开通做出过重大贡献,而道路的形成也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裴文中先生曾认为“湟水两旁地广肥沃,宜于人类居住;况湟河河谷文化发达,由史前至汉,皆为人类活动甚盛的地方,史前遗物,到处皆是,与渭河及洮河流域相类似”,因此推断“汉以前的东西交通,是以此为重要路线”,而且“是主要之道”。裴先生此论无疑是极有见地的,湟水正北通往张掖的古代道路至迟于西周晚期已经开通。比如成书于东周时期的《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就有关于湟水流域北向前往张掖里程的记载;再如,西汉北征匈奴等也大都启用这个通道。湟水正西通往西域的古代通道至迟商周至两汉间已经开通,这些原始道路的开辟者无疑是逐牧于此的羌人部落。
西汉时,汉与匈奴因战争对峙。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原居住在祁连山麓、后被匈奴人赶到中亚地区大月氏人共同抗击匈奴。张骞途中被匈奴扣留,十年后才逃出,继续西行。张骞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人已经习惯新居地的生活,不愿再返旧地。张骞的使命虽未完成,但了解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后来,汉朝军队打败了匈奴,控制了原由匈奴人占领的河西走廊。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与西域各国加强了联系。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的中原王朝首次对西域的形势、地理、物产等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西域的许多国家有了正式的往来。张骞带回的情况,对于汉朝军队打败匈奴,维护东西方交通的畅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史书称张骞西行为“凿空”。“凿空”有开辟道路的意思,后世据此把张骞作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在《汉书》卷61《张骞传》中记载:“(张骞)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虽然张骞最终并未能从羌中道,也就是青海境内的通道返归西汉国都长安,但一句“欲从羌中归”足以说明当时青海地区已经开辟出了通往中原地区的交通路线。这条交通路线在今青海境内主要经过了湟水流域、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三个地区,一般是由今甘肃兰州或临夏过黄河,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西行至青海湖,在横穿柴达木盆地而到达今新疆若羌等地,与通往西域的道路相衔接。这就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雏形,由于主要通过羌人聚居的地区,历史上也称之为羌中道。
张骞“凿空”西域以后,西汉王朝在河西地区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河西路因此而兴盛了起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中西陆路交通东段的主要干线。中原商旅一般都是先到达河西走廊的武威(凉州),然后从这里出发,沿线经过张掖、敦煌、楼兰(鄯善)、西州(高昌)、龟兹、于阗,翻越帕米尔高原,最终前往印度和中亚。居延路和青海路虽然相对冷落,但作为重要的辅道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由于战争和割据等原因,丝绸之路上的一些通道时常会出现断绝的现象,在主路壅塞的情况下,辅路的作用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以上通道就会显得至关重要。在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经常南下骚扰河西走廊和西域,“河西路”就曾经三绝三通。而在河西主道断绝的情况下,处于其南线辅道的青海道往往会得到充分利用。从这里可以沿着河湟地区向西,穿过青海湖滨以及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若羌。也可以从河湟地区向北,逾祁连山脉,到甘肃的武威或张掖。青海道与河西道隔祁连山而并行,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作用。总的而言,丝绸之路河西道通畅,青海路的作用则相对变小。河西道一旦阻隔,则青海路的作用变大。由于两条通道的相辅相成,丝绸之路在实际上未曾有过彻底断绝。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西域各属国纷纷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河西走廊也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地方割据政权,战祸频仍,河西走廊以及由此分支的南北两条故道时常阻塞不通。在这一中华大地四分五裂,国内局势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以青海为中心的吐谷浑政权顺应时势,“秣马厉兵”,“争衡中国”,成为一个地跨东西数千里的中国西部强国。在伏连筹时期有效控制西域若羌、且末地区以后,丝绸之路青海道便与西域通道顺利连接。过往的使团、商旅在吐谷浑辖境内横穿柴达木盆地向西,不经河西走廊便可通达西域。古“羌中道”由此演变为“吐谷浑”道,进入到了历史上最为兴盛的一个时期。这条通道的主要干道,西通西域,东与传统的丝绸之路陇右道(由长安沿渭河西行,过天水、临洮,经临夏过黄河到河西的路线)相衔接。由东到西,大致走向为:由临夏过黄河,西北方向行至乐都,再沿湟水西行至西宁,由西宁继续西行,进入柴达木盆地。在柴达木盆地形成了进入三条通往西域的道路:其一是由伏俟城经今海西都兰,西北至今小柴旦、大柴旦到达敦煌,由敦煌向西至今若羌;其二是由伏俟城经白兰地区,西至今格尔木,再向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过阿尔金山至若羌。其三是从伏俟城经白兰、格尔木一带,往西南的布伦台,溯今楚拉克阿干河谷进入新疆。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具体线路不是一成不变的,丝路沿线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态势和格局的变化往往导致线路走向的相应调整,不断有新的道路开通,也有一些路段会逐渐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西晋永嘉之乱以后,河山破碎,南北分裂。受其影响,在河西走廊及其附近地区相继出现了前凉、后凉、前秦、后秦、西凉、北凉、南凉、西秦、高昌等割据政权。这些政权相互敌视,竞相对其他政权进行军事掠夺和经济封锁,最终导致丝绸之路河西道几近瘫痪。顺应时势,吐谷浑建立起横跨千里的草原王国以后,在几代国主的积极主导与精心经营下,其辖境内的青海道成为连结中西交通的纽带,肩负起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对于国内各割据政权而言,吐谷浑更是一个联络塞北与江南的中继站。南朝使者从建康溯长江而至益州,进入吐谷浑境内,由吐谷浑人送到都善,再经高昌达柔然之地,柔然使者同样地由高昌、都善国,经吐谷浑地而顺江而下安全到达南朝。总之,吐谷浑在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大动荡时期,发挥了沟通中外交通、联系塞北与江南的重要作用。
学术界相关研究表明,在吐谷浑的大力经营之下,其辖境内实际上一共形成了四条通往各地的分道,即西蜀分道、河南分道、柴达木分道和祁连山分道,这四条分道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吐谷浑道。由于吐谷浑控制的地区主要在黄河以南,有些史籍中称吐谷浑政权为河南国,吐谷浑路也就被称之为河南路。其中,西蜀分道是由吐谷浑境通往四川的通道;河南分道是沟通西蜀道与柴达木分道及祁连山分道的通道;柴达木分道是沿柴达木南、北通往西域的通道;祁连山分道是由河湟通往河西走廊的通道。这四条主干道之间相互衔接,即西蜀分道北接河南分道,河南分道西接柴达木分道并北接祁连道,而且这主干道枝桠绵绵瓜瓞,形成一个通达四方的交通网络。陈良伟先生在其所著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一书当中,对这一交通网络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证,编者加上湟水支道:
“四条分道可细分为十条支道,即可分为岷江支道、白龙江支道、河源支道、隆务河支道、洮河支道、湟水支道、柴达木南支道、柴达木北支道、扁都口支道和走廊南山支道。它们是相互并行或相互串行关系。比如在西蜀分道下,岷江支道与白龙江支道原是相互并行关系,但其中段又可串行经行;再如在河南分道下,河源支道、隆务河支道和洮河支道原是相互并行关系,但其中段又可串行经行;再如在柴达木分道下,柴达木南支道和柴达木北支道原是相互并行关系,但在中段同样有串行经行的可能;还有在祁连山分道下,扁都口支道和走廊南山支道原是相互并行关系,但其中段原也可串行经行。除了上述四条分道和十条支道外,丝绸之路河南道沿线还有若干间道和辅道”。
终吐谷浑之世,以上诸条通道中西蜀分道与柴达木分道使用最为频繁,对吐谷浑政权而言显得尤其重要。这两条通道,一条通往益州(成都),然后与其他道路相接,能够沟通长江流域;一条连接西域,然后通往西亚、中亚乃至北非、欧洲,沟通中西。其作用无法替代,其影响不容低估。
秦汉大一统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中西的国际通道,其线路也主要开辟于北部中国。不论从长安出发还是从洛阳出发,主要走的都是穿越河西走廊的河西路,青海境内的中西通道,仅对河西走廊通道起辅助作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互相敌对。即便是在河西走廊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南方六朝与西域乃至境外的沟通问题也无法解决。而南朝所据地区恰恰是丝绸的主要产地,四川盆地内的成都早在两汉时期即已经成为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吐谷浑境内通往四川的西蜀分道就成为西域客商前往巴蜀、江南的必经通道,吐谷浑也因此成为他们之间的中介。西域客商通常经由柴达木分道横穿柴达木盆地以后进入今环青海湖地区,然后转向东南,从今龙羊峡或尕马羊曲过黄河,经今贵南县、泽库县,越甘南草原,然后南下龙涸(今四川松潘),沿岷江进入益州(今四川成都),再顺长江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也可以从今兴海县曲什安乡渡黄河,经今同德、甘南,沿西倾山北麓东南行,至四川境。由于行经吐谷浑境内可以直通巴蜀乃至江南,中原、江东、吐谷浑、柔然乃至西域各国均以成都为中心进行贸易活动。《太平御览》卷815引山谦之《丹阳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乃有之”。《宋书》卷45《刘粹传》附《道济传》载:“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贷资或有直数百万者”。《周书》卷37《裴文举传》则记载:“蜀土沃饶,商贩百倍”。类似记载史籍中尚有很多,充分说明当时成都商贸的繁盛。陈寅恪先生据此认为:“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而大多数西域客商都是经由吐谷浑境内前往成都的。
吐谷浑存国期间,一直充当着中西客商的向导、保护者以及贸易中继人的角色。吐谷浑“地兼鄯善、且末”,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车尔臣河上中游广大地区,都为它所占据。“蠕蠕(即芮芮)、嚈哒(即滑国)、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这条史料明确指出西域各国与中土联系须经吐谷浑,说明吐谷浑提供了进入今新疆后经高昌北上的路线。《梁书》中记载,当时嚈哒、波斯、龟兹、于阗均遣使与梁通好,“与旁国道,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其言语待河南人译而后通”。说明这些国家通使贸易需要由吐谷浑人担任向导及翻译。
吐谷浑之所以在其辖境内积极开拓沟通中西,连接内地的交通孔道,潜心维护并经营丝绸之路青海道,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
吐谷浑立国时期中国东部的大地上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北方依次是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和北周;南方依次是东晋、宋齐、梁、陈。为了减缓来自这些政权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吐谷浑立国350年中,在政治上始终与政权南北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当时南方诸朝为了牵制北朝,都在积极拓展其外交,广结盟友,意图联合西北各个割据政权共同抗击北方诸朝。南朝虽弱,但被视为正统,加之吐谷浑与北方政权相邻,时刻都能感受到来自于北方政权的政治、军事压力,吐谷浑对于这种联盟的倡导反映极为积极。同时,由于自身的弱小,出于夹缝中生存的需要,吐谷浑与北方各政权也保持着密切交往。
除了政治上的动因,经济上的需求也促使吐谷浑积极经营丝绸之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吐谷浑与其他游牧民族在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商业在吐谷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吐谷浑人一方面充分利用丝路南道青海路的优越条件,与西域各国展开贸易交往,获得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在同南北诸政权政治交往的同时,进行“以献为名,通贸市买”的商业活动。吐谷浑与南朝的经济具有非常实用和现实的互补性,南朝经济以农业为主,需要大量的畜牧业产品,吐谷浑是畜牧业经济,需要大量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品。这种经济结构造成的互补现象,在封建时期的中国是极其常见的,也是极其正常的。《梁书》中记载:“其(吐谷浑)地与益州相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书之辞译,稍桀黠矣。”由于吐谷浑政权非常重视商业,甚至所有国赋开支都需依赖向商人抽税。文献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因此,崔永红先生在其著作《青海经济史》中指出:
“由于商业的兴盛,吐谷浑人积累的财富较多,他们富藏金银财宝,还曾引起北朝统治者的垂涎和觊觎,甚至成为北魏北周多次发动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争的诱因。”
由于强烈的政治需求以及巨大的经济诱惑,吐谷浑对于丝绸之路的维护与经营可谓不遗余力,把道路通达视为国之命脉。“其国内实行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往往是从维持和发展中西交通的目的出发的,如吐谷浑的国都最后迁至青海湖西十五里的伏俟城;于鄯善置兵戍守;采取与北朝、南朝各政权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接受封号,不断朝贡;统治阶级信奉佛教;抽取富室、商人赋税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无一不与其加强和发挥在中西交通上的作用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南北分裂,河西走廊壅塞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原本作为丝绸之路辅路的“吐谷浑路”成为承担起由南朝前往西域以及漠北的商业交流和运输任务,中外商旅“相继而来,不间于岁”。使得“吐谷浑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成了西域和西方诸国同中原各朝进行经济联系的重要枢纽”。
相关学者研究表明,当时的往来商旅经常与使团以及求法的佛教僧侣相伴而行。有的时候,使团就是商团,打着使团的幌子从事商业活动。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3年),吐谷浑夸吕通使于北齐,回返时经过凉州,“凉州刺史史宁占知其还,率轻骑袭之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这一史料表明,有重臣、将军率领的高级使团,实际上是由胡商组成的商队。这就证明了使团与商队的一体性,也说明了当时的商队规模庞大,货物运输能力相当可观。吐谷浑立国期间,“国无长税,调用不给,辄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向商人征税。这就需要充分保障境内商旅的安全,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商人选择从吐谷浑辖境内通过,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吐谷浑的立国之本。所以《宋书》中记载:
“吐谷浑逐草依泉,擅强四表,毛衣肉食,取资佃畜,而锦组缯纨,见珍殊俗,徒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虽复苞篚岁臻,事惟贾道……送迓烦扰,获不如亡”。
可见,当时吐谷浑辖境内西域及外国商旅行人往来不断,过境贸易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财富,也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1955年在西宁曾一次性出土了七十六枚波斯萨珊卑路斯王朝(公元457-483年)的银币为当时吐谷浑路上的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实证。萨珊王朝是丝绸之路中国境外线路的重要开拓者和维护者,河西地区不断有该国货币的出土,说明其在丝绸之路贸易上非常活跃。史籍中也屡见萨珊王朝遣使南朝的记载,“梁中大通二年,(波斯)始通江左,遣使献佛牙。”“是岁(公元553年),河南、波斯、盘盘等国遣使朝贡。”“(公元535年)波斯国献方物。”就其地理位置而论,其向南朝遣使朝贡应当是由西域进入柴达木盆地后,经吐谷浑境前往四川,再趋江南。西宁地区发现该国银币,也证明了萨珊王朝正是通过吐谷浑路与中国内陆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所论述的:
“以前我们常以为中西交通孔道的‘丝路的东端,是由兰州经过河西走廊而进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次西宁发现这样一大批的波斯银币,使令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我以为由第4世纪末到第6世纪时尤其是第5世纪中(包括卑路斯在位的年代),西宁是在中西交通的孔道上的。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他的地位的重要在当时决不下于河西走廊。”
吐谷浑路不仅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对于国内割据四方的分裂政权而言,也是一条有效的连接纽带。十六国时期,河西的前凉、西凉、北凉等几个政权始终与东晋以及南朝的刘宋政权关系密切,使臣来往不断。当时秦陇地区被北方政权所隔绝,从河西到达东晋、刘宋所处的江南只能以益州为中继站。这几个政权的使者基本都是从敦煌或张掖进入青海吐谷浑境内,然后前往益州。北凉覆灭以后,其残余势力沮渠无讳以及安周兄弟在西域高昌建立了政权,史称高昌北凉政权。为了对抗强大的北魏,高昌北凉政权一直与刘宋交好,接受刘宋的官爵。史籍当中有五次沮渠无讳向刘宋遣使的记录,分别是公元442年两次、公元443年一次、公元444年一次以及公元459年一次。前四次或是由敦煌南下入吐谷浑境,或是由高昌出发通过焉耆到若羌,越阿尔金山进入吐谷浑控制的柴达木盆地,穿越其境,前往益州。第四次则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略而无法确定其具体路线,估计仍是经吐谷浑境而前往益州,直至江南。《宋书》当中还有两次中亚粟特国向刘宋入贡的记载,第一次是在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史籍中仅简略的记载了一句“是岁,河南、肃特……等国并遣使来朝贺。”肃特即粟特,音译不同。第二次是“大明中(公元457-464年)遣使献生狮子、火浣布、汗血马,道中遇寇,失之。”早在公元439年,北魏就已经占领了北凉都城姑臧,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粟特使者去江南自然不能通过与刘宋对立的北魏控制区,只能是从西域进入吐谷浑境内才能到达目的地。相关研究表明,粟特商人是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转运商,他们在中原地区主要购买成匹成捆的丝绸、香料、纸张等贵重商品,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转手卖给波斯人、罗马人、印度人以及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粟特遣使的真实目的应该是为了通商贸易,使团即是商团。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吐谷浑路的兴盛不仅带来了吐谷浑经济的繁荣,同时对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传播人类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周伟洲先生所言:
“在公元五世纪中至七世纪初,吐谷浑所据之青海地区事实上成了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从青海向北、向东、向东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国与漠北西域、西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往,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
经营丝路
丝绸之路不能回避的浓墨重彩一笔也无可匹拟就是青海。它美在其中,畅于四通,纯粹内实,光辉外著。丝绸之路是以古代民族迁徙所形成的“民族走廊”为基础,通过生计往来而形成的互补型贸易通道。
我国境内的陆上丝绸之路,以草原道、河西道和吐谷浑道(亦称青海道)三条主线并驾齐驱,四令五达,互为依托,互相相连,互为复线。其中,青海境内的丝绸之路为彼此贯通的叶脉网络型商道,自北魏起,吐谷浑擎天驾海、能力非凡,以羌中道为基础干线,联通河湟道、西蜀道、吐蕃道、雪山道、西域道等路线,随吐谷浑的兴衰而波动始终,兴盛五百余年,余绪达千年,其地位绝不亚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河西走廊,在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中做出过不可取代的杰出贡献,另垂青目。
自魏晋以来,西域各属国纷纷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河西走廊也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地方割据政权,战乱频发,多行苟政、暴虐无常,河西走廊以及由此分支的南北两条故道时常阻塞不通,当时在今甘肃西南部及青海草原由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吐谷浑国,经过树洛干、阿豺、慕璝、慕利延等几代人的尽其敏思、烁其才华,独出新招,开拓经营,已经成为地跨东西数千里,包括鄯善、于阗在内的中国西部强国。吐谷浑立国350年,而且始终与中原王朝以及南北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兴盛提供了时间、空间上的条件和必要的政治军事保障。
河南道,古称羌氐道,又因这条道路是沟通雍、梁二州间的古道,故亦称雍梁道。早在战国初期,秦献公权倾一世,兵临渭首,河湟羌人为避其兵威,不谋此功,不计其利,向黄河以南迁徙,艰辛苦涩,循悬幽径,移居到岷江、白龙江、西汉水乃至长江上游一带,和氐人生活在一起,精心呵护,顺势而为,应时而动,形成所谓越(今四川西昌)羌、广汉(今四川广汉)羌、武都(今甘肃成县)羌等,这是河南道见之于史籍之始。
公元420年进入南北朝之后,星转斗移,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北魏统一了北方,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对峙,兴起于漠北的柔然又与北魏相对峙。在青海和陇右、河西建立政权的南凉、西秦、北凉先后灭亡的同时,吐谷浑却在西部崛起。在这种形势下,柔然、吐谷浑以及西域各国均同时与南北两大政权交往。而南方汉族政权也力图打通与西方的交通,以便于西方贸易。可是从江南向漠北或西域的主要道路均为强敌北魏所据,于是南朝历代政权只有从四川西北经吐谷浑与漠北柔然和西域交往,河南道声名鹊起,更加兴盛起来。
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河西的北凉江且渠氏和吐谷浑阿豺均向刘宋朝贡,并接受其封号,然后双方不断有使臣往返。因为此道必经青海黄河河曲以南之地,故史称“河南道”。亦因吐谷浑国又称为河南国,史籍中把贯穿吐谷浑的道路称之为“河南道”或“吐谷浑道”如《南齐书·芮芮虏传》所云“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南齐书·皇后传》载:“永明元年,有司奏贵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绶,佩于阗玉。”于阗玉即和田玉,也是通过河南道转输到南齐的。关于这条路线,吐谷浑王慕利延在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上宋文帝刘一隆的表文中说的更具体:“若不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西门”。说明吐谷浑不仅与南朝刘宋王朝关系密切,而且对进入蜀地的交通道路也十分熟识的。
由吐谷浑早期牙帐所在地莫贺川(今青海贵南县茫拉河流域)沿黄河南东达洮河上游,经龙涸再沿岷江南下至益州;或经洪和(今甘肃临潭县)沿嘉陵江或汉江入长江,而后自长江而下抵达建康的道路,即是丝绸青海路河南道东段的主要干线。吐谷浑竭尽全力,枕戈待旦,上通下达,游刃有余,享誉一方。
湟中道:从关中过陇西,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经鄯州(今青海乐都)抵达西平(今青海西宁),并向西、向南、向北辐射,西接羌中道,南连河南道,北面通过乐都武威道、西平张掖道至凉州。人们把湟水流域这条四通八达的主干道称之为湟中道与河南道比翼双飞。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名僧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自长安出发西行,过陇西,经湟中道,越过养楼山(今大坂山),出扁都口至张掖,转往西域至天竺求经。
更具说服力的是,1956年在西宁出土的76枚波斯银币,据鉴定均系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王时代(公元457-483年)的银币。当时,这种银币在中亚和西亚流行很广,属国际性的货币。70年代大通县上孙家寨乙区第3号墓出土一件单耳银壶,从形体和纹饰观察,当出自古代西亚大国安息人之手。这些波斯银币及安息银壶等物的出土,就是当时青海路兴盛,湟中道成为中西交通重要通道,西平成为中西方贸易重要集散地的可靠历史见证。
由陇西西渡黄河进入湟中道,虽有多处古渡口,但自汉以来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是由枹罕西行,至今炳灵寺及大河家过黄河至官亭。二是由金城往西渡黄河,有钟泉河、新城、八盘峡、小寺沟四渡,其中小寺沟是首要津渡。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西秦在炳灵寺的黄河上架起了长40丈、高50丈的“飞桥”,从此,大大方便了丝绸之路青海路东端的交通。刘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僧人法勇(昙无竭)等一行25人就是经过此桥入青海境往西域求经的,大气犹在。
羌中道:羌中道就是指沿青海湖南北两岸西行,横贯柴达木盆地进入南疆的道路。有学者认为羌中道为汉武帝时霍去病或公孙敖出征河西过程中打通的路线;也有人认为是元鼎六年筑令居寨后开通了羌中道;还有人认为是北魏吐谷浑时,慕利延败退柴达木盆地,由白兰西入鄯善、于阗,开辟了这条道路。学派纷争,其实不然,羌中道是古代羌人在早期大迁徙中自已探险走出的道路,若羌以及西域的众多羌人原是从今甘青地区西迁的,长期以来,相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一直通过这条“羌中道”来维持着。同时,羌中道很早就已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张骞出使西域,雄风豪气,返程时“欲从羌中归”,说明他早已厚此薄彼,知道这条“羌中道”的存在,不虚此行。
河南道和湟中道西段,都交汇于羌中道。南梁时,远在中亚的波斯(今伊朗),厌哒(今阿富汗北)和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等国,相继遣使通贡,基本上都是由羌中道转走河南道往返的。吐谷浑始邑于伏罗川后,与北魏的交通,日渐深入,也是多由羌中道入湟中道的。
吐谷浑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光彩的一页是他们在经济活动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吐谷浑在阿豺时,南北对峙已形成,特别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对南朝通西域是一大障碍。而吐谷浑地处中西陆路交通要塞,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其西可通西域、中亚,西南连西藏,可通印度,东北通向北魏,南接刘宋王朝。因而,南朝经柴达木盆地进入西域的青海路,就逐渐兴盛起来,成为吐谷浑经济繁盛的一条通衢广陌的黄金大道。特别是自阿豺开辟的从吐谷浑地龙涸沿岷江入南朝的道路,更促进了吐谷浑与巴蜀江南一带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北方的芮芮(柔然)由吐谷浑境而达益州的河南道的畅通。南朝的丝绸、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的经吐谷浑地输入今新疆的鄯善、且末、流向西域、中亚,西域以外的物产也从吐谷浑境流入中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促进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吐谷浑国内建立起的许多草原城堡,供沿途客商歇脚、中转,提供牦牛、骆驼等交通运输工具。同时吐谷浑在中西贸易中还充当翻译和向导的角色,起到了保护商旅的作用。史书记载:当滑国(哒哒)的使臣去南梁时,“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这里的“河南人”就指的是吐谷浑人。吐谷浑在中西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不仅便利了不同国家商人之间的贸易,同时也使自己大大得利,致使吐谷浑国内形成许多富商大贾,而且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吐谷浑“国无常税”,调用不济时,便向富室商人征收,这在中国古代所有政权中也使极少见的。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吐谷浑境内中转贸易繁盛,国库比较充足。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青海西宁和都兰地区都先后发现过充当古代中东国际性货币的波斯银币和中原丝绸,而这些物品又都留有吐谷浑时代的痕迹。吐谷浑国内商业经济繁盛,及吐谷浑在中西陆路交通地位的重要,有成为吐谷浑政权立国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晋南北朝时,吐谷浑凭借丝绸之路之优势对青海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晋书·吐谷浑传》称吐谷浑“国用不足,辄敛富室商人”。说明吐谷浑国商人阶层早已形成,商业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吐谷浑与南北朝之间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梁书·河南王传》云:“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矣”就是说吐谷浑不只与南朝汉族政权进行朝贡贸易,而且于双方接壤地带进行互市和民间贸易,并开展文化交流。至于吐谷浑与北朝的通使贸易就更频繁了。《魏书·吐谷浑传》说:“终世宗世至于正光,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据统计,从公元431年至520年,《魏书》帝纪所载即达64次,居边境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朝贡北魏次数之首。在北朝分裂,东西敌对的情况下,吐谷浑除直接同北周进行贸易外,还绕道经北方的柔然到东方的东魏、北齐进行贸易。《北史·吐谷浑传》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夸吕又通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探知其还,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綵丝绢以万计”。可见吐谷浑商贸使团队伍规模相当庞大,所拥货物数量极为巨大。吐谷浑的贡物一般是地方特产,如牦牛、战马、舞马、毡等,还有从西域或别的部族、属国得来的诸如女国金酒器、胡王金钏、乌丸帽、玉器等珍玩奇宝。南北王朝的赏赐品主要是丝绢布帛以及各种精致的手工产品和生产工具等。这样的贡赐往来,一方面是政治上隶属关系和亲善友好的表示。另一方面是经济上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客观上有利于吐谷浑与南北朝三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联系。
同时,吐谷浑还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虽邈如山河,却引导和护送西域商使,充当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当时地处中亚的阿穆尔河、锡尔河流域地区,自古为东西方文明的中转站,贸易集散地。久居住此地的安、石、曹、史、米等九姓粟特人,很久以前就以中原洛阳等地为依托,开展双向贸易,世称“昭武九姓”。他们为了便于和中原交流,妙言要道,特意取了中国人的姓氏。精明的吐谷浑人很快与“昭武九姓”建立了牢固的贸易关系,从而进入到波斯、东罗马帝国、直至欧洲。他们充分利用地理、人际、语言及熟悉东西商情的条件,充分发挥与南北朝关系和好的政治资源优势,以过境贸易、合伙、中介、期货囤积、武装护送、向导翻译等多种方式,开展和参与东西方贸易往来。其规模相当大,时间相当长。这可从都兰吐谷浑古墓群中出土的大批文物及上世纪50年代出土于西宁的77枚萨珊银币等。还有史书上记载的吐谷浑可汗的金狮子床、胡王金钏、玛瑙金钟、进贡南朝的赤龙舞马等等,得到重复的印证。再现了吐谷浑人开拓的丝绸南道的昔日辉煌。即便在吐蕃收服吐谷浑后,丝绸南道仍然繁华不减,而且一枝独秀。
青海丝路因吐谷浑内部政权的更迭,异名众多,诸如河南道,吐谷浑道、白兰道等。随着吐谷浑入青,西晋末年南北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青海丝路由南向北,自东向西都有了新的发展。吐谷浑国力盛时,领有青海全境并与吐蕃发生联系,向西北可达新疆东南部,向东南可达川西北松潘草原广大而宽阔的区域,沟通东西的青海丝路犹如完全舒张延伸的叶脉,进入全方位的交通交往阶段,这一时期延续到隋唐,丝绸之路成为最为繁忙的中西交通线,也是最富庶的贸易生命线。吐谷浑以羌中道及其延长线河湟道横贯青海高原,东达长安、洛阳。西达中亚、西亚,以这条主干道为主轴,在北方自东向西分别延伸出经庄浪进入河湟或河西道,从祁连山门源、峨堡、扁都口等关隘入河西道,从柴达木盆地北缘进入敦煌、昆仑山以及西部的若羌、且末、于阗等西域南部地区,与河西道进入网络化交通时期;吐谷浑处于强势阶段时,在青海打通了吐蕃道(由吐蕃过吐谷浑进入西域)、河南道南线(从青海湖南岸和柴达木盆地南缘进入玉树联系吐蕃,该线路在唐代连接长安成为著名的唐蕃古道)、河南道东南线(从玉树囊谦进入昌都,以及从西倾山、阿尼玛卿山过久治进入川西高原与西蜀道相连,远达成都、宜宾、武汉)。吐谷浑时期的青海丝路的蛛网布局,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丝绸贸易意义,约有五条重要分线:一是从羌中-湟水通往白龙江的西蜀道,含松潘道、岷山道;二是沿羌中-湟水逆行从祁连山各口进入河西走廊、张掖的南山道;三是沿湟水西南通往河源的白兰道;四是湟水向西域的羌中古道;五是吐谷浑接续吐蕃的吐蕃道。
吐蕃道和河南道南线的贯通,使得远在青藏高原西南端的吐蕃的视野被引向远方,开始吐谷浑的富庶,为吐蕃兴起以及最终灭吐谷浑留下了伏笔。在游牧以外,吐蕃通过课税、导引、护卫繁忙的商贾,使节往来所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一方面开始借吐谷浑提供的商道密切地与西域诸国进行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强烈地意识到吐谷浑已经成为其交往东方中原的最大障碍,吐蕃最终借由丝路形成的通道占据青海,东向长安,青海诸多民族融入吐蕃,建立具有特色的安多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吐蕃文化、古羌文化延伸到川西高原,为长江流域各民族的源头文化及其多元特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某种意义上上说这一地区的各族族源追溯、历史记忆、民族文化、族群界限都与青藏发生密切而深刻的关联。与此同时,丝绸不仅成为东西贸易的最大宗商品,而且成为主要实物货币,最后将西方的金银元、货币引入这一地区,丝绸之路发育完全成熟,中外通过丝绸等东西互补型贸易往来,结成了以贸易为主体经济,宗教为主体文化的利益共同体,古代青海的民族战争与和平,都以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动因。青海与南疆成为沟通东西最大的贸易、文化、政治中转站,尤其是当北方、中原动荡的重大历史时期,丝绸贸易始终可经由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联结的丝路相沟通,从未发生中断,直到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才渐次沉寂。
吐谷浑时期的青海丝路的开通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东西往来,吐谷浑国内商贾云集,五音繁会,一个充满自信的高原民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其实力因商业贸易繁荣昌盛而扩展到整个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其次,完成了高原羌族与吐谷浑民族融合,促进了芮芮、粟特、哒哒、高昌等西域诸国的发展,吐谷浑作为青藏高原的主流文化屹立于东西文化的制高点;其三,促进了佛教在青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额手称庆。
“在公元五世纪中至七世纪初,吐谷浑所据之青海地区事实上成了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从青海向北、向东、向东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国与漠北西域、西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往,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
可以说,古往今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依托交通,发展经济最能体现吐谷浑国威、军威和综合实力,因而吐谷浑最感光荣、最感振奋、最感骄傲、最感自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