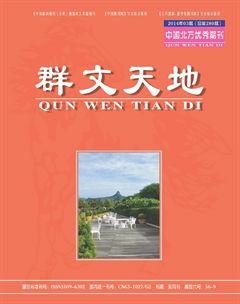青海“花儿”中石榴与鹦鹉的文化意蕴
进来大峡是小峡,石榴花,鹦哥儿搭了架了;
千留万留的留不下,你去吧,再不说难心的话了。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石榴”和“鹦哥儿”是青海河湟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一组意象,歌手们这样唱,人们也这样听,但未必唱的人明白、听的人清楚,石榴与鹦鹉之间到底有何关系?半个世纪以来,惟刘凯先生对此进行过一些思考,试图揭开其中的谜,他说:“原来它反映的是解放前兰州西宁交通险阻的情形。那是乐都老鸦峡以西至小峡一带,路很难走,一边是湟水,一边是悬崖,凿石崖为狭小的小路,险要处,赶着牲口都不易通过。老鸦峡西有个地方,崖上的石头凸出来,下面凿石为道,凸出部分像鹦哥的嘴。由于这个地方狭窄难走,靠河的一边不得不用木头搭起架子,以稍稍将路加宽,‘绿鹦哥搭架(者)过了的掌故,即由此而来。”刘凯虽然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可惜纯属形象性阐释,没有看清“石榴花”和“鹦哥儿”之间存在的深层文化内涵。
在青海河湟地区,劳动人民非常喜欢一种叫“石榴儿”的植物,几乎每家每户都把它种植在当院里。“石榴儿”枝干不足一米高,花色呈粉红,形状如“心”,花朵小巧玲珑,一串串,红红火火,充满喜气。湟中、大通人美其名曰“石榴儿”,青海“花儿”中时不时就出现它的身影:
高墙园里的石榴儿,白牡丹底下的兔儿。
心肝花想成了三绺儿,路远(者)听不上信儿。
———《大通花儿集》
其实“石榴儿”的学名叫荷包牡丹,湟水下游的乐都等地就叫它的学名。青海不种植石榴,自然也不产石榴,“石榴儿”是外来的文化移植行为。
好不过五月的热暑天,石榴花长在个路边,
千思万想不见面,清眼泪淌在个地边。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这首“花儿”的“好不过五月的热暑天”符合青海河湟地区实际,譬如西宁在湟水中游,夏天平均温度18益,一年中超过30益的天数就那么几天,农历五月至八月期间,最适宜出游。然而“石榴花长在个路边”不符合青海实际,青海人家一般都不会把荷包牡丹种植在庄窠外面;“石榴花”也不是青海民间口头普遍表达的词汇,实质上是江南的“石榴花”只出现在民歌中。譬如:
一溜儿山来二溜儿山,石榴花赛过了牡丹,
一日想来二日算,我没有忘你的半天。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在青海“花儿”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些古老的“花儿”,把这种外来的石榴文化意象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如:
修房要修三合头,房子后头栽石榴,石榴不死根不朽,贤妹不死不丢手。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这山望见那山平,三根石榴长成林,
三根石榴都结子,看你选上那一根。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这两首作品,与其说是青海“花儿”,还不如说是江南民歌在青海“花儿”中的移植。“修房要修三合头”、“这山望见那山平”是江南民歌特有的两种起兴方式。“房子后头栽石榴”显然更不符合青海实际。“三根石榴长成林,三根石榴都结子”进一步证明了花儿中的“石榴”非青海的“石榴儿”,而是江南的石榴树。
珍珠玛瑙的石榴儿,嫑挂在门前的树上;
实心实意的一个儿,嫑丢在空中的路上。
———《青海花儿选》
近几年来,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云南等地的石榴才进入西宁市场。然而,这一文化意象却在青海传播了数百年,地域封闭,交通不便的河湟地区,怎么会有这么多涉及石榴与鹦鹉的“花儿”呢?又怎么会有“珍珠玛瑙”如此形象、美丽、动人的描述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明代的江南移民,习惯了江南的文化生活,将荷包牡丹权当作石榴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石榴儿”便成了青海河湟地区约定俗成的民间称谓。所以石榴这一来自江南的文化记忆,居然在一些古老的青海“花儿”中得到了传承!
在江南民歌中,以石榴起兴的作品很多,如:
五月榴花红似火,梅雨过后天放晴,
芒种开始天气热,夏至夜短两分明。
———《南京歌谣谚语》
石榴打花叶又细,阿哥出门做生意,
十天半月唔回转,阿妹怎么舍得你。
———《江南民间情歌八百首》
第一首是南京鼓楼区的民歌,以石榴开花的时间和石榴花的色泽入手起兴。第二首是江西省南康县的一首民歌,用石榴打花的叶子生发起兴。
姊在院中折石榴,郎在院外抛砖头;
要吃石榴拿一只,要偷私情叩个头。
———《江苏南部歌谣简论》
姐在园中采石榴,郎在外边掷砖头;
要吃石榴拿只去,要想阿姐夜头来。
———《江苏歌谣集·沪海区》
这两首江南民歌大致相同,传递出江南女性大胆的示爱方式。而下面这首流传在南京雨花台的民歌,则把女子在荷包上绣石榴的场景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小小荷包四角叉,里绣绫罗外绣纱。
荷包没有铜钱大,高头绣的石榴花。
———《南京歌谣谚语》
在中国古代,荷包是男女间爱情的信物,石榴花象征着火一样的爱情(还代指女性),石榴果则是爱情的结晶。“荷包没有铜钱大,高头绣的石榴花”一句在凸显了女子高超的针线手艺的同时,含蓄婉致地表达了女子对爱情生活的向往之情。
与石榴出现的另外一个意象就是鹦鹉了。汉代郑玄《礼记注》云:“鹦鹉,鸟之慧者。”我们知道,鹦鹉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江西等南方地区;石榴虽然分布较广,若与鹦鹉叠加在一起,则体现了南方的一种文化认知模式。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青海“花儿”中“石榴花,鹦哥儿搭了架”的说法了。在青海方言中,人们把鹦鹉叫“鹦哥儿”,这是明代浙江等吴语方言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儿尾”词汇,与普通话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青海少年“儿尾”方言刍议》一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红嘴儿绿毛的尕鹦哥,两股儿铁绳俩拌了;
人伙里看下的你一个,两股儿眼泪俩盼了。
———《花儿集·西宁演唱特刊》
在《红楼梦》41回中,也能看到和青海一样的关于鹦鹉的同等描述与相同称谓:
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与她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刘姥姥一一的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它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讲话。刘姥姥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黑老鸹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众人听了都笑将起来。
刘姥姥虽然粗俗,却给人欢乐,她的行动与语言总是那么富有幽默感。“绿毛红嘴是鹦哥儿”和青海方言相同,但在这里只是一种铺垫,“那笼子里黑老鸹子(八哥儿)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才是搞笑之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对民间人物是多么的熟悉,多么的了解,为我们研究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提供了优秀的范例。
石崖(哈)瞅成草垛了,奈何的桥,我当成鹦哥儿架了;
煨人的世事(哈)看透了,我心(哈)好,人把我哄害怕了。
———《青海大通花儿集》
这首“花儿”明确告诉我们,主人公因为误判,所以把通往阴曹地府的“奈何桥”,看成了通向美好婚姻生活的“鹦哥架”,而心有余悸。我们认为,鹦鹉不同于其他动物,鹦鹉多产自印度,使得鹦鹉在印度佛经中身份特殊。鹦鹉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过去身。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昔者菩萨为鹦鹉王,常奉佛教,归命三尊。时当死,死不犯十恶。慈心教化,六度为首。……佛告诸比丘,时鹦鹉王者,吾身是也;人王者,调达是也。”佛教传入中国后,鹦鹉的神异性在我国古代叙事作品中也有体现。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一回《盂兰盆佛爷揭谛补陀山菩萨会神》:“右傍立着一个小女徒。弥陀满口。绿鹦哥去去来来,飞绕竹林之上;生鱼儿活活泼泼,跳跃团蓝之中。原来是个观世音,我今现尽世问人。”第七十八回《宝船经过刺撒国宝船经过祖法国》:“……原来是个南无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左边一个龙女,右边一个鹦哥。龙女儿指手指脚,鹦哥儿跳上跳下。番王看见不胜之喜,连忙的走到香炉底下来,再三叩头,再三礼拜……”青海“花儿”中所谓“鹦哥儿搭架”体现的正是一种佛教文化中的普度精神,对于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的人们来说,能够与心爱的人相厮守,是多么美好的愿望。
在我看来,“鹦哥儿搭架”的掌故,还融会了中国文化精神,譬如中国民间的“乞巧”节,也讲究一个“度”字。唐代福建诗人林杰的“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就非常生动地记录了牛郎织女“渡河桥”的江南节日民俗。而据青海传说,七月初七这一天,人间看不到喜鹊,因为所有的喜鹊都飞到了天上,为牛郎织女搭桥去了,有了喜鹊的帮忙,牛郎和织女就能团聚了。未尝不可以说,“喜鹊搭桥”与“鹦哥儿搭架”的文化内蕴是相同的,是人们渴盼幸福、追求美好婚姻生活的文化象征。
将美人、鹦鹉、石榴并提的是元末的江南人张昱。旺扎勒镇守江浙时,任用张昱为参谋军府事,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旺扎勒死后,张昱弃官不出。朱元璋闵其老,厚赐遣归,张昱终老于西湖山水之间。张昱在《题鹦鹉仕女图》中云:
美人应自惜年华,庭院沉沉锁暮霞。
只有旧时鹦鹉见,春衫曾似石榴花。
这首诗将美人、鹦鹉、石榴花溶为一炉,通过刻画美人虚度年华,深锁闺阁,只为鹦鹉所见的情景,传递出作者壮志难酬的落寞心情。有趣的是,曹雪芹也在其《红楼梦》35回中通过鹦鹉传音,细致含蓄地表达了林黛玉的多愁善感。
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他怎么记了。”
林黛玉是扬州人,自父亲去世后,寄居贾府。除了老太太,没有别人可以依赖;除了贾宝玉,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所以常幽居闺阁,难以表露对宝玉的爱,惟有廊上那只鹦鹉与丫鬟紫鹃,见证了黛玉寂寞无助的闺阁生活。所以,鹦哥诵诗就显得别具深意了。“长叹一声”和“吁嗟音韵”,把林黛玉的无奈与悲情展露无遗;《葬花词》是宝、黛“草木之恋”的高潮部分,浓缩了林黛玉深深的情愫,而终成虚幻的爱情,却被紫鹃“难为他(鹦鹉)怎么记了”一句,把读者引向深层的思考空间,颇给人同情与怜悯之感。鹦哥传音一节,彰显了曹雪芹对中国仕女文化独特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从文化属性上看,曹雪芹笔下的鹦哥传音与张昱的《题鹦鹉仕女图》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鹦哥儿搭架”,绝不像刘凯所说的那么简单。“石榴花”是女性的象征;“鹦哥儿搭架”则是通向爱情终极目标的理想通道,是渴求美好婚姻生活的文化意象。这样一种文化意象,自元末明初之后,从江南传到青海,在“花儿”等民间文学中扎下了根,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作者简介:杨生顺(1973.10-)男,青海湟中人,青海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指导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中国古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