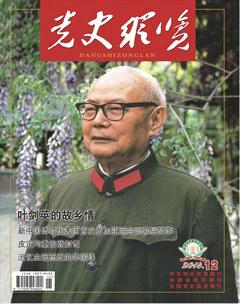一个战士的足迹——李清泉自述
李清泉



参加革命
1919年3月21日,我出生在江西鄱阳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李福喜,母亲汪清香,我们兄弟姐妹共7人。我们家开了一家名叫“同顺号”的鞋店,由于生意不好,一大家生活比较艰难。
我7岁时入学,念过私塾,也上过小学。我小时候喜好画画,全家人省吃俭用,在11岁那年,让我考入设在鄱阳城内的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艺术系学习。1934年毕业后,我考入江西陶业管理局附设陶业人员养成所。
当时的陶业管理局局长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杜重远,他是一位陶瓷实业家,为振兴景德镇瓷业,他在上海、南昌两地设考场录取品行端正、爱国有志的青年人,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思想进步、初步掌握陶瓷知识和技术、可以担负振兴陶业使命的人才。
景德镇管理局的职员和养成所的教员大多是东北沦陷后,跟随杜重远进关的进步人士,对养成所学员的思想影响较大。在这种氛围下,我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并和同学们一起在景德镇积极进行爱国救亡的宣传和社会活动,如举办工人训练所、开设露天讲演场、举行大众同乐会、唱歌、演戏、办壁报等等,搞得轰轰烈烈,经受了社会实践的锻炼。
养成所毕业后,我被分配在陶业管理局一个负责陶瓷设计和美术的部门当助理技佐。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个把我引向新的革命征途的人——陈毅来到了景德镇。陈毅是在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来到景德镇的。他会见了我们歌咏队的全体成员,讲述了卢沟桥事变后我国形势的深刻变化,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抗战的发展前景。陈毅说:延安固然是个好地方,但是全国的抗日青年都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当前最需要你们去的,是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到杀敌的战场上去!离景德镇不远的瑶里就有一支红军游击队。他风趣地说:愿意去的可以报名,我陈毅给你们当“红娘”。陈毅那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豪放的风度把我们这批年轻人深深地吸引住了。
当时,红军游击队改名为江西人民义勇军,在景德镇设立了办事处,主任为李步新。我们和办事处取得联系后,告别了景德镇,前往瑶里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瑶里是坐落在皖赣交界江西一侧的古老村镇,原分散在皖赣两省边界一带的各支红军游击队陆续到这里集中整编为江西人民义勇军第一支队。1938年初,江西人民义勇军第一支队正式被编入新四军系列,成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第三营。我们这批从景德镇来参军的青年被编入新四军一支队战地服务团。
1938年2月,战地服务团随新四军一支队二团第三营从瑶里出发,来到岩寺附近的潜口集中。不久,又随同陈毅前往浙西迎接新四军第三支队。在浙西之行的约一个月时间里,陈毅同我们一起行军、宿营,给我们讲革命斗争的经历和革命的理想信念。服务团一行每到一地都要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小戏,吸引了很多群众前来观看,每次演出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和徐上庸等二三个人还在服务团里担任画宣传画的工作,这些画有的后来被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选中,带回美国用作中国抗日募捐宣传展览。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领导机关需要充实人员,我被调到军政治部宣教部文娱科工作。1938年5月,我随军部离开岩寺,移驻泾县云岭村。
1939年,我被调到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任宣教科科长,不久又调到四支队九团担任政治处主任。遵照军部命令,四支队开赴舒城、合肥、巢湖一线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6月,部队挺进至淮南路路东、津浦路西,创建了淮南津浦路西敌后抗日根据地。这里地处敌伪顽与我方犬牙交错的地带,斗争复杂而残酷。皖南事变后,四支队被改编为二师第四旅,原来的九团改为第十一团,我担任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其间,经历了多次反“扫荡”和反摩擦的残酷战斗。
1945年7月,我调任二师兼淮南军区政治部宣教部长,参与和领导了反攻日寇、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的一系列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我调任华野二纵四师第十二团政治委员。
我和团长阮贤榜率领十二团先后参加了临蒙公路出击作战、孟良崮战役阻击战和南麻、临朐、莱阳、胶河等战役。十二团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战斗力进一步提高。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华野二纵是淮海战场的主力之一。在整个战役中,二纵能攻能守,善打阻击战,为保证兄弟部队围歼敌军起了重要作用,为围歼黄百韬兵团、截击杜聿明兵团等战斗取得的重大胜利做出了贡献。
淮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统一改编,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华野第二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一军,所属的四师改编为第六十一师,我被任命为第六十一师政治部主任,胡炜为师长、王静敏为政委,参加渡江作战。
突破长江后,我们六十一师从泾县以西地区出发,沿着皖南、浙北的崇山峻岭,冒着江南的梅雨,先占领杭州,随后解放溪口奉化。
溪口是蒋介石老家,部队对蒋介石怀有刻骨仇恨。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席及时发来指示:“在解放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我们迅即认真贯彻落实,对部队反复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强调蒋介石老家不但不能破坏,而且要很好保护。
六十一师军容整齐,雄赳赳地开进溪口。溪口镇镇长带着一些人举着彩旗在镇口欢迎我们。当晚,我和民运科长召集部分居民开会,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六十一师进驻溪口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丰镐房、蒋母墓等重要地方,派出部队看守,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溪口群众对解放军热烈欢迎,有的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有的说“大军纪律严明,对老蒋家什么东西都不动,我们老百姓还怕什么呢”。5月27日,六十一师奉命移师宁波附近休整,镇内群众夹道欢送。
1949年5月,浙江大陆绝大部分已经解放,国民党军残部退守舟山群岛,但敌八十七军仍盘踞在象山半岛,企图阻止或延缓我军对舟山群岛的攻击。为歼灭象山半岛残敌,六十一师由六十五师一个团协同向敌发起攻击,从7月3日至8日先后攻克宁海、石浦、象山等地。浙江大陆全境解放。endprint
象山半岛作战后,六十一师在象山地区休整。休整期间,我们抽调力量大力协助地方政权建设,开辟新区群众工作。此时,我由师政治部主任升任六十一师副政委。
8月31日,六十一师奉命归二十二军指挥,担负从南侧攻击舟山群岛任务。10月初,六十一师顺利攻占敌六横岛、虾峙岛,做攻占桃花岛的准备。
桃花岛是舟山群岛南侧的一个较大的岛屿,面积约30平方公里。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正在构筑工事,但防卫体系尚未形成。胡炜和我分析敌情,决心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攻占桃花岛,并得到军部批准。
18日晚,潮水初涨,风微浪低, 100余只木船乘风破浪一齐向桃花岛急驶。布置在虾峙岛上的我炮兵向敌阵地展开火力猛袭,各突击营的火力船也一起向敌阵地开火,一阵激烈的枪炮和手榴弹声后,部队全部登陆成功。到23日夜桃花岛之敌被全部歼灭,除毙伤外,共俘敌1300余人。战后,七兵团、二十二军、二十一军均来电嘉奖六十一师。
外交工作
1950年1月20日,我在桃花岛前线接到调令,被告知调中央分配做外交工作。
从军队工作到外交工作,是我一生中的一次大转折。进京后,我先参加武官训练班的学习,听取了许多负责同志的报告,周恩来总理还亲自给我们作了重要讲话。短期的培训,主要是学习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方针政策,学习包括外交文书、外交礼仪、外交程序的课程,还学习了跳交谊舞、吃西餐等西方生活方式。
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分配担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首席政务参赞。由于驻捷大使谭希林身体不好,经常回国养病,我长期担任临时代办,主持馆务。1959年4月,我被任命为驻瑞士大使,从此开始了在瑞士近7年的外交生涯。
新中国建立后,除英国、荷兰和我国有半外交关系外,其他西方大国都没有同我国建交。但在中法之间存在民间友好来往,也有一定的经济贸易关系。法国方面还有议员以及其他政界人士来华访问,主张增进两国关系。1958年戴高乐上台重新执政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反对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称霸和美国对西欧的控制。法国还联合联邦德等国组建欧洲共同体,力图在西欧形成以法国为核心的反苏抗美的第三种势力。戴高乐为实现其全球战略,除团结欧洲有关国家外,还需要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同中国的关系。因此,戴高乐上台后虽仍然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保持所谓“外交关系”,但是未接受台湾派驻“大使”,使双边关系维持在“临时代办”级的水平上。1959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提案时,法国投了弃权票,表明了与美、英不同的立场。
对戴高乐采取的独立自主政策,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在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左右国际局势的情况下,我国除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外,也希望进一步开展同西欧国家的交往,以利于争取更多的朋友,挫败国际反动势力反华的阴谋。
埃德加·富尔,法国激进社会党人,曾两度任法国政府总理。他和戴高乐关系密切,在法国政界有较高的声望,并同中法两国领导人都有较好的友谊。正因为如此,戴高乐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代表,来华同我国领导人商谈发展两国关系问题。1963年8月20日,富尔来到中国驻瑞士使馆同我见面,表达了再次访华、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推动法中两国关系发展的意愿。我即向国内报告富尔来访情况,很快得到指示,同意富尔于10月中下旬访华,让我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向他发出邀请,并和他商定访华的具体细节。31日,我到瑞士著名的休假地达沃斯富尔的住处,向富尔转达了张奚若会长的邀请。富尔夫妇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给予热情招待,对邀请他访华表示感谢,并立即由达沃斯返回巴黎。不久,他打来电话,告知抵华日期。过了两天,他又专程来到瑞士,告诉我他此次访华是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携有戴高乐给他的一封授权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亲笔信。因此,此次访华实质上具有官方性质,但对外只能说是个人旅行,希望保密。
富尔10月22日抵京,次日周恩来就与他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以后又和陈毅一起与富尔进行了多次认真、坦诚的会谈。毛泽东、刘少奇也分别接见了富尔。会谈中,富尔多次表达了戴高乐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法国绝不采取英国式的拖泥带水的半建交办法,如果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是,富尔又再三要求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交,不要使法国为难,而是让法国根据中法建交后产生的后果去处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考虑到中法建交对发展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以及反对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会谈中,周恩来在反复阐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也同意法方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当局断交的方案。具体步骤是法国先照会我国愿意建交并互换大使,我国复照同意,然后相约同时发表来往照会。在周总理运用高度原则性和适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引导下,中法建交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随后,中法两国就建交的具体事宜在瑞士进行谈判,我被定为中国方面代表。
富尔在北京同我国领导人会谈虽然是受戴高乐的指派,但他终究不是正式全权代表,因此,法国外交部部长派法外交部公使衔的欧洲司司长雅克·德·波马歇来瑞士同我方正式谈判。1963年12月12日上午,谈判在中国瑞士使馆进行。波马歇在会谈中说,中法双方都有建交的共同愿望,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主要是研究公布这一决定的方式。他提出:双方同时发表建交的联合公报,或者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并口述了一个公报内容的大意。我告诉他,将报告政府后再予答复。
波马歇所提方案同周总理与富尔商定的互换照会的方式有所不同。这样,法方可以不必首先照会我国,从而避免造成法方主动的印象,同时,这种方式也更符合法国在承认中国后不立即主动驱逐蒋介石“代表”的做法。对此,我提出了在谈判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及预案报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我直接飞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向正在那里访问的周总理请示汇报。见到总理后,因为谈判的所有情况总理都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很少提问而是要我复述一遍中央的谈判方针及设想的各种方案。在认为我复述无误之后,总理作了一些新的指示,然后要我把所理解的中央方针及各种情况下的处置原则及他的新的指示,综合起来写个报告给外交部。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报告给外交部,随后返回瑞士。很快外交部批准了我的报告。endprint
1964年1月2日下午,法方代表波马歇来使馆继续会谈。我按预定方案先表示:中法建交现在只是程序问题,如法方实质上坚持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为了照顾法方的困难,我们可以同意法方提出的方式及公报措辞。但是,中国政府将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说明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波马歇当即表示已经听清楚了,将把会谈情况报告法国政府后再答复。
根据这次会谈的情况,我估计下次会谈可以达成协议。为了避免耽搁时间,争取下次会谈一次成功,从做最周密的准备出发,我又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及相应对策报告外交部。外交部根据周总理指示报党中央批准后,给我发了关于9日会谈的新指示。
1964年1月9日,波马歇如约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他说法方认为中、法双方已就建交公报内容和发表方式达成了协议,提出在1月27日或28日巴黎时间12时,在北京、巴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对我国将单独发表声明一事,波马歇未正面表态,而采用复述我方方案的方式予以确认。至于公报发表的时间,我根据国内指示,提出在北京时间1:30或2:30即格林尼治时间17:30或18:30。法方解释说,法《世界报》每日下午3时出版,希望能及时在该报宣布建交消息,故提出在巴黎时间12时发表建交公报,希我谅解。我当即表示同意。这样,建交协议就达成了。根据国内指示,达成协议后不必搞会谈纪要,双方代表在公报的中、法文本上草签即可。对此,波马歇坚持认为无必要,我表示可以不草签,但是我将把协议内容报请政府最后批准。
在周恩来总理出访十四国胜利归来、在成都召开使节会议时,我又见到了总理。总理说:中法建交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时,你那点机动是对的。我知道总理是指我没有坚持双方代表在建交公报上草签,也没有坚持按我方的要求确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令我惊异的是,周总理在阅读有关谈判的报告时,是如此仔细,他抓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建交公报公布后,我国政府单独对外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领土割裂出去或者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在北京、巴黎同时公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成为新中国外交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法国是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大国,中法建交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
1966年2月,我奉调回国。3月4日,瑞士联邦委员会为我设宴饯行。联邦政府主席沙夫诺致词说:“联邦委员会和我对李大使的离任感到惋惜。李大使创造了一种谅解、友谊和越来越紧密的合作气氛。从两国的贸易数字,也可以看出你有效地完成了你的崇高使命。”出席招待会的有瑞士各界朋友、也有其他国家的朋友。他们祝愿“中国日益强大”,有的连连喊着:“团结,友谊!团结,友谊!”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1966年3月,我从瑞士卸任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不久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调查部也同其他部门一样乱了起来,负责人都“靠边站”。这时,周总理提名,经毛主席批准,调我参加中央调查部的领导工作。赴任之前,周恩来总理专门召集我和中调部有关人员到他的办公室,宣布我参加中调部的业务领导工作。可在我参加中调部工作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形势日趋恶化,我已根本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工作了,不久,本人也不得不“靠边站”了,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方才出来工作。
* * * * * *
1980年5月,我调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半年后当选为安徽省副省长,主要分管全省的外事、旅游和侨务工作。过去二师长时间驻淮南路西抗日根据地,我把安徽看成第二故乡。回到安徽工作,我十分高兴。
安徽和沿海省市相比,外事工作不是很繁重,但我认为随着安徽以经济为中心的各项建设的发展,外事工作也必须有相应的发展。我着重在民间外交工作和配合全国外事工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83年,我调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除协助主席管理日常事务外,主管文史工作。
1987年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为发挥余热,曾担任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学术研究会会长、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省及省直老年书画联谊会名誉会长等社会团体职务,做到了离休不离志,退休不褪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贡献了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吴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