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走水跳
吴柏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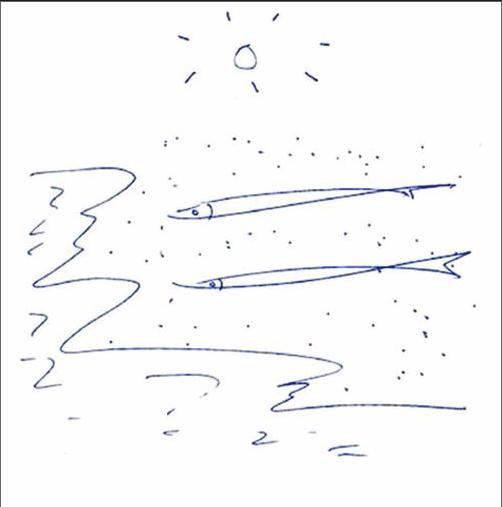
我对山水大抵是没有太多印象的,单是听爱出游的朋友说起罢了。我以为,水总是蒙着一层薄薄的细纱,终辨不清颜色。有的地方水是绿的,也有地方是蓝的。或蓝或绿,总是幽深莫测。山就显得更为陌生了,有人说高耸入云的山奇绝,有人说连绵不绝的山秀丽,所有的山都静静地立着。
颠簸上山,踩着渔网,闻着鱼腥,才知道是入了乡村。不知道太阳为何异常猛烈,好像头顶着炽热的火球,旋转燃烧。同行的人一路上嘀嘀咕咕的,大概是大城市来的。他们要不是抱怨鱼腥味太难闻,就是后悔大热天出来受罪。
我并不和他们一样想。旅游往往都是如此,享受的是过程,经历就是一种享受。譬如路旁的老树和攀缘的古藤就别有一番风味。古藤遮挡着斜斜而下的猛烈阳光,露着斑斑驳驳的圆点,稀稀疏疏地投落在行人的衣服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截断了顺序排列的点,却化生为浮动的错落有致的光斑,光影自然地铺展开来。
我忽然察觉到山竟不是青的。它不是一味地耸起或是柔情地连绵,而是片片山峦几欲断裂而又粘连在一起,山峰斜斜地偎依着旁边的山峦。没有异军突起,而是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和谐。我没能看见山的尽头在哪里,几处的山峰似乎汇成无解的裂谷,小浪潮冲荡其间,迸溅出朵朵俏媚的水花。好像在一瞬间,山无底洞般地沉了下去,恰好捧住那群相继绽放的水花,犹如无垠的田野上开遍了玉洁的百合。
爸妈都忙着拍照,嚷嚷着叫我一起拍,他们说旅游就是多拍照。而我不愿,径直往前走。年轻人以为旅游是来亲眼目睹风景的,或许中年人只想把美景保存在记忆里。他们沉浸在拍照的喜悦中,我只是一路向着山走,向着水去。
山间尽是简约的溪河,许多游人买了斗勺状的渔网,听说是来捞鱼的。
“这鱼捞不起来!”陪同玩的当地朋友不屑地说。
“为什么捞不起来?”
“来捞鱼的人太多了!”他叹了口气,“活下来的鱼儿早都成精了。它们见过的人比我们见过的多得多!”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优胜劣汰吧。望着河边尽兴捞鱼的人群,三四岁的小孩光着脚丫挥动着斗勺,渔网不时地打在水中的石头上;也有三四十岁的男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一旁的女人不时地尖叫着:“这儿有鱼,看,这儿有鱼!”但我发现散布在一个一个小石头上的小桶里大多没有鱼。看着他们忙活了一阵,究竟是捞不上来,但他们还是要捞,用的还是五彩斑斓的渔网。
我才不会这样傻傻地去捞鱼呢!
绕过成群的捞鱼者,我恍然注意到这儿的水,异于所谓的“蓝绿一体”。我似乎迷失了双眼,那好像打翻了的调色盘混合在一起的颜色让我无法相信。最远处是墨绿,直系着云天,那搅合在一起的天和水已难分清了,我想远处的水还在远处,天却离我愈近。淡淡的蓝在缓缓靠近我,那是一种淳朴和典雅的交融。还不知道为什么淡蓝色的水与天际相接如此地密,眼前的水确乎是灰白色的。浅浅的灰色笼罩在纯白的水上,我不敢相信,而那确实存在,像掺了芝麻似的牛奶正向前缓缓地流。双手轻轻地捧起水,远远近近,而终于不能采集到灰白的那片,我所能看到的灰白色的水也只局限于眼界,只能留在欣赏的这段时光里。
水灵动地变换着颜色,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淡蓝又交错着露出来,而这淡蓝略显灰暗,更趋于银黑的墨蓝。终于分不清哪儿是淡蓝,哪儿是银黑了。水在打着波涛,那潮儿很小,却愈打愈大,撞击在岩壁上、石滩上、赤脚上。贴在眼前的水确是或蓝或绿的,一会儿小浪潮打来是绿的,过会儿大浪潮打来就是蓝的了。或许太多的人关注的只是最近的那簇或蓝或绿的水花,忘了看看更远的淡蓝、灰白、墨绿了。
我不由自主地想去捞捞鱼了,那样和水会更亲密些。沿路往下看,溪河里的鱼确实不少,便多了几分自信。可一下水就见不着鱼了,苦苦地等待着,根本没有心思看水了。一旁观看的人不时地叫喊着:这儿有很多鱼,你看你看,很多呢!我便快步上前,终不见鱼影儿。好一会儿终于有条小鱼从我的眼前游过,我急忙扑上了渔网,可惜那网也不着边际地按在了石头上。几番折腾,连条小鱼都抓不着,只怪自己太愚钝,索性无获而归了。走几步就开始懊悔起来,如此长时间地站在阳光下暴晒却心甘情愿地狼狈而归。先前是谁在痴笑那些捞鱼者的无知?人生不也是像捞鱼一样?
我又开始望着灰白色的那片水出神。很小的时候,我很不屑整天端着相机的摄影师。大概是一次学校的演出,缺个拍照的人,老师以为我学得快,喊我去帮忙。他教了我一点摄影的技巧。没想到我就这样生了兴趣,还和同学赌气入了摄影这一行。我跟那个同学打赌在两年内拍出一张获大奖的照片。那些天我都早早地起床,反复掂量内容和角度,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获了一个小型比赛的一等奖。我把奖状拍下来,发给了那个同学。可获大奖实在难,虽然我每天都是分秒必争地思考,但是三年多了,我还是没有兑现承诺。
现在的我已经很少摄影了。我会静静地看着父母嘻嘻哈哈地玩着傻瓜机,做着不必细究章法的娱乐。我突然很想亲手拍下这山、这水。但我没有做,真实的山、真实的水只会出现在我的眼界里。就算我聚精会神地拍它们,傻瓜机也没办法把我心中的感觉点缀在这山上、这水中。
还有人置身于或高或大的山上,沉浸在或蓝或绿的水中,他们根本不能知道“山是会走的,水是会跳的”,也不会被说服。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产生错误的潜意识,就像钻进了深不见底的洞穴,他会学着生火取暖,却怎么也唤不出来。
从前的水无声无息地流过了,携着藏在心底的往事,奔向曾经牢牢记得的或高或大的山间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