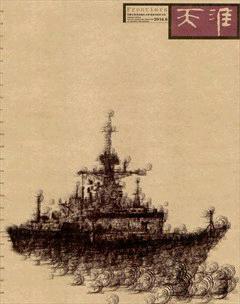大正时代日本知识分子制度观初探
谭仁岸
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1925—)曾在其《制度论》中提出,广义的“制度”包括“习俗、习惯、文化(包含语言体系或感性结构)等人类的无意识规范,亦即看不见的制度”,但本文使用的“制度”概念,主要宽泛地指称整体的国家政治制度。在前现代社会,制度一般被视为某种先验的、不言自明的、客观上优先于个体的宿命性存在,然而随着现代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变迁,人类个体逐渐脱离各种组织的身份性控制,开始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以自由选择为特征的“社会”慢慢压倒了以血缘结合为特征的“社区”。
众所周知,近代日本有过三次比较突出的制度性变更运动:明治十年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大正年代风靡一世的民主普选运动;二战后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民主改革。无论哪一次,都少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先行与鼓吹呼应。大正更是后来被直接冠以“大正democracy”、国民的民主意识迅速觉醒的时代,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高等教育普及、知识分子的启蒙活动皆有关系。各种关于制度的思想形态、国家论、社会论同台竞演,可谓步入昭和军国主义之前的一个短暂春天。此时的言论空间中,既有维护与保守天皇制的“天皇亲政论”(上杉慎吉),也有避开主权问题、直接诉求主权之目的与运用的“民本主义”(吉野作造);既有要求彻底的制度革命的社会主义(山川均),也有拒绝一切专政(包括布尔什维克独裁)的无政府主义(大杉荣)等等。有岛武郎(1878—1923,以下简称为有岛)作为当时知名度极高的畅销作家、一位影响过鲁迅与周作人的知识分子、一位深切关注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的思想者,也以自己的特有方式介入了关于制度变革的众声喧哗之中。
制度迫害观的萌芽
1901年,二十三岁的有岛入信基督教,1910年左右因对信仰产生根本怀疑,最终离教而去。对“形式”(制度)的抵触,早在他加入札幌独立教会、提出无须洗礼、免去晚餐仪式的建议之中便可略窥一二。后来有岛参军,逐渐萌生国家批判思想。在他退伍之后所写的《在营回想录》(1902年)中,有这样的激烈记述:“何谓国家?何谓对国之义务?……人与人相争,世人责之;企业与企业相争,世人责之;国与国相争,世人皆慎言沉默。何等权威国家,方可如此?退去吧恶魔!……所谓对国之义务,便是国家之命令。换言之,便要听从一个“无”的命令。……国家应喻为何物?粪桶之盖是也!世人积淀欲望罪恶于此,为掩其臭,遂以国为粪桶盖。”
有岛在此尖锐提出,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空虚的“无”。具体生命受制于一个空虚之物的命令和左右,在他看来显然是荒唐的。四十三年之后,丸山真男(1914—1996)发表其经典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伦理》,剖析日本国家主义在天皇制的绝对性笼罩之下,混淆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政治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后果。丸山的论述与有岛的“无”之体察有异曲同工之处:“日本在明治以后的国家形成过程中,从未曾试图表明国家主权的技术性、中立性性质。结果,日本的国家主义总是要在某种内容价值的实体上,安置自己的统治根据。”显然,两者都看出了国家的虚构性。不同的是,丸山重在解构附着于国家之上的某种“内容价值”,而有岛的国家批判更多是感性的全面拒绝。
丸山另外指出,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与“自我”成长过程发生联系的仅限于“生活世界”、“社会”、“家庭”,但由于天皇制的隐蔽性和整体性,国家这一维度反而脱落了。所以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等白桦派作家的“反社会主义”和“反权威主义”,仅是“不理睬强权”的逻辑,但“不能直接把对国家的‘无视’或‘轻蔑’等同于对国家的批判态度”。相对而言,丸山比较认可有岛,认为与其他白桦派作家相比,他具有相对冷峻的国家认识。
然而,有岛的不足却也很明显:“(这些批判)没有超出基督教常识。反过来说,当时他的洞察之中,完全没有立足于社会科学认识的现实分析,纯粹是伦理性的批判。”(安川定男《有岛武郎论》)亦即有岛尽管在白桦派作家中仿佛卓然迥异,但其实并没有高出太多。从上述引用也可看出,有岛虽然在国家批判的勇气与先驱性方面值得尊敬,但其中确实缺乏厚重的学理,更多是来自于某种敏感于压迫的青年的正义感。
正如丸山所言,对国家的条件反射性厌恶,与对国家的理性认识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容易转化为对权力的隐士式逃避,停留在封闭的自我满足和道德陶醉里面,而后者才能开启更多公共的政治参与路径。
二十世纪初期,可能很少有思想家像马克斯·韦伯(1864—1920,正是有岛的同代人)那样,对试图以主观伦理来超越现实制度之恶的倒错进行了如此痛切的批判。他在《作为职业的政治》里面,严格区分了伦理与政治的功能:“就连古代的基督徒也清楚知道:这个世界是由魔鬼们统治的。参与政治的人,亦即与作为手段的权力或暴力发生关系的人,也就与恶魔签订了合约。而且,对于他的行为来说,善只会导致善、恶只会导致恶的那种情形并非真实,其反面往往才是真实。谁若看不到这点,他便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幼童。”为了把高谈爱或善而搁置手段之暴力问题的“信念伦理”相对化,韦伯对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提出了更加现实、顾及政治后果的“责任伦理”。他所说的“伦理与政治”,在本文中可置换为“伦理与制度”的问题。此时的有岛,显然在这一价值冲突中,处于“伦理”一方。从他对国家的激烈诅咒之中,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他对制度禁锢的绝对排斥态度。
迫害的永恒循环论
1921年11月11日的《读卖新闻》刊登了有岛的一篇谈话录《宛如绝缘之电》。记者询问有岛关于日本的“平民宰相”原敬(1856—1921)被刺杀事件的看法,对此,有岛回答如下:“我现在对当前政治可以说毫无兴趣。也许是因为,本来我对政治问题也给不出什么专业意见。但我觉得理由并非只是如此。现在这个国家所进行的政治,实际上和我的生活并无太大关系。开设国会也好,有了选举也好,内阁更迭也好,对我而言,听起来并非什么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我变得如此冷淡,是我自己的责任还是政治家的责任,只能交给他人判断了。总之,我对这些提不起兴趣乃是千真万确的。”
日本政党政治的真正确立,始于1918年原敬内阁的诞生。原敬暗杀事件实际上有点类似于中国宪政先驱宋教仁之死,已经反映了威胁日本政党政治的某种退步征兆,然而,对这种使用体现个人“自由意志”的暗杀手段直接破坏制度的行为,有岛没有任何评议。从他对政党政治、民主选举的淡漠来看,政党政治与他心目中的理想个体、理想生活是无缘的。
同年11月19日的《夕刊时事新报》上,有一篇有岛的《关于军备削减问题》的谈话笔记。有岛如此批评当时在华盛顿召开的裁军会议:“他们还是从肯定既存国家制度的前提出发。为了既存国家本身的膨胀而牺牲个人自由与权利。”他警告说,削减军备无非是国家主义的意图表现,不可被其欺骗,然后提出的对策是:“我必须以绝对的无视,回应他们的企图、思想、事业。一旦关心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增强他们的力量。”
从以上资料来看,当然不能说有岛对制度问题完全不关心。但他的关心以“彻底拒绝”的姿态呈现,并没有对制度本身进行更多的探寻。在他看来,似乎只要闭目无视既存的现实制度,便可防止个人自由与权利遭受侵害。这种“与政治完全断绝关系,在政治圈域之外,构筑一个包围政治的其他世界,以此取消政治本身”(大泽正道《石川三四郎论》)的思考路径,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有岛显然深受影响。
有岛关于制度的直接发言,记载在一篇题为《关于惠特曼》的演讲词里。1921年3月,有岛受东京帝国大学的社会主义学生团体新人会的邀请,赴会演讲。这是个关于诗人的演讲,而有岛却偏偏意味深长地先从人性、制度问题谈起。他首先提出,人类之中“先天”地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主义者”,亦即“为了自己信奉的主义,宁死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另外一种恰是与惠特曼相似的“浪荡子”。浪荡子不像主义者或理想家那样具有清晰的思想轮廓,他们不受制于某种唯一的价值,而是以自由为最高目的的不羁游荡者。
主义者为了贯彻自己的理想,要为社会创建“一个制度约束,亦即institution”,他们往往会产生一个倾向:“根据自己的理想,为人类生活设计某一外部规范,然后把该范畴套入所有人的生活,把生活的多种趋向统合为单纯一致的状态。”(前掲《有岛武郎全集》)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必须毫不留情地破坏、改造既有制度,因此,主义者在其事业初期,必然受到既存制度的迫害。
但是,当主义者获取胜利,以制度形式彻底推行自己的主张、统一社会生活时,“过去曾被不断迫害的主义者,遂成为自己所建筑之理想的开山鼻祖,成为某种人类生活的支配者。不仅是主义者如此,制度本身也将成为支配者。”(前掲《有岛武郎全集》)
换言之,有岛认为,制度的僵化、异化,不仅导致新的压迫,甚至会反过来控制制度的创立者。接着他进一步描绘主义者转化为迫害者的过程:“制度一旦被建立,便开始拥有对自身的执著,会抵抗任何来自外界的压迫,或者征服外界的压迫、谋求自己的存续与繁荣。因此,曾经处于被迫害位置的主义者,在实现自己目的的同时,自然会站到统治者立场上,露出迫害者的面目。因为唯有如此,才是对自己所尊奉之理想的最忠实态度。……一个制度(不管是何种制度,终究是主义者聚集而建)一旦形成,最终都会导致某种形态的迫害产生。不管这种制度建立在多么人道的理想或主义之上,只要其存续,随着这种存续的强固和有力,必然产生对他者的压制结果。”(同上)
显然,在有岛看来,主义者从“制度受害者”到“制度加害者”的身份转换,是历史的一种永劫循环。事实上,这一判断建立在他的基督教史认识上:作为被迫害者的初代基督教徒,最后成为迫害异端的罗马天主教会;被天主教会迫害过的英国国教后来迫害清教徒;逃亡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后来又迫害“异端”托马斯·潘恩——有岛痛切地看到,这一可悲的“受害者—加害者”之间的转换,通过制度的绝对化、凝固化,不断在历史上重演。他明确宣告,自己“对作为制度的宗教毫无同情毫无共鸣”。连标榜无私之爱的基督教都如此不宽容,更何况以暴力作为后盾的政治制度?于是,有岛如此断言:“我相信,只要是被冠以制度之名的东西,我这一想法完全适用。无论是国家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绝无例外。”
这种“迫害之永恒循环”的制度观,首先从宗教史导出,然后通过把“主义者”等同于“原教旨主义者”来完成其架构。对这种“价值一元化”的恐惧和抵触,来自于有岛身上强烈的“流动化”冲动。这种以刹那体验为追求的流动化冲动,与大正时代流行的柏格森生命主义哲学互为表里。“主义者vs浪荡子”的二元对立,在有岛那里成为支配性的思考模式,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逻辑跳跃和事实误判。例如,在所谓主义者中,既有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尽力固定制度的保守主义者,也有永不满足现状、不断破坏自己创建之制度的激进主义者。毋宁说,后者那样的“永恒革命者”,比起“浪荡子”更加敏感于制度的僵硬,并且轻蔑制度的公共约束力。而且,不同于仅停留在文化或思想层面的“浪荡子”,他们常常毫无忌惮地把社会政治生活从安定状态拖曳到过度疲劳的动荡状态。
“主义者vs浪荡子”的分类,反映出有岛的制度理解的重点,并不在于作为形式的“规则”,而是在于运营制度的“主体”。他严厉批判企图用某种单一制度来全面介入人类生活的乌托邦设计论,但在他眼里,通往救赎之路的,却只有游离于制度外部、永受制度迫害的孤独的自由人。
如何摆脱迫害的永恒循环?
有岛这种“反制度”观,当然与他所呼吸的时代空气有关。例如与其有过交往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运动家大杉荣(1885—1923),便激昂地批判各种现代制度的虚伪:“历史是复杂的,但有着贯穿这些复杂的单纯。例如征服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古今一切社会,必有两极:征服者阶级与被征服者阶级。……社会进步了,因此征服的方法也在发达。暴力与欺瞒的方法,组织得愈发巧妙了。政治!法律!宗教!教育!道德!军队!警察!法院!议会!科学!哲学!文艺!其他一切的社会制度!”(大杉荣《征服的事实》)
就像有岛从一切制度之中发现了“迫害的事实”一样,大杉也从一切制度之中发现了“征服的事实”。两者基本上都在强调制度的恶之属性。不同的是,有岛把所有制度都视为同质性的东西,制度变换颇类似于王朝更替,但王朝赖以存身的结构却是“超级稳定”的:不管任何制度,总会产生排斥少数群体的暴力性效果。而大杉作为社会主义的激进理论家,则认为一切制度皆不过是权力者的统治工具而已。
无论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图景,他们提供了何种抵抗方法?有岛把希望寄托在他的理想人类“浪荡子”那里:“他有时候被目为国家组织的破坏者,有时候被视为民主的主张者而遭到排斥……浪荡子在任何社会任何地方都会蒙受迫害。若没有外界迫害,他便自己迫害自己。”(有岛武郎《独行者》)
换言之,除了学习“浪荡子”永远的叛逆精神,同时保持对制度之恶的警惕以外,人类并没有办法从迫害的轮回之中解脱。
“浪荡子”形象对应着有岛描述过的生命最高形态“本能生活”,但是这种乌托邦想象乃以绝对自由为基础,在不得不接受社会历史条件约束的人类生活之中,只能起到望梅止渴的效果。而且,很多时候对瞬间的、绝对的、永远流动不居的社会形态的追求,反而吊诡地助长了制度之恶,这可能又是简单否定俗世政治生活的有岛所意料不到的。
与有岛通过自我生命力来对抗制度之恶相似,大杉用于对抗“征服之事实”的,也是“生命的憎恶和扩张”:“在这里,生命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诞生对那种征服之事实的憎恶。憎恶必然催生叛逆。新生活的要求必然发生。人上不存在人之权威,自我主宰自我,自由生活的要求必然发生。”(大杉荣《生命的扩充》)这种玄秘语调,同样是伦理性的。叛逆之伦理对于大杉而言,同时还是审美:“我在生命扩张中发现生命之至美,只有在叛逆和破坏之中,才能看到今日生命的至美。在征服之事实达到顶峰的今日,和谐已非美,只有狂乱才是美。和谐是虚伪的,真实仅存于狂乱之中。”因为制度意味着秩序与和谐,故搅乱秩序便等于打倒制度,真善美在此仿佛浑然一体;制度问题,成了一个哲学上事关存在的问题。
有岛与大杉,在思考如何超越制度性压迫时,并没有提供更多现实的制度手段,而是试图提醒人们,一切制度之恶的背后,总有人性的固执和弱点在作祟。他们深信,能够抵抗制度的自我目的化(异化)的,依然是强大、独立、自由的自我生命,而不仅是大正时代的其他关键词“民本主义”或者“宪政”等等。大正时代,依然处于明治时代的家父长制度阴影的笼罩之下,尽管个人主义抬头,但前路依然障碍重重。这个时代,人们患的是以赛亚·柏林所说的“密室恐惧症”(鲁迅的“铁笼”意象亦是如此),还不是后现代社会的“旷野恐惧症”,他们对禁锢的恐惧远远超过对王纲解纽、秩序混乱的“失范”状态的担忧,这正是有岛他们所面临的生存性境遇。
关于制度的自我目的化,有岛的朋友、另外一个思想家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不经意地从不同角度回应了有岛的担忧。他在1921年刊行的《现代国家批判》中指出:“制度不是生活的抽象理想,而是生活的具体手段。”“基于意志目的的生活追求,乃通过运营社会生活的个人所构成的集团来实践,这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生活组织便是‘制度’。个人在制度之中,试图实现他所意识到的生活目的。家庭、寺院、工会、结社、学校、政党、军队、自治团体、国家等,都是自觉的人类,为了达成其意志目的而存在的集体组织,应该在‘制度’之名下同列并存。”在他看来,制度并非固定的无机物,而是根据主体意志可以改变的东西。而且制度必须与人类实际生活保持灵活而密切的关系,否则,一旦离开具体生活,制度便成为观念,反而自我目的化,变成监控个人生活的强制性力量。所以为了把制度从观念拉回到现实里来,长谷川强调,必须让制度与实际生活保持良性的接触。因此,通过与制度、国家生活的有机性联系,自然会产生广泛的公共精神与健全的市民主体。可见,长谷川的制度论虽然也涉及阶级问题,但总体而言,他的思考属于如何重建制度与实际生活之和谐的范围之内。这点与有岛、大杉对制度的凛然拒绝,差别颇大。
虽然有岛在《关于惠特曼》的演讲中,毫不吝啬地赞扬了主义者对人类社会进步所做的巨大贡献,但他认为制度迫害的不断循环、无限扩大依然是不可避免的。他一方面对制度作为压迫工具的加害性极度敏感,另一方面却又忘却或轻视了制度作为反权力之媒介的有效性。
与有岛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1876—1936)在其大作《政党政治的社会学》中,提出过著名的“寡头铁则”:民主主义离开组织不可能存在,但任何组织却都天然具有“寡头化倾向”。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如果不把权力集中在顶层少数者的话,就难以维持组织——国家、工会、政党、教会——的有效运转。但是,这一过程中,组织指导者在知识教养、行政能力、宣传资源方面逐渐与一般成员拉开距离,统治权力便随之加强。一般成员做决定时,不得不愈发依赖指导者,又反过来强化指导者的地位。在米歇尔斯看来,这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两难问题。
但是,与有岛的绝望相异,米歇尔斯依然对民主主义制度的免疫力和反抗能量充满希望:“寡头现象的历史必然性,绝非意味着民主主义者应该放弃与其的战斗。我们的某些旧同事,不久必然会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指导者’。但是如果放弃对他们的规制,且从一切政治活动中抽身而退,那么不仅会给对于任何社会阶层都必须的‘组织’带来损害,而且还会产生强化指导者权力的意外后果。”
米歇尔斯在深刻认识组织/制度之原罪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通过组织/制度进行抵抗的重要性。历史也在证明,虽然历来遭受各种指责,但利用权力分立的制度来防止制度的作恶,已是宪政制度的一个客观成果。
制度迫害的两张面孔
有岛与大杉的制度怀疑,无疑在大正年代构成了对制度僵固和制度异化的有力反省与批判。直到今天,在制度压迫越发隐秘的情况下,如何彰显被各种标榜“民主”的制度所排斥的少数派,如何使用阶级视角来暴露各种同质化、均一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依然是不断需要叩问和实践的新课题。在此意义上,有岛和大杉关于迫害、征服的问题意识永远不会过时。
而且,有岛对人类做出的两种理念型分类(主义者与浪荡子),客观上已经在提醒制度原教旨主义者:人类个体如此不同,制度必须考虑具体生命的多样性,而非暴力切割、裁断、规制社会生活。如果说长谷川批判了制度形骸化之后与实际生活的脱节,那么有岛更担忧的是制度对生活的过分嵌入。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有岛所警惕的制度,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后来被称为“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的政治制度。极权主义制度不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从审美、信仰、语言到服饰、身体、生育,全方位地介入、管理、控制个人生活。这确实如有岛所指,乃诞生于一种“价值绝对主义”之中。但有岛虽然看出制度之恶来自“价值绝对”的无限侵略,却忽略了还有一种制度之恶来自于“价值虚无”。当一切事物脱离了价值,只受到赤裸的现实利益、权力斗争支配时,制度才真正会堕落为执行者的统治工具。此时,即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道德律,也会被扭曲为攻击敌手的武器(只要强行把对方解释为“非人”的“牛鬼蛇神”,即可随心所欲地“施”给“它”了)。
绝对价值和一元制度笼罩人类所有生活的时候,其危险毋庸赘言,但价值虚无所导致的制度沦丧,同样可以陷人类于灾难之中。有岛过度憧憬无媒介、无条件的自由,反而忽略了只能依靠制度才能从制度那里夺回自由的现实限制。同时由于缺乏对制度性迫害的具体分析,也就难以导出具体的抵抗性、建设性策略。倘若走上了与制度互不干涉的方向,剩下的路径便只有两条:要么开展恐怖主义式的制度破坏,要么被迫从公共领域撤离,退回到自欺欺人的“内部自由或灵魂自由”。当然,所谓不干涉本身,其实已是另一种隐秘的政治立场。在大正时代,众多知识分子投进了民主和宪政的激烈讨论,加入护宪运动的行列,不再视国家制度的存在为不言自明的神话,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意义与效用的不懈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