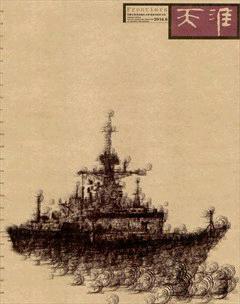我有这样一个父亲
张琪利
我的父亲是2005年6月9日因病去世的,父亲的一生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多。我想只要能够写下来,哪怕只是一些零星的记忆碎片,对我自己都将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慰藉。
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威严的神态始终伴随着他,偶尔有过一些微笑,也都是那种严肃的微笑。父亲是那种典型的内热外冷的人。
在我孩童时期,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个神奇的人,是我极为崇拜的偶像。父亲脾气有些暴躁,敢说敢作、敢为敢当,不管与己是否有关,颇有绿林好汉的风范。父亲到了晚年之后,虽然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但已经看不到他再为什么不平之事而火冒三丈,看不到他再为什么难容之事而大发雷霆。他已经完全是一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慈祥而善解人意的老人。
一
父亲是1943年参加革命的,那时候村里过队伍,我父亲背着我的爷爷、奶奶,偷偷地跟着队伍跑了,从此参加了八路军(父亲在晚年时,曾多次对我们坦言,那是他一生中对父母的最大不孝)。父亲在世时经常说那时每天都在打仗,但没听说参加过什么著名的战役。日本战败后,又与国民党的军队打了几年仗,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等。全国解放后,又跨过了鸭绿江赴朝参战,后来在朝鲜战场上负了伤,左手拇指被打掉,身上留下了几个弹片,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据父亲自己讲,掉一个手指头根本算不上什么残废。可组织在评定时,硬说属于断肢范围,按评定标准应划在一等残废之列,父亲也只好接受了。抗美援朝结束后,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县法院当了一名普通干部。父亲一生没有上过正式学堂,是到部队以后扫的盲,掌握了一点文化知识。父亲天资不笨,他告诉我们说,那时候部队的官兵很多都是文盲,他在那些文盲当中,属于佼佼者,扫盲过程中他是出类拔萃的,其学业成绩是最好的。这已经无从考证了,但从我记事时起,我知道父亲的字写得工整秀丽,非常漂亮。他的文章也写得语句通达,没有废话。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党有着深刻、朴素、醇厚、诚挚的感情。他的一生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神,只信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也是在他老人家的影响下,我过了十八周岁就积极争取加入了党组织。记得那是1973年的秋季,当他得知我成为了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之后,欣喜若狂,其反应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好像我做了一件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当晚对着我拉开了话匣子,把我教诲了半宿,什么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啦,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分清敌我啦,什么清正廉洁、甘愿奉献啦等等。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家人在一起,谁也不敢对党组织有丝毫的不满言论,那怕是丁点抱怨也不行。如果那样定会导致他老人家大发雷霆,定会闹得全家不得安宁。父亲对毛泽东主席的感情,那真是比天高,比海深,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嚎啕大哭,是因为毛主席逝世了。那不是一般的哭泣,而是那种撕心裂肺般的痛嚎。紧接着他老人家生了一场大病,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让我们全家人着实紧张了一阵子。在我印象当中,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变得有些寡言少语,经常拿着《毛泽东选集》在翻弄,还时常对着毛主席画像发呆。我的爷爷、奶奶去世时我都经历过,实事求是地讲,我只是看到父亲掉了几滴眼泪,我没有看到父亲有过如此深痛的悲伤。
父亲一生仗义疏财。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直接定为行政19级,每月六十多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的确是很高的了,同事们大多是三十多元。每当月初发工资时,父亲总是找到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同事,给这个十元,给那个五元,最后落在自己手里的所剩无几。父亲在离开部队时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国家每月都要发给固定的补助金,金额相当于普通干部一个人的工资。父亲在有了固定的工资级别后,坚持要向国家退回残废金,理由是仅仅没有了一个大拇指,干什么都不耽误,何必每月要领这个钱?刚开始组织告诉他,这是政策,不允许拒收。可是父亲还是不肯罢休,后来几经周折,父亲把残废金作为永久性党费一次性捐献给了国家,自此才算了结了他老人家的一桩心事。父亲从朝鲜战场转业到地方工作时所定的工资级别,直到他离休回到农村老家时始终没有变过,不是没有赶上涨工资,而是每次涨工资时他都会早早地与领导打招呼,逼着领导把他从涨工资的范围内去掉。他说同事们比他的工资都低,涨工资的事让给工资比他低的同事。就这样,工作四十余年,父亲没长过一次工资。
二
父亲当年曾担任过县法院法庭的庭长,法庭的每名干部配发了一辆自行车,用于公干,父亲规定,配发的自行车只能用于公事,私事一律不准动用。父亲的一位同事讲,由于是你父亲规定的,大家也就没有多少怨言了,因为你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对自身的要求比谁都严格。这让我联想到一件事,那就是父亲在担任法庭庭长时,我到父亲办公室,父亲让我到商店给他买包香烟,我出了办公室后,见到父亲的自行车停在门口,且没有落锁,便骑上自行车去把香烟买了回来。回来后让父亲整整训了我一个多小时,反复告诫我,买香烟是私事,私事是不能动用公家的自行车的。
记得我第一次挨父亲的打是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工作的法院旁边有个小礼堂,晚上在放电影《上甘岭》,连放了几个晚上,头天晚上父亲领着我去看过,但我没有看够。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了小礼堂门口,里面已经开演了,枪炮声不断,真想进去看,可五分钱一张票,我又没钱,只好在礼堂门口转,礼堂传出来的声音诱惑力太大了,我终于忍耐不住,瞅准看门收票的那个叔叔不注意,一头钻了进去。这可闯了大祸,等电影散场回到家里,父亲二话没说,劈头盖脸地砸了我一顿,当即打得我鼻青脸肿,打完之后告诉我,你这是偷窃!这还不算完,第二天晚上又给了我五分钱,去重新买了张电影票,父亲领着我当面补交给了看门的那个叔叔,并让我做了一番检讨,此事才算了结。还有一次,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天放学后,我到了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不在,我看到父亲的办公桌上有几张空白的信纸,便在信纸上写起了作业。父亲回来发现后,罚我站了两个小时。理由是信纸是公家的物品,个人岂能随便占用?并训诫我:这样的行为同样属于偷窃,小时能偷一张纸,长大就敢偷一叠钱;小时能偷一根针,长大就敢偷一桶金。当时我感到很委屈,因为我一丁点偷的意念都没有,怎么能说成是偷呢?
父亲属于抗战时期的老兵,离休回家后医药费全额报销,医院给他配备了一个小药箱,里面放置了一些感冒冲剂、去痛片、创可贴之类的常备药品。有天晚上,我母亲突然犯了头痛病,这是母亲的老毛病了,能立即吃上一片去痛片就会好些。母亲便让我父亲从他的小药箱内拿一片去痛片给她吃,被父亲一口拒绝,母亲当即承诺第二天一定到医院买了还给父亲,父亲依然是不答应,为此老两口吵了起来。父亲的理由很简单,我母亲的医疗费用是自理的,不能报销,而他药箱里的药属于公费的,借他药箱的药品就是想占公家的便宜。
在六七十年代有句话曾经很流行,就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当年对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不甚明了,可当我把这句话与父亲相联系时,才有所感悟。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确很是特殊,特殊得让人难以理解。
三
我于七十年代初参加公安工作,开始在一个沿海的派出所当民警。父亲办理了离休以后,主动申请回到了农村老家,老家离海较远,很少能吃到海鲜,所以每当我回家休假时,都买一些海鲜带回家。刚开始父亲就给我立下了规矩,我每次回家所带的鱼虾等海产品,必须要有购买的发票,否则不准带回家。我知道父亲是担心我利用职务之便向渔船索要或者接受渔民的送礼。因此我也严格按照他立下的规矩去办,每次我回家带的海鲜及其他物品,都一一备齐发票,回家后给他过目。因为我知道,假如没有发票给他过目,就是把海鲜做好了端到他的面前,他也不会动一筷子的。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爱做事,爱管事,特别是爱管闲事。父亲离休前曾做过很多年的民事调解工作,对邻里之间的疙疙瘩瘩、房屋土地的确权归属、老人赡养问题、红白喜丧之事、婆媳兄妹纠纷等等,平衡调解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时间长了,在父老乡亲中就有了权威。无论什么样的矛盾,只要是他定的调子,绝大多数都会按照他定的调子去解决。偶尔个别人不理他那一套,他脾气暴躁的特点便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了。他曾经打了村里一个不孝逆子好几个耳光,但乡亲们对他就是很服气,因为他讲道理,替弱者说话。
我在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以后,时常提醒自己别忘了普通一兵的本色,这种不敢忘记,其中很大的成分是怕因此引起父亲的不高兴。但还是有一次,父亲把我搞得当场下不来台,场面极为尴尬。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我刚担任县公安局的副局长,那年县公安局刚买了辆前苏联产的黑色伏尔加轿车,我和同事们一起坐着那辆车去办案子,时近中午,办案地离我家很近,我就和同事们一起来到家里,想让我母亲给我们做顿午饭吃。车就停在我家门口,那时轿车很少,在农村就更少见了,很快就围上了一些老人和孩童观看,恰在此时,父亲从外面回家了,一进门就愤怒地指着我训道:“你把那个东西停在门口干什么?你不嫌丢人现眼吗?以前国民党的军队谁升了官都回老家显摆一下,你是不是也学的那一套?”我知道父亲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如果继续待下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急忙带着我的同事们离开了家里,搞得我的同事们都很难堪,我就更难堪了。从那以后,连续很多年,我回家时从来不敢把车停在家门口,很多时候都是司机把我送到村头,我再步行回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轿车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为止。
父亲对我们子女家教很严,历来都是疾言厉色,不论遇到什么事,都是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要发脾气的时候,谁也甭想阻撞拦。好在家人天长日久也都习惯了,没有人故意与他对着干。可有一次,我终于与他老人家对着干上了。那是九十年代初发生的一件事情,我父亲一生喜欢喝酒,但都喝的是那些低档白酒,当地酒厂生产的地瓜干老烧之类。我那时滴酒不沾,平时人情往来有瓶好酒我都存起来。有一年的春节,我把积攒下来的十多瓶茅台、五粮液等高档名酒全带回了家,目的是想让老父亲看见后高兴一番,没想到老父亲见后一连串的质问对着我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档名酒?这是从哪里来的?这需要多少钱啊?这是正道来的吗?”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对我父亲这一连串的质问没有正面回答。父亲见我始终没有回答,便坚决地说道:“把这些酒拿走!像这样不明不白的酒我不喝!”这次我终于忍不住了,憋在胸中的委屈一下子全爆发了出来,瞪着父亲说道:“老爸,你儿子也是将近四十岁的人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儿子心里有数!你能不能施舍一点信任给你儿子?信任是最起码的尊重,你是不是也应该给你儿子最起码的尊重?至于这些酒,你想看发票,没有。这都是我平时一瓶一瓶积攒的,是儿子拿回家孝敬你的,你愿喝就喝,不愿喝就扔到大街上吧!”说完我抽身离开了家中。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当面顶撞父亲。从那以后,父亲很少再过问我的事情,再也没有因为我带了什么东西回家而向我索要发票了,脾气也改变了很多,很少看见他老人家发火。也许他老人家感到他的儿子真的长大了,再不需要他过多地操心费力,也许他一下子感到自己已经到了古稀之年,闲事莫管,应该颐养天年吧。总之,从那次以后直到他老人家去世的十余年间,父亲彻底改变了自己。虽然观点依然明朗,但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强求别人必须遵从,父亲已经由一个强势老人,变成了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
父亲性格上的改变,让我想了很多,我总感到是我的顶撞,给父亲造成了伤害,迫使他老人家不得不改变自己。这对一位古稀老人来讲,确非易事。父亲的这种改变,让我隐隐感到心痛,不时地激起我对父亲的负疚和歉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