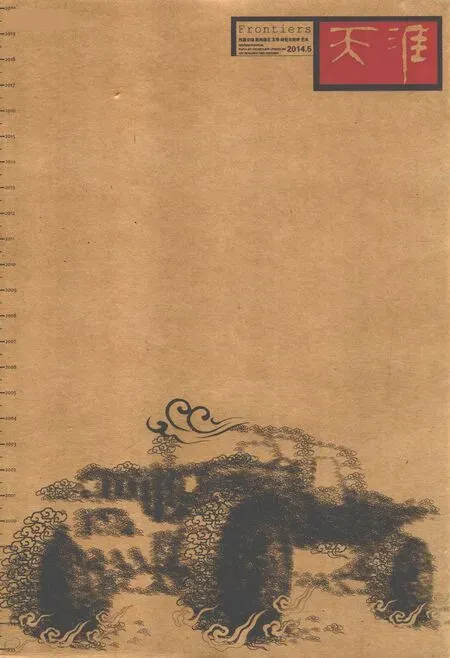菩提钟
王保忠
菩提钟
王保忠
这个区的文化馆,坐落在一条不起眼的街道,卑微、安静,与世无争的样子。按说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活动中心,可因场地经费的问题,一年到头就做不了几件事,还不如同一条街上的慈云寺忙碌些。那寺院没几个殿堂,主持也一大把年纪了,做事却极讲规矩,不说别的,光每日的早晚钟,细听,就知道没一下是偷懒的。或许是受了影响,老周坚持每日来馆里坐班,有事做事,没事也会守着看看报,练练书法。搁在面前的电话,有时会象征性地响几声,更多时候却沉默着,不吱一声,好在老周也习惯了,不会认为是出了故障或欠了费。但今天好像有些不同往常,他一进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稳,电话铃便啦啦啦地响了起来。
“是周同志吗?”一个陌生的南方口音问。
“是,我是周广远。”
“周广远同志你好,这是最后一次通知,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一直未领取。请你在下午四点前到市中级人民法院……”
“够了。”
老周咔地挂了电话。这种诈骗手段他早听说过,心想跟我来这一套,你也太小瞧人了吧。办公室有些憋闷,老周起身推开窗子,嘈杂声立刻从纱窗眼硬硬地挤了进来。对面那家卖电器的商铺在搞促销,引得街上开了锅似的,人声鼎沸。铺门前新搭的台子上,一个女的在扭来扭去地唱,唱一会儿便拿起一个电饭煲说话。老周眉头由不得挽了个疙瘩,赶紧推上了窗子,刚坐下,电话忽又啦啦啦地响了起来。他怔了怔,接起来一听,是文化局办公室主任,说各家的捐款都已交齐,就剩你们一家迟迟不动,局长问你还想不想当这个馆长了?老周这才记起有这么回事,是给正在扩建的区中学捐款的,据说这是区主要领导的意思,上周局里还专门开过会,但他对此类事一向很反感,所以也不管这是哪一级的号令,没作安排。局办主任这一催,他说好好好,我这就再动员一次,尽快把任务完了。说是这么说,放下电话,老周就再懒得去想了,对不想办的事,他的主意就是拖,事怕三疲,拖一拖就过去了。文化馆这么不起眼的单位,没人硬盯着,也犯不着打肿脸充胖子。至于他头上这顶帽子,什么时候想拿去就拿去呗,反正一两年他就退休了。
现在,老周开始琢磨另一件事,他打算在清远镇建个文化活动中心,真要做成了可以示范全区。几天前,他和那个镇的书记碰过头,对方应承得很好,可他心里却一直悬悬的,害怕这件事又会流产。正想着怎么再去落实一下,办公桌上的电话又啦啦啦响了,老周心里就犯嘀咕,怎么今天接二连三地有人找他呢?接起来一听,这回是书协秘书长邱平。
“老周,”邱平在电话那头说,“有个年轻书法家,专门从厦门那边赶过来向你讨教,你看是不是接待一下?”
“专门?不对吧,我有那么大的名声?”老周笑了笑。
“笑什么?他真是慕你的大名来的。”
“那也不行,我还有事,得马上去一趟清远镇。”
“老周,这个年轻人可是非同寻常啊。”听得出邱平对客人印象不错,“他的字写得很好,尤其是行草,更显功力,书体风格有点像你。还有,你在报上发的文章他也看过不少,还能谈出个头头道道呢。”
老周又一笑:“一个毛头小子,字能有多好。”
“我会骗你吗?”邱平就差对天发誓了,“不要说人家是专门奔你来的,即便是个不起眼的书法爱好者,你这书协主席也该见见吧?”
没错,除了文化馆长,老周还兼着区书协主席一职。几年前书协换届,宣传部长点名让他接任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老周啊,咱们这个区小,数来数去也就你的字拿得出手了,这个职务非你莫属,你得多给我们培养些书法人才啊。老周听了不仅没受鼓舞,反而心里犯了愁,他知道书协的条件连文化馆都不如,财政不拨一分经费,当主席肯定是活受罪。可领导发了话,老周不当也得当,就拉了喜欢书法的高中同学邱平做秘书长,帮着处理一些事。邱平在区民政局工作,一直想混个一官半职,却始终未能如愿,让他当这个秘书长竟有些受宠若惊,自然在认真地做,单位没事就跑到书协守着了。
“那,”老周迟疑了一下,“要不你领他过来吧。”
“这会儿我还有个事,”邱平不好意思地说,“先让他过去吧,中午吃饭时我们见面。”
“中午还要吃饭?”老周眼睛睁得多大,“邱秘,你有没有搞错?书协有半分经费吗?你请还是我请?”
“不请就不请,”邱平随和地一笑。
挂了电话,馆员小刘进来了,她是来送今天的报纸的。小刘可以说是这馆里最勤恳的一个,别的人就不好说了,不是这个领导的亲戚,就是那个局长的公子小姐,常常十天半月逮不着个人影儿。老周为此抹下脸整顿过几回,却也不见什么起色,人是懒洋洋地来了,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好好做事,搞得他心灰意冷,再懒得去跟他们较真了。老周对小刘笑笑,接过报纸看了一眼,上面有他一张稿费单,三百四十块,是一家书法杂志寄来的。他又对小刘笑了笑,很快在单子上写了身份证号,签了名,让她帮着到邮局取一下。
小刘刚出去,外面就有人怯怯地敲门,老周应了一声,一个细细瘦瘦的年轻人进来了。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拘谨地立在门口,羞涩地问,这是周老师办公室吗?老周点点头,我是周广远。他觉得这年轻人好像在哪里见过,蓦地想起来了,他和儿子长得有些相像呢。说话的声态也像,动作也像,都是那种稚气未脱的样子。年轻人眼一亮,上前几步,冲着他伸出手来。老周把手递过去,你是邱秘书介绍的那个青年书法家吧?年轻人点点头,忽又摇摇头。
“老师可不敢这么说,我只是个书法爱好者,得多向您学习。”
“你坐!”老周笑了笑,转身去倒水。
等他捧着水过来时,年轻人刚好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身子朝前倾着,屁股只有半个落到实处。见他过来,马上又站起来,接了杯子,连声说,谢谢老师。说过后,却又把杯子放在了面前的茶几上,再没去碰,好像那不过是一件摆设。杯子也确实好看,是一个朋友为报答他赠的字送过来的,景德镇出产的小紫藤青花手绘方杯。
“这个你吸吗?”老周又从抽屉里找出包烟。
是那种硬盒的包装,一面是一座古城楼,一面是一个男人的头像。这包烟藏在抽屉有些时日了,还是教育局的赵局长给儿子办婚事时发的喜烟,好几十块钱一包,他一直没舍得吸。他觉得抽这么贵的烟太奢侈了,还是等有贵客上门时再拆封吧。他抽的一直是那种四五块钱一包的“红河”。
“我还没学会。”年轻人摇摇头。
“不吸好。”老周听了就没去拆封,又把烟放进了抽屉,顺手拿起桌子上的“红河”,抽出一支点了,“吸烟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戒过几年,感觉挺好的,可后来还是没管住自己,又吸上了,这一吸上就再戒不了啦。这大概跟练书法、上网一样,都是种瘾啊。”
“老师真幽默,对了,您也上网?”
“偶尔也去书法网逛逛,一只蚂蚁有时也要看看另一只蚂蚁怎么工作,是不是?”
“老师可不是蚂蚁,您是书法界的大象啊。”
老周微微一笑,忽然记起了什么:“你在哪里高就?”
“大学毕业后,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年轻人迟疑了一下说。
“如今就业难啊。”老周点头表示同情,心里却微微有些失望,“听说你是专门而来,你从哪里打听到我的?”
“我有个亲戚也喜欢书法,就在老师你们这个市做生意,他常常对我谈起您。”年轻人眼亮亮地说,“我上网百度了一下,发现您果然是个造诣极高的书法家,打那以后就开始关注您。不瞒您说,老师的书作和文章我能搜到的都仔细研读了,受益匪浅啊。”
“也没你说得那么玄乎,你倒是个有心人。”老周笑了笑。
“老师太谦虚了,您的书法是宝贝啊,怎么会没价值呢?”年轻人摇摇头,“您这么说,也太让我们这些晚辈汗颜了。”
老周没吭声,心里却有点喜欢这个年轻人了,他觉得他虽有些羞涩,却很懂礼貌,比馆里那些人素质高。说实在的,老周喜欢别人叫他老师。在这个小城,他觉得自己无论比学问还是论人品,都配得上这个称呼。但是馆里的人却要么叫他馆长,要么叫他老周,这他都不喜欢听,却碍于面子不好去纠正。时间久了,他似乎也习惯了别人这么叫,偶尔有人叫他老师,反倒觉着生疏,甚至别扭了。但现在,这个年轻人却叫得那么自然、顺口,让他不能不接受。
“书香致远,墨韵流长啊。”老周感慨地说,“你这么年轻就专注于书法,将来会有好前景的。”
“老师您得经常指点我。”
老周笑笑,又向年轻人看去,时令都仲秋了,他还穿一件白半袖衫,裤子是米黄色的那种,看着有些单薄。鞋子呢,还是夏天那种皮凉鞋,棕色的,露出一双有点脏腻的白袜子。老周心里就有些感叹,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儿子远没有这年轻人朴素,吃穿都讲究得过分。大二谈上女朋友后,就更是不像话了,一来电话就会问他要钱,好像除了钱不会说别的了。
“出来有些时日了?”老周忍不住问。
年轻人好像晓得了什么,窘迫地点了点头。
这时,小刘敲门进来了,是来给他送那点稿费的。老周随手把钱塞进了衣袋,忽然记起身边有客人,脸就红了一下。等小刘带上门走了,老周发现年轻人正盯着墙上的书法端看。那是他的手书,用淡黄色的仿古宣装裱出来的,看起来颇为雅致。书的是苏轼的《赤壁怀古》,笔势飞扬,每个字好像都裹挟着千钧之力,波浪滔滔,风雷滚滚。本来,他是个不事张扬的人,可邱平看了却百般称赞,迫不及待地拿去裱了,又自作主张地挂到了墙上。这一来看的人就多了,都说好,有大家风范。他也渐渐习惯了人们这种评价,不忙时,他会仰倒在椅子上,目光自然而然地探向这幅字,品上半天,觉得还真的很养眼很有味道呢。但有时他心里也犯疑惑,他的字真要像人们说的如此那般地好,怎么就不能给自己换来符合想象的润笔费呢?
说实话,老周这两年日子过得有点紧,他们刚刚买下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儿子就上了大学。虽说他的字也能赚点润笔费,可毕竟谈不上畅销啊,再加上妻子一直没个正经工作,养家糊口就主要靠他的工资了,他真的希望自己的字能畅销一些。可这话他又不能对邱平说,他觉得说不出口,有失身份。于是他给自己解释说,你是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啊。妻子晓得他的心思,说你就别等着有人上门买你的字了,你得出去推销自己,现在有点手艺的人不都这样吗?会画几下的办美术班,会唱几下的办音乐班,你会写几下该办个书法班呀,连邱平都办班挣学生娃的钱了,别人能挣你就不能挣吗?老实说他不是没动过这心思,可后来到底没有付诸行动,他觉得真要去办什么书法班,那就跟街上的艺人没什么两样了。他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是的,他固执地认为那就是同流合污。早过了天命之年,退休近在眼前,单位也什么事都做不成,他心里唯一的寄托就是书法了。倘若连这点都守不住,那他还有什么呢?
“老师的字真是名不虚传。”年轻人忽然转过脸来,激动地说,“这些年我走过好多地方,看过的字不下千幅,但说句不客气的话,能打动我的少得可怜,您这字让我震撼啊。气吞万里,举重若轻,看不出一点暮气,要不是先见了您的面,我还以为这幅作品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呢。”
老周听了心里有些得意,嘴上却说:“嬉戏之作,登不得大雅之堂。”
“老师,您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书作呢?”年轻人看了他一眼,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刚才我和邱老师已交流过了,他研习的是三希堂法帖,字不能说不好,好就好在端庄娟秀,疏朗飘逸,可恕我直言,他的字缺点也很明显,中规中矩,有些太过拘泥了。您也学王羲之王献之,但随性运笔,舒卷自如,有如行云流水,太有收藏价值了。我觉得您的书法作品,有些被忽略了,还尚待书法界充分认识、发掘。以您目前的功力,至少能够在行草的领域坐上前十把交椅。”
“是吗?你这样认为?”
老周的口气有些平淡,也包含着疑问,但心里对这说法却是认同的,他觉得这年轻人对书法很有见地。邱平的字也确实那样。至于他自己的字,老周认为也确实有些被忽略,他身居一个小城,人有些愚钝,更不会花钱买奖炒作自己,自然热闹不到哪里去。
“老师,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当然……”老周本想说什么,却又打住了,看了年轻人一眼,心里忽然生出了让他展示一下的想法,就拿了墨砚,又在桌子上铺了纸,“你对书法的理解很深,字想必也写得好,来,让我也开开眼吧。”
“这,您这不是让我班门弄斧吗?”年轻人摇摇头。
“不要推辞了。”老周鼓励说。
年轻人还是显得很为难,又看了他一眼,刷刷刷写了起来,书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气呵成,颇有气势。老周在一旁看了,不由暗暗叫绝,这狂草也确有几分功夫了。赞叹之余,又觉得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仔细看了看,是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欲求太重了,少了一种浩然之气。无欲则刚,一个人的欲求太重,那种气怎么会有栖身之地呢。无气则无神,无神则浅薄,又谈何境界?
“不简单,年轻有为啊。”想是那么想,老周还是赞扬道。
“老师千万不能这么说,”年轻人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对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您肯赏脸不?”
“说吧,只要我能办到。”老周笑了笑。
“是这样的老师,”年轻人诚恳地说,“想请您去我们那里一趟,讲讲学,谈谈书法,毕竟我在书协有不少朋友。”
“去讲学?”老周一下瓷在那里。
“是啊,”年轻人恳切地点点头,“若是方便的话,您还可以带上师母,带上邱老师他们。对了,我们那地方离鼓浪屿没多远,顺便可以去观观光,也不知您去过没有?”
“我还真的没去过,”老周摇摇头,“上了岛能看到海吧?”
“当然能,这岛就在海上呢。”
老周觉得自己像是被什么击中了,有一种眩晕的感觉。说实话,他到现在还没见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海。年轻时,有好多次可以看海的机会,可每一次都因为工作忙没有成行。如今,时间是宽裕了,日子却也过得紧了,真要让他去,他也不想花那个钱了。可心里还是有个结,想去看看海,想在海边坐坐,体验一下什么叫心胸开阔,什么叫真正的安静。有一次,他跟妻子说了这个梦,说什么时候咱们一起去看看大海呢。妻子说,去一趟至少得花费你两个月的工资,等咱们的儿子大学毕业了,再谈这事吧。这话说得很没趣,却在理,是的,看海得花钱呀,等儿子不问他们要钱时再想那事吧。前几天,儿子还来过电话,说想买台笔记本电脑。他听了很生气,说上个月刚刚给你打走几千块,现在又要,你以为我是开银行印钞票的吗?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妻子不满地说,你开个书法班不就有钱了吗,还用这么跟孩子发脾气?
“老师要觉得不妥,”年轻人见他不吭声,忽又出了声,“就当我没提这个请求。”
老周赶紧表态:“行,我看完全行。”
“那就太谢谢老师了,”年轻人脸上有了喜色,“回去后我就给您正式发函,你们此行吃住的费用全包在我身上。”
“这,不用这么客气嘛。”老周摆了摆手。
二人正谈得投机,邱平的电话来了,问聊好了吗,都到吃饭的时间了。老周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确实快正午了,也该去吃午饭了。他看了年轻人一眼,不知该不该请顿饭,请又怎么请,钱从哪里挤?自从儿子上了大学,不仅工资卡被妻子要走了,连偶尔赚的一点稿费也得上缴。蓦地记起了小刘送过来的稿费,就觉着腰干粗壮了不少,心说这回怎么也得请客人吃个饭,不能再听妻子的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更何况,人家还要请他去讲学呢。
“这么吧,你先去千佛岭羊肉馆占个位,我们这就动身。”老周终于出了声。
电话那头的邱平忽然笑了,“不是说不吃饭了吗?”
“来了客,怎么能不吃呢。”
挂了电话,见年轻人正看着他,便说:“走吧,一起去吃个便饭。”
“我正要说呢,早想请老师吃顿饭了。”
“这你就不要操心了,”老周摆摆手说,“到了我的地盘,哪有让你花费的道理。”
就要出门,却见年轻人又走到了那幅字前,两只眼睛几乎是伸出了手,要攫走什么似的。老周忽然明白了,他该送年轻人一幅字呀,人家那么崇拜他,那么爽快,不送幅字说不过去。便打开书柜门,从里面找出一卷已经裱好的《滕王阁序》,展开看了看,又卷好了,这幅字他写了整整八个小时呢,是他很喜欢的一幅长卷。半年前,有个老板说想收藏他一幅字,并表示愿出六千块润笔费,他面子上没表现出个什么,心里却高兴,下功夫写了这幅字,但裱好后,那人却好像忘了这回事,再不提了。他也不好去问,这字就存了下来。书柜里还有几幅字,都是来了灵感时写的,还没有来得及装裱。
“这幅字,”老周顿了顿,终于下了决心,豁出了似的说,“你拿去作个留念吧。”
“老师,这我哪好意思啊,您的字金贵着呢。要不,我留点润笔费吧。”年轻人喜出望外地说,说着就要把手伸进衣袋里。
“见外了,我们之间不谈钱,是不是?”老周将书卷塞到了年轻人怀里。
年轻人如获至宝,连声称谢。
老周只是笑。
“老师,”年轻人忽又出了声,“我还有个想法,可以对您说说吗?”
“尽管说。”
“刚才看到您柜子里还有几幅写好的字,”年轻人一脸诚恳地说,“您要没什么急用,不如让我带回去吧,一来让更多的人欣赏一下您的作品,二来也可以赚点润笔费。书作一出手,我就给您把钱寄回来。您看如何?”
“也好。”老周迟疑了一下,还是把那些字拿了出来。
等年轻人把那几幅未装裱过的字卷进了长卷里,老周便带他出门,刚出了单位院,却听得自己衣袋里的手机响了,响了几声忽又断了,他看了看,是家里的电话。这是妻子和他约好了的,响几声便断,然后老周再用单位的电话打回去。这也是儿子上了大学之后的事,妻子让他必须维护这个约定。老周一开始心里很不舒服,也很有些不习惯,说这也太那个了吧。妻子就开导他,说你该知道自己挣不了几个钱的,挣不来就得节省,省下就等于挣上了。现在,远方的客人待在身旁,老周真是很难为情,他本想用手机打回去,又怕回了家妻子没完没了地唠叨,就对年轻人笑笑,说有件东西落在办公室了,得回去拿。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赶回了办公室。等他用固定电话打回去,妻子劈头就问,你怎么回事,都这会儿了还磨蹭着不回家?
“有客人呢,我得陪着。”老周赶紧赔笑。
“有客人,你也不吭个声?”妻子没好气地说,“说句话能低了你,还是高了我?”
“先别这么电闪雷鸣的,”老周还是低声下气的样子,“有好事呢,客人说要请我们去鼓浪屿看海。”
“去鼓浪屿看海?”妻子冷冷地说,“大白天的你就做美梦吧,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们。都五十多的人了,想得实际点好不好?”
“是真的,人家请我去他们那边讲学。”
“请你讲学?”电话那头的妻子忽然笑出声来。
“有什么好笑的。”老周不满地说。
“这人不会是个骗子吧?”
“骗子?”老周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他很快摇了摇头。“怎么会呢?我会那么轻易上当受骗?我有那么幼稚吗?跟你说吧,今早一上班倒是遇到了个骗子,可他一说话就给我看出来了,想跟我玩那一套,没门!”
“老周,我还是提醒你小心点,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妻子仍不放电话,“对了,一会儿请客谁掏钱?不会又是你个冤大头吧?”
“这次是邱平,”老周撒谎说,“客人是冲着他来的。”
“那就去吧,别喝醉就行。晚上早点回来,我们商量一下怎么给儿子买台笔记本。我觉着你还是办个书法班好,没钱你就没面子。”
老周不想听她再唠叨下去了,说邱平在催了,这些事回去再说。说着赶紧挂了电话。正好邱平的电话也来了,告诉他房间已经订下了。老周说知道了,我们这就过去。出了单位院,走不了几步就是慈云寺。老周看了年轻人一眼,说你对这类建筑感兴趣吗,要不要进去看看?年轻人笑笑,没吭声。老周就想他这肯定是不好意思,就推开门往寺院里走。年轻人夹着那幅长卷后面跟了上来。这院子老周常去,几个和尚、还有那些打杂的,没有不认识的,进来后就没人拦挡。老周带着年轻人各个殿走了一回,每一处都作了些讲解,年轻人哦哦地应承着,显得很有兴致。最后,老周在大雄宝殿门前停下来,指着里面的一口大钟对年轻人说,这菩提钟是寺里传下的宝物,有些年头了,声音却还是悠扬悦耳。又说,我喜欢听这钟声,听了心里就会安静下来。年轻人点点头,一脸敬仰地说,老师一看就是高人,心中有佛啊。老周摇摇头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佛性是什么,就是一种向上向善的德性,可是我们很多人却不去发掘,任尘土把它埋了。年轻人怔怔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这时,邱平的电话又来了,老周说在慈云寺看了看,这就走。
他们要去的千佛岭羊肉馆在前边不远的一条街上。老周也不急,边走边介绍这家馆子。千佛岭是采凉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家家户户都养羊,因为吃的都是山上的药材,羊肉的质地就好,本市的星级饭店都从这里进羊肉,炒得越来越火,价钱要比别处高好几倍。所以村子虽小,可随便拿出个放羊汉都是腰缠万贯,肥得不得了。这千佛岭羊肉馆就是这村人开的。年轻人吃惊地点着头。老周注意到他把那幅字夹得紧紧的,像是担心一松手就飞了似的。
到了饭店,邱平出来把他二人带进了雅间。
老周让邱平点菜,又吩咐上酒。
酒要的是那种小瓶装的滹洲老窖,净含量125ml。商标特别强调说这是“革命小酒”,还用繁体字印了两句“最高指示”:酒是粮食精,少喝为革命。老周喜欢喝这酒,可到现在他也搞不清这话出自毛选哪一卷、哪一章、哪一节、哪一段。虽然价钱便宜,酒却是地地道道的,落口很爽。酒瓶也好看,细腻的白瓷,精美的图案,瓶口还扎了根红丝带。
“今天我们落实一下最高指示,多喝点。”老周微笑着对年轻人说。
“那是那是,多为革命做点贡献嘛。”邱平附和说。
年轻人却显得一脸茫然,看那样根本就不懂“最高指示”什么意思,“革命”又是什么意思,样子就有些呆。老周自是看在眼里,劝他不要拘束,来了就是朋友。年轻人反越发拘谨了,两只手也不知往哪里放,好像放哪里都是多余的。老周不敢再劝,心说搞书法的大概都这样,只有谈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时,才会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今天没多少客人,菜不一会儿就陆续端了上来,除了店里的看家菜炖羊肉之外,还有蒸水蛋、豆腐海带炖猪肉、小白菜嫩豆腐、凉拌苦菜等。这时,老周听得自己的手机颤了一下,一看,是儿子发来的短信,儿子说他昨晚提的那个要求有些过分了,等你们将来宽裕些再给买也不迟。老周看了心里就有些感动,他没想到儿子一夜之间就长大了,知道体谅父母了。老周又看了身边的年轻人一眼,催促他下筷子,又往他碗里夹了一块羊肉,好像他就是自己的儿子。
“千万不敢客气,不能饿着肚子呀。”老周说。
“不不,在您这里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年轻人受宠若惊地说,“等过些时日把您二位请去了,我一定陪着好好走走。”
老周便扭过头对邱平解释,“这小伙子邀我们去他那里讲学呢。”
“这好啊,这好。”邱平眼睛睁得很大。
喝了几杯酒,年轻人不再拘束了,话也渐渐多了起来,谈起了他见识过的一些书法家以及他收藏的名家字画。年轻人说的这些名人,老周只是在电视里的书法讲座或书法杂志上看到过,没想到他都认识,有的还请他吃过饭呢。而他收藏的那些名家作品,有的在市场上可以卖个天价。老周听着,忽就犯起了疑惑,一个既没有固定职业又没有多少名气的年轻人,怎么会认识那么多名家大腕呢?还有,他的字为什么欲求太重,多了几分浮躁呢?这一点他觉得不能忽略,人一浮躁,什么有悖心性的事做不出来?忽又想到了妻子的话,这个人真的不会是个骗子吧?
“哦,对了,你们书协主席是谁?”老周装作很随意地问道。
年轻人微微一怔,很快报了个名字。
老周哦了一声,劝年轻人接着喝,脸上显得很轻松,心里却越来越觉着不踏实了。后来等年轻人上洗手间时,老周赶紧吩咐邱平,让他马上和那边的书协联系一下,查查这个年轻人的来历。邱平吃惊地看着他,老周你怀疑他?我真想不明白,你送了他那么一幅长卷,让我都有些嫉妒呢,怎么忽然又怀疑起他来了?老周也不作解释,板着脸让他快点去,要做得不动声色,不露破绽。见他这么严肃,邱平摇摇头去了。
那年轻人很快回来了。
老周笑笑,招呼他坐下接着喝,边喝边谈书法,但这回谈书法是假,喝酒是真了。老周想把他灌醉,醉了他就得说真话了,但没想到对方酒量大着呢,自己即便再减去十岁,也不是对手。没喝醉对方,老周倒先觉着有些晕乎了,却还是硬撑着,盼着邱平能快点回来。当然,他不希望查出什么问题来,虽说和这年轻人认识才小半天,可他已经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了。是的,这年轻人不光是才华横溢,人也是那么彬彬有礼,更重要的是,若真的没什么差错,他就可以到鼓浪屿去看海了。去的时候,无论如何也得把妻子带上,让她开开眼界,知道自家男人绝非等闲之辈,他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啊。
“邱老师呢,他怎么不喝了?”年轻人忽然问。
“去接电话了,这个老邱啊,搞什么名堂呢。你稍等,我出去喊他一下。”老周冲年轻人笑笑,摇摇晃晃出了门。
出了门,恰好看到邱平往这边来了。邱平脸灰灰的,老周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心一下悬到了嗓子眼。邱平说查了半天总算和那边联系上了,人家说听都没听过这个人,还有,他们书协主席也不是年轻人说的那个。老周就知道这年轻人确实有问题了,悬在嗓子眼的心一下又沉了底,看来,他想得太简单了,竟然没有看出这是对方设的套,他甚至还没有妻子目光犀利。是的,哪里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就是有也轮不到他头上。可他居然就信以为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还不是因为他不知不觉就被对方灌了迷魂汤?还不是因为他心里一直潜藏着看海的欲求吗?他总嘲笑别人心里的欲求太多太重,又自认为是个淡泊之人,可事实证明,他心里的欲求一点都不比别人少,也不比别人轻。真是可悲啊。
“妈的,都骗到我们头上来了。”邱平气极败坏地说,“这家伙也真是胆大包天,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报警呢。”
“报警?”老周迟疑了一下,“你觉有必要吗?”
“当然有,不报他还会到别处去行骗的。”
“那就,那就报……吧。”
“我这就打电话。”邱平摸出电话就要打。
“算了算了。”老周忽又制止了邱平,报了警这事就会传出去,不到天黑,一个县城的人就都知道这事了。到时人们会怎么看自己?不仅不会同情他,还会说周馆长这人居然也会鬼迷心窍,一个毛头小子就把他骗了。
“为什么又不报了?”邱平愣愣地立在那里。
老周欲言又止,他不想让邱平知道为什么,他还得装下去,维护自己这点可怜的面子:“或许他们并不了解他,你想想,一个还没找上工作连饭碗都没有的大学生,他们会了解他?”
“老周,你不能心软呀,此时心软就是纵容犯罪,姑息养奸。”邱平急得直瞪眼。
“听我的,回去喝酒。”
老周狠狠地摆了摆手,像是极力摆脱什么似的。
“你的字呢,还给他?”
“给。”
再回到酒桌上,老周发现他们要的三小瓶酒都快喝光了。就让邱平再去要,邱平一个劲地朝他使眼色,意思是已经知道了是个骗子,怎么还陪他喝?你钱多得没处花了?老周却坚持再上一小瓶,邱平没法,只得又要了酒,他自己却不去拿杯,冷冷地坐在一边看。老周不管邱平什么态度,对年轻人依然很客气,且还是那么谈笑风生的。邱平看了就更不满了,一眼一眼地剜他。老周只当是没看见,照旧跟年轻人交杯换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的样子。渐渐地,两个人舌头都有些大了。
“老师,我们不敢再喝了。”年轻人僵着舌头说。
“喝好了,你真不喝了?”
“是,不喝了。”
“那就不喝了,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撤吧。”
几个人便往外走。
老周注意到年轻人起身时没忘把那幅长卷带上,他心里真有些疼,好几幅字呢,都是一笔一笔写成的,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去把它们要回来了。邱平自然也盯着,不停地朝他使眼色,意思是你怎么不把它要回来,多好一幅字呀。老周装作没看见,先行一步,到吧台去结账。从衣袋里掏钱时,他的动作显得坚决有力,不像平时那样拖泥带水的。待邱平和那个年轻人过来时,他已离开吧台,朝门外去了。
“这账该我结呢。”年轻人追上来说。
“哪能让你结呢,你是客人,不能让你破费的。再说,你不是还没找上工作嘛,身上可能一点钱都没了。后生,听我的,我希望你的字越写越好,等你在那边找上工作了,生活安定了,再来请我吃饭,是不是?”老周盯着年轻人说,这时候,他的眼前忽又浮出了儿子的影子,他们长得是多么相像啊,“我相信你会好起来,一定会的,是不是?我相信天下所有有才华的人都能好起来,是不是?”
“老师,”年轻人声音有些哽咽了,“回去以后,我就……”
一旁的邱平忽然怪怪地一笑。
“回去以后,你就要给我们发函是吧?”老周瞪了邱平一眼,又把脸转向年轻人,他觉得自己的目光是善意的、慈祥的,是一个父亲面对亲生儿子的目光,“这事不急,等你好起来,再请我们去讲学,是不是?”
“这,老师,我听您的。”
“我相信你会好起来的,等你找上工作,日子有了起色,你肯定会请我去讲学。你还会带我们去鼓浪屿看海,看那一望无际的大海,是不是?”
“老师,我……”年轻人说着就要跪下来。
“你这是要干什么呢?”老周有些慌了,一探手将他拉住了,“都什么年代啦,不兴这样拜师的。”
“老师,您真会收我为徒?”
“都拜过了,我能不收吗?”老周淡然一笑,“其实你的书法已很有些劲道了,所以我欣赏你,相信将来你也会超过我的。当然,你要是能耐住性子,少一些浮躁,会有更好的前景。”
“老师,我都记下了。”年轻人点点头,忽又指着腋下的长卷说,“这字……”
“你都拿去吧。”老周挥了挥手。
“那就太谢谢老师了。”
年轻人说完,看了他们一眼,夹着那幅字朝街上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加快了步子,很快就要汇入人流中了。
“老周,那是你辛辛苦苦写下的呀,真就让他大模大样地拿走了?”邱平望着远处,心急火燎地说,“现在你发话还来得及,我一个电话,警察就来了。”
“老邱,”老周沉着声说,他没敢说几幅没装裱的字也一并给拿走了,“你还想不想把字练好?”
“当然想。”
“那就得冷静,不能太急躁,明白吗?”
老周说完,丢下邱平,朝单位的方向走去,越走越快。走到文化馆这条街,又到了寺院门口,他由不得停下来,恍惚听到了那悠扬的钟声。多么撼人心魄的钟声啊,每一下都毫不含糊,先紧敲十八下,再慢敲十八下,如此往复两遍,不多不少共一百零八百下。老半天,邱平喘着粗气追上来,问他走那么快干吗?老周看了他一眼,说:“你听到钟声了吗?”邱平愣了一愣:“没,没听到。”老周说:“你再听,再细细听。”邱平便侧着耳朵认真地听,忽然咧开嘴笑了:“这会儿哪会有钟声呢?”
“怎么就没有呢?”老周不屑地看了邱平一眼,旁若无人地吟诵起来:“钟声闻,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
“老周,你高了,你真喝高了。”
“你真觉得我喝高了?”
老周瞪着眼看他,像看一头怪物。
“不是吗?”邱平懦懦地说。
老周收回了目光,忽然想大笑一通,敞开怀、无所顾忌地大笑一通,笑这些人心中没有菩提,俗不可耐,眼前却倏地飘过了那年轻人的影子,还有被卷走的几幅字,心里不由又狠狠地一疼,再没有了笑的意思。他又看了邱平一眼,摇摇头,自顾自往前走了。
王保忠,作家,现居太原。主要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张树的最后生活》、《尘根》等。
订阅邮购启事
2015年报刊征订已经开始,欢迎到邮局订阅本刊。由于办刊成本提高,本刊明年调价,定价18.00元/期,全年6期108.00元。
本刊邮发代号:84-12,各地邮局均可订阅。亦可到《天涯》杂志淘宝店(tyzzz.taobao. com)购买,或直接汇款到杂志社邮购,平邮免收邮费;如需挂号,请加挂号费每期3.00元。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人大政协楼6层《天涯》杂志社邮购部
邮政编码:570203
联系电话:(0898)6533280365360004传真:(0898)65353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