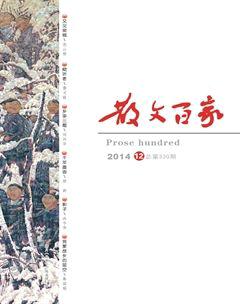不懂爱情
一
我十九岁订婚,二十一岁完婚,即便在农村,也算早婚。从此,那个被人叫做我媳妇的人,风风雨雨里,伴我走过了三十个春夏秋冬。
人家说,婚姻是为两个寂寞的人找个伴侣,是为两颗孤独的心寻找依靠和支撑。但当时青春年少的我,对爱情的认知,除去懵懂的向往,别的一无所知。只是为了一份温暖且又无奈的责任,才答应父亲订一门亲事。晚上,躺在学校的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描摹想象着等待我的那个人的样子,心里一片混沌和茫然。
二
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第三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三哥来学校找我,说是表姐给我介绍了一位姑娘,让我晚上去相看一下。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机械地听从三哥吩咐,换了身洗干净的学生装,向老师请了假,和三哥分别骑一辆自行车去表姐家。表姐家距学校大概四十华里,离我们家却很近。虽分属两个地区管辖,却只隔两道堤、两条河,直线距离三华里。我们没回家,直接去了表姐的村子。表姐嫁在本村,按照约定,相亲的地点选在了姑姑家。到了那儿,天已黑透了,正赶上停电,姑姑家点了盏冒着油烟的煤油灯,屋子里透着昏红的光亮。姑姑、姑父简单招待我们吃了点东西,就带三哥到邻家去串门。表姐是个爽直性子,过了一会儿工夫,就高门大嗓地领着一位姑娘进门来了。表姐笑着分别介绍我俩的名字,说了句“你们好好聊聊”,就也躲出去了。平生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我羞涩拘谨地不敢抬头,坐在靠北墙的板凳上,两眼望着自己的脚尖和砖地。相比之下,姑娘要比我大方得多。从跟着表姐进门,她就一直“咯咯”在笑,笑声很清脆、很干净。这时她坐在我对面的炕沿上,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穿了件粉红的上衣,但半天的工夫,我还不知道她长什么模样。沉默是她打破的,她先是“咯咯”笑了一阵,然后站起来,说:“我刚下地干活回来,挺渴的,麻烦你给我倒杯水呗!”我一想,这姑娘够聪明,她是想借机看看我的身材、身高和长相。于是,赶紧慌乱地站起来,从柜子上拿起暖壶。她也站了起来,两手捧着玻璃杯子笑吟吟地看着我。对面近距离地相视,我的心“怦怦”乱跳。从进门到现在才真切地看清姑娘的模样:她中等身材,略显瘦削,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鸭蛋形的脸庞黑里透红,一双杏核眼明亮清澈,笑吟吟的,羞涩含情;她着装简朴,甚而有些土气,但干净整洁。那一刻我有预感,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和我牵手一生的人。给她往杯子里倒水的时候,由于手抖,水溢了出来,烫得她尖叫了一声,又“咯咯”笑了起来。接下来聊了一会儿,都是她问我答,像老师考核学生一样。姑姑和表姐她们回来的时候,姑娘起身告辞,表姐追到门口问:“芬儿,怎样啊?”姑娘笑了一阵,说:“倒是够老实,够利索。”表姐也笑着说:“那我就算你愿意啦!”回到屋里,表姐同样问我:“行吗?”我吭哧半天,红着脸说:“听你们的。”表姐一拍巴掌,兴奋地说:“妥了!”又发自内心地感慨:“表弟,你有福哇!这闺女是头大的,上过学,知书达理,能干、利索、勤俭、孝顺,又俊,哪样儿都占,你算捡了个宝贝。”
接下来表姐安排,到姑娘家,让她的父母家人相看我一下。我已知道姑娘姓王,叫翠芬。她的家坐落在大清河沿儿上,三间老屋,一个小院儿,挤着父母和她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一大家人,生活显然很贫苦。我去时,她家里除了她家人,还挤着闻讯而来的一帮小姐妹。我站在柜角,在一群人的目光聚焦下,羞臊无助得手足无措。五月的夜晚很凉爽,我却已汗流浃背。逃也似的重新回到姑姑家,表姐反馈过来的信息是:
翠芬的弟妹小,没意见,只觉得很新鲜。她父母亲的态度模棱两可,只说:“这小人儿长相一般。怎么手脚没地方放,腿也抖,头也晃,怕是有毛病?”
翠芬说:“那是嫌臊。”
她的小姐妹们七言八语说:“你这么俊个小闺女儿,就挑这么个人儿?”
翠芬说:“长相又不能当饭吃。”她让表姐明确告诉我,她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听了,既自惭,又感动。
第二天是星期六,按照约定,表姐和翠芬的叔叔带着她来到我家相看房子,在农村叫“相房”。相房的目的,一则是女方看看男方的经济状况;二则男方要赠女方相房钱,少的给二十元,多的三十元,那时的物质条件不能和现在同日而语,前些日子我侄子相房,出手就给女方一万元。我父亲看了翠芬两眼,当时就很满意,他说:“这小孩儿挂个利索劲儿,是个能过日子的主儿。”破例给了五十元的相房钱。父亲征询几个嫂子意见(我的态度他已知道了),嫂子们一迭声说:“好。”父亲说:“选日子不如撞日子。后天四儿还去上学,要不明天咱就把亲订了吧!”
翠芬的父母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体谅我家兄弟多,一切从简。那是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年份,大哥和二哥开了个屠宰场,摆酒的下酒菜是不用愁的。第二天,我去史各庄镇上早市买了两条大鲤鱼和几样素菜,办了两桌酒席,双方家人至亲吃了顿饭,我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订了下来。酒席结束后,翠芬的父母先行回家,我父母给了她300元钱,让我带她到镇上供销社买点东西,我用自行车带着她,从大清河堤上前往史各庄供销社。五月初的天气,阳光明媚,堤下的大清河碧波荡漾,河两岸的麦田正欲含苞,堤上槐花的芬芳裹了绿草青苗的香气,漫天漫地,身后再带了一个订下终身的姑娘,本应万分高兴,可我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想到不管以前多么心仪、以后再碰上多么动心的人儿,从此和我再无关系,既失落,又迷茫。到了供销社,她原想买两件衣服,左挑右拣,都嫌贵,一样也没舍得买。我暗自欣慰,如表姐所说,她是个节俭的人。最后,她花一角钱买了两根冰棍,一人一根吃完了,我直接把她送回了家。那是我长这么大,除去母亲之外,第一次吃女人买的东西。
第三天清早我就返回了学校。
三
在学校,除了紧张的学习,我成了一个有秘密的人。复习班的学生,成绩都很优秀,又大都是普通的农家子弟,考入大学,是我们改变生活命运的唯一途径,因而,一个个心无旁骛,刻苦用功,同学们根本没想到,回家两天,我就订下了终身大事。我怕被人嘲笑,只字未提过这事儿。事实上,因为之前和翠芬并无感情基础,加上冲刺在即,学习紧张,想这事的时候并不多,只有晚上偶尔睡不着的时候,她的身影才在我眼前浮现几回。听表姐说,曾有人给翠芬介绍过几个对象,都被她婉拒了,这让我一直疑惑,因为她们村是个有名的大村庄,分成三个大队,有一万多口人,选择的余地是很大的。这个疑问,是麦熟之后解开的。
我们这一带的婚姻习俗,订下亲事的男方每逢麦熟、秋收后和大年初二,都要接没过门的媳妇来家住几天,一来为未婚男女创造见面的机会,联络感情;二来让没过门的媳妇提前熟悉婆家的环境,临了,公婆还要给准儿媳一点零花钱。相思中的男女,热切期盼着这些时日的到来。订亲之后的第一个麦熟过后,也是利用周日的时间,我把翠芬接了过来。麦熟过后,地净场光,秋天的籽种撒播完毕,玉米、黄豆等已露出了浅绿的禾苗,这时正逢短暂的农闲期,改革开放不久的农村人很悠闲。然而,白天,我们俩并没多少说话的机会,我扎在屋里复习功课,她帮着母亲干家务活。我三个哥哥已分家单过,剩下父母和我三个弟弟住着六间房、一个院子,母亲原是个特别能干的人,但七个儿子的衣食起居早已拖累得她精疲力竭,那一年又检查发现患了高血压和冠心病,每天长吁短叹,虚汗淋淋,什么活也做不了,家中屋院都又脏又乱,用村里人的话说,叫插脚不下。翠芬进门后,稍做休息,就脱了外套拾掇起来,她用上午的工夫把每间屋子都擦拭打扫了一遍,大到玻璃窗,小到茶杯碗筷,都洗得干干净净,柜子底下乱扔的全家的鞋子,也都翻腾出来,齐齐刷了一遍,晾晒的时候,把六间屋子的窗台都摆满了。中午,她手脚不停,和过来帮忙的嫂子们蒸了两锅韭菜馅包子,包子蒸得皮薄馅大,表皮雪白,我几个弟弟吃得上牙膛都烫破了皮儿。吃着饭,她和几个弟弟商量,下午少玩一会儿,和她一起在院子里进行一次大扫除。几个顽劣成性的弟弟诺诺称是。紧挨着院子东面墙头,是我家的猪圈,圈里养着黑白两头猪,当时已脏得分不出上下圈,暑期将近,恶臭扑鼻。她领着几个弟弟把上下圈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把猪粪运到了屋后的庄基上,紧接着,又把院里的树枝柴草垛好扎捆,整整齐齐码在了院外的墙根下,把整个院子细致清扫了一遍,然后泼洒了清水。看着宽敞明亮的院落,弟弟们兴奋得在院子里翻起了跟头。这一切,我看在眼里,说不上自豪,却为她的大方和勤劳而感动。爱干净的父亲,寻常日子回到家,看到家里狼藉不堪的样子,总是紧锁着眉头,却因疼苦母亲,又很无奈地摇头叹息。那天得知我接来了翠芬,特意回家看看,一进家门,他就被院儿里洁净的景象惊呆了。我和翠芬迎出来的时候,六弟表功说:“是四姐领俺们拾掇的。”父亲脸上难得一见地绽放出舒心的笑容。进了屋子,他又是一番目不暇接,左顾右盼,而后说:“我都快不认得咱的家了。”我瞥了一眼翠芬,她那么自信、那么阳光地笑了,接着,大大方方喊了声“爸爸”,说:“我给咱包饺子。”父亲兴奋地笑起来,跟六弟说:“快喊你大嫂她们来帮忙!你四姐都累一天了!”我想,父亲已是把翠芬视为家庭中的一员了,并且格外喜欢。我偷偷听到父母对话,母亲感慨说:“要是早生个闺女,也能帮我搭把手了。”父亲不屑说:“生个闺女儿,也未必有人家这么能干!”
吃罢晚饭,弟弟们跑出去看电影,我们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我由衷地说:“这一天你挺累的,不如早点歇着吧。”这是我订亲以来第一次主动找她说话。
她红着脸说:“我不累,习惯了,你陪我说会儿话行吗?”
沉默了半天,我终于想起一个疑问:“你怎么从没有问过我能不能考上大学?”
她疑惑地反问我:“考上考不上能怎样?”
我说:“考上了,你不怕我把婚退了吗?”
她丝毫没有迟疑,想来已是思虑过了:“你不会,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再说,真是那个结果,我也不怪你,毕竟身份不一样了。那是命!”
从表姐口中,我知道我们俩同龄,但我却着实惊异她的成熟淡定。她那样回答,倒显得我有些矫情了。于是,我跟她交底说:“其实,跟你说实话,我从小学习偏科,本来寄希望通过一年的复习能把理科成绩赶上,可是,没有厚实的基础,那些课半道上是学不好的。因而,我考上的希望不大。”
她一听,竟“咯咯”笑起来,说:“那倒好了,我就用不着再担心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如释重负般地轻松了许多。接着,就把一直以来的另一个疑问也提了出来:“我知道,你们村上的年轻人都订婚早,以你的条件,不会没人介绍对象,怎会偏偏看中了我?——我家条件差,人也长得一般。”
她的眼睛里掠过一丝忧伤,说到:“我也跟你说实话,这一年多,亲戚朋友确实给我介绍了不少人,但是,听说他们都没上过学,不论丑俊,条件好坏,我连见都没见,就辞了人家。我跟你一样,都是第一次相亲,就把事定了下来。也许,这就是缘分吧。”接下来,她又缓缓述说了一些往事,使我更加清晰地解开了一直以来的疑惑。
翠芬的父亲兄弟两个,解放前,他的伯父为缓解家庭困难,盲流到东北,在铁岭下煤矿当采煤工,解放后录用为煤矿工人,在那里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回家看望弟弟,见翠芬的父亲拉扯着五个儿女生活吃累,就想帮着他养育一个孩子。翠芬聪明伶俐,十二三岁的年纪,已会烧火做饭,做一手好针线活。觉得这孩子不上学太可惜,就决定带她去东北上学。从四季分明的冀中平原,到寒天雪地的北国,她就读于铁岭煤矿子弟学校,没有一点不适应。因为能圆从小上学的梦,她高兴极了,每天放下书包,就赶紧帮伯母升火、洗衣、做饭,有时还替她做些针线活儿。伯父、伯母打心眼里喜爱这个勤快的侄女,更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翠芬门门功课优秀,一年后,从一年级直接跳班到三年级,转年,又从三年级跳班到五年级。老师说,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聪慧姑娘,照此发展,将来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十七岁,她上初二的时候,父亲来到铁岭,执意要她回河北老家。伯父、伯母生怕耽误孩子,一番苦劝。奈何亲生父亲很坚决,孝顺的她,也挂念亲人伙伴,只得跟随父亲回来了。然而,回到家,一个残酷的现实将她憧憬的大学梦击碎了。父亲带她回来,不是让她继续学业的,而是让她退学,帮助家里解决生活困难。当时河北农村刚刚分田到户,她们那儿,除了田地,生产队所有的家当也全部分开,还把一项传统副业——磨光厂的家当也分了,她家有幸通过抓阄分了台磨光机。这就意味着,她家拥有了十几亩土地和一台挣钱的机器。父亲雄心勃勃,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彻底告别穷苦的日子。为解决人手困难,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让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再上学。看到两个弟弟也辍了学,翠芬只得把泪水吞咽下去,默默接受了现实。他们家和几家抓到磨光机的人家搭伙,建起了磨光厂,主要的生产项目是把西餐用的刀、叉、匙的毛坯打磨抛光,出口西方国家。这是个工序并不复杂却又脏又累的活,一个工时下来,人就变成了黑灰色,身上的肥皂布灰味,洗都洗不掉,但收入颇为可观。除了上班,还要帮母亲料理家务,帮父亲打点责任田,身上的汗水几乎被挤干了。经过两年多打拼,家里日子得到了改善,为大弟建起了新房子。准备再吃几年苦,为二弟也准备所新房。一家人都很高兴,唯有翠芬总感到寂寞失落,一个人独处,常常无语流泪。她想的最多的是,既然自己的命运已无力更改,将来嫁的人,一定要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她讲述到这里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我听了,这才知道她的口音里何以有很重的东北味儿。看着她粗糙变形的手,不禁替她惋惜和酸楚。经过一晚的倾心交谈,两颗年轻的心,因此拉近了距离。第二天下午送她回家的时候,竟有些缠绵难分。
四
跟我预料的一样,第二次冲击高考,我再次落榜。我考的是文科,语文成绩特别突出,政治、历史、地理的成绩也说得过去,但数学和英语成绩加起来也只有二十多分。考完了,因为对结果早有准备,所以并没像好多同学那样寻死觅活地难受。只是,不甘心就此延续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知为什么,未婚妻那期冀酸楚的眼神总在我眼前浮现。这,就更加坚定了我另觅通道、改变命运的信念。老师不是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文学鼎盛的时候。因为从小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和文学作品,无意中积累了比较深的文学素养,从小到大,我的语文课,特别是作文课,在班级里都是最突出的,而且早在上学时就向报刊杂志投寄发表过文章,只是因为当时文学空气还没那么浓,作为学生作文选登,也没人注意。落榜之后,因为没有了学习的压力,我对文学的热情和渴望,像干柴烈火一样,“轰”地燃烧起来。落榜后的第二天早上,父亲把一柄锄交给我,说:“孩儿呀,认命吧!”我没理由、也没底气拒绝,扛上锄就去责任田里干活。侍奉农田之余,我把能够借到、有能力买到的书,不知翻了多少遍。与此同时,每天晚上开始了业余创作。稿子寄出去,等待回音的过程是最煎熬的。那时候,不管多累,我都会准时到村里的供销点等信等报纸,盼着自己的作品开花结果。虽然等来的是一封又一封退稿信,但我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秋后家里盖房子,我接翠芬来帮忙,把自己的想法和状态和她说了,她没多说什么,只满含深情地望着我说:“你行!”从此以后,我学习和业余创作的热情几近痴狂,没有老师,没有系统学习创作理论,全靠自己摸索,有时由于坐的时间太久,刚刚站起来就晕倒过去。
大年初二,我去接她的时候,她说“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接着把一个木箱子搬到了炕上,我原以为是一件好看的衣服之类,等她打开箱子,我一下惊呆了,那是满满一箱精美的书籍,除了中外名著,还有部分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我曾跟她念叨过特别喜欢法国作家的小说,于是,这些书里就有了一串闪光的名字——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左拉……难为她是怎样记住的。看我惊讶地看着她,她解释说:“咱订亲和后来你接我去爸妈给的钱,我一分没舍得花,全托在北京工作的表哥为你买书了。”对于一位普通的农家女儿来说,这份赠与不亚于一份壮举。深情厚谊,让我感动得双眼噙泪。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是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地区报纸副刊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安机器》,不到千字的小文章,让我喜极而泣。那天晚上,天还没亮,一夜没睡的我,把自家院子和长长的小巷都打扫了一遍,还从一里地外的水井里把能盛八担水的大缸挑得哗哗溢流。母亲懵懂地说:“这孩子撒癔症了吧?”此后不久,河北和山西的文学刊物分别头条刊发了我的小说《洼地儿女》和《乡歌》,在市、县引起了很大轰动。那个时候,封建思想禁锢还很严重,除去那些约定俗成的日子,平常日子,未婚男女是不到对方家走动的。然而,我再也顾不了许多,只想让翠芬分享我的喜悦。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我带上报纸刊物,骑上自行车,翻堤越河来到翠芬家。到了那儿,她父母下地还没回来,邻家办喜事,她和一帮小姐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看热闹。看见我的时候,她满脸羞涩,一副嗔怪我唐突的神情。小姐妹们一窝蜂地起哄,簇拥着我俩回了家。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出了自己的鲁莽和唐突,一时手足无措。我把报纸和杂志拿出来,嗫嚅道:“我是想让你高兴一下,看,发表了。”她把那些报纸和杂志接过去,急切地翻看起来,看着看着,手竟有些抖,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她跟姐妹们说:“看看吧,他写的。”紧接着,她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突然把我抱在怀里,边哭边语无伦次地说:“我就说你行的,你行的……”平复了一下情绪,她擦干眼泪,招呼姐妹们:“你们搭把手,我要包饺子犒劳他。”
我总以为,我付出的艰辛,不足以回报这么快这么多的幸福。一九八三年七月的一天上午,我夹着一本书,扛了把锄头,准备去南洼的一块玉米地松土锄草,刚走到村口,就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拦下了,他说:“小伙子,知道焦喜俊的家在哪里吗?”我一愣,说:“我是。”他上下打量我一眼,兴奋地说:“那太好了!我是乡党委宣传委员崔彦文,乡党委看过你写的文章,现在还缺一个新闻报道员,特地让我来看看你,想去试试吗?”我半天才回过神来,兴奋地一蹦老高,说:“当然想去。”
就这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爱情的感召,两年时间,我完成了从学生到农民再到工人的蜕变。
五
我刚满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就紧锣密鼓地张罗操办我的婚事。他的理由很充分,一则,我的三个哥哥分家单过,母亲有病,他和剩下四个儿子的生活起居需要人照顾;二则,他身边没个女儿,翠芬进门,他会拿女儿一样疼爱,他从内心喜欢这个聪慧勤劳的姑娘。这样的理由,善良的岳父母是不好拒绝的。只有我心里明白,他其实还有一层担忧,生怕我参加工作后,心气儿高起来,遗弃了翠芬,对不起姑娘。那样的话,我一家人的人品就会遭人嫌恶,势必影响他三个小儿子的婚姻。
一九八五年的隆冬时节,一辆小拖拉机、一辆马车把她送到了我们家,没有几样像样的家具,只有几身新衣服、几床新被子,我们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十年,靠着微薄的工资和责任田的一点收入,我们伺候积劳成疾多年的父母入土为安,又和三个哥哥协力为三个弟弟娶了媳妇、盖了房子,同时养大了两个儿子。我们结婚十年间没添过一身新衣。有一年我去省里参加小说创作班,因为仅有的两条裤子太过破旧,只好穿了妻子的裤子,既瘦且窄,赶上有天我蹲下为宿舍的炉子添煤,一下子把裤裆撕裂了,女同学为我缝补的时候,才发现那裤子是偏开口的。每每回忆起来,夫妻只有自嘲地相视一笑。
日子虽然困苦,但我们相依相伴一路走来,踏实而温暖。现在日子好起来,我们也过上了理想中的生活。妻子说:“回想起来,我们就该一辈子不分开。”
第三次人口普查,我们分别自报家门,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夫妻俩一点也没有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