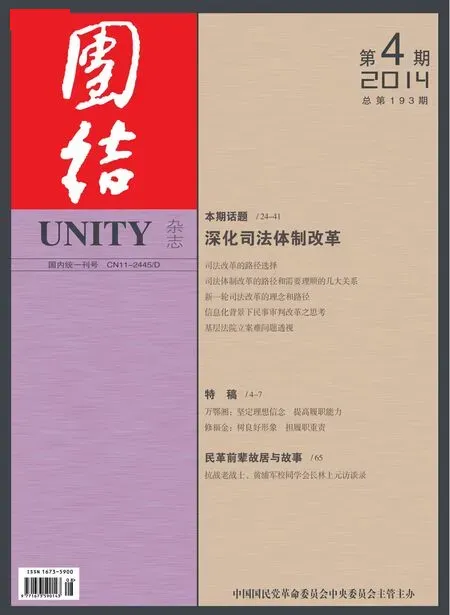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
◎汤维建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责编刘玉霞)
20 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此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召开了两次高层会议,分别于2014年3月和2014年6月通过了 《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以及 《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等政策性、指导性文件,随即司法改革的试点也分别在上海、广东、湖北、海南、吉林和甘肃等六省 (市)展开。
笔者认为,本轮司法改革在路径选择上主要分布在五个领域,分别是:司法权独立的深入化、司法职权配置的合理化、司法机制的科学化、司法保障的充实化以及司法责任的制度化。以下分别阐述。
一、司法权独立的深入化
司法权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当下的司法改革主要围绕这个中心展开。
1.紧紧围绕着司法的 “去行政化改革”,实现司法机构的相对独立和职能纯化。
司法行政化有四重表现:一是司法的横向行政化,二是司法的内部行政化,三是司法的纵向行政化,四是司法职能的行政化。司法横向行政化实为司法地方化,司法地方化是司法横向行政化的表现形态,因此,司法去地方化本质上也属司法去行政化改革。司法内部行政化的表现形态是法官、检察官被打上了深刻的行政官员及其级别烙印,使法官和检察官处在科层化、官僚化、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中,难以独立行使职权。司法的纵向行政化则体现在上级司法机构对下级司法机构的层层控制之中,使法院的审级监督关系异化成为行政领导关系,致使下级司法机构丧失行使职权上的独立性。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同时还要行使执行权,这便是司法职能行政化的表征之一。目前所采取的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举措,便旨在解决上述司法行政化问题。只有克服了司法行政化,司法机关的机构独立或整体独立以及司法人员的个体独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方能获得其实现的前提条件。
2.将司法业务权与司法行政权相分离,实现司法人员的相对独立性。
司法业务权便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上的司法权。司法业务权由法官、检察官行使,司法行政权由司法行政人员行使。为了使法官、检察官更好地行使司法业务权,有必要为其配置司法辅助人员。这样就形成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体制。为防止司法人员及司法辅助人员屈从于司法行政人员、从而为司法行政人员干预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提供管道和条件,尚需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将司法行政权从司法机关分离出去,将其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
将司法机关人财物等行政管理权从司法机关分离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后,又会导致一个问题出现,此即 “行政干预司法”的问题。为克服此一弊端,则又需要对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司法行政权的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与完善。为此,有必要根据 “人财物”管理的不同特点和性质,分别设立两个管理委员会行使实质的统管权能,而司法行政机关只是该两个管理委员会的依托载体和服务机构,其对两个管理委员会不享有实质性的主导权、支配权和控制权。该两个管理委员会,一是用来管人的,称为 “司法人事管理委员会”;一个是用来管财物的,称为 “司法财物管理委员会”。该两个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
3.整合和调整法院和检察院的内设机构,完善办案组织模式。
应当取消法院的审判庭和检察院的业务处室,对法官和检察官实行扁平化管理,消除办案组织模式结构中的中间层,法官和检察官直接面向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同时模仿大学的学科群模式,建立司法业务群制度,分为民事法官(检察官)业务群、行政法官 (检察官)业务群和刑事法官 (检察官)业务群,业务群仅仅讨论行使职权中的业务问题,此外别无职权;该业务群仅设业务召集人,尤其轮流召集业务研讨会,而不设行政级别的管理人员。
二、司法职权配置的合理化
“决定”指出: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笔者认为,当下我国司法职权配置主要分布在纵、横两个维度上。
1.从横向关系上看我国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
一是对法院来说,审判权与执行权的混合配置易致 “审执不分”的弊端。迄今为止,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一直在兼做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工作,可谓审判与执行 “双肩挑”,这种做法背离了 《宪法》第123条关于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的定性规定。应当将执行权从法院的职能体系中分离出去,将之交予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或者设置专门的国家执行机关 (可称之为 “执行总局”或 “执行总署”),统一行使包括刑事执行、行政执行和民事执行在内的完整的执行权。
二是对检察院来说,法律监督权与诉讼职能应当合理配置。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改进:其一,在检察院内部建立单独的、统一的 “法律监督部门”,将其法律监督的职能与其诉讼职能在机构与人员上分离开来。其二,强化检察院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克服其向来就有并一直存在的 “重刑轻民”的监督观。其三,加强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察活动的法律监督。建议将当下检察机关内部设置的 “侦查监督部门”改造成为 “侦查指导部门”,专门负责对侦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2.再从司法职权配置的纵向关系上看。
目前司法机关上下级之间的职权配置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缺陷,应予改进。其一,实行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取代目前实行的二审终审制。实行三审终审制有利于极大地改善法制适用不统一的局面,有利于增强司法公信力,尤其对最高法院而言,也有利于其通过亲自直接审判案件形成指导性的判例,改变司法解释 “空对空”的现象。其二,将基层法院改为 “调解法院”,同时将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改造为 “小额速裁法庭”。凡所有依法可调解的案件,无论其标的额大小,应一律进入调解法院先行尝试调解。基层法院为此需要配置有别于审判法官的调解法官。经过调解法院的调解,若调解成功,则赋予其与生效裁判等同的法律效力,相关的调解书或调解协议可成为强制执行的根据。若调解不成功,则转由中级法院继续进行审判。此外,所有需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等案件,也由调解法院管辖。其三,将中级法院确定为初审法院,管辖所有依法不宜进行调解的案件以及经过基层法院调解不成的案件。将高级法院确定为上诉审法院,专门管辖不服中级法院裁判的上诉案件。将最高法院确定为终审法院,管辖不服高级法院裁判的部分上诉案件。对于不符合上诉到最高法院条件和标准的案件,仍然实行二审终审制。为使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能够确保便民诉讼,有必要推广巡回审判制度,同时在必要时考虑设立相应的分院,以使民众能够便利地行使诉权。其四,建立司法判例制度。最高法院应将具有宪法和法律解释意义的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纳入自己亲自审判的范围,由此所产生的判决和裁定,直接具有判例效力,发布后将会对各级法院裁判类似的案件具有参酌适用和相对的法律拘束力。
三、司法机制的科学化
构建一个良好的司法体制,是为了形成一个科学的司法机制;司法机制是司法体制的贯彻落实。目前我国司法机制存在着诸多缺陷,应予克服。
1.借鉴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做法,制定专门的“司法公开法”。 “决定”也指出,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但目前司法公开仅有原则的规定,而缺乏具体系统的规则保障。通过司法公开的专门立法,便可将司法公开的内容、主体、制度保障、权利救济、不公开或公开有缺陷的法律责任等诸多事项做一系统的规范和调整。
2.深入进行司法民主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应当同步推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完善。应当扩大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使符合一定条件的普通公民均有同等的机会参与司法。应当改变由法院和检察院自己遴选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的做法,将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的挑选和管理、培训等工作纳入司法行政的范畴,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起相应职责,从而使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能够真正发挥司法参与和司法监督的作用。同时,应当加强对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进行立法调整的力度,在条件成熟时,尽快推出 “人民陪审法”和“人民监督员法”。同时要考虑在适当时候将当事人有权获得人民陪审员陪审和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权利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使之成为一项有宪法保障的基本程序权利。
3.强化和完善司法监督制度。司法监督对确保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权威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决定”指出: “健全 ‘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为此建议:一是加强人大监督司法的力度。应当完善人大监督司法的体制和机制,加强机构建设和专业人才建设,提升人大监督司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能力与水平。二是重视和强化检察院对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在司法改革中,应当置重于检察院和法院 “二元司法关系”的合理构建与配置。建议尽快制定独立的“检察监督法”。三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调整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四是建立健全对司法的民主监督机制,使各种分散存在的民主监督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这其中,应当更加重视发挥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应当为党派团体的司法监督积极创造条件,开辟渠道,创新方式,切实使协商民主进入司法领域,构筑中国特色的协商司法机制。
四、司法保障的充实化
完善司法保障制度体系是我国司法改革要致力于完成的重要任务,其在整个司法改革链条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性作用,对于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提高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年龄标准和学历要求。在法官和检察官实行分类管理后,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年龄底线标准应当加以改变,防止法官、检察官任职年龄过分年轻化的现象出现。笔者认为可从目前的23周岁改为28周岁。同时,应当规定凡是担任法官和检察官者,均必须具备大学法律本科以上的学历,而不是目前规定的 “大学本科学历”。
2.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笔者认为司法考试可分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层次进行。高级阶段的司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方面。通过高级阶段的司法考试还只算是仅仅具备到法院和检察院担任司法辅助人员的资格,若要从司法辅助人员晋升为法官和检察官,尚需经过专门化的司法研修,然后再进行司法研修合格考试,通过后方能被遴选为正式的法官和检察官。以上三种考试可分别称为 “初试”、 “再试”和 “终试”。
3.建立司法职务保障制。据此制度,法官和检察官一经法定程序获得任命,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非依据法定理由和经过法定程序,不得被解免职务,也不得未经其同意而调动其工作岗位。这样就可以增强法官和检察官独立履职、抵御干预的能力,使其免除职业上的后顾之忧。
4.完善法官和检察官的退休年龄和退休保障制度。目前法官和检察官的退休年龄确定为男60、女55,显得过于提前,不利于充分发挥资深法官和检察官的作用,也不符合司法职业需要丰富经验和素养的要求和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适当延长法官和检察官的退休年龄,可以考虑设定两个退休年龄段:一是可退年龄,也即达到该年龄,法官和检察官就有退休的权利。该年龄可分别确定为男65,女60。二是必退年龄,也即达到该年龄,法官和检察官就必须退休。该年龄可分别确定为男70岁,女65岁。
五、司法责任的制度化
建立健全司法责任的制度体系是我国司法改革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现行司法体制和机制难以真正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此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立法和制度化建设:
1.成立司法惩戒委员会,明确对法官和检察官的惩戒权主体。我国应分别建立由各级法官和检察官以及专家学者等人士组成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和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使其隶属于省级以上权力机关独立开展活动。其中可分为三个层次考虑:一是触犯刑律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二是违规违纪严重、但尚未触犯刑律者,则启动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官和检察官的罢免、弹劾程序;三是一般的违规违纪以及错案责任者,则由惩戒委员会进行惩戒,如警告、通报、责令书面检查、降级使用、停职培训、引咎辞职、司法追偿等。
2.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终身追责制。为将司法责任真正落实到个人,应当建立错案责任追究终身制。据此,对于办了错案的法官和检察官,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都要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发现的可能构成错案的线索,即使被调查对象已经退休或者变换了工作岗位,仍要接受组织调查,对于明确认定为错案的,便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3.建立干预司法登记备案和通报制度及责任追究制度。维护司法独立,完善我国司法责任制,除了需要对主审法官和主办检察官进行错案问责之外,对于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单位和人员,同样也要设立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由于司法干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作为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保障司法权力依据法定程序在不受外界不当干预的阳光环境下顺畅运行,因而应当作为司法责任制的配套措施加以推行。